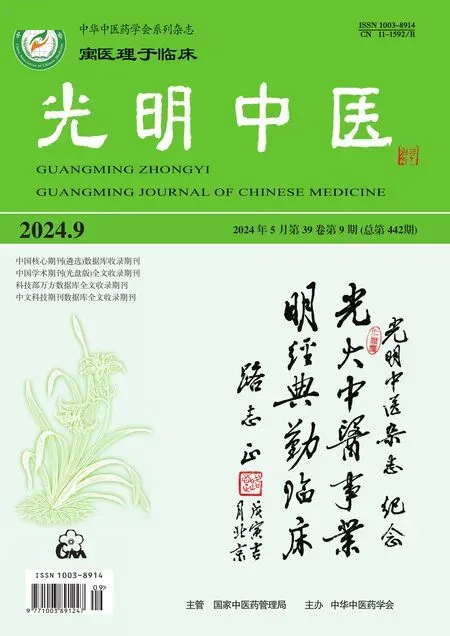徐健眾教授論治痛風臨床經驗*
李 歡 徐健眾
痛風是由多因素引起的體內嘌呤代謝異常,血清尿酸濃度升高,單鈉尿酸鹽晶體沉積在關節囊、滑囊等組織中引發急性和慢性關節炎癥及病損的代謝性疾病[1],其臨床表現為關節紅腫疼痛,屈伸不利,甚則病灶局部腫脹變形、周圍有硬結出現等癥狀,發作時疼痛劇烈,隨病情進展還會伴發關節畸形、腎臟損害。近年來,中國痛風發病率持續增長[2,3],痛風患者群體眾多,嚴重危害到人類的健康。目前痛風的西醫治療以使用藥物降低尿酸、消炎鎮痛等為主[4,5],但其作用靶點單一,且有一定不良反應[6];中醫除口服中藥治療以外,還有藥物外敷、針灸等外治法,治療效果好且毒副作用不明顯[7],在痛風的治療上占有優勢。根據痛風發病時的臨床表現,歸屬于中醫“痹證、歷節、白虎病”等范疇[8]。陶弘景在《名醫別錄》中最早提出“痛風”一詞:“獨活……百節痛風無久新者”;朱丹溪于《格致余論》中最早提出這一病名:“痛風者……夜則痛甚,行于陰也”;王燾在《外臺秘要》中所說:“其疾晝靜而夜發……故名曰白虎之病也”;喻嘉言《醫門法律》記載:“痛風……實則痛痹也”。現代醫家認為,痛風的發作主要責之肝、脾、腎三臟功能失調,痰飲、瘀血、濁毒內蘊,加之外感風寒濕熱之邪各有側重,臨床表現亦有不同[9]。重慶地處四川盆地,三面環山,氣候潮濕,徐健眾教授結合重慶的自然環境、飲食文化、個體體質等,認為痛風的治療應以脾胃為中心,以健脾除濕、通絡止痛為主要治法,兼以清熱、消食化滯、理氣、活血化瘀等。
徐健眾教授從醫30余載,是全國第二批優秀中醫臨床人才、全國第三批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繼承人、全國第七批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繼承指導老師,師從戴裕光、李乾構、張之文、胡天成等名中醫,在內分泌代謝疾病、脾胃疾病的治療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臨證中擅于從脾胃入手進行診治。筆者有幸跟隨徐師學習,收獲頗豐,以下概述其治療痛風的臨床經驗以供交流。
1 病因病機
徐師認為此病多因飲食失宜、耗損脾胃、脾失健運;先天稟賦不足,后天年老久病,外感風寒濕邪等,導致脾腎虧虛,體內水液代謝失常,水濕痰瘀蘊結所致。脾為后天之本,脾胃主升清降濁;腎為先天之本,腎主蒸騰氣化。飲食不當可損傷后天脾胃,導致脾胃功能障礙,喪失升清降濁功能,水液運轉輸布障礙,痰飲水濕內停;腎氣虧虛則蒸騰氣化失司,水液代謝異常,代謝濁物不能排出體外;或感受風寒濕邪,邪氣搏結,水濕、痰瘀、熱毒等流連于筋骨、關節等部位而發為此病[10]。
1.1 以脾胃為中心徐師認為痛風的治療應以脾胃為中心,脾胃虛弱為此病的發病基礎。“脾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飲食物進入人體經由胃受納腐熟之后,精微者傳輸至脾,通過脾的運化,再由脾氣將精微物質輸送至各臟腑器官,濡養全身,人出生后的生命活動都有賴于后天脾胃攝入營養物質來提供能量。若脾胃受損則疾病始生,李杲曰:“內傷脾胃,百病由生”。脾胃一旦受損,飲食物不能消化吸收,脾胃之氣不能充養身體元氣,機體疏于保護則疾病發生。《景岳全書》有云:“脾為土臟,灌溉四旁,是以五臟中皆有脾氣,而脾胃中亦有五臟之氣……故善治脾者,能調五臟,即所以治脾胃也”。指出脾胃在五臟中的重要性以及通過治療脾胃來達到治療五臟疾病的效果[11]。
1.2 補脾不如運脾脾胃同居人體中焦,為氣機升降之樞紐關鍵,脾主升而胃主降,二者主司飲食水谷精微的受納腐熟、轉化運輸,負責為機體提供精微物質,維系生命活動。《四圣心源》曰:“脾升則腎肝亦升,故水木不郁;胃降則心肺亦降,故金火不滯。火降則水不下寒,水升則火不上熱。平人下溫而上清者,以中氣之善運也”。脾胃為中焦升降之樞紐,肝腎隨其升,心肺因其降,則氣血陰陽平衡[12];朱震亨有云:“脾具坤靜之德,而有乾健之運,故能使心肺之陽降,腎肝之陰升,而成天地交之泰,是為無病之人”。脾胃以運為健,其氣機升降功能正常,氣血陰陽得以相交調暢則身體無恙[13]。陳士鐸曾在書中道:“虛不用補何以取弱哉。愈補愈虛者,乃虛不受補,非虛不可補也。故補之法亦宜變。補中而增消導之品,補內而用制伏之法,不必全補而補之,更佳也”[14]。若飲食不當、攝入過度,損傷脾胃,氣機升降出入異常,此時若只一味補脾,恐加重脾胃負擔,補而不得成效[15],應于補益中配伍些許理氣健脾、消食導滯的藥物,以漸復脾胃功能。
1.3 重慶地區加減化裁重慶市內江河縱橫,自然氣候多潮濕,脾生理特性為喜燥惡濕,同氣相求,最易招致濕邪侵襲人體。為了抵御濕邪侵襲、驅趕潮氣,人們常食用火鍋、辣椒、燒酒等辛熱油葷的食物,長此以往易導致脾虛濕滯。徐師認為該病初起多為脾胃受損、運化失司導致脾虛濕滯,需以健脾行氣化濕為治,常配伍白術、茯苓、陳皮、姜厚樸等,再加上雞內金、山楂等健脾消食。日久脾胃虛弱,濕熱內蘊,蘊久化熱,治法為健脾清熱除濕,配伍黃柏、龍膽草、茵陳、澤瀉等清熱除濕之品,若是熱甚則加強清熱,兼以除濕;濕甚則強化除濕,兼以清熱。病程反復,久病及腎,或既往有腎功能損傷者,脾腎俱虛,虛實夾雜,水濕痰瘀互結,則治以健脾補腎、活血散瘀等,用藥可在健脾基礎上配伍淫羊藿、巴戟天等補腎燠土;川芎、當歸、赤芍等活血化瘀。
2 日常調護
痛風是一種與機體嘌呤代謝異常直接相關的代謝性疾病,與生活方式密切相關[15,16]。徐師認為除服用藥物治療以外,應從根本抓起,注重在生活起居、飲食習慣等方面進行調護。患者應學習此病基本知識,盡量避免在預防調護上出現差錯。從生活起居方面來說,不應過度勞累、情志失調等,以防身體免疫力下降不能御邪,正所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患者不應當進食含高嘌呤、果糖以及酒精等飲食物,其會導致機體尿酸生成過多引起痛風的發作。還應保證每天充分飲水,飲水量大于2000 ml,多飲水可加快身體新陳代謝的速度,促進體內的尿酸排出。除此之外,痛風患者還應進行適量地運動來提高身體素質,但要注意,痛風急性發作時應制動、忌熱熨。罹患痛風之人常合并肥胖,而該病又可從多途徑加重患者肥胖狀態,故適量運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7]。成曉翠等[18]認為,痛風患者進行規律的有氧或者中等強度抗阻運動都可以使血清中尿酸含量、血脂水平降低,還能改善情緒狀態,減少痛風的復發。
3 醫案舉隅
3.1 脾虛濕熱證梁某,男性,27歲。2021年8月4日初診。主訴:痛風發作5 d。患者訴5 d前吃火鍋后右足踝、左足背紅腫疼痛;于重慶市中醫院完善血尿酸檢查,結果示:538 μmol/L,予服用非布司他、苯溴馬隆、小蘇打等藥物治療后,復查血尿酸降至436 μmol/L;近期稍感鼻塞不通,無惡寒發熱、咳嗽、流涕、咽喉等不適,納可,睡眠較好,大便不成形,每日解2~3次,小便色黃,無尿頻、尿急、尿痛。查體可見患者右踝部以及左側足背紅腫,疼痛拒按,舌暗紅,苔薄膩,脈沉滑。既往血壓偏高、血脂偏高、過敏性鼻炎。西醫診斷:痛風;中醫診斷:痛風(脾虛濕熱證),治以健運脾胃、清熱化濕為主。擬方如下:黃芪30 g,麩炒白術20 g,土茯苓30 g,黃柏10 g,升麻10 g,葛根30 g,防風10 g,淫羊藿10 g,威靈仙15 g,獨活15 g,茵陳15 g,廣藿香(后下)15 g,豬苓10 g,鹽澤瀉15 g,赤芍15 g,當歸10 g,姜黃15 g,凈山楂40 g,辛夷(包煎)15 g,川牛膝15 g,生甘草10 g。共7劑,水煎服,每日1劑,每日3次,分溫服之。
2021年8月12日二診:患者現已停止服用非布司他,未監測血尿酸,訴服用前方后,足踝、足背未再疼痛,鼻塞較前緩解,納食可,睡眠較好,大便仍不成形,每日解1次,小便黃。舌紅,苔膩、有裂紋,脈沉細。隨后予原方加減繼續服用,患者病情穩定。
按語:患者為青壯年男性,飲食不當,禍損脾胃,故方中黃芪、白術二者健脾氣、祛水濕;廣藿香芳香化濕,促進脾胃運化。加之重慶地區濕熱較甚,濕熱之邪蘊久釀為熱毒,瘀滯筋骨、關節出現局部疼痛不適,予土茯苓、威靈仙、獨活除濕通絡止痛;升麻、葛根、防風升舉脾胃清陽之氣,清陽升而濁陰自降,恢復脾胃氣機升降,使痰濕壅滯疏通,同時發散關節肌肉間風濕;黃柏、茵陳、豬苓、澤瀉使濕熱從小便除,又寓上下分消之意。升麻又善清熱解毒;葛根又能通經活絡。淫羊藿一則溫腎助陽,推動機體水液代謝,增強抵抗力,一則加強祛風除濕之功效,再有防止寒涼太過傷及機體正氣。濕熱為患,氣血運行受阻停而成瘀,故予赤芍、姜黃活血通絡、行氣散瘀;當歸補血活血,預防苦燥之品損傷陰血;川牛膝通關節、逐瘀通經;山楂健胃消食、化濁降脂。同時叮囑患者合理規劃飲食結構,多喝水并結合規律、適量的運動。
3.2 脾腎兩虛 濕熱內蘊證賀某,男性,58歲。2021年2月26日初診。主訴:痛風反復發作5年,再發3 d。患者訴5年前無明顯誘因痛風發作,于外院治療后病情好轉。3 d前患者飲酒后再發痛風,訴第一跖趾關節疼痛劇烈,休息后疼痛稍有緩解,自訴平素尿酸值在580 μmol/L左右,近3個月未規律服用藥物碳酸氫鈉片、非布司他片。現口干多飲,納食尚可,腹脹,大便不成形,每日解1~2次,夜尿2次。查體:第一跖趾關節紅腫明顯,舌質紅,舌苔薄膩,脈沉滑。既往血壓值、血糖值偏高。中醫診斷:痛風(脾腎兩虛、濕熱內蘊證),治以健脾補腎、清利濕熱。擬方如下:當歸10 g,黃連15 g,防風10 g,升麻10 g,川牛膝30 g,茵陳15 g,葛根30 g,麩炒白術20 g,土茯苓30 g,黃柏10 g,澤瀉15 g,威靈仙15 g,獨活15 g,雞矢藤30 g,杜仲15 g,山楂40 g,姜黃15 g,黃芪30 g,山藥30 g,雞內金30 g。7劑,日1劑,分3次溫服之。
2022年3月17日二診:患者訴第一跖趾關節疼痛消除,復查尿酸值降至300 μmol/L。晨起自覺口干、口苦,納可,腹脹減輕,眠安,大便較前稍成形。舌紅,舌苔薄膩,脈沉滑。濕熱之邪去除速度慢,復診繼以前方加減善后。
按語:患者痛風反復發作,脾腎虧虛,故處方中予黃芪、白術、山藥、川牛膝、杜仲補益脾腎,土茯苓通關節。濕熱內蘊,耗傷津液,氣血壅滯成瘀,故配伍黃連、黃柏等清熱燥濕,再加上當歸、姜黃等活血行氣、散瘀止痛,予升麻、防風、澤瀉等分消濕熱,予雞矢藤、山楂、雞內金等健運脾胃、消食化積。諸藥合用,則脾腎調、濕熱清、氣滯通、瘀血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