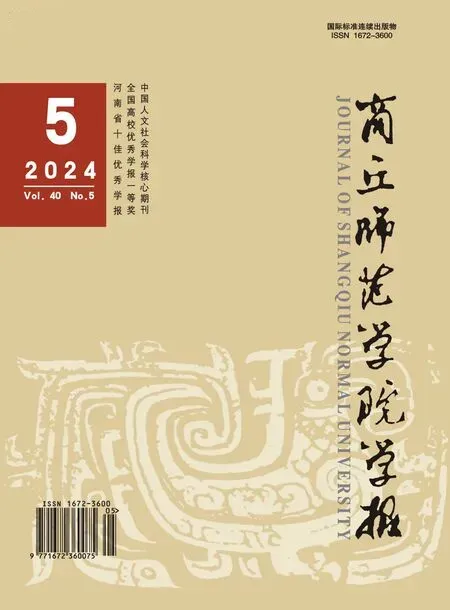劉濬《杜詩集評》編撰背景考論
王 辰
(河南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學院,河南 洛陽 471000)
劉濬,字質文,號寓槎,浙江海寧(今屬浙江省嘉興市)人。監生。生年不詳,約卒于嘉慶九年(1804)后。作為一位普通文士,他的政治影響和學術影響不大,僅以選輯《杜詩集評》而著稱。此書凡15卷,按體編選,共收杜詩1454首,匯錄清初李因篤、王士禛、錢陸燦、朱彝尊、申涵光等15位詩論家的評杜之語,且“未敢妄參一語”[1]31,有嘉慶九年(1804)海寧劉氏藜照堂刻本。《杜詩集評》廣搜博采,保留了大量清代學者治杜的可靠材料,對后世研究清人的杜詩接受具有重要價值。
劉濬編纂《杜詩集評》并非偶然隨意之舉,而是在客觀和主觀上都存在著一定的必然性和目的性。有鑒于此,本文試從時代環境與社會生態、文化基礎與地域氛圍、個體愿望與接受心理三方面出發,以期對這部選本的編撰背景作出系統、全面的考察。
一、時代環境與社會生態的有機統一
順治、康熙、雍正三朝是清帝國從江山易主的動蕩中迅速恢復過來,并逐步走向安定復興的歷史階段。在戰爭逐漸平息、各地叛亂陸續被鎮壓以后,官方政策的重心亦明確轉向了“偃武修文”。得益于此,原本因兵燹、天災、瘟疫而遭受重創的政治秩序很快便回歸正軌。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勵精圖強,至乾隆即位,更是迎來萬邦覲賀、天下太平的盛景。嘉慶登基后,雖無父皇“文治武功”均達到登峰造極的本事,但執柄之初仍能修明律令、整頓吏事,使得疆域依舊保持著穩固的狀態。
自康熙中后期開始,由于胸懷大志、精明強干的上層統治者親賢遠佞、敬德保民,并且大刀闊斧地采取了一系列順應人心的舉措:如獎勵耕織、蠲免賦稅、賑濟窮困等,其時的經濟得以快速恢復,國勢日臻鼎盛。龔自珍《京師悅生堂刻石》對此稱贊有加:“我圣清之休養民,同符乎三代。”[2]188雖不無諛頌,然大體屬實。至乾隆、嘉慶之交,隨著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走向巔峰,傳統的農業、手工業也達到了封建君主政體之下的最高水平,從而助推了市場的火旺和城鎮的昌隆。
清廷定鼎后,滿洲貴族出于鞏固政權的考慮,宣布開科取士。此舉既安撫了廣大漢族知識分子的心靈,又方便執政者掌握民間士人的思想動向。統治階級還確立了以“程朱理學”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之根基,明文將“雅正”當成文化衡鑒的標準:“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曉諭考官,所拔之文務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備。乾隆三年,復經禮部議奏,應再飭考試各官,凡歲科兩試以及鄉會,衡文務取清真雅正,以為多士程式。”[3]13與此同時,自康熙以降,皇帝們崇文尚教,組織編纂各類大型史書、類書、叢書。《御定淵鑒類函》《子史精華》《古今圖書集成》等的面世,不僅彰顯了國家實力的強盛,而且促進了世人精神的提升。待到清中葉,一個“全民重學”的知識型社會順勢而生。上起王侯將相、天潢貴胄,下訖士庶鄉黨、販夫走卒,多以讀書、著述為樂。及至后來,當文藝政策變得越來越極端,清初實學中“經世致用”的意識愈發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為學問而學問”的乾嘉考據派逐漸興起。
清軍入關建立起大一統王朝后,面對百廢待興的殘局,最高統治者主動采取順國安民、蓄元養精的策略,以此來恢復社會發展。在順治、康熙、雍正三位君主的不懈努力下,最終開創了盛世偉業,彪炳史冊。繼任者乾隆雄才大略、文武雙全,終將大清王朝的輝煌推向極致。乾末嘉初,江浙一帶既沒有前期外族叩關入侵之際的暴力踐踏,也沒有后期太平軍及西方列強的武裝進犯。這一時期人口飛速增長,為荒地的墾辟、水利的興修、作物的種植、用品的生產、商貿的往來貢獻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環太湖流域經濟由此騰飛起來。清人陶澍曾說過:“天下之水利,莫大于江南,太湖又江南水利之大者也。……旱潦于是乎備,衣食于是乎生,財賦于是乎出。”[4]26—27此方水土之豐饒富庶可見一斑。而浙西的杭州、嘉興和湖州三府又恰處于該片區,其繁華程度可想而知。
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作保證,相應的文教事業就很快地興盛起來,這可通過科考和藏書兩個指標得到驗證。就科考而言,清代兩浙及第入仕者,“杭嘉湖紹寧共出2553名進士,占整個浙江的91%。杭州共有893名進士,紹興有563名,嘉興有504名,湖州有368名,寧波有225名。這五個府平均所屬各縣人均進士也是杭州最多,99人,嘉興72人,紹興70人,湖州53人,寧波38人”[5]115。浙西與浙東所占比例分別為62.9%和37.1%。顯然,前者比后者更具人文底蘊。從浙西各府看,杭州府主要集中在錢塘、仁和、海寧諸縣,嘉興府主要集中在嘉興、秀水、嘉善、平湖、桐鄉諸縣,湖州府主要集中在烏程、歸安、德清諸縣,證明通過科舉“躍龍門”來改變命運的優良傳統在浙西長盛不衰。至于藏書,有清一朝浙地也名列前茅。據范鳳書統計,清代萬卷私人藏書家總共543人,浙江有137人,其中杭州49人、嘉興28人、湖州8人、紹興16人、寧波17人、臺州4人、金華7人、溫州5人、處州3人[6]268—322。杭嘉湖紹寧五府凡101人,占全省的73.7%;浙西、浙東分別占比62%與38%。由是可見浙西私家藏書的發達程度。海寧文士劉濬結輯《杜詩集評》正得益于此,誠如劉氏《自序》所言:“嘉興許晦堂先生淹博好學,酷愛藏書,乃鉤求而盡得之。余于許氏為葭莩親,因得借歸,錄而藏之。”[1]21據此知道,劉書材料的來源乃出自遠房表兄弟許燦所藏典籍。
二、文化基礎與地域氛圍的同頻共振
清朝初期,統治階層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就是要盡快消除與漢族士人的心理隔閡。為此,他們實行全面“漢化”“儒化”的國策,“以漢治漢”“以儒治儒”。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做法如下:一是力倡儒術,對儒學領袖推崇備至。如順治二年(1645),朝廷“更國子監孔子神位為‘大成至圣文宣先師孔子’”[7]93。再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上詣先師廟,入大成門,行九叩禮。至詩禮堂,講《易經》。上大成殿,瞻先圣像,觀禮器。至圣跡殿,覽圖書。至杏壇,觀植檜。入圣承門,汲孔井水嘗之。……詣孔林墓前酹酒。書‘萬世師表’額。留曲柄黃蓋。賜衍圣公孔毓埏以次日講諸經各一。免曲阜明年租賦”[7]216。二是國君本人極其注重學習漢語文明。如順治在開始執政時很難看懂向他呈遞的漢文奏折,深感因自己的無知所遭遇的阻礙。于是,他以巨大的決心和毅力攻克漢文化,短短的幾年時間就能讀寫了。再如康熙對中華古典文學抱有極大熱情,常與臣下在朝堂上賦詩。這種將治統、道統、文統“三位一體”的皇帝,古往今來實不多見。總而言之,上述舉措對于扭轉清政府形象、籠絡士子之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后雍正、乾隆、嘉慶也想盡辦法拉攏漢人。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緩和了民族矛盾,也為滿漢文化的相互了解與融合架設起了溝通的橋梁。
清前期的當權者好以“右文興學”相標榜,是大有功于文化的。順治十二年(1655),皇帝詔諭禮部:“帝王敷治,文教為先。臣子致君,經術為本。自明末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闕焉未講。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爾部傳諭直省學臣,訓督士子,凡理學、道德、經濟、典故諸書,務研求淹貫。明體則為真儒,達用則為良吏。果有實學,朕必不次簡拔,重加任用。”[7]3114康熙主政時期曾責成朝廷內外官員:“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親試錄用。其內、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督、撫,代為題薦。”[7]3175—3176雍正時重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感奮發,亦興賢育材之一道也”[8]153。上述種種措施的推行,為此后文藝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乾隆統治期間,政府在大西南“建郡縣,設學校,漸摩以仁義,陶淑以禮樂”[9]17。該地區遂“人文振起”[9]15,通漢話、習漢俗蔚然成風。嘉慶繼位,多承襲祖制,彼時“崇儒重道”的風氣愈加濃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乾嘉時期文人學士嗜書成癖,矢志不渝。葉德輝在《書林清話》里還說到一件趣事:“每于退值或休務日,群集于廠肆。至日斜,各挾數破帙驅車而歸。”[10]225除訪書不遺余力外,這些人校書也是愈久彌堅,經學大師盧文弨就是其中優秀的代表之一:“喜校書,自經傳子史,下逮說部詩文集,凡經披覽,無不丹黃者。即無別本可勘同異,必為之厘正字畫然后快。嗜之至老逾篤,自笑如猩猩之見酒也。”[11]551另有周春“泣而鬻書”、李文藻“性好聚書”、黃丕烈“歲常祭書”等。這些軼事反映了此期知識分子手不釋卷的面貌。受此影響和感召,劉濬決定編選《杜詩集評》。
齊梁以前的江南,由于遠離中原地區,避免了戰亂所帶來的劇烈動蕩,擁有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來進行經濟建設。從唐末開始,江南地區憑借優越的自然條件、便利的水陸交通和良好的人文基礎而逐漸成為全國經濟發展的命脈。到南宋中期,更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說。明清時期,江南文化高度開放和活躍,文人社群活動異常興盛。據王文榮《明清江南文人結社考述》一書的研究,康熙至雍正朝,江南文人結社出現復興的局面。到乾隆年間,文人結社活動達到鼎盛。如果按地域劃分,又以蘇州府、嘉興府、松江府、杭州府、湖州府居多[12]27—35。劉濬出生與生活的海寧在清代隸屬于杭州府,文人社團眾多,結社之風盛行。劉氏成長于這樣一個讀書、會文風氣濃厚的文化氛圍里,激勵了他的治學精神,提高了他的學術素養,也為其后來編撰《杜詩集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除此之外,從杜詩學發展的角度來看,有清一代杜詩研究者的占籍多集中在江浙一帶。文人結社大大便利了他們的交流,使得這一時期治杜學者之間交往緊密、互動頻繁,形成了一個個互通有無、彼此對話的學術群體。受這種文化風氣的影響,劉濬自覺地參與到學杜、研杜的隊伍當中。
江浙自古就有“尊師重教”“崇文尚藝”的優良傳統。宋代以來,鑒于杜甫崇高的地位、杜詩巨大的成就,杜詩學的發展不斷地向前推進。明清易代,浙江是當時“反清復明”最激烈的地方之一,相當一部分人懷有強烈的“夷夏之辨”情緒,這些在注杜與評杜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流露。清初浙地杜詩學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各種杜詩全集校注本、各體杜律選評本都大量涌現,如張遠《杜詩會粹》、陳訏《讀杜隨筆》、張雍敬《杜詩評點》、仇兆鰲《杜詩詳注》、張涵《杜律近思》、范廷謀《杜詩直解》、沈炳巽《杜詩集解》等皆取得了突出成就。乾嘉時期,兩浙杜甫詩歌輯注輯評本興盛,其中劉濬《杜詩集評》所錄清初諸名家評語簡練通達,亦多獨到精辟之處,不失為較有代表性的杜詩匯評本。作者在書中特別強調“忠君愛國”的思想,極力宣揚以“溫柔敦厚”為核心的“詩教說”:“世之所以重杜者,尚不以其詩之奪蘇、李,吞曹、劉,掩顏、謝而雜徐、庾,得古人之體勢,兼人人所獨專,如元相所言已也。尤在一飯不忘君國,雖遭貶謫而無怨誹,溫柔敦厚,洵得《三百篇》遺意,所謂‘上薄風雅’者,其在斯乎?”[1]22此舉迎合了上層統治集團的價值觀念和審美趣味,符合他們政教宣傳的基本要求。
三、個體愿望與接受心理的高度契合
《杜詩集評》成書以前,宋人方深道《諸家老杜詩評》、黃希黃鶴《補注杜詩》、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元人高楚芳《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1)據《杜集敘錄》介紹:“劉辰翁批點本,流傳刊刻情況比較復雜,其名稱、卷數,亦不盡相同。約有《集千家注批點補遺杜工部詩集》《須溪批點杜工部詩注》《須溪評點選注杜工部集》《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重刊千家注杜詩全集》《集千家注杜詩》《纂注分類杜詩》《劉須溪杜選》《杜子美詩集》《杜工部詩集》等名稱。”詳見張忠綱等編著《杜集敘錄》,齊魯書社2008年版,第107頁。鑒于《文淵閣四庫全書》收有《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一部,因此這里取四庫館臣之說,以元高楚芳本稱之。、范梈《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明人單復《讀杜詩愚得》、王嗣奭《杜臆》、胡震亨《杜詩通》等杜詩匯注匯評本早已蜚聲學界。清代錢謙益《錢注杜詩》、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仇兆鰲《杜詩詳注》、江浩然《杜詩集說》、張甄陶《杜詩詳注集成》、楊倫《杜詩鏡銓》等論著在杜詩學領域依然頗具影響力。以上撰作雖然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果,但是仍舊存在不盡人意之處。這既是劉濬編選《杜詩集評》面臨的詩壇現狀,也是劉濬決心編選《杜詩集評》的動因所在。具體來講,劉濬編選《杜詩集評》的主要意圖有三。
其一,彌補前人著述疏失。作者在《自序》中首先對于前代杜詩學的發展情況進行了簡要回顧:“詩自漢魏而后,至少陵止矣。大含細入,包羅萬有,謂之‘圣’,謂之‘史’,前人之論備焉。”[1]21緊接著表達出其意欲編纂出一部超越前人杜詩評本的愿望:“第淺學未易窺測,譬行遠者無指南之車,涉海者無濟渡之筏,不能循途而入,沿流以至也。是不可以無評,然非切中肯綮,則又不如無之為愈。”[1]21之后,劉氏又在洞悉以往研杜專著流弊的基礎上,明確地告知讀者自己編撰此書的目的:“薈萃一編,時時展玩,無支離影響之弊,無穿鑿傅會之習,提要鉤元,張皇幽渺,使杜詩全旨無捍格不通之處,庶幾循途而入,沿流以至,可免岐路望洋之嘆矣。”[1]22使人一覽了然。
其二,彰顯自家詩學主張。從康熙到乾隆朝,正統文人普遍認為“杜詩之所以能成為‘千古絕業’,主要在于它體現了‘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傳統”[13]34。如仇兆鰲《杜詩詳注自序》指出:“孔子之論詩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明人之論詩者,推杜為‘詩圣’,謂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萬世也。”[14]1再如楊倫《杜詩鏡銓凡例》亦強調:“詩教主于溫柔敦厚,況杜公一飯不忘,忠誠出于天性。”[15]12劉濬《杜詩集評自序》同樣展示出“溫柔敦厚”的詩教觀念:“諸先生所評,往往觸類引伸,揭明此旨(指‘溫柔敦厚’),尤具千古只眼,豈世俗評杜者可同日語哉?”[1]22—23與前賢一脈相承。
其三,為后來者導夫先路。劉氏曾明確表示:“吾不知詩,又敢知杜?諸所評者,未知其皆能知杜與否?而‘依附影響’之說,知其必無也。讀杜詩者,繹而尋味之,以己之所得,驗其離合向背。辟之欲浮海者,具陳舟楫帆檣之用,道路所經之險易以導之;欲適市者,列龜貝金錢與夫良楛貴賤之異,宜以告之。雖未必皆是,其不至漂流于斷港,眩惑于市儈也審矣。”[1]12—13可見為初學者“啟途徑、植基礎”是他輯錄本書的一個重要初衷。對此,陳鴻壽就說:“杜詩渾涵汪茫,千匯萬狀,得此(指《杜詩集評》)庶足以導示源流、尋求奧窔,不可繼夢弼‘千家注’卓然成一家言乎?”[1]5錢沃臣也講道:“昔蔡夢弼集宋以前評杜者曰‘千家注’,既已抉摘略盡矣。海寧劉君寓槎又取國初以來諸家評說,會緝之曰《集評》,則更補前人所未道,于理體多所發明,讀之豁人心目,開人識見。”[1]18均肯定《杜詩集評》啟益后學良多矣!
永嘉以后,隨著中原地區政局動蕩、戰亂頻仍,北方士族不斷南遷,生態環境良好、居住條件相對穩定、農漁經濟富庶的浙水之東西逐漸成為全國人才聚集地。“經過漫長的歷史演化,發展至明清時期,這一區域的家族普遍崇德尚文,重視儒業,家學代際傳承,井然有序,家族數量、規模、影響力均頗為可觀,兩浙由此成為清代人文淵藪之一”[16]。以杜詩學為例,清初至中葉浙地涌現出不少治杜世家:如海寧陳之壎、陳訏、陳世佶三人皆研習杜詩,其中陳之壎、陳訏是叔侄,陳訏、陳世佶是父子,足見論杜已成為陳門之家學。再如錢塘梁詩正、梁同書父子分別撰有《箋注杜詩》二十卷和《舊繡集》二卷(注:集杜之作,一冊。有乾隆二十一年(1756)寫刻本,又有嘉慶二十二年(1817)刻《頻羅庵遺集》本,名《集杜》)。又如天臺齊召南和齊圖南是兄弟,二人皆有集杜著述。齊召南高弟太平人戚學標亦曾撰《鶴泉集杜詩》二卷。而戚學標祖父戚鳴鳳同樣喜好杜詩,故這一時期的研杜也不乏家學切磋的因素(2)參見蔡錦芳《杜詩學史與地域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3—152頁。。這些濃厚的家庭研杜氛圍,推動了浙江杜詩學的迅速發展。劉濬選輯《杜詩集評》同樣離不開家族文化的熏陶。
首先,海寧劉氏以詩禮簪纓之族著稱于世,名噪一時。長久以來,劉氏宗族非常注重子弟的教育,家風純正高潔。家族成員中癡迷于訪書、購書、藏書、讀書、校書者代不乏人,可以說家學淵源深厚。受這些人的影響,劉濬也酷愛訪書、購書、抄書、藏書、校書:“諸先生評本,濬皆散購于藏書之家,隨時借錄,但與鈔本校對無誤而已。”[1]31他能輯成《杜詩集評》明顯得益于此。
其次,清代海寧一帶的文化相當發達,數百年間不僅科第繁盛、官宦輩出,而且學術興旺、大師云集。這其中文化世家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就杜詩學而言,形成了以地域、家族聚集為特征(3)沈亮指出:“在清代杜詩學發展的過程中,杜詩學者和尚杜詩人表現出明顯的地域聚集特征。清代文化發達的江、浙、徽一帶,匯集了大批杜詩學者和研究著作。而在某個特定地域,這種聚集特征又表現為圍繞當代某些文化家族所形成的詩人群落,文化家族的族人以及與他們有姻親師友關系的詩人們,共同形成了一股推動杜詩學發展的不可忽視的力量。”詳見沈亮《清代海寧陳氏家族杜詩學研究》,《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第29頁。的杜詩研究風潮。拿劉氏家族來講,族人們或同里交善、或同門交流、或同道交往,杜詩學在這些群體之間得以賡續延展。劉濬亦是如此,這從郭麐《杜詩集評序》中可得到驗證:“吾友劉子質文,以所輯《杜詩集評》示余:皆取近代諸人丹黃甲乙者,薈萃而臚列之,無所去取。”[1]12二人通過互相切磋,傳杜之聲不輟。
再有,海寧劉氏世家作為書香門第,深受儒家傳統文化的浸潤。家族子弟對杜甫“致君堯舜”的宏遠志向和“憂患蒼生”的高尚情懷推崇備至,對杜詩獨特的藝術魅力與豐富的精神內涵大加贊賞(4)曾紹皇認為:“杜詩在后世的興盛與杜詩忠君愛國的思想主旨和時代變遷帶來的家國之痛、杜詩的集大成特征與科舉取士以詩賦論選的標準、文學流派與地域文學風尚等息息相關。杜詩學家族傳承特征的明顯凸現,則更加反映了杜詩作為日常課讀典籍成為老百姓主要精神食糧來源的特質。”詳見曾紹皇《試論明清杜詩未刊評點的家族傳承特征》,《杜甫研究學刊》2013年第2期,第83頁。,劉濬當然也不例外。加上杜甫與劉濬均來自士族家庭,他們身上都具有強烈的家國責任感和重大的仁者使命感,只可惜后者時運不濟,僅為監生。由此,相同的出身、遭際很容易在情感上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讓兩人進行超越時空的對話。這也是促使劉濬選編《杜詩集評》的重要原因。
綜上所述,劉濬編撰《杜詩集評》絕非率意而為,亦非一蹴而就。相反,此書最終能成稿,實乃客觀和主觀條件影響下,多種因素合力作用之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