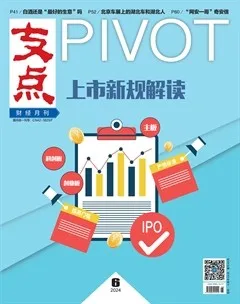當(dāng)下增加國債發(fā)行的五重意義
張明
2023年10月24日,中國政府宣布增發(fā)1萬億元國債,發(fā)行國債募集資金全部通過轉(zhuǎn)移支付方式安排給地方,集中力量支持災(zāi)后恢復(fù)重建和提升防災(zāi)減災(zāi)救災(zāi)能力。2024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起擬連續(xù)幾年發(fā)行超長期特別國債,專項用于國家重大戰(zhàn)略實施和重點領(lǐng)域安全能力建設(shè),今年先發(fā)行1萬億元。2024年4月23日,財政部表態(tài)支持央行在公開市場操作中逐步增加國債買賣,充實貨幣政策工具箱。央行有關(guān)部門負責(zé)人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國央行在二級市場開展國債買賣,可以作為一種流動性管理方式和貨幣政策工具儲備。上述一系列事件在有關(guān)各界得到高度關(guān)注,這意味著未來中國政府可能顯著增加國債發(fā)行規(guī)模,且中國央行未來將把在二級市場上買賣國債作為常態(tài)化操作。
在當(dāng)前形勢下,中國政府顯著增加不同期限的國債發(fā)行,具有如下至少五重意義。
增加國債發(fā)行的意義之一,是有助于為實施更具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提供充足資金。
當(dāng)前中國宏觀經(jīng)濟的最突出矛盾依然是總需求不足,存在顯著的負向產(chǎn)出缺口。截至2024年3月,CPI同比增速僅為0.1%,PPI同比增速連續(xù)18個月負增長,就是產(chǎn)出缺口為負的明證。在復(fù)雜外部環(huán)境以及三年疫情沖擊下,迄今為止,無論是企業(yè)還是家庭的資產(chǎn)負債表均處于修復(fù)過程中,對未來的預(yù)期與信心仍較低迷,主動加杠桿投資與消費的動力不強。在此背景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效果不佳,必須依靠擴張性財政政策來主動創(chuàng)造需求。然而,受經(jīng)濟增速放緩、房地產(chǎn)行業(yè)結(jié)構(gòu)性調(diào)整的影響,一方面全國稅收收入并不盡如人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債務(wù)已經(jīng)高企,因此要為更具擴張性的財政支出提供資金支持,中國政府增加國債發(fā)行就成為題中之意。
當(dāng)前,中國政府增加國債發(fā)行,有兩個便利條件。第一,發(fā)行國債的空間非常充足。中國中央政府債務(wù)占GDP比率低于30%,目前美國超過100%,日本超過200%;第二,發(fā)行國債的成本相對較低。當(dāng)前中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僅為2.3%左右,遠低于美國的4.5%上下。
增加國債發(fā)行的意義之二,是有助于成功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wù)風(fēng)險。
平心而論,即使加上地方政府隱性債務(wù),中國政府債務(wù)負擔(dān)在全球范圍內(nèi)并不算太高。例如,根據(jù)IMF的估算,中國全口徑政府債務(wù)占GDP的比率約在100%-110%,顯著低于日本與美國。但中國政府債務(wù)的問題在于結(jié)構(gòu)不合理。如果包含地方政府隱性債務(wù)的話,那么在中國政府債務(wù)中,成本低、期限長的中央政府債務(wù)僅占五分之一,而成本高、期限短的地方政府債務(wù)占到五分之四。這與美國剛好形成鏡像關(guān)系,在美國政府債務(wù)中,國債占五分之四,市政債占五分之一。特別是,在中國地方政府債務(wù)中,成本相對較低、期限相對較長的省級政府債務(wù)占比很低,而成本相對更高、期限相對更短的三四線城市地方政府債務(wù)占比很高。換言之,中國政府債務(wù)的問題不在于總量而在于結(jié)構(gòu),結(jié)構(gòu)不合理導(dǎo)致中國地方政府債務(wù)存在收益率與期限雙重錯配。
因此,要成功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wù)風(fēng)險,除了要通過財稅體制改革使得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權(quán)事權(quán)變得更加均衡之外,從增量上而言,這意味著未來應(yīng)該增加國債與省級政府一般債這樣的高等級債券的發(fā)行,降低三四線城市的新增舉債規(guī)模,從存量上而言,未來可能會進行更大規(guī)模的存量債務(wù)置換。對財政實力較強的省份而言,通過增發(fā)省級債券來置換三四線城市債務(wù)的做法可能就足夠了,然而對一些財政實力較差的省份而言,未來中國政府可能不得不通過發(fā)行國債來置換當(dāng)?shù)氐牡胤秸畟鶆?wù)。通過發(fā)行更低成本、更長期限的國債與省級一般債來置換掉高成本、短期限的地方政府債務(wù),中國政府就能成功化解地方債相關(guān)風(fēng)險。
增加國債發(fā)行的意義之三,是有助于向中國金融體系提供新的抵押品,促進金融周期觸底回升。
2024年年初至今,中國宏觀金融數(shù)據(jù)出現(xiàn)了“打架”的情況。一方面,消費增速、制造業(yè)投資增速、出口增速、工業(yè)增加值增速、采購經(jīng)理人指數(shù)等實體經(jīng)濟指標大致均在回升,另一方面,金融相關(guān)指標表現(xiàn)非常低迷。截至2024年3月,狹義貨幣M1同比增速僅為1.1%,創(chuàng)下自2022年1月以來的階段性新低。新增人民幣貸款同比增速在2023年2月和3月則分別為-46%與-17%。實體數(shù)據(jù)與金融數(shù)據(jù)打架的深層次原因,在于當(dāng)前中國經(jīng)濟周期與金融周期存在顯著的錯配現(xiàn)象。
當(dāng)前,中國的經(jīng)濟周期已經(jīng)處于反彈階段。然而,由于房地產(chǎn)市場處于結(jié)構(gòu)性調(diào)整階段,使得依靠房地產(chǎn)作為主要抵押品的銀行貸款市場運作不暢。抵押品價值下跌甚至抵押功能的喪失,是中國金融周期依然處于下行階段的重要原因。在此背景下,大規(guī)模增加國債發(fā)行,能夠為中國金融體系提供新的高質(zhì)量抵押品,這有助于緩解中國金融周期的下滑,促進其盡快觸底回升。而一旦經(jīng)濟周期與金融周期雙雙回升,這不僅將夯實中國經(jīng)濟增長的基礎(chǔ),而且有助于降低宏觀數(shù)據(jù)與微觀感受之間的溫差。
增加國債發(fā)行的意義之四,是有助于央行重構(gòu)基礎(chǔ)貨幣發(fā)行機制與完善利率傳導(dǎo)機制。
在1999年至2011年,中國連續(xù)13年出現(xiàn)了經(jīng)常賬戶與非儲備性質(zhì)金融賬戶雙順差的格局,外匯儲備不斷飆升,使得外匯占款成為當(dāng)時唯一的基礎(chǔ)貨幣發(fā)行機制。為避免外匯占款過度增長導(dǎo)致流動性過剩,中國央行還不得不通過發(fā)行央票與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方式進行沖銷。2015年“811匯改”前后,外匯儲備停止增長甚至開始下降,中國央行不得不尋找新的基礎(chǔ)貨幣發(fā)行機制。央行的公開市場流動性操作(OMO)和各種形式的再貸款成為新的基礎(chǔ)貨幣發(fā)行機制。而在大多數(shù)發(fā)達國家,央行在二級市場上買賣國債都是主導(dǎo)的基礎(chǔ)貨幣發(fā)行機制。因此,加大國債發(fā)行力度,并將央行在二級市場買賣國債的操作常態(tài)化,這有助于讓中國基礎(chǔ)貨幣發(fā)行機制與國際主流接軌。
目前中國貨幣政策傳導(dǎo)的一大問題是從短期利率向長期利率的傳導(dǎo)不暢,其中一個重要障礙即是中國缺乏完善的、富有彈性的國債收益率曲線。國債收益率曲線能夠向市場展示對期限結(jié)構(gòu)的確切定價,有助于短期利率變化向長期利率的傳導(dǎo)。因此,增加不同期限的國債發(fā)行,有助于完善中國的國債收益率曲線,疏通從短期利率到中長期利率的傳導(dǎo)。
增加國債發(fā)行的意義之五,是有助于推進中國金融市場高質(zhì)量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
目前,中國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已經(jīng)通過若干管道互聯(lián)互通,例如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跨境理財通、QFII與RQFII、QDII、QDLP等。然而,制約中國金融市場開放進度的關(guān)鍵障礙之一,是中國債券市場上高質(zhì)量債券(例如國債、國開債以及部分銀行發(fā)行的金融債等)的供給不足。因此,加大國債發(fā)行規(guī)模,可以給境外投資者提供更大規(guī)模、更高流動性的金融產(chǎn)品。
此外,從2018年開始,中國央行開始將加大國內(nèi)金融市場對境外機構(gòu)投資者的開放力度作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抓手之一。無論是在境內(nèi)人民幣金融市場還是在離岸人民幣金融市場,高質(zhì)量人民幣計價金融資產(chǎn)供給不足始終是制約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大短板。因此,同時在在岸市場與離岸市場加大人民幣計價國債的發(fā)行規(guī)模,既有助于政府融資,也有助于繁榮金融市場,還有助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可謂一舉三得。
在俄烏沖突爆發(fā)后,美國政府聯(lián)合盟國凍結(jié)了俄羅斯的外匯儲備,這實際上意味著美國國債對俄羅斯主權(quán)投資者的定向違約。這種美元武器化行為損害了美國國債作為安全金融資產(chǎn)的聲譽。作為回應(yīng),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新興市場國家將會加大在全球范圍內(nèi)配置新的安全資產(chǎn)的力度。中國國債,作為一個中高速成長、自身規(guī)模巨大、歷史資信極佳的大型新興市場經(jīng)濟體發(fā)行的高等級債券,具有成為全球重要安全資產(chǎn)的潛質(zhì)。中國政府應(yīng)該抓住這一機會,盡快將人民幣國債發(fā)展成為受到全球投資者公認的安全資產(chǎn)。這對人民幣國際化而言無疑是一個重要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