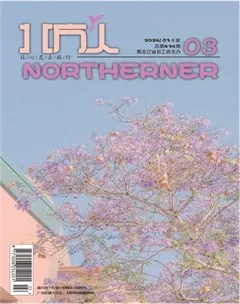人生急轉彎
裴思童

陳行甲的人生分為上半場和下半場。
之前,他最廣為人知的場面是2015年在湖北省巴東縣紀委全會上的講話,他在會議中怒斥腐敗官員,因此成為“網紅書記”。
2016年,在獲得中組部頒發的“全國優秀縣委書記”一年后,陳行甲辭職,創辦深圳市恒暉公益基金會,轉型成為一名公益人。最近,他將從事7年公益的經歷寫成新書《別離歌》,記錄生死離別。
路雖遠,行則將至
肖立是陳行甲的大學同學兼幾十年的好友,他一度不贊成陳行甲轉型。陳行甲總是聽著對方勸說,有時甚至還會拿紙筆記下來,“但我不覺得他是一個很容易受別人影響的人,他有自己的想法”,肖立說。
陳行甲做公益,發起的第一個項目是針對白血病患兒的“聯愛工程”。他不愿“靠販賣窮人悲慘故事來獲得富人捐助”,而是在經濟援助之外,為患兒做從心理輔導、生活照顧到社會回歸的全流程支持。
“在我們的項目中,給錢僅占5%,剩下的95%都是服務。”陳行甲說,“對于那些患者,除了給錢之外,他們漫長的治療過程中心理上有沒有得到支持?有沒有給他們科普應該怎么配合治療?在他們因為生病和社會脫節后,怎么重新和社會鏈接?有沒有人管這個事情呢?”他希望能夠探索出一個體系,幫助患者解決這些問題。
在所有幫助過的患兒中,扎西是令陳行甲印象深刻的一個。因為覺得求醫無望,扎西的父母拒絕為他治療。基金會成員反復溝通,用一周時間完成扎西醫保的補繳工作,最終幫助扎西成功獲得救助。后來,陳行甲一直將他與扎西的合照擺在桌上。
另一個令陳行甲印象深刻的患兒是李瑩(化名),她是所有患兒中病情反復時間最長、治療費用最高的一個,“用醫生的話說,李瑩幾乎將白血病患兒移植后可能經受的感染全都經受了一遍”,也因此讓這個普通的農村家庭背負了很多債務。
“聯愛工程”為李瑩進行了醫保目錄內的補充報銷。陳行甲認為,慈善應該有“行動的邊界”,不可無止境地付出,他希望能夠借此推動醫保目錄外的好藥進入國家醫保。
一些患者家屬茫然無措,“聯愛工程”幫助他們科普病情、緩解焦慮;患兒的治療周期漫長而痛苦,有專業社工進行“游戲陪伴”或是“藝術療愈”;近兩年元旦,“聯愛工程”為100名患兒實現了新年愿望;患兒病愈后,團隊成員也會時不時跟蹤回訪,幫助患兒重返社會。
2017年,在“聯愛工程”落地廣東省河源市之前,河源市的白血病兒童只能去廣州治療,后來,“聯愛工程”推動河源市人民醫院建立了兒童血液科。5年時間,“聯愛工程”在青海省成功救助了118名患兒,并將模式推廣至甘肅省。
山那邊是海
轉型做公益不是陳行甲唯一一次令人意外的轉身。
1988年,他從湖北興山縣城考入位于省城武漢的湖北大學數學系。肖立記得,新生見面會那天,陳行甲在自我介紹時一上臺便說:“我是從山里來的,畢業以后還會回到山里去。”
當時的肖立對這番言論感到不屑:“我覺得這話太做作了,說出來誰會信呢?”那正是改革開放浪潮興起的時候,大家都希望在時代風口中抓住機遇。
但沒想到,4年后的畢業關頭,陳行甲真的回到了從小長大的興山縣,在大山待了20余年。他在書里寫道:“除了對家鄉的留戀,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沒有那么自信,我不敢邁出自己的舒適區,在我內心深處,自己的能力只能勝任回到山區老老實實地做點小事。”
與此同時,與他上下鋪的肖立卻踩著時代機遇的浪花,先是南下深圳,后又北上北京,最終選擇前往美國。后來,陳行甲作為湖北省的后備干部來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與肖立在波士頓相聚。還沒見面,陳行甲便提出一定要去看海。在大西洋邊的峭壁上,陳行甲動情地講起小學時的一篇課文——《山那邊是海》,這播種了他人生中的某粒種子。
10多年后,陳行甲成立基金會,發起了一個名為“讀書,帶我去山外邊的海”的公益夏令營,將幾十個來自貴州山區的兒童帶去大海邊上了一堂詩歌賞析課。
別離歌
基金會員工史策始終留著一張照片,那是基金會成立之初,深圳社會組織總部給陳行甲批了一個辦公場地——一個大辦公室角落里的兩個工位。照片里,陳行甲坐在堆滿東西的擁擠角落,頭頂的架子上擺滿了獎杯獎狀,他蜷縮在下面,單手捂住雙眼,睡著了。
做公益,有時比起精力,更耗心力。做公益7年,陳行甲救助過很多兒童,卻也曾用盡全力依然無法挽回患兒的生命;他幫助過許多人,卻也曾被受助人攻擊;他鼓勵過抑郁少年,但最終那個少年依然選擇了離開……生離死別,在他的生活中如此密集地上演著。
他將這些故事寫進新書《別離歌》里,試圖通過書寫來安放自己的情緒。肖立沒能讀完這本書,他感到痛苦,忍不住對陳行甲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你這樣可持續嗎?”
講到這段時,陳行甲流下淚來,用一張面紙蓋住了雙眼,但很快又調整好自己,說:“我并不難受,因為我在這一路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與溫暖。”
陳行甲的微信界面時常跳動著他幫助過的孩子們的信息,孩子們跟他匯報自己的考試成績,為他唱生日歌;他去中國人民大學演講,有山區長大的女孩在演講結束后給了他一個淚流滿面的擁抱。
做公益以來,許多知名的企業家愿意支持他的事業。但他最難忘一對夫婦的捐款,他們來自縣城的工薪階層,家中有兩個正在上學的孩子,夫妻二人為基金會捐出了30萬元,他們說:“把錢給你,我覺得你會用好。”
陳行甲現在的公益團隊中,基本都是“90后”,多數人被他吸引而來。陳行甲身邊的志愿者趙英(化名)說,他曾經一度懷疑自己想要堅持的善良與正義是不可持續的,但他從陳行甲身上看到了某種可能,“至少有人和我結伴同行,我不孤獨”。
(摘自微信公眾號“冰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