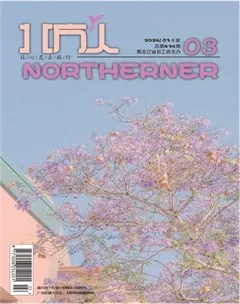撩去生活堅固的面紗
梁永安

母女關系是英國作家毛姆的《面紗》中值得細細體會的一點。
凱蒂的媽媽賈斯汀夫人“是個尖酸刻薄的女人,她支配欲極強,野心勃勃卻又吝嗇小氣、十分愚蠢”。她年輕時的愿望是丈夫可以飛黃騰達,自己跟著享受榮華富貴。這個愿望落空之后,她隨之而來的愿望是女兒嫁到上流社會,讓自己風光無限,“要給女兒找的不是一個好丈夫,而是一個杰出的丈夫”。是用女兒的婚事實現自己的人生夢想,還是讓女兒在自己的愛情選擇中建立獨立生命的起點?這是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劃分了母女關系中的惡與善。年輕的凱蒂,面臨著生命中第一次巨大的考驗。
可悲的是,盡管凱蒂反感母親的強勢安排,但她在家庭生活的潛移默化中,還是繼承了母親的生活邏輯。她被大家稱為“美人胚子”,這天生的漂亮反而害了她。母親不斷地提醒她,“再過一兩年她就不那么漂亮了,而漂亮姑娘可是年年都有”,但凱蒂挑花了眼,總是要找“更好的”,在一場場舞會中她不冷不熱地與追求者們友好地交往,同時小心地和他們保持著距離。她的博弈策略很實際:女人既然都要結婚,那就一定要找個性價比最高的。她雖然身處20世紀初期女性覺醒的時代,但她從來不會用現代的眼光看生活。現代女性的愛情,絕不宿命般地信奉“一定要結婚”,也不會像灰姑娘一樣日夜盼望夢幻般的王子,最有力量的信念是獨立,很多女性甚至根本不想結婚,只是遇上了那個不得不和他結婚的人,世界才瞬間柔軟下來,愛情才熠熠閃光。
一晃經年,凱蒂25歲了,按照通常的慣性,凱蒂大概率是朝著大齡未婚的方向發展。這沒什么不好,至少不會喪失自由。但風云突變,她以超快速度嫁給了病菌學家瓦爾特。這個瓦爾特“根本不是她喜歡的那種類型。個子不高,一點也不強壯,又小又瘦。和他漸漸熟悉之后,凱蒂覺得跟他待在一塊兒會讓她渾身不自在。他太死氣沉沉了”。凱蒂嫁給他,表面上是因為母親不斷地催婚,因為妹妹已經有了結婚對象,更深的緣由是來自她的沖動型性格。和瓦爾特結婚后她可以遠走高飛,跟隨丈夫去中國香港,徹底告別壓力如山的舊日子。沖動中她完全沒有意識到一個根本的問題:她不愛他,她的青春還缺少一次烈焰飛騰的戀愛。她帶著這樣一個龐大的問題結了婚,這能量不會消失,必然會在時間的燃點中爆發。這也是世間通則:問題都是擊鼓傳花,為“解決問題”而結婚,總會埋下更大的問題。
果然,來到香港,凱蒂遇上了唐森,一個精致優雅的利己主義者。他風度翩翩,情話綿綿,淋漓盡致地表現著一個不負責任的男人能夠多么瀟灑。凱蒂向發現私情的瓦爾特攤牌。她萬萬沒想到,平日木訥拘謹的丈夫竟然有著洞察一切的高智商,他痛切地告訴凱蒂:“我知道你愚蠢、輕佻、頭腦空虛,然而我愛你。我知道你的企圖、你的理想,你勢利、庸俗,然而我愛你。我知道你是個二流貨色,然而我愛你。我從未奢望你來愛我,我從未設想你會有理由愛我,我也從未認為我自己惹人愛慕。對我來說,能被賜予機會愛你就應心懷感激了。”如果我們因此把瓦爾特想象成一個癡呆呆的情種,那就大錯特錯了。他因為擺脫不了對凱蒂的愛而極其痛恨自己,并為此做出一個決定:帶著凱蒂去中國南方暴發霍亂的湄潭府,在病菌亂飛的死亡之地葬送生命,或她,或他,或全部。
寫到這里,故事的色調來了個大轉換,凱蒂帶來的問題像霍亂一樣傳染到瓦爾特身上。他變成了一個奇怪的混合體,一半是復仇的希斯克利夫,一半是疑慮滿心的哈姆雷特。他埋頭于拯救病患的繁忙中,每天敲擊死亡冰冷的大門。最后,他真的染上了霍亂,奄奄一息。在凱蒂痛苦的呼喚中,他說出人生的最后一句話:“死的卻是狗。”
是啊,“死的卻是狗”,他什么都明白,更知道一切不能重來。凱蒂為了解決自己的困境嫁給了他,卻像狗一樣傷害了自己的丈夫;受傷的瓦爾特反過來也煥發了“狗性”,逼迫凱蒂來到湄潭府這個死地。他沒有想到,艱難中的凱蒂已經變化,她奮不顧身地看護貧苦的霍亂病人,在忘我中發現了新世界:“她感覺自己在不斷地成長。沒完沒了的工作占據了她的心思,在和別人的交往中,她接觸到了新的生活、新的觀念,這啟發了她的思維。她的活力又回來了,她感覺比以前更健康,身體更結實。如今她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會哭了。”這個“新凱蒂”,瓦爾特并沒有看到,他怨憤,打不開天高云散的新生活,走不出愛的掙扎,歸根結底,他走不出對自己無限的恨。
《面紗》云遮霧罩,深藏著現代人生命中的一道道高坎。明察者未必自明,起點未必決定終點。世上的人大部分都是凱蒂,脆弱、單薄、渾身掛滿局限,很難像《面紗》中的女修道院長“拋棄了瑣屑、庸碌的一生,把自己交給了犧牲與祈禱的生活”。人生就是撩去面紗的過程,勞作、戀愛、婚姻、獨行,都是修煉。撥開陰影一重重,才發現逝者如斯,萬事都流走,只留下一句《面紗》中的箴言:“征服自己的人是最強的人。”
(摘自海南出版社《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