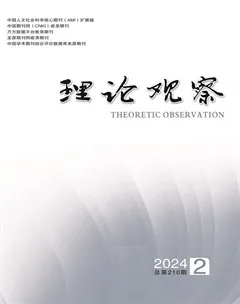具身認(rèn)知視角下文學(xué)語言特性反思與重構(gòu)
劉帥
摘 要:傳統(tǒng)的“形象論”視閾下對文學(xué)語言特性的界定,只關(guān)注到文學(xué)語言進(jìn)入公共場域后的特點(diǎn),而忽視了文學(xué)語言發(fā)出的生理機(jī)制以及文學(xué)語言從私人語域跨越到公共語域的過程。身體敘事學(xué)主要考察了內(nèi)文本身體與敘事之間的關(guān)系,但卻忽視了文本外身體對敘事的重要作用。在兩個(gè)殘缺的理論體系中我們需要反思與重構(gòu),重新恢復(fù)身體、語言與敘事的天然聯(lián)系。基于此,我們一方面需要借文本外身體來重探文學(xué)語言特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借文學(xué)語言來揭示文本外身體在敘事中的重要作用。進(jìn)而在對文本外身體與文學(xué)語言關(guān)系的考察中,我們窺見文學(xué)語言的特性在于具身與構(gòu)象。
關(guān)鍵詞:具身;文學(xué)語言;身體敘事學(xué);賽博格
中圖分類號:I045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1009 — 2234(2024)02 — 0102 — 06
文學(xué)語言特性的反思,是文藝?yán)碚摰囊粋€(gè)經(jīng)典議題。對文學(xué)語言特性的反思經(jīng)歷了從語言論視閾向形象論視閾的轉(zhuǎn)變,但隨著“后理論”時(shí)代的到來, 單純“形象論”視域研究出現(xiàn)了一系列的弊病,如何在“后理論”時(shí)代重塑經(jīng)典文論命題是我們當(dāng)下面臨的重要任務(wù)。身體敘事學(xué)以其獨(dú)特的理論關(guān)懷和學(xué)術(shù)建樹為我們反思和重構(gòu)文學(xué)語言特性提供了新視角。
一、辨正:文學(xué)語言與身體敘事學(xué)及其關(guān)系
(一)概念探微:“文學(xué)語言”與“身體敘事學(xué)”
對“文學(xué)語言”的概念界定,重點(diǎn)在于“文學(xué)”一詞的認(rèn)定,具體有兩條路徑:其一是將“文學(xué)”視為文學(xué)性,其二是將“文學(xué)”視為具體文學(xué)作品。文學(xué)語言也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學(xué)語言是指規(guī)范化的全民語言,它在口語的基礎(chǔ)上加工而成,也泛指各種文學(xué)書籍中所運(yùn)用的書面語言;狹義的文學(xué)語言則專指文學(xué)作品中的語言。[1]我們在此反思的文學(xué)語言不僅是狹義的文學(xué)語言,更是廣義上的文學(xué)語言。對文學(xué)語言特性的反思經(jīng)歷了從語言論視角向形象論視角的轉(zhuǎn)變 。首先 20 世紀(jì)初的語言論轉(zhuǎn)向直接催生了對文學(xué)語言的關(guān)注,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的理論家都相繼對文學(xué)語言特性做了探索,雅各布森認(rèn)為文學(xué)語言的本質(zhì)在于能指與所指的不穩(wěn)定性;什克洛夫斯基認(rèn)為文學(xué)語言的特征是拒絕簡化,以達(dá)到一種“陌生化”的效果;瑞查茲認(rèn)為文學(xué)語言是“內(nèi)指” 的。進(jìn)而在語言論研究基礎(chǔ)上,以童慶炳、趙炎秋為代表的當(dāng)代中國學(xué)者以馬克思主義文論為基點(diǎn),對文學(xué)語言特性作出了進(jìn)一步反思與修正。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中就曾對語言與物質(zhì)的關(guān)系做過探討,指出“‘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質(zhì)的‘糾纏,物質(zhì)在這里表現(xiàn)為振動(dòng)著的空氣層、聲音, 簡言之,即語言。[2]作為意識(shí)物質(zhì)性外殼的語言從出場伊始就同時(shí)與“精神”和“物質(zhì)”保有密切聯(lián)系:一方面語言是精神的具象化存在,另一方面語言又是物質(zhì)生活的產(chǎn)物。由此,當(dāng)代中國學(xué)者從形象論角度出發(fā),對文學(xué)語言特性進(jìn)行了修正,他們提出文學(xué)語言特性在于構(gòu)象性這一基本論斷。所謂“構(gòu)象性”即文學(xué)語言構(gòu)建形象的能力,這一觀點(diǎn)恢復(fù)了文學(xué)語言與生活的聯(lián)系,突出了語言論視角中被遮蔽的語言與生活的互動(dòng)性關(guān)系。趙炎秋在《形象詩學(xué)》中從“文學(xué)語言并不是一個(gè)獨(dú)立的自主體,總要表現(xiàn)出一定的生活內(nèi)容”[3](p167)、“文學(xué)語言表現(xiàn)的總是感性具體的生活”[3](p169)、“文學(xué)語言總是運(yùn)用各種手段,調(diào)動(dòng)自己塑造形象的潛能, 以滿足表現(xiàn)具體生活的感性形態(tài)的需”[3](p171)三個(gè)角度論述了文學(xué)語言特性在于其構(gòu)象性,并且對語言如何構(gòu)象作了充分的論述。自此“文學(xué)語言特性在于構(gòu)象性”這一論斷基本成為形象論視域下文學(xué)語言特性研究的最新成果,這一觀點(diǎn)在傳統(tǒng)理論語境之中具有強(qiáng)大生命活力和深遠(yuǎn)理論意義。但隨著后理論時(shí)代的到來,也出現(xiàn)了理論與文學(xué)實(shí)踐斷裂的情況,顯露出一系列的弊病。
身體敘事學(xué)即以身體為視點(diǎn)的敘事學(xué)研究。作為一種具有全球性視野的敘事學(xué)形態(tài),其理論構(gòu)設(shè)橫跨中西方語境。西方語境中身體敘事學(xué)的出場始于對經(jīng)典敘事學(xué)與身體美事的雙重反思,一方面以索緒爾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xué)為核心的經(jīng)典敘事學(xué)因?qū)v史社會(huì)文化觀照不足,進(jìn)入21世紀(jì)后其發(fā)展已經(jīng)顯得疲軟;另一方面“盡管身體在文學(xué)和文化批評中產(chǎn)生了興奮,但它對敘事學(xué)幾乎沒有任何影響”[4](p02)。基于此美國學(xué)者丹尼爾·潘戴以身體為視點(diǎn)對經(jīng)典敘事學(xué)進(jìn)行了重構(gòu)。在《敘事身體:建構(gòu)身體敘事學(xué)》一書中,他將身體與敘事都置放于歷史化進(jìn)程中,還原歷史語境中身體與敘事的交織性關(guān)系,進(jìn)而激活身體的敘事活力。立足于此,他指出身體敘事學(xué)主要有兩條研究路徑:其一是觀照“身體是如何被建構(gòu)為故事的一個(gè)組成部分”[4](p03),其二是探尋“身體是如何影響我們思維方式和敘事分析”[4](p03)。而當(dāng)代漢語學(xué)界對身體敘事學(xué)的探索,則可以溯于2008年許德金、王蓮香發(fā)表的《身體、身份與敘事——身體敘事學(xué)芻議》一文。首先他們對西方語境中身體敘事學(xué)建構(gòu)作出了反思,他們指出“潘戴所做的工作在敘事學(xué)界具有某種開拓的意義”[5],但其理論內(nèi)部因?qū)Α吧眢w”定義模糊而導(dǎo)致其理論效力不足。進(jìn)而他們建構(gòu)了當(dāng)代中國身體敘事學(xué)的研究框架:其一在于“身體”概念的定義,他們認(rèn)為有兩層身體即“文本外身體”與“內(nèi)文本身體”,“文本外身體”是指文本創(chuàng)作者和接受者的真實(shí)身體;“內(nèi)文本身體”則是指作為文本形象存在的想象性身體。其二在于通過“身份”這個(gè)中介將“身體”與“敘事”放置到更為廣闊的社會(huì)語境中,“從文化詩學(xué)的角度探討身體與身份在敘述中的作用”[6],憑此建構(gòu)中國式的身體敘事學(xué)。
(二)致思理徑:文學(xué)語言與身體敘事學(xué)的互滲
那么我們?yōu)楹我獙⑸眢w敘事學(xué)引入到文學(xué)語言特性反思之中呢?原因可以從三個(gè)方面說明:第一是身體敘事學(xué)理論亟待構(gòu)建與豐富。現(xiàn)階段的身體敘事理論大都集中在內(nèi)文本場域,主要揭示內(nèi)文本中的身體形象是如何推動(dòng)敘事,而缺少文本外身體的觀照,即需要恢復(fù)真實(shí)作者與真實(shí)讀者的身體在敘事理論中的地位。而文學(xué)語言正是文本外身體與敘事文本的交互中心,由此對文學(xué)語言特性的反思可以補(bǔ)寫文本外身體在敘事場域的理論缺位;第二是文學(xué)語言特性研究亟待發(fā)起新一輪自反性重構(gòu)。自提出“文學(xué)語言的特性在于其構(gòu)象性”后,學(xué)界少有對這種觀點(diǎn)的反思,理論與理論之間的對話關(guān)系被切斷。引入全新的身體敘事理論或許可以重新恢復(fù)起這種理論的對話關(guān)系,推動(dòng)文學(xué)語言特性研究向縱深化方向發(fā)展;第三則是以賽博文學(xué)為代表的新型文本實(shí)踐需要召喚新型文藝?yán)碚摗K^“賽博格”強(qiáng)調(diào)的是一種人機(jī)融合,唐娜·哈拉維在《賽博格宣言》中指出:“賽博格是一種控制生物體,一種機(jī)器和生物體的混合,一種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生物,也是一種科幻小說的人物……生活于界限模糊的自然界和工藝界”[7]。賽博格反映在文學(xué)領(lǐng)域,一是作為內(nèi)文本身體的賽博格,即文本中存在的以“人機(jī)交互”為特征的身體形象;二是作為文本外身體的賽博格,即以智能機(jī)器為主體的文本創(chuàng)造者與接受者,如微軟公司所制造智能作家“小冰”。賽博格在文學(xué)場域中的興起對文本敘事方式也產(chǎn)生了影響,凱瑟琳·海勒指出在賽博格對文本的介入中,敘事也被迫裂變——“文本分裂成主干和枝節(jié),主干包括主要的敘述,枝節(jié)主要是由插圖和線條構(gòu)成的假肢性的延申”[8]。綜上而述,賽博格文學(xué)的出場重新定義了“身體”,也重新定義了“敘事”,因此作為“身體”與“敘事”交互中心的文學(xué)語言也應(yīng)該作出進(jìn)一步的探索,以呼應(yīng)新型的文本實(shí)踐。
二、反思:文本外身體與文學(xué)語言的關(guān)系
許德金、王蓮香在《身體、身份與敘事——身體敘事學(xué)》對“身體”進(jìn)行了界定,據(jù)此將“身體”分為文本外的身體即真實(shí)作者和讀者的身體,以及內(nèi)文本的身體即文學(xué)形象的身體。從理論發(fā)展史看來,身體敘事學(xué)的研究主要圍繞內(nèi)文本身體進(jìn)行建構(gòu),而對文本外的身體討論不足。但文本外身體既是語言的發(fā)出者,又是語言的接受者,基于此筆者對文本外身體與文學(xué)語言的關(guān)系進(jìn)行了反思。
(一)文本外身體生理向度與文學(xué)語言的出場
一方面,文本外身體的生理屬性是文學(xué)語言出場的前提條件。文學(xué)語言的出場,即文學(xué)語言從創(chuàng)作者身體發(fā)出的過程,大致包括物象刺激、思想形成與語言發(fā)出三個(gè)階段。第一階段,文本外的身體是直接的感受器。這一階段,創(chuàng)作者依靠生理器官對外部世界(即自然與社會(huì))和內(nèi)部世界(即自我意識(shí))進(jìn)行觀照,以得到物象,進(jìn)而給予大腦刺激。這一階段直接決定了語言的特性。文學(xué)語言的出場要求這一階段身體對外物的感知必須是具身的,所謂具身是從屬于認(rèn)知科學(xué)的概念,這一概念至少包括兩重內(nèi)涵:“其一,認(rèn)知依賴于經(jīng)驗(yàn),而經(jīng)驗(yàn)來自擁有不同感覺運(yùn)動(dòng)能力的身體;其二,個(gè)體的感覺運(yùn)動(dòng)能力與一個(gè)更廣泛的生物學(xué)、心理學(xué)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9],其本質(zhì)在于打破認(rèn)知過程中的身心二分,強(qiáng)調(diào)身體在認(rèn)知過程中的構(gòu)成作用。具身性認(rèn)知才有足夠的動(dòng)力催生文學(xué)語言而離身性認(rèn)知催生的則是科學(xué)語言和日常語言。第二階段,文本外的身體是直接的儲(chǔ)存器和處理器。在這一階段,創(chuàng)作者依據(jù)第一階段所形成的認(rèn)知類型(具身認(rèn)知或離身認(rèn)知)來進(jìn)行編碼處理,形成思想。如果第一階段產(chǎn)生的是具身認(rèn)知,那么在這一階段,創(chuàng)作者的身體會(huì)更大程度介入到思想形成過程之中,使思想帶有創(chuàng)作者的主觀意圖。而如果第一階段產(chǎn)生的是離身認(rèn)知, 那么在這一階段,創(chuàng)作者的身體不會(huì)參與到思想的構(gòu)建之中,所謂的“思想”更多的則是一種社會(huì)意識(shí)或者信息編碼,而少有創(chuàng)作者的主觀意圖。第三階段,創(chuàng)作者的身體是直接的傳達(dá)器。著名心理學(xué)家 A.P.魯利雅曾繪制過思想到語言過程線路,這個(gè)過程可以分為四個(gè)階段:“(1)超始于某種動(dòng)機(jī)和總意向,(2)經(jīng)過內(nèi)部言語階段(3)形成深層句法結(jié)構(gòu),(4)拓展以表層句法結(jié)構(gòu)為基礎(chǔ)的外部言語。”[10]在這個(gè)階段,身體承擔(dān)的是傳達(dá)器的作用,身體需要將內(nèi)部言語外化為外部言語,完成語言出場的任務(wù)。
(二)文本外身體社會(huì)向度與文學(xué)語言的入場
另一方面,文本外身體的社會(huì)屬性是文學(xué)語言入場的先在條件。文學(xué)語言在實(shí)現(xiàn)出場之后,面臨的又一問題則是文學(xué)語言的入場,即文學(xué)語言如何從私人語域跨越到公共語域?根據(jù)拉康鏡像理論,人類從私人領(lǐng)域進(jìn)入公共領(lǐng)域,是以身體認(rèn)同為前提的,即認(rèn)識(shí)到身體是自我的且與外界分離的,那身體的社會(huì)屬性在很大程度上會(huì)影響到我們從私人語域進(jìn)入公共語域。美國社會(huì)學(xué)家約翰·奧尼爾在《身體形態(tài):現(xiàn)代社會(huì)的五種身體》中對身體作了分類,即世界身體、社會(huì)身體、政治身體、消費(fèi)身體、醫(yī)學(xué)身體。筆者認(rèn)為在這五種身體形態(tài)中,政治身體與文學(xué)語言入場關(guān)系尤為明顯,政治身體直接決定了文學(xué)語言能不能進(jìn)入公共場域。王一川先生在《近五十年文學(xué)語言研究札記》中提出“近五十年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語言呈現(xiàn)四種演化狀態(tài):大眾群言(1949—1977)、精英獨(dú)白(1978—1984)、奇語喧囂(1985—1995)和多語混成(1996 至今)”[11],由此觀之文學(xué)語言的入場,實(shí)際上與我們的政治身體密不可分。近五十年來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語言呈現(xiàn)的四種演化狀態(tài)實(shí)際上與我們四種政治身體有關(guān):1949 年—1977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biāo)志著現(xiàn)代中國人政治身體的成型,在這一剛剛成型的政治身體的影響之下,我們的文學(xué)語言面臨的任務(wù)便是以通俗化的方式來重建民族記憶,所以這一時(shí)期的文學(xué)語言更多地體現(xiàn)人民的意愿,呈現(xiàn)出大眾化的特點(diǎn),如《小二黑結(jié)婚》中鄉(xiāng)土性的語言風(fēng)格。1978—1984 年,政治環(huán)境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文學(xué)語言面臨的任務(wù)是反思與解放, 所以這一時(shí)期的文學(xué)語言呈現(xiàn)出濃厚的精英反思意識(shí)以及自由意識(shí),如以北島、江河為代表的朦朧詩人的語言風(fēng)格;1985——1995 年,城市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賦予政治身體以消費(fèi)的屬性,這一時(shí)期的政治身體被嵌入了消費(fèi)文化的元素,在這一身體的影響之下,文學(xué)語言呈現(xiàn)出奇異性的特點(diǎn),變得多元與豐富,如先鋒小說、尋根小說中的語言使用;而自 1996 年以來,隨著市場經(jīng)濟(jì)的逐步建立,我們的政治身體越來越開放和多元,據(jù)此也影響到文學(xué)語言,在這一身體影響下,文學(xué)語言也變得更加多元開放,比如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中的語言以及賽博格文學(xué)中的語言。此外,世界身體、社會(huì)身體、消費(fèi)身體、醫(yī)學(xué)身體都會(huì)給予文學(xué)語言入場以影響,在此因篇幅問題,就不多做論述。
綜上而言,文學(xué)語言與文本外身體呈現(xiàn)出兩層關(guān)系:一方面,身體的生理屬性賦予文學(xué)語言出場的生理基礎(chǔ);另一方面,身體的社會(huì)屬性也會(huì)影響到文學(xué)語言能不能進(jìn)入到公共話語空間,以實(shí)現(xiàn)語言的價(jià)值。基于此,在文學(xué)語言與文本外身體的緊密纏繞中,我們又如何來推進(jìn)文學(xué)語言特性重構(gòu)?
三、重構(gòu):具身與構(gòu)象
對文學(xué)語言特性的考查,經(jīng)歷了從語言論視閾到形象論視閾的轉(zhuǎn)變。趙炎秋在《形象詩學(xué)》中提出了“文學(xué)語言的特性,就在于它的構(gòu)象性”[3](p167)的觀點(diǎn),同時(shí)圍繞文學(xué)語言何以具有構(gòu)象性,語言如何參與構(gòu)象做了詳細(xì)的論述。這一觀點(diǎn)突破了語言論的狹窄視角,恢復(fù)了語言與生活的聯(lián)系,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價(jià)值。但是這一觀點(diǎn)沒有涉及到文學(xué)語言與文本外身體關(guān)系的考察,忽視了文學(xué)語言的出場,而僅僅關(guān)注文學(xué)語言的入場。
構(gòu)象性是文學(xué)語言的特性,這一論斷有以下弊病。第一,只從文學(xué)語言出場這一端考慮,而忽視了文學(xué)語言入場這一端。構(gòu)象性是指文學(xué)語言能夠構(gòu)成某種形象。但是這一特點(diǎn)僅僅是從文學(xué)語言的作用來進(jìn)行界定,是文學(xué)語言已經(jīng)具有“文學(xué)性”之后的反思,而對于文學(xué)語言產(chǎn)生之前的過程沒有反思,即沒有考慮到文學(xué)語言到底是如何被創(chuàng)造。我們認(rèn)為文學(xué)語言的生成,既要考慮到文學(xué)語言入場之后的效用,同時(shí)也要考慮到文學(xué)語言出場之前的過程,唯有從這兩端入手,才能進(jìn)行全面的界定。第二,構(gòu)象性不僅僅只是文學(xué)語言的特性,憑此無法區(qū)別文學(xué)語言與日常語言、科學(xué)語言。雖然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很難找到文學(xué)語言和日常語言、科學(xué)語言的準(zhǔn)確邊界,但是即使在理想形態(tài)之下,構(gòu)象性也不是文學(xué)語言與日常語言、科學(xué)語言的區(qū)別。日常語言和科學(xué)語言同樣具有構(gòu)象性,構(gòu)象性是語言的基本特性之一。如果語言不能構(gòu)建形象,就無法傳遞意蘊(yùn),進(jìn)而也無法承擔(dān)交際或表達(dá)的任務(wù)。這兩大問題的存在,推動(dòng)我們對文學(xué)語言特性反思進(jìn)一步深化, 在此我們將基于“具身認(rèn)知”這一新型原理,在認(rèn)知科學(xué)與文學(xué)的交叉視野中,重新思考文學(xué)語言特性這一重要問題。
“具身認(rèn)知”是20世紀(jì)80年代認(rèn)知科學(xué)中所出現(xiàn)的一種新型研究取向,意在強(qiáng)調(diào)身體在認(rèn)知活動(dòng)的重要作用,以突破傳統(tǒng)身心二元論的桎梏。1945年法國哲學(xué)家梅洛·龐蒂出版《身體現(xiàn)象學(xué)》一書,在其間他自覺避開了笛卡爾所制造的身心二元論陷阱,將身體視為知覺的主體,主張感知活動(dòng)中身體與心靈的互通,這一觀點(diǎn)還原了認(rèn)知過程中的身體維度,反駁了傳統(tǒng)視閾中認(rèn)知離身性的看法。進(jìn)而立足于這一概念,我們可以探賾到文學(xué)語言特性反思的新方向,即在身心統(tǒng)一論中重新還原文學(xué)語言的生成過程,進(jìn)而探尋其具體特性。在這一考察方向中,我們發(fā)現(xiàn)文學(xué)語言的特性在于具身與構(gòu)象。
從具身到構(gòu)象的過程,是文學(xué)語言從出場到入場的過程。文學(xué)語言的生成, 實(shí)際涉及到兩個(gè)加工端,一個(gè)是出場前作者的加工,另一個(gè)是入場后讀者的加工。具身是對前一個(gè)加工端的界定,而構(gòu)象則是對后一加工端的界定。下面我們對文學(xué)語言的生成過程做一描述:首先物象給予作者以生理刺激,形成具身認(rèn)知;其次在具身認(rèn)知的指導(dǎo)下,身心界限被打破;進(jìn)而在身心合一的基礎(chǔ)上,作者的主觀意識(shí)外化為生理動(dòng)作,形成文學(xué)語言;最后文學(xué)語言進(jìn)入公共場域,發(fā)揮構(gòu)象能力,形成形象,完成語言目的。在實(shí)際操作過程中,這一運(yùn)作過程也存在一些問題。按照問題的屬性我們可以分為兩個(gè)大類:實(shí)踐論問題與本體論問題,實(shí)踐論維度的探討主要觀照文學(xué)語言的生成機(jī)制,本體論的討論主要觀照文學(xué)語言的本體屬性,憑此在實(shí)踐與理論兩個(gè)維度共同揭示文學(xué)語言的生成與本質(zhì)。
(一)文學(xué)語言的實(shí)踐論思考
1.文學(xué)語言的生成是否一定需要物象刺激?
物象刺激是引發(fā)作者生理體驗(yàn)的前提,這里所談到的“物象”可以是實(shí)在的物象,也可以是儲(chǔ)存在作者大腦中的虛擬物象。沒有物象的刺激,一方面作者沒有形成語言的材料,另一方面作者也無法進(jìn)入發(fā)出語言的狀態(tài)。陸機(jī)《文賦》中就曾對物象與文學(xué)語言生成的關(guān)系進(jìn)行探討,“遵四時(shí)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11],物象刺激構(gòu)成了文學(xué)語言生成的必要條件。
2.具身認(rèn)知是否決定文學(xué)語言的生成就一定是即時(shí)性的?
我們認(rèn)為具身認(rèn)知與文學(xué)語言的生成不一定是即時(shí)性的,在實(shí)際的文學(xué)語言發(fā)出過程中有兩種情況:一是具身認(rèn)知與文學(xué)語言同步出場,即在具身認(rèn)知萌發(fā)的瞬間,作者的心理狀態(tài)直接外化為規(guī)范化口語或者書面語言;二是具身認(rèn)知與文學(xué)語言出場的延誤,即在具身認(rèn)知萌發(fā)之后,作者可能會(huì)出于某些考慮而延誤文學(xué)語言出場,這種延誤與作者的主觀審美、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以及社會(huì)的文化環(huán)境相關(guān),作者可能會(huì)在認(rèn)知形成之后對語言進(jìn)行二次加工,造成文學(xué)語言出場的延誤。但需要說明的是文學(xué)語言的延誤出場并不代表文學(xué)語言具身過程的無效,作者對這一語言的再次加工始終都是需要圍繞具身認(rèn)知進(jìn)行,具身認(rèn)知是文學(xué)語言出場的必要環(huán)境。
(二)文學(xué)語言的本體論思考
1.文學(xué)語言是否具有具身性?
我們認(rèn)為文學(xué)語言與具身性并不是一種所有關(guān)系,二者構(gòu)成了雙重因果關(guān)系:一方面在文學(xué)語言出場之前,必須經(jīng)由具身認(rèn)知喚起,才能催生文學(xué)語言誕生;另一方面則是在文學(xué)語言入場之后,由于文學(xué)語言具有構(gòu)象能力,其構(gòu)成的意象又能夠喚起語言接受者的新一輪具身性認(rèn)知。立足于此,我們沒有以“具身性”和“構(gòu)象性”來表述文學(xué)語言的特性,而是用“具身” 與“構(gòu)象”兩個(gè)過程來定義文學(xué)語言的特點(diǎn)。
以“具身”和“構(gòu)象”兩個(gè)過程來定義文學(xué)語言的特性,一方面能夠區(qū)分文學(xué)語言與日常語言、科學(xué)語言;另一方面又沒有否定在現(xiàn)實(shí)語境中文學(xué)語言與日常語言、科學(xué)語言的相互滑動(dòng)。
2.立足于“具身到構(gòu)象”這一過程,我們?nèi)绾螀^(qū)分文學(xué)語言與日常語言、科學(xué)語言?
需要表明的是文學(xué)語言與日常語言、科學(xué)語言在實(shí)際語言運(yùn)用過程中并沒有明確邊界,因此我們談?wù)撊叩膮^(qū)別是基于這三種語言在出場之前和入場之后所呈現(xiàn)出的不同分野:
首先,我們談文學(xué)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差異:第一,在出場之前,文學(xué)語言更靠近身體;而日常語言與身體的距離更遠(yuǎn)。在具身認(rèn)知指導(dǎo)之下,文學(xué)語言離身體的距離更近,有兩種表現(xiàn):一是文學(xué)語言在表現(xiàn)形態(tài)上會(huì)融入更多創(chuàng)作主體的身心感受;二是文學(xué)語言在語言性質(zhì)上會(huì)表現(xiàn)更多創(chuàng)作主體的身心狀態(tài)。以勸酒場景為例,《赤壁賦》中蘇子勸客飲酒的表達(dá)是“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12],可以見出《赤壁賦》中的勸酒辭更多地觀照到創(chuàng)作主體的生理體驗(yàn),將蘇軾的眼部視覺體驗(yàn)與心理感受融合在一起,一方面以一葉扁舟寫眼部視覺,另一方面以舉樽相屬寫心理活動(dòng),這種身心融合的表達(dá)方式也使得文本語言更能透徹地表達(dá)出蘇軾的曠達(dá)之感。而日常語言由于認(rèn)知的離身,往往與身體距離更遠(yuǎn),如“您喝酒嗎”則是創(chuàng)作主體直接以心靈控制身體,在身心二分的情況下,對他者的簡單詢問,而少觀照創(chuàng)作主體自身的生理體驗(yàn)與狀態(tài);第二,在出場之前,文學(xué)語言更為純粹,而日常語言則是多維復(fù)合的。文學(xué)語言因更靠近創(chuàng)作主體的身體,所以能夠保留更多創(chuàng)作者身體的原始印記,維持語言本真狀態(tài);而日常語言因?yàn)檫h(yuǎn)離身體,故少有創(chuàng)作者身體痕跡,顯示出更加復(fù)雜的情況。仍以上面邀請喝酒的語境作說明:“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13]同樣是保留了創(chuàng)作者眼部視覺與心理感知的文學(xué)語言,而“您喝酒嗎?”這一日常用語體現(xiàn)出社會(huì)禮制的介入,發(fā)言者在發(fā)言之前總要考慮到發(fā)言的場合、語言接受的對象等因素,使語言呈現(xiàn)出更加復(fù)雜的面貌。第三,在入場之后,文學(xué)語言更具多義性,日常語言的意義則較為單一。由于在出場前文學(xué)語言始終保有一種純粹性,所以進(jìn)入到公共場域之后,文學(xué)語言像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擁有了更大的闡釋空間,進(jìn)而形成了文學(xué)語言的多義性。而日常語言由于在出場之前,就受到了語境、語言接受對象等因素的多重限制,在入場之后它的闡釋空間反而被限制與壓縮,進(jìn)而能夠?qū)崿F(xiàn)準(zhǔn)確的語義表達(dá)。第四,在入場之后,文學(xué)語言更具有構(gòu)象性,而日常語言的構(gòu)象能力較弱。由于文學(xué)語言更多地表現(xiàn)了身體多維器官的感知,其語言狀態(tài)相較于日常語言則更為形象。具體體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文學(xué)語言所構(gòu)成的“象”比日常語言更為形象; 二是文學(xué)語言所構(gòu)成的“象”的意義比日常語言更深遠(yuǎn)。比如在一個(gè)下雪的天氣, 日常語言的表達(dá)可能是“好大的雪啊”,而文學(xué)語言的表達(dá)則是“未若柳絮因風(fēng)起”[14],這兩句話相比,一方面日常語言是單純靜態(tài)的抒發(fā),我們只能看到大雪的形象,而文學(xué)語言則是以柳絮作比,馬上浮現(xiàn)在我們眼前的就是白雪紛飛的動(dòng)態(tài)形象;另一方面在意象之外,文學(xué)語言的表達(dá)使我們看到了發(fā)言者的想象使白雪穿越了季節(jié),化作紛飛的柳絮,體現(xiàn)出發(fā)言者獨(dú)特的意趣,而日常語言在這一點(diǎn)上,顯然是不及文學(xué)語言的。
其二,我們來談文學(xué)語言和科學(xué)語言的分野。第一在出場之前,文學(xué)語言是身心合一,而科學(xué)語言是身心二分的。文學(xué)語言與日常語言關(guān)于具身與離身的區(qū)別表現(xiàn)在語言與身體的距離,而文學(xué)語言與科學(xué)語言關(guān)于具身與離身的區(qū)別則是表現(xiàn)在身心關(guān)系上。文學(xué)語言在入場之前身心是合一的,而科學(xué)語言則是主體的心理直接控制了主體的身體呈現(xiàn)。科學(xué)語言是以表達(dá)真理為目的,在入場之前在發(fā)言者頭腦中的不是具體物象,而是抽象概念,這個(gè)抽象概念無法引發(fā)發(fā)言者的具身性認(rèn)知,因此身心也無法融合。比如對“靈感”一詞的定義,科學(xué)語言是“文藝、科技活動(dòng)中瞬間產(chǎn)生的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突發(fā)思維狀態(tài)”,而文學(xué)語言則是“眾里尋他千百度,慕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15]。第二在入場之后,文學(xué)語言構(gòu)建形象,科學(xué)語言闡明概念。由于入場之前,身心關(guān)系的不同,二者出場后的語言效用也不同。文學(xué)語言始終以構(gòu)建形象,營造審美氛圍為目的,而科學(xué)語言則是以還原現(xiàn)象,表達(dá)真理為目的。我們?nèi)砸詫Α办`感”的發(fā)言為例,文學(xué)語言側(cè)重描述的是靈感產(chǎn)生的過程以及心靈體驗(yàn),而科學(xué)語言則是對“靈感是什么”進(jìn)行了界定。
四、結(jié)語
文學(xué)語言被兩個(gè)身體共享,具身是面對語言發(fā)出者身體的特性界定,構(gòu)象是面對語言接受者身體的特性界定。單單只從一端界定文學(xué)語言特性,是無法形成理論內(nèi)部的自證循環(huán)。從具身到構(gòu)象既是文學(xué)語言從出場到入場所需要完成的任務(wù),也是文學(xué)語言與其它語言的特性差異。但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本來就不存在文學(xué)語言和日常語言、科學(xué)語言的明確區(qū)別。日常語言、科學(xué)語言與文學(xué)語言之間是不斷滑動(dòng)的,這種語言的滑動(dòng)實(shí)際上也是我們認(rèn)知的滑動(dòng)即從離身到具身的滑動(dòng)。
從具身到構(gòu)象,基本還原了文學(xué)語言出場與入場兩個(gè)環(huán)節(jié),恢復(fù)了文學(xué)語言與身體聯(lián)系。但是新一輪人機(jī)融合思潮下所產(chǎn)生的賽博格文學(xué)以及機(jī)器人文學(xué),可能會(huì)重新定義文學(xué)語言的特性,如此種種都會(huì)將文學(xué)語言的特性研究推向深化。但無論是賽博格文學(xué)還是機(jī)器人文學(xué)下的文學(xué)語言都始終是一種身體語言,只不過是從單一身體走向了多維身體,從現(xiàn)實(shí)身體走向了虛擬身體。具身與構(gòu)象仍會(huì)是文學(xué)語言從出場到入場所必不可缺的質(zhì)素。
〔參 考 文 獻(xiàn)〕
[1]趙炎秋.文學(xué)原理[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6:106.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1.
[3] 趙炎秋.形象詩學(xué)[M].北京: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4:167,169,171,167.
[4]PUNDAY D.Narrative Bodies:Toward a Corpreal Narratology[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02,03,03.
[5]許德金,王蓮香.身體、身份與敘事——身體敘事學(xué)芻議[J].江西社會(huì)科學(xué),2008(04):28-34.
[6]唐娜·哈拉維.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河南: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2016:314-315.
[7]凱瑟琳·海勒.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xué)、信息科學(xué)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7:166.
[8]湯擁華.重構(gòu)具身性:后人類敘事的形式與倫理[J].文藝爭鳴,2021(08):56-63.
[9]衛(wèi)志強(qiáng).當(dāng)代跨學(xué)科語言學(xué)[M].北京:北京語言學(xué)院出版社,1992:105.
[10]王一川.近五十年文學(xué)語言研究札記[J].文學(xué)評論,1999(04):16-26.
[11]陸機(jī).張少康集釋.文賦集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
[12]蘇軾.蘇軾文集[M].孔凡禮,點(diǎn)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6.
[13]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C]//白居易.問劉十九,北京:中華書局,2006:1358.
[14]朱鑄禹.世說新語匯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9.
[15]辛棄疾.稼軒詞編年箋注[M].鄧廣銘,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0.
〔責(zé)任編輯:楊 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