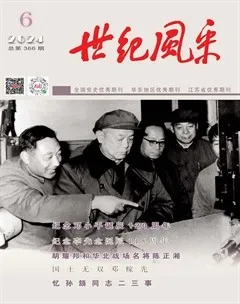宜興革命之花陳掌倫
張靜靜

1924年5月,陳掌倫(參加革命后改名為朱虹)生于宜興縣楊巷鎮的一戶貧苦家庭。全國抗戰爆發后,在表兄梅應章影響下,陳掌倫決心投身革命。1940年9月,她考入江蘇省第五臨時中學(簡稱省五臨中)高師,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黨組織委派下,她積極在校園內建立地下黨小組,團結眾多進步青年。1941年5月,她與該校的余仁溥等地下黨員一起轉移到新四軍根據地,參加青年訓練班學習。不久被分配到中共句容縣委任秘書,1942年下半年調到中共茅山地委宣傳部印刷所油印組工作。她以堅定的信念和頑強的毅力,在艱苦環境中為革命事業貢獻力量。1943年4月,日、偽軍對茅山地區進行大“掃蕩”。陳掌倫因奸細告密被捕,雖遭受敵人嚴刑拷打,但始終堅貞不屈,守口如瓶,最終因傷勢過重,于同年10月離世,年僅19歲。
“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在一百多年的黨史長河中,那些為革命獻身的英雄人物,如璀璨繁星,熠熠生輝,照亮了前方的道路。他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用鮮血澆灌理想之花,用生命捍衛信仰之炬,大義凜然,英勇獻身,譜寫了一曲曲感天動地的英雄贊歌。
今年,恰逢宜興女英烈陳掌倫誕辰百年,盡管她的生命旅程短暫,卻如流星劃過夜空,留下一道絢麗的光軌,她的精神永遠璀璨,激勵著我們前行。讓我們一同追尋她的奮斗足跡,重溫她那不屈不撓、英勇無畏的革命歷程,感受那份為國家、為民族、為理想而英勇奮斗的崇高精神。
投身革命,青春熱血鑄忠魂
她7歲時,父親亡故,自此一家老小7口人全靠母親作為小學教員的微薄薪金來養活,日子過得十分艱苦。吃的是菜粥、菜飯,穿的是親友們贈送的舊衣,還經常要借貸和干雜活才能勉強糊口。年幼的陳掌倫常問媽媽:“我們窮人為什么這樣苦呢?”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陳掌倫的表兄梅應章(上海地下黨員)因病回楊巷休養,住在陳掌倫家里。在這期間,梅應章和幾個同志辦起了楊巷快報社,自任編輯,筆名美弓,積極開展抗日宣傳活動。在表兄的教育和幫助下,陳掌倫14歲就閱讀革命書籍,學習寫稿,逐漸懂得不少革命道理。她深刻認識到社會的貧困與落后源于舊制度,唯有推翻舊制度,窮苦人民才能過上好日子。可惜,沒過多久,表兄肺病惡化,不幸去世。陳掌倫化悲痛為力量,決心以表兄為榜樣,投身革命,為窮人的解放貢獻自己的青春。
1940年9月,陳掌倫進入胥井省五臨中高師讀書,并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支委會經常到校外樹林里秘密研究工作和學習。他們藏有一箱馬列書籍,在黨員和積極分子中傳閱,閱后交流學習心得。上級領導也曾幾次深入胥井,作關于形勢和任務的傳達報告。
1941年上半年某天下午,國民黨第三戰區第二游擊區總指揮冷欣率軍隊突然包圍學校,揚言要搜查共產黨,并在通道口架起機槍,隨即進行了翻箱倒柜的搜查。好在同學們早有準備,將書藏在宿舍的竹椽內,有的還巧妙地用教科書的封面紙包好,沒有被敵人發覺。敵人一無所獲,只得在操場集中訓話,亂說一通后,灰溜溜地走了。為保存革命力量,陳掌倫與部分黨員被安排轉移至蘇南敵后抗日根據地。
1941年暑假開始,省五臨中要搬遷到安徽柏墊,組織上決定叫余仁溥(化名承滬)、夏荷芬(改名梅章)、陳掌倫(改名朱虹)及非黨同學小任4人在芳莊集中,一路有秘密交通員護送。他們巧妙地以暑假回鄉為名,攜帶成績單作為通行證,順利通過了幾道國民黨哨所,最終抵達了溧陽北部的16旅旅部和蘇皖區黨委。分道到達的還有杜雄飛(改名嚴群),他們是該地區轉移出去的最后一批黨員。
在動身的前幾天,陳掌倫回到家中,母子4人聚在后門口的大樹下乘涼,興致勃勃地講故事、唱歌,陳掌倫反復吟唱著《別娘行》:“別娘行,戎裝今日上兒身,娘莫言兒心腸狠,敵比兒心狠萬分……”聲音越唱越激昂,越唱越響亮,誰也沒有想到,她這是在向母親和弟弟妹妹告別呢!
7月1日早上,陳掌倫瞞著家人,背了一只大書包,里面裝著幾本革命書和幾件換洗衣物,悄無聲息地離開了芝菓圩村,前往芳莊與余仁溥、夏荷芬等人會合。她臨行前留下一張照片和一封家書,大意是:親愛的媽媽,我們的學校要遷往柏墊去了,家里不可能有那么多錢供我上學,現在我長大了,可以獨立出外謀生,一方面可以減輕媽媽的負擔,另一方面也可以出去鍛煉鍛煉,為民族解放事業出把力。
兩天后,當妹妹陳掌明在芳莊拿到這封信和照片時,眼淚奪眶而出,母親更是悲痛欲絕,暈倒在地。村上的群眾見狀,無不為之落淚,好心的婆婆阿姨們前來勸慰,告訴母親不要生氣,女兒家長大總歸是別人家的。誰知越勸,母親哭得越厲害。她說:“你們別弄錯,我的女兒決不是那等人,她是去參加革命的。”未曾想,就這幾句話,無意中為日后埋下了禍根。
堅守信念,鐵骨錚錚斗敵頑
陳掌倫踏入新四軍根據地后,隨即投入到青年訓練班的學習之中。起初,她參加民運工作,領導減租減息運動。不久,被分配到中共句容縣委擔任秘書一職,1942年六七月間,又被調至中共茅山地委宣傳部印刷所油印組工作。他們白天駕著小船在蘆蕩中流動辦公,夜晚則在老鄉家中分散住宿,平時一星期搬一次家,遇到緊急情況,甚至一夜之間輾轉三四個地方。
盡管生活和工作條件極為艱苦,但印刷所的每位同志都學會了撐船。陳掌倫雖身為女同志,也毫不遜色。她吃苦耐勞,每日堅持學習,并在艱苦的環境中關心、幫助同志。嚴峻的形勢也使他們養成了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靈活的應變能力。
有一次,陳掌倫與一名男同志前往丹陽城執行任務。返回時,他們攜帶了大量宣傳品和重要文件。為了掩人耳目,他們喬裝成新郎新娘,挑著紅籃回娘家,文件等物被巧妙地藏在籃底,上面則擺放著紙包、糕點、雞蛋等物品作為掩護。經過崗哨時,幾名偽軍攔住了他們,厲聲質問:“干什么的?”男同志順勢將紅籃往前一推,回答:“回娘家。”偽軍們嘻嘻哈哈,伸手便去搶籃里的東西,只顧往嘴里和口袋里塞食物,并未察覺籃底的秘密。他們成功地混出了城。為了盡快趕回駐地,他們加快腳步。這時,迎面走來一個人,目不轉睛地盯著他倆,似乎發現了什么。男同志見狀,機智地放下擔子,假裝去小便。他邊走邊思考,這里離城很近,如果被敵人抓住,可能會誤了大事。于是,他向陳掌倫使了個眼色,兩人一躍而起,一個箭步抱住那人的腰,陳掌倫伸手去奪武器,那人拼命掙扎。在緊急關頭,他們發現那人的手榴彈柄蓋上有一顆紅星。原來,是自己的同志,三雙手緊緊握在一起,禁不住熱淚盈眶,連聲說:“誤會,誤會……”
印刷所一直輾轉在茅山地區的延陵、西旸、高莊和天王寺磨盤山一帶。陳掌倫對革命工作熱情負責,從不考慮個人的安危。為了趕印當時的整風文獻,在暗淡的豆油燈下常常堅持到深夜,甚至通宵,因此胃病也漸漸加重。
1943年4月,日、偽軍對茅山地區進行了殘酷的大“掃蕩”,形勢異常緊張,組織上決定讓體弱多病的同志暫時回鄉隱蔽,保存力量。陳掌倫因身體欠佳,奉命回家隱蔽。當時,芝菜圩環境錯綜復雜,村上有國民黨的便衣隊,山上有日本的炮臺,安樂山和都山的偽軍也時常出沒。面對陳掌倫的歸鄉,房東石煥文膽戰心驚,立刻跑來勸說:“掌倫啊!你還是到鄉政府去自首吧,否則這里是無法安身的。”陳掌倫斬釘截鐵地說:“頭可斷,血可流,而志不可奪!你們怕,我絕不連累你們,請放心。”
為避免敵人的迫害,陳掌倫只得多次輾轉于親戚家住。在此期間,陳掌倫從未忘記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每天早晨,她都會學習整風文獻與革命書籍,并認真做筆記。每到一處,她都會對周圍的群眾進行革命宣傳。由于家境貧困,長期寄居親戚家并非長久之計,母親就托人在和橋附近的一所小學為她找了一份工作。暑假到來,陳掌倫回到家中,她從不外出,總是在家中看書、學習,看完后便藏書于柴堆或神柜底下,以防萬一。1943年8月底,正當她動身準備去學校時,芝菜圩偽保長手拿繩子,帶著幾個國民黨特務闖進屋,要將她捆綁。陳掌倫毫不畏懼,昂首挺胸,厲聲喝道:“用不著捆,跟你們走好了。”而后,她回過頭,柔聲細語對著母親說道:“媽媽你別難過,譬如少養我一個吧!”又親切地關照弟妹說:“掌明妹,森岳弟,你們要聽媽媽的話,我走了。”
英勇就義,革命精神永流傳
陳掌倫被敵人抓走后,關押在溧陽戴埠慈溪嶺的看守所里。敵人對她軟硬兼施,企圖逼她招供,都被她嚴詞拒絕。敵人氣急敗壞,對她施以進一步的摧殘與折磨,甚至將她拖出室外,假意槍斃,企圖逼她就范。但陳掌倫始終堅貞不屈,與敵人展開了頑強的斗爭。她始終抱著一個信念:共產黨員寧可站著死,不愿跪著生。
敵人窮兇極惡,使盡手段,可陳掌倫還是守口如瓶,不吐一字。她的身體在嚴刑拷打之下日漸衰弱,精神上更是遭受了巨大的創傷,以至于神志不清,奄奄一息。最后還是梅守鶴(梅應章的父親)出面,以監外就醫的名義才將陳掌倫暫時保釋出獄。她出獄時已經不省人事,被打了強心針后用擔架抬下山。回家后,雖然多方請醫治療,但收效甚微。她的鼻、口經常出血,大小便也有血。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陳掌倫依然保持著堅定的革命信念,對革命的未來充滿信心。每當有人對她表示憐憫時,她會非常憤怒地說道:“你們這些怕死鬼,總是怕流血,如果沒有流血犧牲,革命怎能成功呢?勝利就在眼前了,大家等著瞧吧!”她的臉上,總會在這時候露出一絲微笑,那是對革命勝利的堅定信念和對未來的美好憧憬。
回家不到半個月,陳掌倫終因傷情過重,醫治無效,于1943年農歷九月初九的夜里,與世長辭,年僅19歲。
陳掌倫犧牲后,中共蘇皖區黨委為她秘密舉行了追悼會,悼念這位年輕而偉大的女英雄。
1979年4月,為了永遠紀念這位英勇的女戰士,楊巷人民在塍頭地為她建造了烈士墓,樹了烈士碑。曾擔任江蘇省委領導的江渭清同志也曾親自前來拜祭,表達對這位女英雄的深深敬意。
投身革命即為家,血雨腥風應有涯。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陳掌倫用自己年輕的生命詮釋了什么是真正的英雄和勇士。她堅守信仰、不畏強暴、敢于斗爭的精神,將永遠激勵著后人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
(作者系宜興市檔案史志館黨史陳列科(館)副科長)
責任編輯:李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