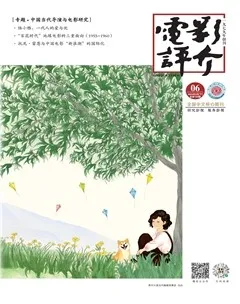中國體育電影運動者形象的成長敘事研究
費辰光 呂蘇雯



體育電影通過扣人心弦的運動場景、快節奏的動作剪輯、熱血的視聽語言表達為觀眾尤其是青少年群體提供了現實世界中的英雄想象。在電影塑造的各類角色中,如果能夠同時具備勵志屬性和偶像特質,那將會成為被廣泛關注的時代熱點,并且被青少年爭相追捧和效仿,而中國體育電影中的運動者形象正是這樣的銀幕典型。
長期以來,基于我國體育領域“舉國體制”,這種敘事場景僅存在于專業領域和國際賽事競爭之間,以“為國爭光”“集體榮譽”“拼搏奉獻”等關鍵詞的英雄敘事書寫幾乎代言了運動者形象的藝術表征。隨著我國社會制度的不斷更新和完善,教育和體育事業的前進和發展,以往專注于文化學習的青少年能夠在日常體育活動中體會運動的樂趣,健全人格的同時豐富人生體驗,傳統競技體育的專業壁壘也被逐漸突破。伴隨著體育社會功能尤其是教育理念的變化,近些年中國體育電影中的運動者形象在保留原有風格的前提下,其敘事主體、敘事空間都突出了以“成長”為主題的新變化。
一、時代變遷下中國體育電影敘事主體的選擇與演變
電影敘事主體的身份界定和自我認知決定了人物形象的文化影響力,人物個體也受限于社會環境的教化和引導。國內觀眾對體育魅力的感知主要來自風云變幻的國際比賽和呈現高水平的專業競技場,運動者要么能夠為國爭光,要么具備超人本領,這種對敘事主體的訴求奠定了過去幾十年間體育電影英雄敘事的基礎。近年來,國內體育題材電影在對敘事主體進行選擇時,除了傳奇人物以外,也逐漸開始關注平凡個體在運動中的成長,敘事邏輯也從高高在上的英雄敘事引申出蕓蕓眾生的成長敘事。這一變化來源于體育和教育思潮的轉變和人們對體育認知的不斷加深。隨著體育功能向大眾傾斜,青少年素質教育的普及,觀眾也會更多地看到貼近生活的運動者形象,看到體育與生活之間的良性互動,并通過電影的成長敘事體驗人物的運動經歷。
(一)從國民英雄贊歌到個人追夢傳奇的敘事轉向
國人心目中傳統且經典的體育電影往往是主旋律式的英雄傳記,如《女籃五號》(謝晉,1958)、《沙鷗》(張暖忻,1981)乃至近年上映的《奪冠》(陳可辛,2020)、《中國乒乓之絕地反擊》(鄧超/俞白眉,2023),其主題皆為運動健兒代表國家參加大型國際比賽為國爭光的故事,這是國內長久以來在舉國體制下形成的文化語境。此類電影的敘事主體呈現了受命于危難到成就不朽傳奇的熱血歷程,遵循了一種英雄敘事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主人公一出場便自帶堅毅人格和獨特個性,朝著帶有強烈家國信念的理想艱苦奮斗。[1]以《奪冠》為例,郎平在教練員魔鬼式的訓練環境中帶著一臉堅毅的神情出場,為全篇所展現的女排精神定調。主人公在經過常人難以想象的刻苦訓練后,逐漸從一名替補隊員成長為主攻手,帶領球隊贏得世界冠軍,完成英雄的第一重考驗;轉眼多年,僑居已久的郎平面對中國女排低谷毅然選擇回國執教,經受住英雄敘事在價值觀層面的問詢;電影最后的爭冠戲份中,鏡頭不斷閃回郎平指導和隊員間的對話,探討有關賽場和人生等競技體育的深刻議題,教練幫助隊員解開心結并贏得比賽,主人公至此達成英雄敘事的終極冒險。從當代電影的傳播媒介這一屬性來說,此類電影的影響力遠不如它的“前輩”《女籃五號》和《沙鷗》在當時產生的影響力和話題性,其票房水平與同期排檔影片相比也沒有競爭力。拋開市場和文化環境的因素,其背后的玄機正如《奪冠》里所講:“以前在乎一場比賽的輸贏,是因為內心不夠強大。”如今中國健兒在國際賽場斬金奪銀已是常態,排球、乒乓球等項目的轟動效應已不如前,民眾更關心切身生活經歷和社會現實話題。
近年來,部分電影中運動者形象的建構開始剝離以往作品中常被賦予的家國屬性,重點呈現體育附著在人物身上的職業屬性,其身份從億萬人中甄選出的天之驕子,落地為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積極進取的追夢者,并通過其個人職業的成長過程,向觀眾傳達勵志的情緒能量,運動者主體身份的變化反映了創作者對于體育功能變化的感知,這種變化源于民眾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經濟生活的多元化,以及體育活動的普及。這種變化為體育題材電影帶來了新的創作思路,更加符合經濟社會發展,人們對于更貼近生活的平民英雄的期待。此類電影如《激戰》(林超賢,2013)、《破風》(林超賢,2015)、《飛馳人生》(韓寒,2019)、《超越》(韓博文,2021)等,《激戰》中的過氣拳王程輝賭博欠債,禍及身邊人,深感內疚,是訓練和比賽使他重塑了積極向上的生活狀態,在拳王賽中拯救了自己向下的人生,也為身邊人爭取了生活的向善;《飛馳人生》中的拉力賽車手張馳經歷了漫長的禁賽低谷,懷揣最初的熱愛,無視外界的奚落嘲諷,忍受現實的冰冷殘酷,本著“奉獻即一切”的人生信念再次征服巴音布魯克。
(二)從聚焦專業競技選手到關注普通青少年
運動者人物形象的另一種轉變是將運動者身份的專業屬性去除,運動者變成普通的青少年。運動純粹的成為一項愛好、一種經歷,運動者引領觀眾一起在體育活動中感受情緒、接受挫折,完成自身的成長和變化。此類電影如《了不起的老爸》(周青元,2021)、《雄獅少年》(孫海鵬,2021)、《五個撲水的少年》(宋灝霖,2021)、《四海》(韓寒,2022)、《熱辣滾燙》(賈玲,2024)等。這些電影的主人公皆是普通學生或者待業青年,不再是遠離普通人生活的專業運動者,他們沒有漫長且封閉式的專業系統訓練,也尚未背負國家榮譽和神圣使命,他們面臨學業和生活的多重困境,靠自身努力突破重重障礙,通過運動感知理想、情感和生活。《雄獅少年》中打工的少年阿娟是未成年兒童群體中的一員,與阿貓、阿狗結隊參加舞獅比賽,他所追求的只是為了證明自己可以成為一頭“雄獅”,其間他感受到現實生活中的諸多無奈,也收獲了真摯的友誼和真切的關心;《五個撲水的少年》中主人公是幾名天賦平平的高中生,以“張偉”擔任花樣游泳隊長這一情節作為主線,呈現了一個毫無特點可言的人,是如何通過組織隊友訓練和比賽,一步一步成長為肩負起責任的“真正的隊長”。近兩年賀歲檔上映的《四海》和《熱辣滾燙》,主人公皆是平凡青年,電影并沒有講述他們在世俗意義里的成功,而是不斷地渲染運動對于個人生活的重大改變。
對于電影中敘事主體的認知及其身份屬性,是需要深刻融入其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的。近年來,體育題材電影中運動者身份屬性的不斷解構和重構,與體育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發生變化密不可分。如今的部分體育電影將運動的快樂和精彩給予更廣泛的青少年群體,觀眾對于運動體驗和體育精神的感知也更加直接和具體。這種建構基于體育對于教育功能的實踐,并在社會文化中積極的客觀反映,是體育觀和教育觀在社會生活中的進步。這種重構表面上是給運動者身份進行落地的降格,但卻更多地為電影創作者對運動者形象的塑造和運動精神的表達提供更廣闊的空間。
二、中國體育電影空間敘事的策略及其藝術效果
電影學者安德烈·戈德羅指出,影片能指的圖像特點甚至可以賦予空間某種優先于時間的形式。[2]電影空間的呈現,可以將觀眾迅速引入人物所處的情境和情緒之內,以實現電影敘事的基本前提。正是這種空間的在場和無蔽,電影敘事才得以從文學敘事中解放出來,在藝術性上呈現其獨立的品格和特征。[3]同時,電影也是一種在時間線上完成空間編碼和解碼的藝術,不僅僅是因為圖像、聲音完成對于空間的編碼,還因為觀看者也是基于觀景過程中對于屏幕信息細節的感知而實現對于空間的解碼[4]。如此一來,電影的敘事空間構建的本身也被賦予了表達的屬性。
在表現時代生活的藝術創作中,如何解構現代城市空間和社會生活的復雜性,一直是創作者面臨的復雜問題。列斐伏爾提出的三元空間辯證法為藝術學里的空間敘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該理論將空間的概念劃分為物理上的感知空間、人為設計的空間表象以及構成社會想象的表征性空間。[5]具體到電影敘事的層面里:感知空間是在資源層面對基礎環境的選擇、是廣義的大地景觀,在電影里可以引申為基本視點空間的選取;空間表象是對狹義景觀的理解,包含了人工感受的規劃設計,電影創作者可以通過鏡頭捕捉環境內部的人為痕跡,塑造背景之內的人文場域;空間表征性是人的社會行為所產生的文化景觀和藝術表現,是電影努力構建的思想境界和精神層面的藝術傳達。
(一)感知空間的動態轉變:拓寬人物的成長環境
綜合國內幾十年來上映的部分體育電影,可以將感知空間即敘事空間的視點選取總結為三種類型。這三種類型隨時代變幻日趨復雜,自然人物的成長經歷也愈發豐富。
第一種是背景交代式,代表作品是20世紀國內的一些類型化體育電影,主人公活動的主要場所通常局限在訓練館或賽場,間或穿插家庭空間。此視點的選取與當時國內職業運動員的成長經歷相對應,其社會生活相對簡單,且有背井離鄉式的狀態,友情也常常局限于隊友之間,他們的成長主要指向其運動成就。電影《女籃五號》里拋開回憶部分以外的敘事空間幾乎都封閉在訓練局大院,宿舍外就是訓練場,所有的沖突由此處展開,也在此化解。《沙鷗》也將故事局限于訓練場和家庭之間,空間背景絕大多數只起到交代場所的作用,并沒有太多復雜的呈現與切換。此類背景的選取是基于當時的社會語境下,運動員在訓練場里艱苦訓練,在比賽場上實現人生價值并為國爭光,即當時國人理解體育和體育人的基本內容,也是電影敘事的主線。
第二種類型可稱為職業成長式,主要作品包括21世紀以來講述職業運動員成長成就的體育電影。這類電影雖然繼承了賽場內外這種兩點式的敘事空間選取,但是將人物賽場以外的空間拓展了許多,生活空間明顯變得豐富而有色彩。電影《激戰》里主人公程輝發生在合租房里的故事,為人物的成長提供了動力,觀眾的情緒也從這里開始積累;電影《破風》里的酒吧、賓館等城市空間元素,則充當了運動員成長的負面空間,為電影的成長敘事設置起伏。這些拓展也是基于時代特征的改變,電影中的人物成長于物質更加豐富的城市環境,成長中面對的利益和情感等挑戰也更加復雜。為了切合體育電影敘事的邏輯,這些空間的拓展無一例外地指向人物更復雜的社會關系,或正面或負面,成為其成長的因素。
第三種類型可稱為社會融入式,這類電影主要講述當代青少年的運動及其相關經歷,電影的敘事空間不再簡單地劃分為賽場內外,而可以看成是將人物成長置于更廣闊的生活環境里,或鄉村某處,或城市一角。《雄獅少年》里無論是訓練和比賽,都基于鄉村或城市本身的風土背景,而不再是封閉的運動場地,少年阿娟蹣跚于城市的樓宇之間,在高樓的頂層執著地練習舞獅動作,呈現出理想與現實巨大反差。《了不起的老爸》中肖爾東父子奔跑于城市的喧囂里,于車水馬龍中追尋自己的馬拉松夢想。《四海》主人公吳仁耀的特技摩托車把故事從海邊帶到城市,歷經種種磨難又載他歸鄉。運動者和運動行為更像是一條線索,串起人物的社會化成長,這樣的敘事結構對電影創作者而言是更大的挑戰,但也會喚起觀眾更多的共鳴。電影中的運動者依托于某一項技能,和社會中的求學或求職青年一樣,面對學習、工作、生活等多方面的場景,去體驗一場復雜的社會角色扮演,并在其中完成自我價值的發掘,實現與紛繁世界的握手。
(二)空間表象的多維設置:角色沖突類型的豐富與生動
對于電影而言,空間感受是觀眾在特定視點選取下能夠感知到的人與人,人與物的具體關系,這里的感受是空間敘事下的人文場,為運動者的成長設置了可視化的沖突和矛盾。這些空間感受以表現運動場景下非主要角色的反應為主要手段(如場邊觀眾、非主要人物的對手或隊友),也會涉及生活場景下具體的景致以及內部物件的擺放等。這些空間表象的設置往往是主人公內在世界與現實世界的交互,是主人公身處第一空間里(前文中描述的感知空間)所表現出的對境地的探尋,抑或是第一空間對角色成長所設置的阻礙或內心投射。隨著電影拍攝和后期制作技術的不斷提高,以及現實社會生活的復雜多元,電影中的環境呈現更加復雜具體,運動場的鏡頭及主人公以外的如球迷、教練、對手的描寫鏡頭越發深刻。這些具體的人物和他們的角色設置是運動者成長的第二空間,人物在其中的交流和沖突中成長,而表現沖突的圍欄,就是身邊其他角色有意或無意制造的困境。
電影《雄獅少年》里阿娟的所有成長空間都有清晰的具象化呈現,鄉鎮里圍繞著阿娟的窮困家境和忙碌的市井,每個角落都透露出麻木而無奈的基調;影片后半程阿娟在繁華都市里打拼的暗影下,其艱難窮苦的生活環境,為觀眾營造近乎絕望的電影基調;最后阿娟重新披上獅頭走向賽場時,影片的色彩開始走向明亮,同樣是城市的一角,但萬事萬物都有了喧嘩的光彩。《熱辣滾燙》里的杜樂瑩從一塌糊涂的人際關系中出場,為人物后半程的蛻變鋪墊情緒,圍繞其身邊依次出場的各色配角都自帶鮮明的個性和話題,影片在高潮部分將這些沖突關系和因果疊加呈現,將人物蛻變的空間一一定格。而這些沖突都是普通青年在日常生活中或關注或排斥的,可以直接帶入觀眾的喜怒情感,電影創作的情境便更加真實可信。
近些年,在體教融合的時代背景下,體育運動在校園生活中被不斷地強調,學生成了體育運動的新主人公。對于廣大青少年而言,訓練、比賽方面的挑戰并不是唯一的,他們會面臨學習、生活等多方面的考驗。國內體育電影中鮮少有對青少年學習場景的描寫,這是長期形成的一種認為二者間毫不相關的觀念。當代中國電影能夠為青少年及廣大觀眾呈現教室和運動場兩個空間的良性切換,對于時代而言是迫切的需求,借以表達體育是教育的部分或環節,青少年在運動場上面臨的競爭,和在教室里面臨的問題,都是他們在成長中必須跨越的難關。
《了不起的老爸》中的肖爾東是一名高中生,因為雙目失明的身體原因,他不能參加夢寐以求的馬拉松比賽。電影的敘事空間沒有簡單地執著于訓練場上與身體的糾結,而是擴展到日常生活場景的描寫,比如為了適應可能會“突如其來”的失明而練習鋼琴的場景;失明后父親陪伴他的點點滴滴。馬拉松運動是電影的線索,串起了因運動而改變的生活,使觀眾能夠理解重在參與的基礎不是獎牌,而是家人的溫情。《五個撲水的少年》翻拍自日本同名電影,有些故事前提和假設缺乏國內校園現實支撐,但它所屬題材的教育意義是電影市場和社會環境所稀缺的。電影主人公是五個活力四射的高中男生,他們面臨繁重的學業,卻和女子運動花樣游泳結緣,演繹了一場不可思議的運動童話。童話開端并不美好,他們缺乏專業指導和日常訓練場地,遭到家長和老師的雙重反對、同學和親友的各方非議,而這一切爭議都圍繞著所屬年齡階段的學習壓力鋪開,并從家庭和校園的兩個空間里逼仄而來。
(三)表征空間的精神成長:運動者形象塑造及意義生成
電影中運動場空間的構建,從簡單的場景出發,通過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的融合,最終目的是完成運動者第三空間也就是精神空間的呈現。從這一視角對電影空間的解構,會發現電影被賦予了更多內涵,使其具有精神空間的延展,實現人物精神世界的成長與升華。如同蘇珊·桑格塔所說,每個時代都必須創造自己獨特的靈性。所謂“靈性”,就是力圖解決人類生存中痛苦的結構矛盾,力圖完善人之思想,旨在超越其行為舉止的策略、術語和思想。[6]電影角色精神空間的呈現,與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密不可分。在艱苦奮斗的年代里,人們需要的是全民偶像,為國人樹旗;而在全民小康的時代里,關心個體和青少年的成長,是持續發展的社會基礎。在這樣的時代,運動者既可以是為國爭光的運動健兒,也可以是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既可以是勵志偶像的身份進階,也可以是平民英雄的精神成長。
傳統運動員題材電影的表征空間被國家發展、人民奮進所充當,簡單直接又聲勢浩大。《奪冠》中幾次呈現了兩位教練在場外會面的場景,城市空間的背景起到了強烈的烘托作用,似乎不停地在傳達一種信念,時代變了,中國變了,中國人變強大了。在《中國乒乓之絕地反擊》中,留洋教練戴敏佳從古老且繁華的歐洲大街,穿越回艱苦樸素的訓練大院,其堅毅的目光傳達了一代國人奮起反擊的決心。類似的表達在各類電影中皆有體現,運動者往往身處不同時代的訓練背景下,感受著國家和民族的變化,從始至終都以競技的精神呈現人民身處世界的文化自信。這些傳記類體育電影,通過高燃的運動場面,努力建構一種奮斗時代的心理意象,促使觀眾感受到國家的活力與希望,還有中國不斷提高的國際地位。
在呈現非專業運動者的電影中,主人公往往與運動員的身份存在較大差異,對于單一競技目標的要求相對不高,其中更多的是一種精神追求的表象,是生活、理想等多種目標的綜合化。在這類電影中體育的教育功能會更多地突顯,通過艱苦的訓練,緊密的合作,激烈的比賽傳達體育精神和體育文化。電影中的運動場不再單單是承載敘事的物質空間,同時也是個性與社會性角力融合的精神空間。這里往往呈現了場內場外兩個時空的內容,并在此完成融合。場外的社會空間是延展的,是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個體成長的點點滴滴;場內空間看似是局限的,但又是各種困境的高度濃縮,以場內的各項元素表征少年成長的復雜問題。
《雄獅少年》中的主人公“阿娟”身材矮小,沒有半點舞獅技巧,常常感到自卑。他通過舞獅的訓練與比賽強化自己,從村里人眼中的“病貓”,變成為一頭“雄獅”,讓觀眾感受到一個輟學少年平凡而又偉大的堅持與努力。“阿娟”在別人的眼里也許是一個懦弱無能的人,但有了師傅和好友的陪伴,有了自己不斷的提升,也可以擁有引以為傲的生活。競技場是現代社會的表征,處處充滿了對抗與得失,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事業和生活欣欣向榮,但成功者只是少數,大多數人或失敗或默默無聞。觀眾會通過電影中的競技場,體驗精神成長,從而對照審視自己的問題。《了不起的老爸》中,主人公肖爾東說“我沒有十年的時間,可我想跑贏我自己”。這就是運動者平常又單純的目的,也許僅僅是與自己斗爭,明知自己有天可能會雙目失明,仍然直面困難,繼續訓練。教練員在場邊說“馬拉松的終點是安全回家”,這是電影表達的運動意義,在這場競技與生活的精神融合里,馬拉松成為漫長生活的表征,教會運動者努力的競爭,并且從容地接納結果。這樣的銀幕形象跳脫出原有的以愛國、奪標為主的神話氛圍,使其忠誠于時代,更加貼近當下生活,更易引起觀眾的情感共鳴。
結語
隨著我國科教文衛事業的蓬勃發展,體育已逐漸從職業競技的專門領域擴展至校園教育與社會生活的廣闊天地。時代演進不僅深化體育作為身體鍛煉與國力象征的傳統意義,更在體育與教育的交融中催生出其豐富的教育潛能。在這一背景下,中國體育電影的主題演變顯得尤為引人注目,它們正逐步超越單一的競賽勝負,而更多地聚焦于全民參與、個體成長的深度體驗。這種轉變不僅折射出社會文化的漸進成熟,也為觀眾提供了一個窺探時代精神的獨特視角。
對體育電影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對運動者形象的細致解構,實質上是對當代中國教育、體育以及青少年成長議題的一次深刻反思。電影中的運動者形象,作為深受觀眾喜愛的藝術符號,其在成長敘事框架內所承載的教育意涵為青少年提供了一種模擬體驗社會生活的機會。他們通過角色代入,演繹進取與挫折、合作與競爭、付出與收獲的復雜情感與人生經驗。電影作為一種強有力的文化媒介,不僅放大了這些角色的藝術魅力,更在青少年心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激勵作用的偶像形象。因此,對運動者形象的精心塑造及其教育內涵的深入挖掘,無疑應成為未來體育電影研究與實踐的重要方向。
參考文獻:
[1]李杉.英雄敘事與身體的審美:體育精神在類型電影中的表達與闡釋[ J ].當代文壇,2013(04):115-117.
[2][加拿大]安德烈·戈德羅,[法]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電影敘事學[M].劉云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0.
[3]焦勇勤.試論電影的空間敘事[ J ].當代電影,2009(01):113-115.
[4]高子棋.中國公路電影(2001-2018)的空間敘事藝術[ J ].文藝爭鳴,2019(08):196-199.
[5][法]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M].劉懷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3.
[6][美]蘇珊·桑格塔.激進意志的樣式[M].何寧,周麗華,王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5.
——評《休閑體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