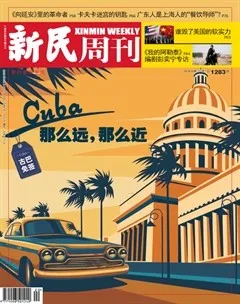曾經的波希米亞人
上海永嘉路上有南國藝術學院舊址,是一棟新式石庫門建筑,建于1927年。田漢1928年在此建立南國藝術學院并居住在371號。田漢當年是個“波希米亞人”,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到上海,帶著田漢出入酒館和歡場,田漢襪子上有破洞,谷崎潤一郎看著田漢頗為拘謹的樣子,稱他為“愛郁病患者”,總問他,“你的憂郁癥又犯了”。田漢寫過一篇文章《我的上海生活》,發表在1926年《上海生活》創刊號上,他引用頹廢派詩人魏爾倫的詩,“去吧,一切虛浮的歡樂啊/你和度你的放蕩生活之夜一般短促/人生沒有一樣甜美的東西我們用明眼看他的時候/有之則為憂郁/啊再甜美沒有的憂郁”。
有一本書叫《戲劇、革命與都市漩渦》,這是葛飛先生的博士論文,副標題是“20世紀30年代左翼劇運、劇人在上海”。葛飛在書中說,當年在上海,左翼文化是風潮,大量文學青年要描寫無產階級,電影要關注勞苦群眾,“電影皇帝”金焰深受觀眾喜愛,他的銀幕形象有不少是工人。左翼小說也許成就不高,但左翼電影《神女》《烏鴉與麻雀》都成了經典。
葛老師在書中分析以田漢為代表的“波希米亞人”的生活狀態。葛飛講先鋒黨對他們的吸引力,“先鋒黨的一個重要職能就是讓大家團結起來,使新階級的激進分子能夠承受同當權勢力對抗所帶來的危險……”
陳白塵是當年“滬漂文藝青年”的代表,只要能以筆墨謀生,窮文藝家就會在城市里聚居,他們具有反抗資本主義生產倫理的意識,但要靠文化市場生存。陳白塵1926年初入上海,為了掙稿費,一年寫五個長篇。他在上海文科專科學校上過學,后來進入田漢主持的南國藝術學院,那是眾多波希米亞青年的據點,他做過賬房先生,憑借南國藝術學院的學歷在安徽和江蘇做鄉村教師。九一八事變后,他因“抗日言論”被捕入獄。他在監獄中不再為生計發愁,專心寫作。1935年3月,陳白塵從“蘇州反省院”出獄,再次來到上海,與朋友合租了一個亭子間,開始寫歷史劇。從初入上海,到獲得一個穩定的住所及一個穩固的文學地位,陳白塵用了九年的時間。

這兩本書雖是學術著作,但對我了解上海文壇舊事和名利場有很大幫助。
葛飛還有一本書叫《左右雅俗之間的三十年代文藝》,他講左聯作家鄭伯奇為了謀生加入《良友》畫報,雖心向勞苦大眾和社會主義,但每天編輯的內容是美女和好萊塢。葛飛發明了一個概念叫“革命超我”,左翼青年應該去工廠做工人搞工運,應該去前線去北方,這是“革命超我”對留在上海的文藝青年提出的要求,不能應對這個“革命超我”就難以自洽。葛飛講左翼戲劇搞起來之后,各劇團都缺劇本,演員白薇去見魯迅先生,請魯迅寫劇本,魯迅很生氣,問了一句:“你們的人呢?”葛飛分析30年代上海文壇人與人的關系——作家群、師門、宗派是邊界較為模糊的關系網絡,公共空間上演“表彰—致謝”儀式是構筑作家群、師門等場域關系最重要的儀式,前輩、文壇宗主通過作序以及其他形式的評論,通過編輯書刊、選文等方式提攜后進,汲引同道,同時也在鼓吹某種文學上的主義,擁有資本較少的作家附和、模仿、致謝,由此來建構身份認同。二三流作家也要納入某個流派、某個社團,才能在當下的文壇/后世的文學史中占有地位。
葛飛現為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他研究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文藝,他這兩本書雖是學術著作,但對我了解上海文壇舊事和名利場有很大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