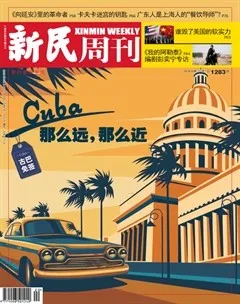遠古詩歌的現代共鳴
上世紀80年代,流沙河宣布封筆不再寫詩,他說:“那時候我名聲很大,但我的腦子是清醒的。我的詩都是骨頭,沒有肉。尤其是讀過余光中的詩后,我說算了算了,不寫了,我怎么也寫不出他們那樣的好詩來。”
雖然不再寫詩,流沙河并未離開詩歌。他選擇以擺龍門陣的方式,來講《詩經》《莊子》包括古文字。從2009年起,流沙河在成都市圖書館開始固定講座,多年從未間斷,成為成都人心中一道雋永的風景。
在回憶錄《鋸齒嚙痕錄》中,他回憶起自己1962年在省文聯圖書資料室的生活,“飯吃飽了,力比多過剩,想做學問,好像發了瘋,有鬼在祟我,拼命去攻許慎《說文解字》。這一部輝煌的文字科學著作,每一頁內都有一個奇妙的世界,任我遨游其中,沾沾自喜自己的后半生找到了一個寄托”。
得益于那段時間如癡如醉的學習,流沙河奠立了深厚的古文字、古文學基礎。深厚的學養,加上來自生活中的智慧,常讓他對古代文字與詩歌有新穎而獨到的看法。
在《詩經·國風·召南·摽有梅》這章,通常標注“摽”為biào,而流沙河則認為應讀pāo:
首先,詩題中這個“摽”字,很多專家都說是“落”的意思,這恐怕不對。我的老師教我讀的是piǎo,后來經過考證,我發覺他讀錯了,這個字應該讀pāo,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拋繡球”的“拋”。只是“拋”字出現以后,就把它頂替了。
這是古代的一種風俗,是女子向自己心儀的男子示愛的一種方式,相當于后來的拋繡球。夏天來了,水果成熟,年輕女子要上樹去摘,如果這個時候她看到了自己喜歡的男子,就會把摘下的水果拋過去打他。這樣的事,在南北朝時期還有一個著名的傳說,說是西晉的詩人潘岳長得很漂亮,每次在洛陽城坐著小車出去,遍街的女子都會向他丟水果,等他回到家水果已經載了滿滿一車,夠吃一個月!因為潘岳字安仁,我們后來說到美男子會說“貌若潘安”,就是出自這個故事。
《野性的歌謠:流沙河講詩經》從《詩經》305篇中擇取81篇典型篇目,從詩歌的本質出發,對《詩經》進行了解讀。流沙河先生在書中的講解非常注重當時的社會場景,注重詩歌的感情,他對于詩歌的理解,一向是契合真實情境,而非憑借臆想或一家之言。
流沙河的夫人吳茂華曾提及一事。
結婚二十余年后,吳茂華腰痛,流沙河給她輕輕捶打。窗外春寒,屋內和暖,他突然有些傷感:“人都老了,還守在一起,我倆就是一捆柴呵。”
他隨后吟誦了《詩經·揚之水》,這是吟詠夫妻之情的:“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流沙河對于《詩經》的應用,是融會于生活,扎根于現實的。
流沙河先生對于《詩經》的理解是基于人的本性去理解,而不拘束于字眼、環境,不受限于時間、文化。文學需要用經歷去體驗,用生活去感悟,用情感去共鳴,不是簡單地說文解字與訓詁。遠古的詩詞呼喚現在的共鳴并非難事,野性的歌謠唱誦的依然是你我千萬人當下的每一個瞬間,美麗的文字必有悠揚的注解,流沙河的文字即是最好的伴奏。

書訊
《雙面人生》
這是一部雙螺旋結構的小說。生活在當代的女孩喬治正和弟弟一起面對母親去世的現實,她回憶起和母親的最后一次旅行是去意大利費拉拉看壁畫;15世紀的意大利畫家弗朗西斯科·德爾·科薩為了進入繪畫領域,從小扮作男孩生活,她正被一個十幾歲女孩的奇怪幻象所困擾。兩人的故事如同藤蔓一般復雜地纏繞、交錯,似乎一個人的記憶在另一個人的故事中延續了完整的生命。
死亡會是終結嗎?在不同的時空中,愛與記憶透過藝術得以永存。在阿莉·史密斯筆下,時間被永恒之物消解,一切虛構之事都變得如此真實,每個人在小說中都獲得了第二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