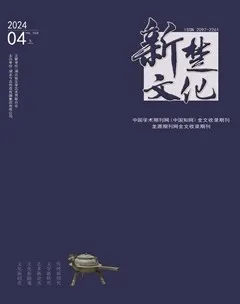文化生態視域下長江流域湖北段歷史文化資源的數字化保護與展示


【摘要】長江流域被視為我國綜合競爭力最強、戰略意義最大的經濟區域,湖北是長江干流流經最長省份,分布在這片地區的歷史文化資源亦是國家和民族的寶貴物質和精神財富。在我國推進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指導意見和數字中國建設布局規劃背景下,文章從文化生態視角入手,研究長江流域湖北段歷史文化發展的資源、環境特征,分析其數字化保護路徑及展示手段,在虛擬展示環境中探索新興的資源利用方式,為歷史文化資源的創新型保護方式及可持續性傳承發展提供思路。
【關鍵詞】文化生態;歷史文化資源;長江流域湖北段;數字化保護;數字化展示
【中圖分類號】G127;TB472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4)10-0065-04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4.10.020
【基金項目】湖北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湖北美術學院現代公共視覺藝術設計研究中心項目“湖北歷史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展示、傳播與利用”(項目編號:JD-2022-06)。
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突破,文化資源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構成要素正逐步實現與數字化方式的融合。當前關于歷史文化資源數字化研究,多是計算機科學研究機構順應文化大發展的時代潮流,將其科研領域拓展到這一范疇,在歷史文化資源的數字化保護與展示研究中依然存在數據要素割裂、數字化水平有待提升的問題。最早由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斯圖爾德提出文化生態理論是指文化與環境——包括技術、資源和勞動——之間存在一種富有創造力的關系[1]。人類的文化、行為,與其所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等各種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制約[2]。“資源”是文化生態的基礎,從文化生態學的“資源”觀可以認識到文化與環境形成的體系,在不斷的調整中以實現整體的均衡。在文化、生態、社會的動態發展過程中,把握整體與要素的辯證關系,這是研究歷史文化資源數字化保護與展示中對文化生態學的主要應用。
一、文化生態視域下長江流域湖北段歷史文化資源的特征和類型
長江流域湖北段歷史文化資源具體指長江流經湖北的地段內,以文化形態存在的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和經濟價值的社會資源,對其資源特征和類型的分析是進行數字化保護與展示應用的前提和基礎。
(一)文化生態視域下長江流域湖北段歷史文化資源的特征
地域性特征。長江流域文化資源展現了根植于環境的文化特征,長江流域的自然環境、地理特征成就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多樣性,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季風氣候、沖積平原和丘陵山地為漢族先民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進程,荊楚文化在此地滋生,民族分布上以漢族為主,土家族、苗族、侗族、彝族等少數民族在局部地區也有較為集中的分布。在山區,少數民族聚居地尤其集中,出現了如土家族人民的藝術之花——擺手舞和西蘭卡普。
開放性特征。首先長江流域文化生態系統具備開放性,主要反映對外部文化的接納與吸收和對內部文化的傳承與創新。長江流域的文化有悠久的開放傳統,其每一個發展階段幾乎都吸納并影響別的區域文化[3]。長江流域的地理單元復雜,從人地互構關系角度看,在這種文化生態中養育出來的史前文化就呈現出“多樣競輝”的格局。雖然歷史上陸路交通發展相對閉塞,基于其水路航運和特殊地理位置帶來的天然優勢,例如中游的楚文化圈得以與上游巴蜀文化和下游吳越文化等主流文化圈頻繁的交流與互動,形成特色。湖北長江流域的文化是流動性的、兼容性強的開放性文化。
變異性特征。長江流域的文化生態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受當時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條件的影響,會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和內涵。比如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土家族擺手舞,起源于土家族祭祀舞蹈,表現土家族人生產、生活和征戰場面。隨歷史發展、社會經濟及其生產方式的變化,其舞蹈動作和反映內容也有更新[4],而現代土家族擺手舞更以一種全民健身的形式走入大眾視野。長江流域湖北段歷史文化資源的變異性在時代發展、地域交流、民族融合、傳承過程中都有體現,把握其變異性也為其保護和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思考。
(二)長江流域湖北段歷史文化資源的類型
本文采用了李樹榕等學者對文化資源提出的分類方法,以文化產業的發展需求為邏輯起點,以“獲取文化資源的途徑”為分類標準,將文化資源分為物質實證性文化資源、行為傳遞性文化資源、文字與影像記載性文化資源[5],其劃分方式旨在減少內容的重疊與交叉問題,且在資源的保護及展示手段上更具針對性。
物質實證性文化資源包含了歷史建筑、歷史文物等以物質為核心價值載體的資源內容。長江流域是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重要發源地,它不僅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還有著眾多的美麗景色和自然資源,按長江流域湖北段歷史文化發源可分為楚文化、三國文化、知音文化等。傳承至今的《離騷圖》和體現楚國漆藝精髓的虎座鳥架鼓都充滿著楚文化的烙印;漢末三國時期,產生了大量的文化遺產,赤壁古戰場、曹操廬江公主墓等重要歷史遺跡成為研究三國時代歷史的重要史料;隋朝時期產生的知音文化,鐘子期墓為整個知音傳說歷史文化傳承的唯一物質載體。位于武漢的琴臺大劇院便以“高山放歌”概念為設計原型,展現了長江流域文化傳統與現代技術的巧妙融合。
行為傳遞性文化資源,其多誕生于長江流域地區人民的生產生活之中,通過長江流域地區的語言和師承行為進行傳承。這些資源形式承載著多元的價值功能,既可以用以祭祀活動、豐富群眾生活,還能夠承擔一部分文化傳承與教育功能。在長江流域湖北段,盛傳著各種傳說、趣聞逸事等,這些元素都可以在當地的曲藝中找到蹤跡。比如恩施土家擺手舞、黃岡黃梅戲等,這些曲藝形式采用的都是地方語言、音樂和舞蹈,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并反映當地人民的藝術表現能力和創作能力。
文字與影像記載性文化資源包含了語言文字、歷史文獻、文學經典、影像資料等載體。以長江流域湖北地區人物與文學作品為代表,例如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愛國詩人屈原所作的《離騷》和宋代文學家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被譽為是文化遺產中的瑰寶,反映出長江流域湖北地區的卓越文化水平和悠久的文化歷程。
二、文化生態視域下長江流域湖北段歷史文化資源數字化保護路徑
(一)基于文化安全的整體保護
“人——社會——文化生態三位一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1]從文化生態系統的整體性來看,就需要在對長江流域湖北段歷史文化資源數字化保護時,將有相同或相近社會文化背景的歷史文化資源進行整合,形成互相支撐、互相依托的共生關系。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面臨互聯網浪潮下面對全球化挑戰,對歷史文化資源進行數字化保護,構筑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對保障國家文化安全和傳統的維護至關重要。構建文化生態的安全屏障,需在內容表達、價值導向、數據安全上把關,應當設計科學的保護機制,引導公眾參與,并在社會監督下成立專門機構或委員會,負責歷史文化資源的普查、評估、保護、利用和監管等工作,建立完善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加強安全保護措施、引入市場機制進行保護等。
(二)基于文化發展進程的分層保護
構成文化資源本體的各個要素存活形態可能并不一致且時刻變化,從動態與過程來進行歷時性分層保護顯得尤為重要[6]。根據長江流域湖北段文化資源的歷史演變采用分層保護形式,原生態文化、次生態文化和新生態文化是文化資源歷史發展的不同形態,它們分別代表了文化遺產的原初狀態、演變狀態和創新狀態。
原生態文化,是接近初始的、質樸的、原始藝術源頭的文化形式。例如以物質實證性資源為主的湖北長江流域的古代城市遺址、陵墓遺址、軍事遺址及其遺址中出土的重要文物,其自身形態不會隨著社會發展和形態而產生變化,同時將這些有初始環境的文物與遺址相分離,在博物館束之高閣,也造成了整體文化生態的分離。因此,此類資源的數字化保護適合通過數字化采集、記錄和保存,建立數字資源庫或借助數字博物館在虛擬環境以數字化復原再現一個完整意義的空間。
次生態文化是指在原生態文化的基礎上,經過一定程度的演變和變化而形成的文化內容,這種演變和變化可能是由于社會環境的變化、文化交流的影響、傳承人的創新等因素引起的。次生態文化既保留了原生態文化的某些特征,又融入了新的元素和內涵,符合當下人們的文化交流與文化消費需求。類似于民間技藝、民俗節慶、民間戲曲等行為傳遞性文化資源在可以在特定環境下通過傳承人和資源保護開發主體進行傳遞,適合采用引導性保護,由政府、專家及企業組織采取積極有效措施,引導民眾進行文化認同,以傳承人為核心,借助多媒體和數字影像搭建交流、培訓平臺,以實現其保護目的。
新生態文化是在現代社會中,通過創新和發展而形成的具有新時代特征的文化內容,其保留了原生態文化的底蘊和精髓,又體現了現代社會的審美觀念和價值取向。此類文化資源可以通過虛擬再現技術和創立數字IP進行開發性保護,實現保護與利用的互動,進行開發性保護的同時,也需關注歷史資源數字化保護與文化產業的發展,讓歷史文化資源在文博產業、影視傳媒產業、游戲動漫和廣告行業中創造新生。例如武漢知音文化,起源伯牙子期傳說,“知音”的本意在故事世代流傳中不斷延伸,知音文化由一種音樂文化擴展出情感文化。2021年王者榮耀項目推出“知音”主題公益皮膚,聯合國家級非遺古琴傳承人林晨打造《流水》一曲作為主題背景音樂,誕生出新的數字產品[7]。
(三)基于文化價值的教育與推廣
價值關系是文化生態的核心,價值體系是文化體系的本質規定,價值的構成就是文化生態的構成[2]。深入挖掘歷史文化資源的文化價值,包括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和社會價值等,為教育和推廣提供有力支撐,擴展其傳播途徑,也是歷史文化資源數字化保護得更為立體化的舉措。當前我國的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開發與利用主要為政府引導,以國家文化公共服務體系為依托,依賴于各地文化基礎設施的建設,民眾的參與度還需提升。在數字技術下,歷史文化資源亦成為一種共享資源,通過數字化手段,可以將歷史文化知識融入各種教育產品和智慧教學平臺中,如在線課程、教育游戲、互動教材等,一方面是重視基礎教育的培養,另一方面是為專業人才儲備做保障,讓學生的成長在多元文化內容中獲得傳統文化價值的浸潤,促進民眾的文化和情感認同。
三、長江流域湖北段歷史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展示及設計應用
數字化保護為長江流域文化生態和文明的維護和促進提供了支持,也有助于促進長江流域文化認同的建立。而數字化展示,則是通過技術手段實現歷史文化資源的高質量傳播,以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當前湖北地區針對歷史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展示,以湖北省博物館和宜昌博物館為代表,多是利用虛擬現實(VR)技術,實現實體博物館展覽的線上游覽。2022年由宜昌博物館牽頭“爭艷——‘宜荊荊恩城市群博物館聯盟鎮館之寶聯展”,匯集長江中游早期文明的核心地帶“宜荊荊恩”地區博物館館藏,通過對文物實物攝影和搭建虛擬展廳進行展示,也體現出長江流域“宜荊荊恩”地域文化脈絡的聯結。
基于以上從文化生態視角對于長江流域湖北段歷史文化資源特征和保護措施進行分析,本研究團隊對長江流域湖北段的物質實證性文化資源、行為傳遞性文化資源和文字記載型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展示進行了初步實踐,希望以此為相關數字化展示作品提供設計思路。
(一)物質實證性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展示
數字化技術可以將物質實證性文化資源進行數字化記錄和建模,將文化遺產資源轉換為數字信息儲存和處理,以數字建模、虛擬還原形成虛擬博物館和數字藏品等數字內容進行展示。“畫說湖北 數繪長江”虛擬博物館設計作品(圖1),利用增強現實(AR)技術以及虛擬場景建模,配合文字、圖像、影音資料,通過挖掘長江流域湖北段地脈與文脈聯系描繪長江流域湖北段文化生態;將自然環境、建筑、繪畫等多種要素進行篩選與整合,選取長江流域恩施、宜昌、咸寧、荊州、武漢、黃岡等城市,展示土家族文化、屈原文化、三國文化、荊楚文化和知音文化,反映長江流域湖北段歷史文化的時代特征與藝術價值;形成“山舞周瑤”“遺世謇謇”“折戟未銷”“荊風楚韻”“古琴吟止”“梅香寒來”等主題板塊,完成虛擬博物館的展陳框架構建。在展覽導覽上可選擇個性化展線進行參觀,完成互動性的展覽體驗和文化交流。
(二)行為傳遞性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展示
行為傳遞性文化資源相對物質實性型文化資源更為脆弱,因為其難以以一種獨立于人類活動和行為的方式保存或傳遞。數字技術可以提供一系列工具,幫助這類文化資源從樣本、自然語言處理到文獻考證、數字可視化和在線展覽等多個環節實現數字化和可視化,針對行為傳遞性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展示技術常見有動作捕捉技術、XR技術、交互展示及多媒體展示,將行為、動作和聲音等轉化為數字信號,再通過各種媒體平臺進行展示。
由于行為傳遞性文化資源還包含了個人及群體故事、生活體驗等,并通過人的行為傳遞信息,是一種活態的資源。因此,除了將信息要素進行數據化和可視化處理,在行為傳遞性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展示上還應注重其活態特征的體現,用數字技術重構敘事素材,呈現多角度理解,進行多樣化的數字敘事。“楚韻流風”武漢戲曲碼頭數字體驗設計作品的展覽框架圍繞湖北地方戲曲歷史發展脈絡、階段性轉變、劇種的文化概念、作品演繹、地域跨界等內容及武漢戲碼頭這一文化現象進行敘事設計,敘事主線為武漢戲曲碼頭中戲曲的誕生到戲曲創新融合再到戲曲的發展現況,通過漢調進京、京劇“打碼頭”、楚劇進京三個故事來串聯敘事線索,不同于常見以某一個劇種的時間順序或劇目展現,其敘事結構采用的片段綴合式敘事結構與多線組合式敘事結構相結合,避免了歷史文化資源通過數字化展示時信息受制于數字媒體的網絡架構而出現邏輯性較差的問題。多媒體技術在敘事素材的加持下,這種多樣的表達方在虛擬展示環境中更能幫助觀眾理解其要素間的聯系。
(三)文字與影像記載性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展示
對于文字與影像記載性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展示首先可以通過數字化技術收集、保存和保護文化資源的原始材料,并進行掃描或拍攝將它們轉換成數字格式,以便于存儲。其次將數字化后的文字與影像資源進行整理和分類,建立數據庫,通過關鍵詞檢索、全文檢索等功能,以實現數據的檢索與展示。虛擬現實技術與互動技術同樣會為文字與影像記載性文化資源的展示帶來更多的參與感和趣味性。此外由于基于文字的閱讀體驗在體驗深度上不如基于圖文影像的視覺和行為參與的互動體驗深刻,因此對于文字與影像記載性文化資源的數據可視化發掘也尤為重要。在對其進行開發時,尊重原作品的版權,并確保數字化展示的準確性和真實性,避免對原作品進行歪曲或誤讀。數字IP作品“香草流芳”(圖2),從楚辭《離騷》中汲取創意靈感,借用《離騷》中“香草美人”的象征系統,將詩句意象、植物形態、楚文化紋飾與現代審美元素結合,通過二維及三維設計創作,以系列潮流IP形象并延展其他數字化成果,激發年輕一代對傳統文化的喜愛。
四、結語
文化生態學展現出明顯的實踐性,主要表現在對文化建設的指導和對文化發展的促進上,運用其生態觀研究文化的存在和發展的資源、環境、狀態及規律。歷史文化資源的數字化保護與展示,是文化生態學時代性實踐,文化資源與數字化保護及展示方式相融合在內涵發掘、資源整合及對外傳播上提供更大的展示平臺。數字化極大地豐富了歷史文化資源的外延,但仍需從文化資源的本體、社會環境和利用主體上去共同構建其文化生態,進行系統的保護和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羅伯特·墨菲.文化與社會人類學引論[M].王卓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2]劉志成.文化生態學:背景、構建與價值[J].求索,2016(03):17-21.
[3]鄧先瑞.試論長江文化生態的主要特征[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02(03):199-202.
[4]馬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旅游生產性場域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
[5]劉燕,李樹榕,王敬超.文化資源學[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21.
[6]譚雪霏.文化生態視域下的三峽宜昌庫區文化資源保護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9.
[7]周靖杰.恰如流水遇知音!當傳統文化傳承人相逢數字新載體[EB/OL].(2021-11-01)[2024-1-21].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211101/6652e4f7135e4630a10a1aadfeb3e3f5/c.html.
[8]戢斗勇.文化生態學論綱[J].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05):1-7.
[9]楊曉輝.長江干流湖北段歷史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20.
作者簡介:
成章恒(1991.9-),女,漢族,湖北宜昌人,湖北美術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文化傳播與展示設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