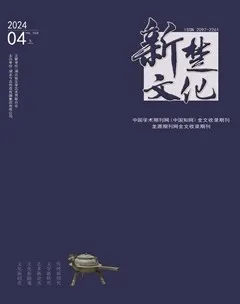社交網絡上自我呈現中的沖突與救贖
【摘要】“微博小號”是指用戶在“微博”社交軟件平臺中擁有兩個及兩個以上賬號,并且此賬號通常以“匿名”形式存在,它與“微博大號”的區別在于賬號社交關系的公開程度。隨著用戶社交范圍擴大,微博作為半社交平臺逐漸涌入用戶私人社交關系,面對不同的社交關系凝視,用戶在自我呈現中面臨著“選擇表演角色困難癥”——在平臺上考慮到不同粉絲對呈現內容的看法糾結是否發送某些日常生活內容,久而久之便演化成自我呈現的沖突。于是小號便成為此類用戶自我呈現沖突中的“救贖”。本文運用深度訪談法在對20名擁有微博小號并使用微博此平臺超過兩年的用戶進行訪談后發現用戶解決此沖突的方法為創建“小號”進行情感發泄。
【關鍵詞】微博小號;自我呈現;私人領域;擬劇理論
【中圖分類號】G206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4)10-0076-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4.10.023
一、引言
隨著科技不斷發展、智能手機的普及,人們使用社交網絡平臺進行日常社交活動也變得越來越普遍。微博作為中國使用普遍的社交平臺之一,也贏得了廣大用戶的喜愛。2021年6月微博的月活躍用戶達5.66億,日活躍用戶達2.46億。數量龐大的用戶賬號中存在一部分獨特個體即“微博小號”。微博“小號”與“大號”相區分,指“正常使用一個賬號的同時,在該社交網站另注冊一個賬號作其他用途”。微博小號為何出現的原因也被廣大學界所探究。綜合國內外文獻得出:目前國內對用戶使用微博小號的行為有“擬劇理論”進行解釋外,也發展了一種新解釋——“策展人”即:“用戶以不同展演舞臺下的觀眾屬性為區分,策劃不同展演行為,塑造不同的自我形象。用戶從表演者成為策展人,每個微博賬號空間不再單純只是用戶表演的舞臺,而更像是用戶不同主題的展覽廳。用戶通過策劃每個展廳的可見內容、可見范圍等進行自我呈現,極大地避免了‘秘密的泄露和自身形象的崩塌。”但本文作者認為“擬劇理論”與“策展人”解釋都不能更完整解釋微博小號出現的動因,本文通過與20名擁有微博小號并使用微博APP超過2年的用戶進行深度訪談,認為“客廳說”更符合使用微博小號的用戶心理。
“客廳說”是指用戶所擁有的賬號就像用戶的家,微博大號為家里的“客廳”,小號則因為用戶使用其功能的不同而不同,有的為“臥室”“書房”“工作室”等。用戶會定時“打掃”自己的家,即用戶對自己所發布的內容進行及時編輯,保證內容信息的可觀賞性,“打掃”這一行為通常出現在微博大號中,為保證“訪客”在進入客廳時所觀看的景象是賞心悅目的。而臥室為私人領域,通常“謝絕參觀”,即微博小號通常不具有用戶的私人社交網絡朋友圈,僅為用戶自身開放。書房開放程度不高,可匿名也可實名,主要為用戶行工作之便所使用,發布內容也僅為工作信息。微博小號的出現是為了解決用戶在印象管理中“真實自我”與“規范自我”沖突的方法,也可視為他們的一種救贖。
二、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質化研究中的深度訪談法,首先挑選了20名來自中國不同省份、不同職業、不同學歷、不同年齡的志愿者進行訪談。志愿者們大多為使用微博APP時間超過兩年且擁有兩個及以上微博賬號的用戶。本次訪談大多以線上語音,文字為主,在對志愿者們進行基本信息詢問之后便往志愿者們在使用微博大號時出現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進行訪談,隨后便對志愿者們在使用微博小號的動因以及感受機型訪談。訪談時長90分鐘,訪談結束之后進行及時的總結與歸納。
三、社交網絡自我呈現的沖突
(一)規范自我的呈現——基于社交朋友關系下的凝視
“微博現在熟人玩得多,而且微博推薦熟人這個功能能讓本來不知道我微博的同事或者普通朋友發現我的微博,所以有時候我在上面發一些吐槽工作的話很可能就被我領導看到,所以我干脆就只在大號上發一些歲月靜好的東西。”志愿者A如是說道。在絕大部分訪談中,所有的志愿者們都提及微博大號被熟人所關注所以有時候為了在他們面前表演一個美好的形象便會盡量美化自己所發表的內容。
戈夫曼“擬劇理論”中的“前臺”能準確闡述用戶在微博大號中的行為,這是一種理想化的表演,用戶在知情有“觀眾”觀看演出時會盡量在舞臺上表演“理想自我”,在微博大號上主要表現為發表正能量的內容。精心美化過的照片,有深度的思考以及精致的生活狀態等。這種“規范”正是基于受眾的凝視下所表演出來的理想狀態,所有用戶在知情自己的社交平臺內容被凝視下都會選擇呈現“規范自我”。
(二)選擇表演角色困難癥——真實自我與規范自我呈現的沖突
“選擇表演角色困難癥”是指當用戶所使用的社交平臺被不同層級的觀眾凝視,因面對不同層級觀眾時用戶所持有表演身份的不同,此角色會被某一圈層的用戶所喜愛,但另一圈層的觀眾不青睞,所以用戶會患上此癥。舉例:志愿者B的微博被自己的男友和親戚所關注,她想在微博中發表與自己男友的戀愛日常,但是考慮親戚看見會告誡自己不要早戀,因此便在發表與不發表中猶豫糾結。所以便創建了一個小號專門用于記錄自己與男友的戀愛日常。此情況在“策展人”解釋中也得到了原因解釋,即從心理層面而言,個體對監視行為表示厭惡,在使用微博時呈現出比較明顯的倦怠情緒。從行為層面來看,用戶無法有效阻止他人的監視行為,只能通過改變自己的行為來緩解被監視帶來的負面感受。這同時也被本文作者認為是在社交網絡平臺中真實自我與規范自我呈現的沖突。
四、社交網絡自我呈現的救贖
(一)真實自我的呈現——無壓力下的自我空間
微博小號的出現為用戶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無壓力的自我空間,讓他們能夠在一個更自由、更私密的環境中表達自己。如志愿者C所述,“微博小號是我的快樂家園,我可以在上面肆無忌憚地‘發瘋”,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小號的本質:一個沒有社交壓力、無需擔心公眾評價的私人領域。在這個領域里,用戶可以擺脫社會角色和期望的束縛,展現更加真實的自我。在微博小號中,用戶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情感、觀點和想法,而不必擔心被熟人或公眾評判。這種情況類似于艾爾文·戈夫曼在“擬劇理論”中描述的“后臺”區域,在這里,人們可以脫下社交場合的面具,無需再進行精心的自我呈現和控制。微博小號成了一個釋放壓力、表達不滿、自我治愈的地方。此外,微博小號的內容有時是大號內容的延伸或反應。例如,如果在大號上發布的內容引起了爭議或負面反饋,用戶可以利用小號來回應這些情況,這樣做既保護了他們的公眾形象,又滿足了他們回應批評的需求。這種互動顯示了小號不僅僅是一個隔離的私人空間,還是與大號相互關聯的,提供了一種復雜的、多層次的自我表達方式。在這個私密空間中,用戶可以探索和發展自己的身份,表達那些可能會在公眾賬號上引起爭議或不適的觀點。這種自由表達的能力是微博小號的重要特征,它允許用戶在社交媒體的壓力下保持心理平衡和情感健康。
(二)“臥室”與“書房”——私人領域的再創建
“臥室說”是本文作者在對以上10名志愿者進行深度訪談后所得到他們一致性認同的解釋。即作者在詢問:“這兩個觀點你更同意哪個?1.微博賬號就像一個房子,每個賬號有每個賬號的功能,客廳,書房,臥室,主人會清理房子,歡迎‘訪客,但是臥室只限于自己‘參觀。2.微博賬號就像一個舞臺,舞者會登上不同的舞臺,有觀眾的舞臺會戴著鐐銬表演,沒有觀眾的舞臺只限于自我欣賞。舞臺表現的節目因觀眾不同而不同。”百分之百的志愿者們都認同了第一個解釋。因此本文作者將詳細以上言論。在微博小號使用中,大號與小號的區別可以使用戈夫曼的“擬劇理論”描述,即大號為前臺,小號為后臺。但本文作者在研究中卻發現小號也有不同功能,也不僅僅是表現真實自我的后臺,有些用戶使用小號也是僅僅用于工作,并無其他用途。因此本文作者將小號規劃為三類——“臥室”“書房”“工作室”。
“臥室”——私人情緒發泄地、滿足性功能。在對志愿者們進行訪談時,90%的志愿者都提到了“發泄情緒”一詞,他們經常會在小號中發表一些在大號不適合發表的言論,大多是負能量的傷感語錄或者指責他人的話語。同時也有20%的志愿者指出,有時候會拿小號去觀看、轉發一些性感男生或者女生的照片,或者就是以小號的身份瀏覽一些成人網站。“臥室”類型的小號通常是匿名的,這種匿名性為用戶提供了一種保護機制,使他們能夠自由地表達負面情緒、私人思考或敏感話題,而不必擔心個人形象或社交后果。這種匿名性的環境有助于減輕社交媒體使用中的心理壓力,尤其是在現代社會中,人們越來越擔心自己的公眾形象和社交媒體上的表現。另一方面,根據志愿者的反饋,一些用戶使用小號來瀏覽和轉發性感的內容,或訪問成人網站。這種使用方式反映了用戶對于私人空間和性自由的需求。在這個“臥室”空間里,用戶可以探索自己的性趣味和身份,而不必擔心社會的審視或道德評判。
“書房”——工作專用、工具性功能。志愿者D是一名體制內工作人員,他所在的單位要求員工每天必須轉發公司相關內容,因此他創建了這樣一個小號專門用于轉發公司的相關內容,這反映了社交媒體在職業場合中的工具性功能。在這種情況下,小號不僅僅是個人表達的空間,而更多地成為完成工作任務的工具。這類“書房”小號通常不涉及個人生活的方面。它們的內容主要是與工作相關的信息,如公司公告、行業新聞或者專業文章。這樣的賬號為用戶提供了一個專業化的平臺,用于展示其職業形象和專業知識,同時也幫助他們保持個人生活的隱私。“書房”小號的另一個特點是其半開放性。這種類型的賬號通常不對外公開個人身份信息,既可以選擇匿名,也可以選擇實名,但不會在這個平臺上發布任何私人生活的內容。這樣的設置使得用戶在保持一定程度的匿名性的同時,也能夠在必要時公開自己的身份,以增加信息的可信度或職業聯系的可靠性。這種類型的小號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用戶對私人領域的再創造。它們將工作與個人生活分離,為用戶提供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工作空間。在這個空間里,用戶可以專注于職業發展、行業交流和專業知識的分享,而不必擔心個人生活受到干擾。微博作為一個公開的社交輿論場,用戶在使用微博的過程中 必然受到來自他者的“凝視”。此處的“他者”,可能是“互關”(指在微博上互為粉絲、處于雙方關注列表里)的親朋好友,也可能是“共景監獄”中的陌生圍觀網民,甚至是“全景監獄”中的社會管理者[5]。
“工作室”——功能性使用。50%志愿者表明會用小號對別人進行“視奸”行為。“視奸”意為“在對方不知情的情況下,瀏覽他的發言、關注與被關注、點贊記錄等歷史記錄,且盡量不留下痕跡——不關注,不評論,不點贊”,因為害怕自己“手滑”不小心點到對方的社交內容留下“痕跡”,所以干脆用小號進行此操作,“就算直接關注她也不知道我是誰,還是小號方便!”志愿者E表明,“用小號視奸更加方便,并且會把小號當成一個監視器凝視別人的社交平臺,這對于我來說只是個工具。”作為“工作室”的小號也謝絕訪客參觀,涉及用戶隱私,因此小號也具有監視別人的功能。
“客廳說”這一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刻的視角,用以理解微博大號和小號在用戶社交生活中的角色和功能。在這個理論中,微博大號被比喻為家中的“客廳”,它是公共的、正式的,代表著用戶對外的形象和身份。這里的互動和內容呈現,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旨在展示給“訪客”——即廣泛的社交網絡觀眾——一個規范化、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大號上的內容通常更加正面、正式,旨在維護和提升用戶在社交網絡中的形象。相對于大號的“客廳”,微博小號則被分為“臥室”“書房”和“工作室”等不同類型,各自承擔著不同的功能和角色。這些小號為用戶提供了更加個性化和多樣化的自我表達空間。“臥室”類型的小號是最為私密的空間,用戶在這里可以無拘無束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情感和想法。這里的內容可能是情感上的宣泄,或是那些不適合在大號上公開的私人事務。在“臥室”中,用戶可以放下公眾形象的負擔,享受純粹的自我表達。“書房”類型的小號則是半公開的空間。它可能被用于更加專業或學術性質的內容,如工作相關的討論、學術分享或特定興趣領域的探討。在“書房”中,用戶可能會保持一定程度的匿名性,同時分享更具深度和專業性的內容。最后,“工作室”類型的小號更多用于功能性的目的。例如,一些用戶可能會用這樣的小號來觀察和分析其他賬號,或用于某些特定的工作任務,如市場調研或競品分析。在“工作室”中,用戶的活動更多是以目的性和工具性為導向。
五、結語
學界對微博小號的用戶使用心理研究已有所成就,在中國知網上搜索“微博小號”的論文一共有10篇,大多為從社會心理學方向分析。本文研究不足之一在于訪談樣本量過于稀少且部分不具有可代表性,在此方面今后將會加強。本文的創新處在于在訪談中得到了更為合理地對微博小號的描述——“客廳說”。戈夫曼的“擬劇理論”可以描述與用戶在自我呈現時“戴著鐐銬跳舞”,那么“客廳說”則可以理解為用戶自我創建選擇私人領域,“臥室”“書房”等名詞概括其自我呈現的功能。隨著社會發展,不同年齡、身份用戶涌入社交網絡,使其心理也會逐漸具有差異化,因此本文作者將持續關注此議題。
參考文獻:
[1]林升棟,余潔.社交網絡用戶非常態使用行為分析[J].青年記者,2017(21):49-50.
[2]程詩語,余來輝.社交媒體用戶“小號”使用行為定性研究[J].傳媒論壇,2022(11):36-38.
[3]姚敬琦.控制“可見”與創建邊界:微博用戶自我呈現行為的衍變[J].新媒體研究,2022(18):36-40.
[4]劉之源.微博小號用戶心理探析[J].新媒體研究,2020(20):43-46.
[5]顧夢然.微博小號用戶的使用行為與自我呈現——基于對當代大學生的深度訪談[J].新聞文化建設,2021(19):73-75.
作者簡介:
曾嘉慧(1997-),女,漢族,廣西桂林人,碩士,研究方向:網絡人際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