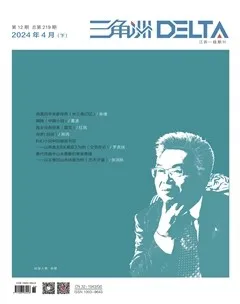《將軍和他的部隊》中的人道主義主題
劉麗 張美
人道主義的主題貫穿于弗拉基莫夫的長篇小說《將軍和他的部隊》之中。作者在小說中將將軍們對人道主義的踐行及極權主義對人生命的漠視刻畫出來,希望恢復人的尊嚴。將人的個體生命價值放在最高處,把人放在思考的中心,這一人道主義思想體現出弗拉基莫夫對蘇聯戰爭文學中人道主義的新思考。這一思考與薩特的存在主義人道主義思想相近,因此,有必要借助薩特的思想來進一步理解小說中的人道主義主題。
格奧爾基·尼古拉耶維奇·弗拉基莫夫以1841年衛國戰爭為背景創作了長篇小說《將軍和他的部隊》。小說于1995年獲得俄語布克獎,這次獲獎為弗拉基莫夫帶來巨大的聲譽。作者在小說中通過刻畫“非英雄式”人物——科布里索夫、如“神行海茵茨”人物——德軍將領古德里安等,將戰爭中無視個體生命及極權主義對人的迫害的反人性描寫出來,體現了作者對人個體生命價值的思考。因此,本文從對個體生命價值的思考與選擇和極權主義對人道主義的踐踏兩個方面入手,并借用薩特的存在主義人道主義思想來解析小說中的人道主義思想。
對個體生命價值的思考與選擇
雖然弗拉基莫夫的《將軍和他的部隊》是一部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但是作者卻舍棄了傳統戰爭小說中對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進行評判的是非觀。作者在小說中將戰爭下人的生存狀態、面臨選擇時的內心活動及“是否用俄羅斯的方式拯救俄羅斯”等問題提出來,這是作者對戰爭觀、戰爭本質的重新認識。作者對陣營中高級將領進行描寫,例如,蘇軍將領科布里索夫與德軍將領古德里安,將軍們被置于戰爭這一特殊的環境中,正因為如此,他們會更直接面臨選擇與被選擇。這與薩特的存在主義“人是自由的,但他的自由選擇擺脫不掉他處在‘一個有組織的處境之中的限制。”(讓·保羅·薩特 《存在主義就是一種人道主義》,周煦良、湯永寬譯)這一觀點有異曲同工之處。
“非英雄式”人物——科布里索夫,他是小說的主要描寫對象。作為一名蘇軍將領,他首先考慮的是手下士兵的生死與忍受戰爭所帶來的痛苦的百姓,他對戰爭是厭棄的,甚至是惡心,在他的頭腦中,人的個體生命價值更為重要,這也是他對人道主義精神的踐行。
科布里索夫命令手下抓來一個“舌頭”,在對他進行審問后,科布里索夫發現即將攻打的小城中的人并不是德國人,而是由一萬多名俄羅斯俘虜組成的隊伍。于是,他后悔在會議上將自己的作戰計劃和盤托出,也后悔做出想要奪取梅里亞津的決定。隨后,在斯帕索-別斯科夫茨火車站的會議上,就攻打梅里亞津的問題與朱可夫、瓦圖京等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他認為不應該用一萬多名無辜俄羅斯士兵的生命來換取攻打梅里亞津的勝利,這樣的話這場戰役的代價很大。因此,他提出繞過梅里亞津這一想法,但是與將梅里亞津攻打下來進而奪取普列特斯拉夫就能讓自己升官以及獲得獎勵相比,這樣撤退的提議遭到了否決。
科布里索夫在安排補修和鋪設顯然不中用的電纜時,想將小伙子換成老練一些的人,因為一想到這些小伙子可能明天就不在人世了,將軍的臉上、脖子上就布滿了羞愧與憤恨,他認為戰爭不僅考驗了這些十九歲小伙子,還有他們美妙的歲月,面對著這些小伙子,科布里索夫內心充滿了同情與無奈。
在西別日登陸場的戰役中,科布里索夫指責捷列先科為進攻型將軍,因為他將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拉入戰場,只為求得戰爭的勝利。因為捷列先科對于戰士們的犧牲并沒有覺得可惜與痛心,所以他對于瓦圖京的責備并不在意。他的集團軍在整個烏克蘭第一戰場上的損失最大,這一點就證明了他是如何不顧惜士兵們的生命。
科布里索夫深知戰爭的殘酷性,可他依舊不愿意“用俄羅斯的價值來拯救俄羅斯”,在與將軍們進行爭論時提出:“這場戰役不管怎么說代價太大了,科布里索夫說,我想過戰前在這個梅里亞津住了多少人。女人、老頭兒和孩子們不算,光能動員起來的成年男人有多少?是的,也許他們有一萬人。我應當打死這么多人。”
科布里索夫是一個諳熟殺人之法的將軍,可是只要他一想到戰爭對無辜人的屠戮,他內心的那份痛苦就始終縈繞心頭,到最后,心中所剩的只有悔恨。
如“神行海茵茨”人物——德軍將領古德里安。雖然蘇德正處于交戰中,但古德里安并未將蘇軍視為死敵,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弗拉基莫夫在創作《將軍和他的部隊》這部小說時拋棄了對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的描寫,因此,小說中古德里安對蘇軍有著自己的評價:“有時,他們絕望的小掌窩死死地扣住一小塊不僅不值得用他們的生命,也不值得用任何一滴血去換取的土地。”
這樣一位桀驁不馴的“海因茨”始終把將士們看作是自己的戰友,他們之間可以用“你”來相稱,并且士兵們可以向將軍提任何問題。面對俘虜,古德里安并沒有傷害他,反而是送給了他一個指南針,便于俘虜辨別方向從而越獄。面對德國元首的命令:“不惜一切代價——奪取圖拉。”古德里安顯然是不認同的。他認為這種不惜一切代價地奪取一座城市顯然是不顧士兵及老百姓的死活,是對個體生命的漠視,這違反了古德里安的準則。他還提出在戰場上也不要隨意耗費自己的坦克力量,因為俄羅斯人會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圖拉與兵工廠,所以不應該作無謂的犧牲與損耗。
即便古德里安見慣了屠戮的場面,但是在面對市監獄的牢房和地下室里的數百具尸體,他還是被眼前的一幕所驚嚇。這些人中無一人有死刑判決書,許多人最多判了五年,其中一些人的刑期已滿,還有一些根本沒有判決書,只是一些受偵訊者而已,大部分是因“破壞活動”“反蘇維埃陰謀”“反革命意圖”而被審。此時,他意識到這樣大規模、毫無意義的處決是多么可怕,這簡直是無視人的生命,是對人生命價值的肆意踐踏。
為了不再讓血腥屠戮繼續下去,古德里安做了總司令部沒有勇氣作出的決定,就是在托爾斯泰莊園中簽下撤退令。他想著將部隊帶到可以站穩腳跟過冬的地方去,等到來年春天讓第二段戰役去繼續那未竟之事。在他看來,“毫無任何價值和意義的血腥屠殺違背了人類的生存法則,隨意消耗人的生命更是犯罪,其罪孽感不言而喻。”(吳萍《從英雄主義到人道主義——蘇聯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的嬗變》)。
科布里索夫與古德里安在面對生命價值選擇的時候有著自己的思考。他們反對借戰爭之名大肆地屠戮無辜的人,他們對處于戰爭中的人始終葆有一顆憐憫之心。薩特認為:“英雄或者懦夫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通過人的主動選擇使他成為英雄或者懦夫。”面對戰爭與人的選擇時,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人,在他們的身上始終散發著人性的光輝,始終在踐行人道主義。
極權主義對人道主義的踐踏
“極權主義是一種現代形式的暴政,是一種毫無法紀的管理形式,權力只歸屬于一人。”(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簡單來說,在極權主義制度的控制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等都受其控制。這樣的現代形式暴政導致人的自然生存權受到威脅,個人的生命價值被忽視甚至被蔑視。弗拉基莫夫在小說中將極權主義社會的惡寫出來,這是對極權主義的批判,體現了作者踐行人道主義的決心。
一、極權主義對人性的侵蝕
阿倫特認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目標不是改變外部世界,或者社會的革命性演變,而是改變人性。”這意味著,如果一個人長久受到極權主義的侵蝕,終有一天他會變成極權主義的擁護者。
透過頓斯科伊的視角可以看出極權主義制度下斯維特洛奧科夫前后的變化。頓斯科伊認識他的時候,斯維特洛奧科夫還是一個上尉,是一個重榴彈炮營的指揮。他會與頓斯科伊在一個極小的地窖里過夜,會將自己儲備的零食及伏特加擺出來,也會帶著浪漫色彩的情感朗讀自己創作的詩篇。斯維特洛奧科夫在軍中深受愛戴,與軍中的士兵如兄弟一般。自從斯維特洛奧科夫加入鋤奸部門后,整個人心性大變。他聯合將軍身邊的司機西羅京打探將軍的行蹤,始終監視著將軍的一舉一動,甚至還會威脅到將軍的人身安全。西羅京問到關于鋤奸部的工作時,斯維特洛奧科夫少校回答道:“我們什么都干。但現在最主要的是使指揮員一分鐘也別從監護下消失。”因此,如果說斯大林的極權主義是他們悲慘命運的根本原因,那么特別處工作人員斯維特洛奧科夫少校之流就是造成他們悲慘結局的直接原因。
副官頓斯科伊對于叛徒逃兵們沒有經過公審法庭審判就被處死這件事是反對的,他認為應該讓所有的人看到,他們在祖國面前錯在哪里,他們的墮落有多么深重。而斯維特洛奧科夫少校對于這些人的處理態度卻是冷漠的,將他們隨意地槍決。
在蘇軍將梅里亞津攻打下來后,少校命人將五十名戰俘趕向河岸,死刑犯被命令從崖上下到水里去。面對戰俘他殘忍,面對自己的同胞更是滅絕人性。少校說只要他們能游過去,就不會開火并且原諒他們,但是最后“派出快艇追隨,之字形地緊靠著他們飛奔,用螺旋槳狠揍猛刺。剎那間,血浪飛騰而起,無一人生還彼岸。”
透過副官頓斯科伊的視角,將少校在戰場上視他人生命如草芥、漠視個體生命價值的一面展現在讀者面前。通過這些,我們可以看出一個長期受到極權主義侵蝕的人會變得冷酷無情,他的人性也會變得丑惡,甚至會做出反人道主義的事情。
對于極權主義的擁護,科布里索夫將軍也是其中一員。科布里索夫有兩個女兒,一個與自己的夫人同名,而另一個小名為斯維特蘭卡,以紀念斯大林的女兒,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將軍對斯大林的親近之情。將軍三次被調離原先的部隊去組建新的集團軍,其中在1941年的春天,他經歷了一場顛倒人生、扭曲人性的大劫難。他在被捕后,經歷了一系列屈辱的搜查,例如,將全身的衣服褪去,赤裸地面對一個女人的檢查,有時還要忍受粗俗的話語攻擊。在小說的結尾,科布里索夫因為違逆了最高司令部的意見而被罷免了職務,但是在隨后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從電線桿上的黑喇叭中聽到有關最高統帥對自己及集團軍的嘉獎:“……授予科布里索夫中將的坦克兵和射擊手……今后將他們命名為……為祖國……自由……獻出生命的烈士……永垂不朽……”科布里索夫面對斯大林對他以及部隊的獎勵,全然忘記了從前受到的迫害以及戰爭勝利所付出的代價,甚至產生了感激之情。
可以說科布里索夫是一個軍事天才,是一個對極權政治制度黑暗有著覺醒的人,但是不能說他是一個真正反叛極權主義的人,他甚至深陷于對這種制度的維護之中。
弗拉基莫夫通過對斯維特洛奧科夫少校與科布里索夫將軍形象的塑造,寫出極權政治制度的黑暗。對極權主義控制人的思想與人性,將人變成為制度所用的工具,使人漸漸地喪失了自我主體性和自由精神,喪失掉個性和人性的本質批判。作者希望人可以重新找到自己,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就如薩特所言:“人可以自由地進行選擇,即把人當作人,而不是物,是恢復人的尊嚴。”
二、極權主義對個體生命價值的蔑視
弗拉基莫夫在小說中極力地寫出極權主義對人個體生命價值蔑視的社會之惡,“在弗拉基莫夫看來,極權主義社會重要原則就是:在這里人的生命價值根本不被重視,人的生命價值實際歸于零。”(Лейдерман Н.,Липовецкий М.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0—1900-ое годы,В 2 Т[M].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я,2003,С. 542.)這些都是與人道主義相背離的行徑。
小說中寫到戰爭期間無數的俄羅斯民眾被無端的殺害以及蘇軍的高級將領為取得戰爭的勝利而不顧士兵的生死。在炎熱的1942年夏天,恐懼在軍中蔓延,因為下達的指令:“可以槍斃因所率士兵全部犧牲、手槍子彈打盡而撤退下來的軍官,可以槍斃因救護重傷戰友而到了后方的士兵,也可以槍斃沒有一點經驗的年輕女衛生員,因為她們不敢看令人恐怖的重傷,什么也干不了。把由于疲憊,由于失血偶然倒下的人擺到隊列前示眾。”早春時節,報復性死刑成風,在刑場上,被判死刑的有四個人:村長,一個身體虛弱、上了年紀的莊稼漢;兩個十九歲上下的年輕人——都是偽警察;還有一個警衛司令部的德國人。他們并沒有犯什么罪,什么也沒做,可是卻要被處死。朱可夫元帥在柏林的澤耶洛夫斯克高地為了讓老戰友杜艾特·艾森豪威爾趕不及前來幫忙,一個星期就讓三十多萬俄羅斯戰士犧牲。
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下,許多人情愿成為極權主義的幫兇,剝奪普通人的正常生命權,也有許多人認識到了極權政治制度的黑暗并與之作斗爭,還有像科布里索夫這樣的人,即使認識到了極權政治的黑暗卻依舊維護它。這些人對極權主義的態度恰恰印證了薩特的存在主義人道主義思想。
弗拉基莫夫在小說中用大量的細節描寫來說明極權主義對人道主義的踐踏,由于紅軍內部的斗爭導致大量的軍民犧牲,這是對個體生命價值的蔑視,將人的價值放在了最低處。從這些對由于蘇軍內部領導者的失誤導致的屠戮描寫來看,極權主義是對人道主義的違背,表達了作者對人個體生命價值的重視,即“把人當作人,不當作物,是恢復人的尊嚴。”
弗拉基莫夫《將軍和他的部隊》與以往的戰爭小說不同,作者并沒有將戰場的血腥畫面與戰斗的激烈場面描寫出來,反而是通過大量的人物對話與思考時的心理活動來將戰爭的殘酷性表現出來。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拋棄了經典俄羅斯文學作品中對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的思考,并沒有從國家的角度而是從人的角度出發來重新思考戰爭,將人性的善與惡、人的個體生命價值、極權主義下人的生存狀態等問題呈現出來,體現出作家對俄羅斯文學中傳統人道主義局限性的超越以及對薩特存在主義人道主義的認同與傳承。
作者簡介:
劉麗,女,遼寧撫順人,研究方向:俄語語言文學;張美,女,山東濰坊人,講師,研究方向:俄語語言文學。作者單位:長春工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