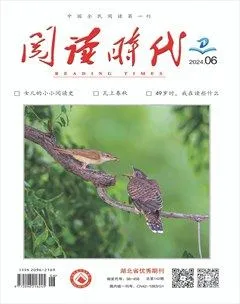《花事》如風來又走
羅拉拉
月初就拿到了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的這一小開本的《花事》,月底才舍得打開。狹長小巧的口袋本,精美可愛。
素凈雅致的馬蹄蓮封面,燙金的法文透著一種細膩與品格。
一向愛花,被南京城的文藝青年譽為“仙林花仙子”的南大法語教授黃葒譯出的文字流暢、詩意,如清風一般。書中還穿插著賈晶清淡溫柔的插畫。法國國寶級畫家科萊特的文字潮水般涌來,有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抒情與疊加風格,仔細品來,卻又別具一格。因為她總有著自己獨特的路數,文字于魅惑里透著危險,草木清香里卻又彌漫著動物的氣息,仿佛自然界環環相扣的食物鏈,自然而然又激情殘酷。
一本好看的小書,讓我看到的卻是中法三位女性之間一種跨時代的交流。
談論梔子花:“她清新怡人,就像少女的乳房,花開得也比我持久。她以此炫耀,含沙射影諷刺我老得快,花開到第三天,我就已經像是一只掉入溪水里的舞會手套一樣了。”
描述蘭花:“事實上,我的蘭花就是一只章魚:雖然沒長八條手臂,但她有八爪魚像鸚鵡一樣的嘴巴,就是我剛才稱作鞋尖的嘴巴……”
介紹芍藥:“芍藥就是芍藥的味道,也就是腮角金龜的氣味。憑借一種微妙的味道,她最能讓我們聯想到真真切切的春天,帶著各種令人猜疑的氣息,混合在一起卻讓我們心曠神怡。”
無論寫及哪種花,科萊特總有一種出其不意,散發出她信手拈來、激情洋溢的才華,和她的人生一樣在一般社會準則與他人的設定之外。科萊特講述花,其實也是在講述她自己。
科萊特后來在法國文壇大放異彩,廣泛涉獵小說、散文、戲劇乃至戲劇評論,甚至曾當選為龔古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主席;逝世后法國政府為她隆重舉行國葬,其生平還被改編為電影《科萊特》,由凱拉·奈特莉主演。然而,這樣一個不可忽略的科萊特,早年居然也曾是一個被丈夫長期PUA(精神操控)的鄉村女子。
她18歲時傾心愛上的作家、樂評人亨利·戈蒂埃·維拉爾(筆名威利)不僅賭博、酗酒,還入不敷出、處處留情。不僅如此,這位大她14歲的男人還長期擁有科萊特作品的署名權。好在科萊特一旦覺醒,就永遠不再是威利的影子。她創作、演戲、進軍時尚圈,也逃離了所謂愛情的“藩籬”。
就像她在《花事》外兩篇中的《葡萄卷須》里所寫的那樣:“脆弱的、柔韌的、苦澀的葡萄卷須也把我牽絆住了,當我青春年少、睡得又香又沉的時候,我會驀然驚醒,我弄斷所有那些纏在我皮膚上的卷須,我逃脫……我大聲抱怨,這才讓我明白那是自己的聲音。”
女人如花花似夢。同樣愛花的黃葒也感覺到了自己的“葡萄卷須”,不同的是,那是一種自由的選擇與沉浸,在日記中,她記道:“終于譯完《花事》,皮膚上爬滿了蛛網般涼絲絲的葡萄卷須。只是我不是那只年輕的夜鶯,我不驚慌,也不想忙不迭地掙扎,我任由自己默默享受這份被文字暫時捆綁住的囚禁。”這樣跨國界、跨時代的對話令我心動,我也關心書里書外花的故事,人的故事,女性的成長。
“緣分不停留,像春風來又走。”女人,花事,相互浸染,互為鏡像,各得啟發。
(源自《北京青年報》,梅之傲薦稿)
責編:曾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