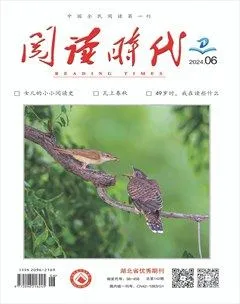《偷書賊》人在低谷,唯讀書可以救贖
北方有佳
在《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上,有一部作品,占據榜單超過10年,先后被譯成40多種語言,感動了無數人。
這個故事,與一個叫莉賽爾的“偷書賊”有關。《紐約時報》這樣評論:“這個故事將改變你的生命。莉賽爾展現出一種無可置疑的人性希望,在戰火、貧困、殘酷的環境中可以依賴的希望。”這份希望,是讀書帶來的,是能讓我們身處低谷,仰望星空的希望。
讀書,是生活的避難所
1939年冬天,一輛開往慕尼黑的火車正在疾馳,車里裝滿了面黃肌瘦、身著破衣爛衫的窮人。一個6歲的小男孩無聲無息病死在車上,第一個發現他的,是他9歲的姐姐莉賽爾。
莉賽爾一邊叫醒母親,一邊使勁搖晃著弟弟,可是無論怎樣哭喊,弟弟都沒能醒過來。火車臨時停靠在一個無名小鎮,她們帶著弟弟的尸體下車,找了一個墓地草草將其安葬。
葬禮上,莉賽爾悲痛得幾乎失去知覺。母親使盡力氣,才把她拖離墓地。在慌亂之中,她看到地上有本書,就偷偷將它撿起來藏在懷里,好讓自己能想起弟弟葬在這里。

母女倆重新乘坐火車前往慕尼黑。火車到站時,她們已經花光了所有路費,兩人餓得皮包骨,生存都成了問題。為了讓莉賽爾吃飽飯讀上書,母親狠心將她塞給了遠郊一戶人家收養,然后頭也不回地走了。
收養莉賽爾的是一對沒有孩子的夫婦,養父漢斯是個粉刷匠,養母羅莎靠替人洗衣養家。他們把莉賽爾當親女兒看待,還安排她去上學。
剛經歷過生離死別的莉賽爾,十分想念弟弟和媽媽,每天都會做噩夢。半夜驚醒時,她就偷偷拿出墓地里撿的那本書一遍遍撫摸。她不懂里面講什么,但這樣能撫慰她對弟弟和媽媽的思念。
有一天,養父漢斯發現了她的秘密。他輕輕讀出書名《掘墓人手冊》,驚訝地發現這并不是兒童讀物。當莉賽爾告訴他書的來歷后,他微笑地對莉賽爾說:“以后我們一起讀這個。”
在漢斯的陪伴下,莉賽爾漸漸學會了認字,并用閱讀搭建起了自己的小世界。那是一個遠離痛苦現實和紛亂環境的地方,那里沒有戰爭,沒有親人的離開,沒有同學的嘲笑……
閱讀,喚醒靈魂的一道光
書籍打開了莉賽爾的新世界,但現實世界遠沒有書中那么美好。
莉賽爾所處的時代,正是法西斯專政時期。各地頻頻清洗知識分子,上演焚書運動。這樣的高壓態勢下,得到一本書十分不易。開啟閱讀之路的莉賽爾,對書籍的渴望越來越深,可是她的手里,根本沒有幾本可讀之書。
有一天,小鎮廣場上又開始焚燒書籍,她乘人不備,從堆積如山的灰燼中迅速撿起一本書,緊緊將其貼在胸口。這是莉賽爾第一次“偷”書。盡管書的余溫灼傷了她的皮膚,但她心中滿是興奮,得到了書,就仿佛得到了全世界。
這一切,被鎮長夫人看在了眼里。幾天后,莉賽爾隨養母來鎮長家送洗好的衣服。鎮長夫人故意將莉賽爾引進書房,那里居然有成排的書架和滿滿的藏書。更令她想不到的是,鎮長夫人默許她每次送衣服過來時,都可以在這里讀一會兒書。
這成了莉賽爾最幸福的時刻。
戰爭爆發后,大家的生活日漸困難,鎮長家成了最后一戶能雇傭莉賽爾家洗衣的客戶。直到有一天,鎮長夫人告訴莉賽爾,他們也要取消洗衣服務了。這讓莉賽爾難過不已,她再沒有地方去看書了。
受不了讀書的誘惑,莉賽爾潛入鎮長家書房,開始偷拿書籍。《吹口哨的人》《送夢人》《黑暗中的歌》……在偷來的書籍中,她看見了被這個高壓病態社會壓抑的正義、秩序、勇敢與光明。這些書籍讓她學會了獨立思考,有了自己的思想和價值判斷。
莉賽爾的偷書行為,早就被鎮長夫人發現。她在莉賽爾偷的書中夾了一封信,上面寫著,希望莉賽爾下一次能主動敲門,以更文明的方式進入書房。
鎮長夫人之所以沒揭穿過莉賽爾,是因為她從莉賽爾身上看到了兒子的模樣。她的兒子年紀輕輕就死在了戰場,除了生前看過的書,兒子什么也沒留下。她失去了兒子,但不愿讓像兒子一樣的孩子失去夢想。如果兒子還活著,他也會像莉賽爾一樣為讀書想盡一切辦法。
戰爭能夠毀滅一切文字,卻無法熄滅藏在文字下面的靈魂。就如莉賽爾從灰燼中“偷”走書,忍受火苗的噬咬時,她的心已經戰勝了恐怖戰爭和政治迫害。就如鎮長夫人默許莉賽爾“偷”走書,她不過是用無聲的行動,對抗這個黑暗瘋狂的世界。
讀書,是托舉人生的支點
被鎮長夫人發現后,莉賽爾便不再偷書了。但她從來沒停止過讀書,她把手中的書讀了一遍又一遍,還通過讀書治愈了周圍的人。
戰爭越來越激烈,一天,猶太青年馬克斯逃到莉賽爾家,請求他們救命。善良的漢斯,冒死將他藏進家中的地下室。地下室潮濕陰冷加上心情抑郁,馬克斯高燒不退。莉賽爾為了讓他振奮精神,坐在床邊一遍一遍為他朗讀,從下午一直讀到深夜。清脆的朗讀聲猶如把他拉出深淵的手,逐漸令他打起精神,戰勝病痛。沒過多久,馬克斯的身體就康復了。
霍茨佩菲爾太太曾是養母羅莎的死對頭,有時她經過莉賽爾家門口,甚至會狠狠吐上一口吐沫。但當她的兒子在戰場上死去后,她精神恍惚,終日以淚洗面。莉賽爾得知后,每天去她家為她閱讀書籍。霍茨佩菲爾太太已經封閉的心,仿佛被女孩的讀書聲喚醒,空洞的雙眸慢慢回過神,開始正視現實生活,不再沉淪于失去。
在令人無比恐懼的空襲日子里,小鎮的人躲在防空洞里,滿臉愁云,唉聲嘆氣。角落里的莉賽爾默默打開一本書,輕聲誦讀起來。漸漸地,哭泣聲、抱怨聲、辱罵聲都安靜了下來,他們的表情隨著故事情節豐富、變化著,每個人都被書中的故事所吸引,暫時忘卻了外面的死亡和殺戮。
莉賽爾堅持讀了那么久的書,戰爭依舊沒有結束,生活依舊艱難,有時她不禁懷疑:讀書教會她珍惜生命,卻救不了那么多生命,讀書教會她熱愛生活,卻給不了她書中美好的生活,文字到底有什么用?
此時,鎮長夫人敲響了她的家門,遞給莉賽爾一個本子,提示她,如果讀書不能消弭掉人性的殘暴和現實的復雜,那么屬于自己的文字,會讓思想永存,讓自己重生。
于是,莉賽爾從閱讀者開始變成一個寫書者。也正是因為在地下室專心寫作,讓她躲過了意外空襲,成為唯一的幸存者。
后來,戰爭結束了,莉賽爾將“偷書賊”的故事記錄下來,講給很多很多人聽。她用自己的經歷告訴人們:讀書或許不能讓人生的每一刻都熠熠生輝,但能在人生低谷時,給予你撫慰和滋養。
在《偷書賊》的故事中,“偷”不是重點,“賊”不是重點,“書”才是。莉賽爾在“偷”來的書中維持自己的生命,她救贖的不僅僅是自己的生活,還為無數身處不幸的人,帶來安慰與希望。
書籍是最有耐心和最令人愉快的伙伴,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時刻,它都不會拋棄你。書籍也是最鋒利和最堅硬的斧子,能鑿開鎖住希望的門,鑿破堆滿層層苦難的高墻。
(源自“每晚一卷書”,有刪節)
責編: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