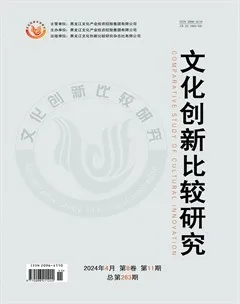以水為媒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傳統技藝中的地方性知識研究”(項目編號:22YJA760076)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吳曉諾(2000-),女,山東青島人,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文化遺產保護,藝術史。
摘要:水在古代神話和民間傳說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意象,因為水的存在,萬物得以孕育、繁衍,水與愛情息息相關。水柔和含蓄的一面又和東方人內斂特性有共通性。水的形態萬千,與人世間各種類型情愛相對應。水的波動對應愛情之痛,水的深廣對應愛情的遙不可及,水的悠長對應愛情的心儀,水的流逝對應愛情的至死不渝。水的變化萬千猶如愛情的變幻莫測。中國傳統神話故事、民間傳說中圍繞著水的故事眾多,關于愛情故事的描述更是數不勝數。該文主要以中國傳統的神話故事、民間傳說中的“水——愛情”為例,選用廩君和鹽水女神、牛郎織女、孟姜女、白蛇傳等故事,通過水這一媒介,探尋水意象與愛情的共同之處。
關鍵詞:水意象;神話;民間傳說;廩君和鹽水女神;牛郎織女;孟姜女;白蛇傳
中圖分類號:I206?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文章編號:2096-4110(2024)04(b)-0006-05
Take Water as the Medium
—Water and Love in Ancient Myths and Folklore
WU Xiaonuo
(College of Art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s, Jinan Shandong, 250300, China)
Abstract: Water is a very important image in ancient myths and folklore,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water, all things can be bred and multiplied, and water is closely related to love. The soft and implicit side of water has a common effec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iental introverted. Water is of myriad forms, corresponding to all types of love in the world. The fluctuation of water corresponds to the pain of love,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water corresponds to the distance of love, the length of water corresponds to the desire of love, and the passage of water corresponds to the death of love. The changes of water are like the changes of love. There are many stories around wat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yths and folklore, and there are countless descriptions of love stories. This paper mainly tak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airy tales and folklore of "water — love" as an example, and selects the stories of Linjun, brine goddess, Cowherd, Meng Jiangnu,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and so on, to explore the common place of water image and love through water as the medium.
Key words: Water image; Myth; Folklore; Linjun and brine goddess; Cowherd and Weaver Girl; Meng Jiangnyu; White Snake
江水、河水、湖水、海水,波平如鏡的水、波濤洶涌的水、一瀉千里的水、曲似柔腸的水……水變化萬千,水的意象在創作者的手中自然也形態各異。水能抒寫友情之長久、離別之愁、相思之苦,水亦能抒不得志之愁、亡國之痛。宋詞《鵲橋仙·纖云弄巧》中“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水在這里又變成柔情蜜意的、纏綿悠長愛情的象征。中華民族對于男女愛情的表達不像西方人那樣開放,往往是含蓄內斂的,這在我國最古老的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中就有體現。
1 水之波動——被棄之痛
目前已知最早的便是廩君和鹽水女神的故事了。在伏羲的后代子孫中,有個叫務相的巴族小伙。在經過重重選拔后,務相做了部落的首領,統領其他幾個部落,改自己的名字為廩君,帶領全族人干出了一番事業。同時,他也留下了一段令人惋惜的愛情故事。
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愿留共居。”廩君不許。
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飛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余日。廩君不知東西所向,七日七夜。
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纓此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鹽神受而纓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天乃大開[1-2]。
廩君和鹽水女神的相遇便是在鹽陽的鹽水河,鹽水女神真心實意勸廩君一行人留下,并且兩人同宿,關系親密。廩君虛意應允,以一縷青絲相送,隨后卻將鹽水女神的化身射死,使天大開。
水本應是纏綿之水,在這里相愛之人只能互訴衷腸后卻不能逾水相會。水面波光粼粼,流水潺潺,一切看起來那么美好,突然一塊石頭被投入水面,泛起陣陣漣漪。廩君和鹽水女神的相遇就像平靜的水面,鹽水女神的阻攔,就像那塊石頭,打破了原有的安寧。
從故事可以看出,廩君和鹽水女神應該是兩個部落的首領,鹽水女神可能還是一個母系氏族的女性首領。而廩君身在一個男性占主要地位的部落。兩者本身就存在差異,再加上廩君部落的去留的問題,兩人的悲劇性結局其實早已注定。并且,廩君部落來的目的是開疆擴土,鹽水女神因為兒女私情提出“魚鹽所出,愿留共居”,而廩君不同意。由此看來,其實他也是有一定野心的,畢竟與鹽水女神共治與自己掌握全部的統治權相比,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鹽水女神最終的結局是被廩君射殺而死,這種方式加重了這段感情的悲劇性色彩,鹽水女神為愛退讓卻換不來廩君的一絲柔情,也不能遏制住廩君開拓疆土的欲望,這是鹽水女神的悲哀之處,更是廩君一生中在情感上的遺憾。
在后來建造的廟中,廩君的塑像旁邊還有一尊神像,其名曰德濟娘娘,當地的人們說她便是被射殺的鹽水女神,兩人最后破鏡重圓了。從這里可以看出,其實當地的人們有一種補償心理,希望廩君最后能夠和鹽水女神破鏡重圓,畢竟國人還是較為喜歡“大團圓”結局。但如果史料記載完全正確的話,兩人又怎么可能破鏡重圓呢[3]?對于流傳至今的各種故事,后世一般都會進行一定的再加工,因此故事具有不確定性。
2 水之深廣——可望而不可即
每年的農歷七月七日是我國傳統上的“情人節”,又叫七夕節、乞巧節。追根溯源,就是牛郎織女的愛情故事。
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女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云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后遂廢織衽。天帝怒,責令歸河東,許一年一度相會[4]。
天帝的女兒織女擅長織布,每天勤勤懇懇地織彩霞,天帝將她嫁給河西的牛郎,然后她不像之前那樣盡心織布,惹怒天帝,天帝讓他回到天河以東,只許他們一年相見一次。寬闊的天河成為兩人相見的障礙,河水之深,不可跨越。
牛郎和織女,當時正深處于甜蜜愛情中的兩個人,又怎么會不希望常常和心愛的人花前月下、長相廝守?但一河之隔,思慕變為求之不得的失落和悵惘,臨水相望,可望而不可即。《牛郎織女》描繪了相愛之人只能隔水相望的愛情悲劇。江水滔滔不絕,卻抵擋不住兩個相愛的人的心,牛郎和織女一年一次的鵲橋相會也顯得尤為可貴。“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秦觀的一句詩道盡了兒女的情絲綿長。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音查,水里漂浮的木頭),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于槎上,多赍糧,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余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來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后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5]。
《博物志·雜說下》中記載天河與海相通,這里可以看出那時候人們對于天文地理的了解不夠深刻,“天圓地方”的觀點深入人心,為牛郎織女相遇的傳說提供了合理性。一個放牛人與一位天上的仙女相遇并相愛。牛郎織女的故事是“女高男低”的模式,這一模式決定了他的悲劇性結局,在兩人相戀過程中也必定充滿困難和挫折[6]。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現實,古代中國封建色彩濃厚,男尊女卑的思想深入人心。
3 水之悠長——心有所儀
前兩個神話愛情故事都為悲劇,而少昊的誕生則是美滿愛情的結晶。帝子和皇娥相遇于水際,志同道合,琴瑟和鳴。帝子對皇娥可謂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游,經歷窮桑滄茫之浦。
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宴戲,奏便娟之樂,游漾忘歸。
窮桑者,四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后天而老。
帝子與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薰茅為旌,刻玉為鳩,置于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
帝子與皇娥并坐,撫桐峰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白帝子答歌。
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金天氏。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于帝庭,因曰鳳鳥氏[7]。
這是一段兩個神仙相戀的愛情故事。大意是說,皇娥晚上在璇宮織布,休息的時候乘著木筏游玩,到了在煙波蒼茫的窮桑之浦,與水際的“太白金星”相遇。帝子和皇娥一見鐘情,泛舟同游。帝子撫琴,皇娥依瑟而唱歌。不久,皇娥便在窮桑樹下生了少昊。海便是他們愛情開始的地方,文中提到窮桑這個地方有一種孤桑之樹,很高,能夠直上千尋,在神界與人間搭建了橋梁,建立了神與人的聯系。帝子與皇娥相遇于水際,碧波蕩漾的春水讓他們陶醉其中,兩人向對方抒發著思慕之情,水似乎就成了兩人相識的媒介,成了少昊誕生的溫暖河床,水乳交融,便產生了少昊。
人和妖亦能相愛,愛可以沖破一切障礙。白娘子和許宣的故事就是人妖相戀的故事。“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許宣非但沒有斷魂反而遇到了一個美嬌娘。
正是清明時節,少不得天公應時,催花雨下,那陣雨下得綿綿不絕。許宣見腳下濕,脫下了新鞋襪,走出四圣觀來尋船,不見一只。正沒擺布處,只見一個老兒,搖著一只船過來。許宣暗喜,認時正是張阿公。叫道:“張阿公,搭我則個!”老兒聽得叫,認時,原來是許小乙,將船搖近岸來,道:“小乙官,著了雨,不知要何處上岸?”許宣道:“涌金門上岸。”這老兒扶許宣下船,離了岸,搖近豐樂樓來。
搖不上十數丈水面,只見岸上有人叫道:“公公,搭船則個!”許宣看時,是一個婦人,頭戴孝頭髻,烏云畔插著些素釵梳,穿一領白絹衫兒,下穿一條細麻布裙。這婦人肩下一個丫鬟,身上穿著青衣服,頭上一雙角髻,戴兩條大紅頭須,插著兩件首飾,手中捧著一個包兒要搭船[8]。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講了藥鋪主管許宣祭祖歸來時,雨中坐船初次遇到了白娘子,白娘子借傘、還傘,讓丫鬟小青送銀十兩,實為官府庫銀,許宣因此發配蘇州,與白娘子相遇。后白娘子盜物連累了許宣,許宣又被發配到鎮江,法海告知許宣白娘子是蛇妖,許宣要求成為法海徒弟,在法海的幫助下鎮壓了白娘子。許宣用化緣所得建造了雷峰塔,能夠永世鎮壓白娘子。
與之前的版本不同,從這一版本開始,白娘子的形象開始出現從惡向善的轉變。她不再是以前版本中的挖人心肝的蛇妖,身上更增添了一種人性的色彩,水邊相遇趁機搭船,交流中透露自己的悲慘身世,引發許宣的憐憫之心,拉近與許宣的心理距離。
白娘子形象的轉變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的作者馮夢龍所處的時代是明代中后期。明代中后期君主專制高度發達,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社會思想隨之發生劇烈變化,陽明心學占據主流。一些西方的思想開始在中國傳播[9]。馮夢龍塑造的白娘子形象與前人相比,更為追求個性自由和自我的幸福。她敢于與法海斗爭,追求與許宣的幸福生活,這恰恰是一個世俗女子不懼重重阻撓追求自己的幸福的真實寫照。雖然白娘子是一個蛇妖,但在馮夢龍的筆下,她具有了人性光輝的一面。當白娘子與許宣的感情出現危機的時候,白娘子先自奉承好了媽媽。她懂得通過討好婆婆來挽救自己和許宣的感情。當許宣發現白娘子是蛇妖時跪地求饒,從白娘子的語氣中看出她對許宣很失望,甚至是埋怨他的懦弱無能。就像世俗間的女子一樣,她用真心待夫君,然而最后收獲的卻只有失望。
作者增加了清明時節這一時間節點,解釋了白娘子清明雨天來到此地的緣由,增加了故事的完整性。俗話說“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兩人在水邊相遇,同乘一艘船,也算是百年的緣分使然。清明時節的雨綿綿不絕,就像情絲,剪不斷理還亂。這樣也讓“傘”這個信物自然而然產生,雨天借傘,自然也會有還傘,一來二去兩人關系便熟絡起來,成為以后兩人戀情發展的鋪墊。
4 水之流逝——誓死相隨
湘水無情,二妃有情。“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這句話用在娥皇、女英兩位身上再確切不過了,兩位妃子跟隨舜出征,聽聞舜在洞庭湖、湘水附近犧牲,兩妃淚撒在竹子上,成為湘妃竹。娥皇、女英在湘水投江自殺,成了洞庭湖女神,出入狂風暴雨。舜和娥皇、女英夫妻情深,像水一樣纏綿,就算是面對死亡也不膽怯,誓死追隨。水流滔滔不絕,前赴后繼。
大舜之陟(音志)方也,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10]。
斑竹即吳地稱湘妃竹者,其斑如淚痕,世傳二妃將沉湘水,望蒼梧而泣,灑淚成斑[11]。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12]。
娥皇、女英其實都是堯的女兒,堯將兩個女兒許配給舜,其實也想通過這一方式,讓“臥底”打入“敵軍”內部,考察舜的品性道德,也因此傳出了禪位的佳話。舜的父親和弟弟多次謀害他,舜都是在娥皇、女英的幫助下逃脫險境,避免了兄弟相爭局面的發生,卻沒有追究他父親和弟弟的責任。
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出:“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這句話用在舜身上再合適不過了。為人仁善,有能力,所以能被堯賞識,通過禪讓制成為首領,并且迎娶到堯的兩個漂亮女兒,在父親和弟弟的多次謀殺后仍能既往不咎和睦相處,也是一種大善。
娥皇、女英的殉情似乎是人神身份的一個轉換,兩人生前與舜相親相愛,死后化作神也在保護自己的夫君。舜和娥皇、女英的愛情故事反映了當時社會一夫多妻的婚姻形式。眾所周知,文學創作會有一定的藝術加工,藝術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兩人的行為向世人展現了一種貞潔烈女的形象,為丈夫守貞,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引導古代女性學習這一行為。
淚水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淚水可以是梨花帶雨的哭泣,可以是喜極而泣,也可以是號啕大哭。孟姜女的淚水力量是巨大的,甚至能夠哭倒宏偉的長城。孟姜女哭倒長城后,找到了丈夫萬喜良的遺體。
第二天傍晚,孟隆德從外面回到家里,向家人講起一件新聞,正是關于秦始皇張榜捉拿萬喜良一事。聽孟隆德一說,一家人都很為萬喜良鳴不平。孟姜女聽得心中煩熱,就叫上丫環來到花園。
這萬喜良此時正躲在孟家花園,聽見來人,趕快躲入樹林。
孟姜女見花好月圓,不覺心曠神怡,信步來到了荷花池邊。
這時飛來一對大蝴蝶,盡在荷池里采食花須,孟姜女見了,就用紈扇去撲。一不小心,掉進池里,弄得渾身是水,兩腿是泥。孟姜女見四下無人,忙把衣服脫了,用水去洗身上污泥。
那萬喜良本來躲在樹后,料不到有此眼福,因為看得入了神,沒想到男女授受不親,來不及回避。那孟姜女一上岸,抬頭發現樹旁有個大男人,直羞得無地自容,急急忙忙把衣服穿上[13]。
這個愛情故事講的是秦始皇建長城時,勞役繁重,在民間大肆強征青年勞動力,男主人公萬喜良落難,與女主人公孟姜女在后花園相遇并喜結連理。新婚后的萬喜良就被迫出發前去修筑長城,不久因饑寒勞累而死,尸骨被埋在長城墻下。孟姜女歷盡了千辛萬苦終于來到了長城邊,得到的卻是丈夫死亡的噩耗。孟姜女在長城上哭了三天三夜,忽然長城坍塌,露出了萬喜良的尸骸,孟姜女安葬了萬喜良,后于絕望之中投江而亡。
歷史上,為了抵御敵國的進攻,統治者修筑了宏大的防御工程——長城。修建長城給人們帶來了繁重的勞役。萬喜良就是被強征的農夫之一。孟姜女、萬喜良只是其中被涉及的典型代表。一個養尊處優的千金小姐與萬里尋夫路上的艱難險阻形成鮮明對比。孟姜女凝聚了當時的婦女們身上的善良和堅貞不屈的性格。這個故事寫出了繁重的徭役帶給人們的苦難,表達了人們對于封建統治者勞民傷財行為的厭惡,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當代與古代相比,對愛情的表達更加直白,青年男女不再接受以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婚姻,更多的是青年男女的自由戀愛。人們也不需要像古代那樣遵從“三從四德”。愛情其實是一個很美好的東西,不然醉心的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中也不會多有提及,從廩君和鹽水女神到后來的孟姜女哭長城。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現代人們不僅追求物質的享受,也越來越重視精神上的享受。世界成為一個開放的世界,各國之間的交流也變得頻繁了,思想上也出現了兼容并包的現象。河水、海水,甚至是淚水,都是男女愛情中的一個重要的元素,水的意象的豐富性也影響著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中青年男女愛情故事的創作。人們將一些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結合一定的時代背景進行改編,使其更有吸引力。中國古代大多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占主體,男耕女織的生活使人們被禁錮在固定的土地上,每日迎來的都是辛苦的農活,長期的封閉使他們變得更加含蓄內斂,樸實的就像是腳下的農田。
5 結束語
古代文明大多發源于江河湖海,水是孕育文明的搖籃,是生命的象征。通過看著每日熟悉的流水,他們幻想著“水——愛情”的共通之處。水的波動,就像是愛情中的兩人由“怦然心動”到被拋棄的痛苦;水的深廣,就像是愛情中相遇的兩個人能夠遠遠地互相看到,卻不能近距離地交談;水的悠長,就像愛情長跑中的兩個人最終能夠擁有美好的結局;水的流逝,就像對逝去愛情的無限惋惜。那個時候對女性的要求便是柔情似水,向柏松在《中國的水崇拜》一書中指出:“水崇拜的原始內涵是與早期人們求生存、求繁衍的基本要求分不開的。”因為有水的存在,萬物才能孕育成功,人類的繁衍生息自然也離不開水。在古代人們的心里,愛情婚配的最終目的便是繁衍后代。自然而然水就和愛情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水是一個情感符號,也可以是一個環境背景,更是一個中國文學史中最獨特的文化意象。“水”這一意象成了中國古代神話和民間傳說中愛情的代名詞。水本身沒有一個固定、具體的形狀,當愛浸潤在水里,就會浸潤人心,像水一樣無處不在。
參考文獻
[1] 姜莉麗.郝超.《詩經》中“水-愛情”模式的生成與表現[J].哈爾濱學院學報,2011(7):96-99.
[2] 宋衷,秦嘉謨.世本八種[M].北京:中華書局,2008.
[3] 劉守華.廩君與鹽水神女神話新解[J].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5):1-3,22.
[4] 馮應京.《月令廣義·七月令》引《小說》[M].刻本.明萬歷30年秣陵陳邦泰刊,2020.
[5] 張華.博物志[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6] 王瑋薇.基于擇偶理論的中西方經典民間愛情故事比較研究[J].社會科學論壇,2017(10):199-214.
[7] 王嘉.拾遺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5.
[8] 崔云偉,孫緒波.略論白蛇傳故事的主題流變[J].東方論壇,2015(2):81-88.
[9] 陳昶.民間:從文學史走向思想史[J].南方文壇,2023,216(5):65-74.
[10]酈道元.水經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6.
[11]王象晉.群芳譜[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12]方濤,釋注.山海經[M].北京:中華書局,2011.
[13]石玉昆.繪圖孟姜女萬里尋夫全傳[M].石印本.上海:大同書局,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