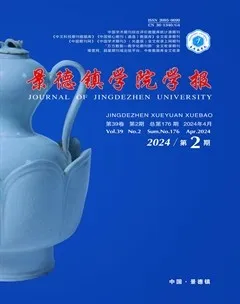伯克修辭學視角下合肥方言外宣翻譯研究
※ 投稿時間:2023-12-26
項目來源:安徽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SK2020B014);安徽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SK2021A0819)
作者簡介:俞瑩之(1978-),女,安徽合肥人,講師,主要從事西方修辭學、英語語言學研究。
摘? ?要: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跨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化,方言外宣翻譯在我國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作為一種跨語言、跨文化的修辭行為,方言外宣翻譯工作具有一定的挑戰性。為一項涉及不同語言和文化的修辭任務,方言外宣翻譯工作具備一定的復雜性和挑戰性。本文從伯克修辭學的視角對合肥方言的外宣翻譯進行研究,從外宣翻譯的目的、受眾和修辭情境等方面入手,發現和總結了銘記修辭目標以堅守外宣翻譯使命,采用與受眾“同一”的修辭勸說模式,依據修辭語境尋找原文和譯文的最佳契合等有效的合肥方言外宣翻譯策略。本研究對合肥方言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合肥方言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進行了有益的探究。
關鍵詞:伯克修辭學; 合肥方言; 外宣翻譯策略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9699(2024)02-0035-06
一、引言
合肥方言屬于江淮官話洪巢片合肥小片,是指安徽省合肥市及其周邊地區本地人所使用的本地方言。合肥方言具有獨特的發音、詞匯和語法特點,與官方標準語(普通話)有所不同。作為合肥地區居民日常交流和社交的語言工具,合肥方言是該地區地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然而,隨著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發展,合肥方言逐漸消失的風險不斷加大。方言的缺失,將不僅阻礙本地文化的傳承,也會妨礙中華文化在國際上的傳播。保護和傳承合肥方言不僅對于本地文化來說至關重要,而且對于中華文化來說也很重要。本文將從肯尼斯·伯克的修辭學視角研究合肥本地方言的外宣翻譯,以推動本地方言及文化的傳播。本文的方言語料來自南方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合肥方言》(完顏海瑞主編,孫金龍作序),筆者將從肯尼斯·伯克的新修辭學視角進行合肥方言的外宣翻譯研究,為保護和傳承合肥方言文化做一份貢獻,同時也為合肥方言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二、肯尼斯·伯克的修辭學理論
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是美國著名修辭學家、文學批評家和哲學家,被譽為“當代西方修辭學泰斗”。他繼承和發展了西方古典修辭學泰斗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思想。他的修辭學體系龐大而精深,其核心是“同一”。伯克認為,修辭過程是修辭者與聽眾/讀者同一的過程,即尋找共同點的過程。伯克的修辭學與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存在密切聯系,盡管兩者的修辭體系和術語不同,但從運作機理來看,兩者卻有交織和變通的可能。[1]
作為肯尼思·伯克修辭學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同一理論指修辭者通過尋求與觀眾或聽眾的“同一”,以達到誘發合作、說服他人的目的。同一理論包括三種尋求認同的方式:同情認同、對立認同和不準確同一。“同情認同”的目的是激發觀眾或聽眾的情感,使之在感情上接受修辭者的觀點;“對立認同”是通過與觀眾或聽眾在經歷或出身上的對立來贏取他們的支持;“不準確同一”是通過對事實的曲解或夸大來達到說服的目的。亞里士多德強調人品訴諸、情感訴諸和理性訴諸,而伯克繼承和發展了他的勸說理論,提出了同情認同、對立認同和不準確同一三種尋求認同的方式。 兩者都強調修辭者在演講中通過建立與觀眾或聽眾的聯系,以達到說服觀眾接受其觀點的目的。伯克的修辭學思想基于這個觀點: 人的本質源自這樣一個事實,即人作為符號使用的動物。我們的一切感知包括理解、態度、判斷、選擇與隨后的行動都是通過我們制造、使用與誤用的符號的介入而形成的。[2]
在伯克看來,修辭研究“用語言這種符號誘使那些本性能對符號作出反應的動物進行合作”。[3]鞠玉梅(2005)[4]認為,這種使用語言進行規勸的做法似乎與傳統修辭學關于修辭的定義沒有什么區別。在伯克的理論中,他在古典修辭學的“勸說”理論基礎上引入了修辭的其他特點,并擴展了修辭學的定義,使其大大超出了傳統修辭定義的范疇。同一理論認為修辭活動普遍存在于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人是修辭的動物,哪里有勸說,哪里就有修辭;哪里有意義,哪里就有勸說。[5]伯克修辭理論的應用范圍及其廣泛,強調一切語言皆修辭。
三、伯克修辭學理論視角下的外宣翻譯
外宣翻譯是指將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以實現跨語言、跨文化的傳播。外宣翻譯的目標是實現對外宣傳目標,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為爭取國際話語權服務,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合作,消除或改善缺失,實現翻譯目的。陳小慰認為,當下我國開展的對外翻譯傳播具有顯著的修辭特性:動機性。對外翻譯傳播肩負國家使命帶有明確的目的和動機色彩,包括“走出去”文學翻譯。[6]外宣翻譯關系到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國際社會中的話語權和形象塑造。外宣翻譯的質量直接影響著對外宣傳的效果,因此,做好外宣翻譯工作意義重大。
外宣翻譯的行為具有勸說性質,即通過傳播內容對外國受眾產生心理、態度和行為上的變化。這與伯克修辭學中的同一理論相吻合。伯克修辭學在外宣翻譯中的作用是幫助譯者更好地理解目標受眾的思維模式和文化背景,從而更好地構建能夠說服目標受眾的外宣譯文話語。通過運用同一理論,可以實現外宣譯文的交際預期,即讓外國受眾接受并認同中國的觀點和行為,從而樹立中國良好的國際形象。具體來說,應用伯克修辭學理論指導外宣翻譯實踐,需要從外宣翻譯的目的、受眾、和修辭情境等方面來考慮。
外宣翻譯與伯克的同一理論均以溝通和說服為目的。同一理論強調修辭的目的主要是溝通和說服,而外宣翻譯作為一種特殊的話語構建活動,其目的在于讓世界了解中國,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爭取國際話語權。因此,外宣翻譯本質上是以語言為媒介進行的跨文化交際與傳播活動,其目的是通過說服工作消除誤解,促進我國與世界各國的相互信任與友好合作。伯克修辭理論應用于外宣翻譯實踐還需要強調受眾的重要性。外宣翻譯的過程中,譯者需要與受眾(讀者)在觀點、態度、價值等方面具有共同點,形成“無意識同一”,從而產生親和力,最終誘發受眾與譯者合作,于“無意識”中接受和認可譯者的觀點。另外,外宣翻譯受修辭情境因素制約。修辭情境是指修辭者所處的語言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等。外宣翻譯作為一種特殊的話語構建活動,其修辭環境是顯而易見的。為了達到外宣譯文的預期交際目的,譯者需提高修辭意識,以修辭者的身份進入跨文化交際這個特定的修辭情境之中進行話語構建。
外宣翻譯與伯克修辭學理論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外宣翻譯者需要提高修辭意識,遵循伯克修辭學理論,不忘外宣翻譯初心,以目標譯文受眾為中心,充分考慮修辭情境,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進行外宣翻譯實踐。
四、伯克修辭學視角下的合肥方言外宣翻譯策略
合肥方言的翻譯策略研究目前還很少有人做,幾乎是個空白的研究領域,成果更是寥寥無幾,本地方言外宣翻譯策略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目前經過筆者對合肥方言和英語的不斷深入研究,總結出了一些策略。這些策略包括銘記修辭動機、不忘譯者使命,采用修辭勸說模式,和與受眾“同一”以及依據修辭語境來尋找原文和譯文的最佳契合。
(一)牢記修辭目標以堅守外宣翻譯使命
伯克修辭學的目的是通過尋找共同點,使修辭者與受眾同一,從而說服他們。伯克認為,修辭過程是修辭者與聽眾/讀者同一的過程,即尋找共同點的過程。修辭的基本手段在于對語言材料的變通運用。修辭的變異性與語法的規范性相對照,反映了它具有一種與語言的結構性相對照的基本性質即解構性。[7]翻譯的目的在于尋求促進不同文化的人類相互理解和尊重、和平共處、共同進步的說服方式。翻譯是一種跨語言、跨文化的交流方式,旨在通過運用語言象征與潛在受眾相互影響,促進合作。外宣翻譯者在進行外宣翻譯實踐時,應該關注譯文讀者的需求和期望,同時會有一個明確的目的,比如傳遞某種思想、文化或價值觀。因此,在翻譯工作中,外宣翻譯者可以在伯克修辭學的指導下進行翻譯工作,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確保翻譯的效果能夠達到預期的目的。這里筆者要討論的是合肥方言的外宣翻譯人員如何通過翻譯,向國際社會介紹合肥,宣傳合肥的人文價值觀等。例如:
[1] 天作有雨,人作有禍。
譯文:
If heaven makes mistakes, there will be rain and snow; if people engage in wrongdoing, they will attract calamities.
原文:
“天作有雨,人作有禍。她遲早也有這一天——許多人這樣說。”①
譯文:
“If heaven makes mistakes, there will be rain and snow; if people engage in wrongdoing, they will attract calamities. Many people say that she will have this day sooner or later.”
“天作有雨,人作有禍”的意思是:“天若犯錯了,就會有雨雪,人要胡作非為就會招來災禍”。此例表達了合肥本地主流的一個關于如何做人的觀點,表達了一種責任感強烈、注重行為規范和后果的人生觀。它認為個體行為具有直接的影響和責任,并強調了行為的倫理和道德標準。這種人生觀強調個人的責任和貢獻,認為個體行為的正確與否對于人生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這句合肥方言的翻譯,可以采用直譯的方法。此句可以直譯,“heaven”和“rain and snow”的隱喻含意很容易被國外讀者理解。這樣的外宣翻譯動機在于傳播合肥本地的一個重要的文化價值觀,即人們要注重自己的行為規范,主動承擔自己的行為帶來的后果。這樣的傳播可以增進國際文化互通、促進不同文化之間更深入地理解彼此的思想與價值觀。通過這樣的翻譯,可以實現伯克新修辭學同一理論強調的主要修辭目的,即溝通和說服,也可以實現對外宣傳目標,樹立良好的合肥形象,傳播本地文化、價值觀和人生觀,建立一種更加包容和諒解的國際社會氛圍。例如:
[2] 叫人不折本,舌頭打個滾
譯文:
When you meet acquaintances, all you need to do is say “Hi!”, you wont lose anything.
原文:
我奶奶曾若干次教導我說:“叫人不折本,舌頭打個滾”②
譯文:
My grandmother has taught me several times, “ When you meet acquaintances, all you need to do is say ‘Hi!, you wont lose anything.”
“叫人不折本,舌頭打個滾”的意思是當你與熟人見面時,只需要簡單地打個招呼,不要過于顧慮或拘謹,一次簡單的招呼而已,不會有什么損失,卻能維系最基本的人際關系,何樂而不為。此句話是合肥本地人,一般指老人勸誡孩子或年輕人,見到熟識的人要打招呼,友好地表達問候,體現了合肥人樸素的人際交往態度。此句的翻譯可以采用意譯,將“不折本”翻譯成“all you need to do”,將“舌頭打個滾”翻譯成“say ‘Hi”。直譯的話很可能會造成國外受眾理解上的困惑,采用意譯就可以了。這樣的外宣翻譯動機在于向國外的人們展示合肥人樸素、友善和輕松的人際交往觀。它傳達出對人際關系的樂觀態度,認為與熟人見面是一種輕松愉悅的體驗。它強調了人與人之間相互友好的互動與和睦相處的重要性,鼓勵人們以輕松的態度來面對社交場合,并相信只需簡單的招呼就能維持良好的人際關系。這樣的傳播有助于加深國際社會對合肥這座友好、包容、開放的城市的理解。
(二)采用與受眾“同一”的修辭勸說模式
西方修辭學認為修辭活動應該以受眾的需要和接受能力為出發點和重心,即在進行修辭活動時需要考慮受眾的語言背景、文化背景、情感體驗、認知水平等因素,以便更好地達到溝通和交流的目的。修辭涉及修辭者、讀者以及修辭話語這三個核心問題。讀者是始終貫穿傳統修辭學及現代修辭哲學的主線之一。[8]在修辭學中,受眾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只有考慮到受眾的需求和接受能力,才能讓修辭活動更加有效地達到預期的效果。同樣地,對于合肥方言的外宣翻譯,翻譯者需要以外國受眾為中心,并且要考慮到外國受眾與中國受眾在語言、文化、習俗、思維習慣、認知特點等方面的差異。在翻譯合肥方言時,翻譯者應該采取一些策略,例如使用解釋性翻譯和釋譯變通的策略。此外,翻譯者應該努力避免采用“字面翻譯”或者“生硬翻譯”,這種翻譯方式容易受限于語言和文化等因素導致歧義和誤解。外宣翻譯的最終目的是讓翻譯結果盡可能地適應外國受眾的語言和文化習慣,與受眾“同一”,實現外宣翻譯的傳播效果。例如:
[3] 鬼不生蛋的地方
譯文:
an isolated place
原文:
王忠鳳:“先后回到了過去,‘窮得鬼不生蛋的深山。”③
譯文:
Wang Zhongfeng said: “One after the other, they went back to the past, the remote
mountain which is ‘so poor that even ghosts cannot live in.”
這句合肥方言,用夸張手法表達一個地方特別荒僻,甚至連鬼都不愿意到那里生蛋。在翻譯這個短語的過程中,譯者需要考慮到不同國家和地區受眾(讀者)之間因語言、文化、習俗等方面的差異,以及受眾是否能夠理解和接受這種夸張的表述方式。對此句進行翻譯是,不宜采用直譯的方式,需使用符合英語國家表達習慣的詞語,例如an isolated place,a remote place或者a desolate place。使用意譯的翻譯方式,譯文易于被受眾理解和接受,更具有說服力,同時也能夠建立起譯者與受眾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共鳴,理解上實現譯者與受眾的“同一”,因而遵循了伯克新修辭學主張的“勸說”效果。例如:
[4] 光朗頭朝刺科里鉆
譯文:
Youve made your bed and you must lie on it.
原文:
“那伢子有工不做,卻去做賊。這一關起來就是‘光朗頭朝刺科里鉆了!”④
譯文:
“The guy had a job but he descended to be a thief instend of going to work. He is imprisoned this time, and ‘It is nobodys fault but his own.”
這句合肥方言的意思是,一個禿頭的人非要鉆進一個荊棘堆中,形容一個人自找麻煩、自作自受。翻譯這個短語時,需要考慮到不同國家和地區受眾的語言、文化、風俗等方面的差異。同時必須確保受眾能夠理解、接受這種表達方式。因此,最好的翻譯方法不是逐字翻譯,而是使用符合英語表達習慣的詞語。例如,可以使用“自食其果”的英語諺語:“Youve made your bed and you must lie on it”,或“It is nobodys fault but his own.”等固定表達。采用這種易為受眾理解、接受的翻譯方式,可以使翻譯內容更令人信服,同時也能夠進一步加強譯者和受眾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協調,達到“同一”的效果。這也是外宣翻譯必須遵守的基本原則之一。
(三)依據修辭語境尋找原文和譯文的最佳契合
任何修辭行為都是發生在某個特定的情境下。勞埃德·比徹爾,著名的修辭學家和修辭情景論的創始者認為,修辭是一種應對修辭情景的行為。 修辭行為是在特定的修辭情景中被“呼喚”出來的。“修辭情境”的因素會限制和影響修辭行為的效果,因此,“對修辭行為的分析和評論必須與其對應的修辭情景聯系在一起;如果沒有修辭情境,就沒有修辭行為。”我國現代修辭學的創始人陳望道先生認為,修辭的首要意義是要適應題旨情境。[9]成功的修辭行為應是修辭者根據場景和受眾的特點確認主要缺失以決定相應的修辭意圖,并選擇成熟的時機投入相當的心力以補足所需的缺失。[10]在語言學領域,修辭情境的對應術語是“語境”,因此,作為現代修辭行為的合肥方言外宣翻譯,必須與外宣的特定語境相符,特別是包括外宣翻譯動機、外宣翻譯目的等在內的“文外語境”,以適應其修辭情景。例如:
[5] 橫草不拿,豎草不拈。
譯文:
being a couch potato
原文:
“他每日睡到日中才起來,橫草不拿,豎草不拈,每日要吃八分銀子藥。”⑤
譯文:
“He sleeps until noon every day, being a couch potato, and takes an amount of medicine worth eight-cent silver daily.”
這句合肥方言的意思是,那個人在家什么事兒都不做,懶惰得很,連地板上的草(喻指垃圾)也不愿意拿起來丟掉。“橫草不拿,豎草不拈”是合肥本地方言對懶惰之人的生動形象的描寫。英語里有一個詞對應的短語:a couch potato,指一個在家里什么事兒都不做,整天躺在沙發上看電視的人。這兩句話在價值觀上有一個契合點,那就是都認為懶惰是一種不應該被贊揚的行為。無論是在家里“橫草不拿,豎草不拈”,還是說一個人是“couch potato”,都是形容一個人過于懶散,沒有努力工作和充實自己的生活。原文是合肥話里非正式的表達,而譯文也是英語里非正式的表達。這樣的譯法將合肥方言生動形象的語言特點與英語語言表達習慣結合起來,兩者語境相似,語義相近。此例翻譯依據修辭語境,找到了原文和譯文的最佳契合點,適應了修辭情景。這樣翻譯的外宣動機在于宣傳合肥人民認可的價值觀,即勞動創造價值,勤奮、努力工作和積極生活是成功和幸福的關鍵,只有通過努力工作和自我增值,才能獲得成功和幸福。
五、結語
合肥方言的外宣翻譯是一種特殊的翻譯形式,不僅涉及語言的轉換,還涉及跨越語言和文化的現代修辭行為。翻譯人員需要努力開闊自己的視野,不僅要從翻譯的角度來研究合肥方言的翻譯,還要從伯克修辭學的角度來審視和研究在合肥方言翻譯中出現的修辭動機、修辭受眾和修辭情境等因素,以使外宣翻譯能夠達到更好的修辭效果。銘記修辭目標以堅守外宣翻譯使命,采用與受眾“同一”的修辭勸說模式,依據修辭語境尋找原文和譯文的最佳契合,是本文從伯克修辭學視角下對合肥方言外宣翻譯策略研究的總結和發現。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合肥方言的外宣翻譯研究還有待進一步的深入和完善。
注釋:
①《合肥方言》第146頁:1990.3.1《逍遙·姊妹易“嫁”,一個現代悲劇故事》題頭
②《合肥方言》第69頁:1994.7.25《合晚·怕打招呼》
③《合肥方言》第53頁:1989.10.17《新民·十二姑娘出嫁攜夫回山村》
④《合肥方言》第52頁
⑤《合肥方言》第60頁: 《儒林》26回
參考文獻:
[1]鄧志勇.試論伯克修辭學與亞里士多德修辭學在運作機理上的關聯[J].外國語文,2011,27(04): 45-50.
[2]鞠玉梅.從伯克對修辭與人的定義看中西修辭學思想的差異[J].外語學刊,2011(05): 111-115.
[3]Burke, K. A Rhetoric of Motive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
[4]鞠玉梅.肯尼斯·伯克新修辭學理論述評:關于修辭的定義[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 2005(01): 72-76.
[5]鄧志勇.伯克修辭學之戲劇主義的后現代思想及其重要啟示[J].上海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34(02): 112-118+168.
[6]陳小慰.對外翻譯傳播:修辭語境視角的案例分析[J].上海翻譯,2023(06): 23-28.
[7]鞠玉梅.論修辭話語的解構性[J].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2002(03): 61-64.
[8]陳昌奇,鄧志勇. 西方修辭哲學核心問題與思考[J].哈爾濱學院學報,2009,30(12): 25-28.
[9]陳望道.修辭學發凡[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10]袁影,蔣嚴.論“修辭情境”的基本要素及核心成分:兼評比徹爾等“修辭情境”觀[J].修辭學習,2009(04): 1-8.
責任編輯:周瑜
On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Translation of Hefei Dialect from Burke's Rhetorical Perspective: Taking Hefei Dialect as an Example
YU Yingzhi
(School of English Language, Anhu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efei 231200, Anhui,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role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that publicizing and translating dialect plays in Chin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s a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cultural rhetorical action, publicizing and translating dialect is challen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enneth Burke's rhetoric, we study publicizing and translating Hefei dialect, and put forward such strategies as adhering to rhetorical goals and missions, employing rhetorical persuasive model that is aligned with the audience, and seeking the best fit between the original text and translated text based on the rhetorical context. Our study will contribute to th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of Hefei dialect culture.
Keywords: Kenneth Burke's rhetoric; Hefei dialect; 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trans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