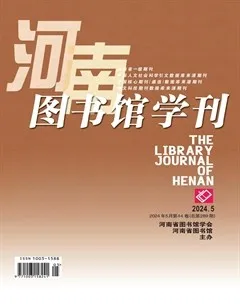首次銷售原則適用限制與圖書館網絡信息服務法律制度的創新
孫麗敏
摘 要:首次銷售原則適用對圖書館業務和服務工作發展的意義重大。但是,基于法理障礙和立法的不完善,首次銷售原則在網絡環境中的適用遇到了較大阻力,從而給圖書館網絡信息服務造成了不利影響。為此,我國應針對性地創新法律制度,措施包括賦予受控數字借閱法律地位,并對該項服務涉及的技術措施、資源對象和服務期限等做出明確規定。
關鍵詞:首次銷售原則;圖書館;版權;受控數字借閱
中圖分類號:G25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88(2024)05-0108-03
“首次銷售原則”(The First Sale Doctrine)創立于印刷技術時代,用于規范作品傳播與使用中的物權和版權的關系問題。該原則的基本含義是:合法制作的作品原件及復制件經權利人(作者、出版商或其他版權主體)授權進入市場后,對于該原件、復制件后續的銷售、收藏、轉讓等流轉行為,無須再征得權利人的同意[1]。首次銷售原則為圖書館外借、閱覽、捐贈、剔除等服務和業務活動提供了重要的法理支撐和制度保證。因此,國際圖書館聯合會(IFLA)曾經主張在全球范圍內施行首次銷售原則[2]。然而,在網絡環境中,圖書館服務的權利規制類型和使用圖書的技術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動搖了適用首次銷售原則的法理基礎,特別是在立法滯后的情況下,致使圖書館無法繼續在首次銷售原則的庇佑下開展數字信息服務。相比較而言,在各種解決方案中,具有治本價值的就是創新版權制度。
1 首次銷售原則適用對圖書館工作的正向激勵
1.1 有助于滿足讀者服務需求
任何權利均有邊界,對權利的行使也應在此范圍之內,否則即構成對權利的濫用[3]。圖書館滿足讀者需求的基本條件是使讀者有更多接觸與獲取作品的機會。但是,如果圖書館的每一次外借、閱覽服務都要事先征得權利人許可、甚至是支付報酬的話,那么這種服務必然是低效率的,或是無法操作的。圖書館擔心,假若沒有首次銷售原則,按照“授權—付費”模式開展服務,讀者獲取作品的難度將會加大[4]:一方面將增加讀者服務的經費成本和時間成本,出現因經濟問題導致的圖書館服務的社會分層效應,即便許多服務的資金由政府或基金會等組織承擔;另一方面增加了接觸和利用作品的中間環節,造成作品傳播渠道不暢。首次銷售原則正是通過權利分配和義務確立保證圖書館對合法收藏作品的處置權,防止版權濫用,以便更好地開展服務工作。
1.2 有助于平衡版權利益關系
法律的規范目的是在個人原則與社會原則之間形成一種平衡,使個人的勞動,無論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盡可能地對他人有所助益,從而也間接地對自己有益。版權法從肇始之初,就秉承著維護權利人利益、促進文化傳播的雙重目標立法原則。然而,隨著科技進步與社會發展,版權成果的應用途徑和表現形式逐漸增多,對私益采取強保護的立法邏輯使權利內容的擴張走上了非理性之路[5]。這種版權擴張的趨勢扭曲了圖書館領域的利益平衡機制,因而有必要引入新的制度機制予以矯正。首次銷售原則作為一種版權限制政策,起到的正是這種功能,該原則表明版權法并不賦予權利人全面和絕對的對版權的控制權、壟斷權,而是只能在特定情形下有條件地行使權利。因此,首次銷售原則體現的核心價值就是平衡利益關系,協調社會和權利人之間基于權利公配及行使產生的矛盾張力。
1.3 有助于提高館藏資源價值
首次銷售原則適用對于提升圖書館資源價值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適用首次銷售原則有利于確認圖書館對數字資源財產的主體地位,激勵圖書館購買或通過其他途徑豐富館藏。如果在網絡環境中,通過“授權—付費”模式只是得到了資源的使用權,而非模擬技術條件下的所有權,圖書館館藏建設的積極性必會受到影響。二是適用首次銷售原則可以促進圖書“二手市場”的建立和市場機制的完善,使圖書館從這些市場中獲得許多斷版、絕版和其他珍惜類型的圖書。三是圖書館合法收藏有許多紙質圖書、電子圖書、學位論文、刊報文等文獻資源,如果按照現行法律法規對其電子副本的使用只能囿于圖書館物理館舍及局域網之內的話,其價值的發揮必然不盡如人意。正因如此,美國圖書館界強烈要求立法創設“數字首次銷售原則”(Digital First Sale Doctrine),以便消除首次銷售原則適用給圖書館工作造成的羈絆。
2 圖書館開展網絡信息服務不適用首次銷售原則的法理分析
2.1 載體的非有形性
無論是美國版權法,還是歐盟《信息社會版權指令》,抑或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都規定:發行權只適用于規制固定在有形載體之上的作品原件或復制件的流轉。司法判例更是明確:只有當某一作品原件或復制件的所有權人處置了對該原件或復制件的有形占有,才能適用首次銷售原則[6]。毫無疑問,圖書館在線下傳播作品的行為符合“載體有形性”條件,可以適用首次銷售原則,因為無論是紙質圖書,還是以膠片、磁盤、光盤等媒介存在的圖書形態,都具有“有形性”。然而,在網絡環境中,圖書館傳遞給讀者的電子書的載體卻是無形的,這就給適用首次銷售原則造成了障礙。有學者認為,對“有形”的解釋不能局限于傳統認識當中的三維“實體”,應包括由數字技術生成,被固定在網絡空間里,并從時間維度上看可以被穩定地提供使用的形式[7]。但是,目前這種觀點并未被法律認可。
2.2 所有權的非轉移性
適用首次銷售原則要求“特定”的復制件是經權利人同意而被復制,并且經過權利人許可,該復制件的所有權即財產權發生了轉移[8]。圖書館開展網絡服務必然要向讀者提供復制件,盡管這種復制件是無形的,但與在印刷技術條件下圖書館向讀者外借圖書不同,這時的復制件不是脫離了圖書館的服務器被轉移至讀者手中,而是在讀者的計算機系統中形成了新的復制件,圖書館的系統中仍然存在該復制件,即權利人制作或許可制作的“特定復制件”并未發生轉移。這種情況同樣存在于權利人向圖書館通過網絡提供作品的過程中,意味著圖書館只是獲得了對作品的“許可使用權”,不是擁有了對作品的所有權。按照美國版權法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等法律的規定,如果在傳播作品的過程中沒有發生所有權的變更,那么不屬于適用首次銷售原則的發行權范疇,應由信息網絡傳播權予以規范。
2.3 涉及權利的多樣性
版權是一種“權利束”,這種權利束中包含多種權利,包括發行權、復制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翻譯權等。但是,首次銷售原則只針對發行權而建立,用于限制權利人對發行權的行使。如果在限制發行權的同時,使權利束中的其他相關權利同樣受到了限制,則很難適用首次銷售原則。美國在《國家信息基礎設施(白皮書)》中指出,網絡傳播具有復制與發行并存的特征,發行是被傳播的復制,限制發行權就必然會限制復制權,具有不合理性[9]。在印刷技術條件下,圖書館向讀者傳播作品的原件或合法復制件由于發生了有形載體的轉移,圖書館無須自行再制作新的復制件,不涉及發行權之外的其他權利,尤其不涉及復制權問題。但是,圖書館通過網絡向讀者提供作品,必然以“復制行為”作為服務活動的技術起點,就無法回避對復制權的使用問題。在這種情形下,如果適用首次銷售原則,那么不僅使發行權受到了限制,也使復制權受到了限制,從而擴大了版權限制的范圍,使版權受到多重克減,不符合版權法的利益平衡精神。
3 網絡環境中改良適用首次銷售原則的立法創新
3.1 借閱比率層面
2016年,歐洲法院在“VOBv.Stichting Leenrecht”案的審理中認為,電子借閱“一使用一副本”具有合理性,即圖書館的電子書由一位借閱者下載之后,在借閱期間內其他借閱者無法獲得該電子書[10]。與此理念近似的實踐范例就是近年來在國際上興起的“受控數字借閱”(Controlled Digital Lending,CDL),該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從發行權的“特定數量的合法復制件”的內涵出發,設定“擁有與借出比率”,控制并發用戶數,從而實現與傳統借閱模式相同的法律效果。所謂“擁有與借出比率”,是指紙質副本數量和電子副本數量之和的恒定性,如:假若一家圖書館收藏某種圖書的紙質復本是5個,那么在任何時候外借的紙質本和電子本之和不得超過5個。打個比方,如果該圖書館已經外借了一個該書的電子副本,那么最多能再出借4個紙質本,而另一個紙質本不得外借,以此類推。2021年,國際圖書館聯合會(IFLA)在《關于受控數字借閱的聲明》中表達了對該新型服務模式的支持,并希望各國立法予以認可。
3.2 技術控制層面
歐洲法院在判決“甲骨文公司訴德國用軟公司案”中認為,在轉售電子書的場合,轉售人在已將其持有的電子書復制件轉售之后,應使其已下載到存儲介質中的該復制件刪除或不能被再次利用,這樣才會發生所有權轉移的效果,不會增加一件作品的平行使用者的數量。美國圖書館界認為,對首次銷售原則不應作嚴格的形式主義的解釋,主張只要在將作品通過網絡傳播給讀者后刪除了原件,首次銷售原則就可以適用[11]。我國有學者指出,通過技術手段控制復制件數量的“絕對增加”,能夠大大提高首次銷售原則在網絡環境下適用的合理性。目前,隨著受控數字借閱服務的發展,“轉發并刪除技術”(forward and delete technology)趨于成熟,可以為該模式的合法性提供技術支撐。
3.3 資源對象層面
為了防止濫用受控數字借閱服務,筆者建議應對適用的作品對象進行限定:一是不適用于熱播影視劇作品、計算機軟件和暢銷文學作品,只適用于經過“商業供應檢驗法”評判,在市場上無法購買或只能以明顯高的價格購買的作品,特別適用于絕版、斷版作品。二是只適用于沒有電子版的紙質本作品,已經在市場上有電子版的作品不在其列。三是只適用于有合法來源的作品,不包括有非法來源而制作復制件的情形。此外,對電子副本使用的期限也應由法律明確規定,一方面,法律規定出版一定年代內的作品不得適用首次銷售原則,以保護權利人的市場利益;另一方面,讀者在有效的閱讀期限內,當“擁有與借出比率”達到最高限度時,其他讀者無法外借和閱讀相同的電子版,也不可閱讀同種書的紙質本,只有等待其他讀者的閱讀期滿,而技術措施會盡可能防止“超期閱讀”或“排隊加塞”以及未經授權拷貝作品等問題的發生。
參考文獻:
[1] 唐艷.數字化作品與首次銷售原則[J].知識產權,2012(1):46-52.
[2] 徐軒,孫益武.論國際圖聯關于圖書館版權限制與例外的立場及其啟示[J].圖書館論壇,2014(12):3-6.
[3] 馬強,王燕.論知識產權窮竭原則的正當性基礎[J].知識產權,2011(1):8-9.
[4] 蔡曉東.電子書借閱與首次銷售原則[J].圖書館,2015(6):82-85.
[5] 李艾真.公共圖書館的受控數字借閱模式[J].圖書館論壇,2022(7):113-121.
[6] 秦珂.首次銷售原則在我國圖書館傳播與利用數字作品中的延伸性適用探討[J].圖書情報工作,2018(16):15-21.
[7] 黃玉燁,何蓉.數字環境下首次銷售原則的適用困境與出路[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6):189-202.
[8] 陶乾.電子書轉售的合法性分析[J].法學雜志,2015(7):80-86.
[9] 王駿.版權窮竭原則適用范圍探析[J].中國出版,2015(10):7274.
[10] 趙力,王澤厚.再議公共圖書館電子借閱新進展[J].圖書館論壇,2017(3):93-100.
[11] 王遷.論網絡環境中的“首次銷售原則”[J].法學雜志,2006(3):11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