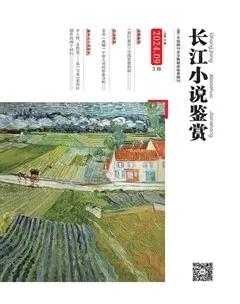結構主義理論視域下的《遠大前程》敘事藝術
俞若彤
[摘? 要] 《遠大前程》是英國小說家狄更斯創作晚期的知名作品,展現了維多利亞時代生動的社會畫卷。小說文本容量大、敘述手法多樣,無論是人物、情節還是主題,都有意蘊深長的解讀空間,具有極高的敘事學研究價值。本文采取普羅普敘事功能理論,探究小說“行動元”彼此之間交織的情節序列,并結合文本中心論,分析其具體的創作手法,以“二元對立”視角分析小說主題的哲學內涵,在結構主義理論視域下更深入地剖析《遠大前程》的敘事藝術。
【關鍵詞】 狄更斯? 結構主義? 敘事學? 《遠大前程》
[中圖分類號] I106[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9-0015-04
狄更斯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杰出的小說家,他一生著作頗豐,享有“英國小說之父”的美譽。1844年至1861年是狄更斯小說創作的鼎盛時期,其作品主要包括《雙城記》《荒涼山莊》《艱難時世》《小杜麗》《遠大前程》等,這一時期的作品描繪了英國極為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其筆下人物栩栩如生,藝術風格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遠大前程》是狄更斯晚期重要的作品之一,被評論家約翰·歐文評價為“英國語言中最杰出、結構最為完美的小說”。
《遠大前程》講述了一個孤兒的“遠大前程”,從理想幻滅再到重拾自我的過程,小說以第一人稱講述了“我”,孤兒匹普,由潑辣的姐姐和老實憨厚的姐夫撫養長大,姐姐、姐夫、匹普過著簡單寧靜的鄉村生活。但因為一次偶然,匹普受雇于郝薇香,郝薇香是一個貴族,有一個美麗而端莊的養女艾斯黛拉,匹普深深愛上了艾斯黛拉,而艾斯黛拉的刻薄與嘲笑深深刺痛了匹普,使匹普開始重新認識自己。他不再以成為一個鐵匠為驕傲,而是幻想能夠成為“上等人”,成為一名與艾斯黛拉能夠發展愛情的“紳士”。就在此時,“幸運”降臨了,一名匿名資助者資助了他,讓他接受上等教育,激動的匹普還以為是郝薇香小姐資助了他,當他得知自己的資助人是自己曾經救過的逃犯,轉瞬間,他所有美好的“遠大前程”都成了幻影:“原來郝薇香小姐對我的厚意,不過是我自己的一場春夢;她并沒把艾斯黛拉許給我。”
整部小說的情節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記述了匹普在鄉間質樸的童年生活,第二部分主要描寫了匹普在倫敦接受教育的經歷,最后一部分記敘了匹普保護潛逃回國的流放犯馬戈維奇的經歷。在一系列的變故中,匹普最終回歸人性之美,深切地體會到友情和親情的可貴。
一、富有魅力的故事形態:《遠大前程》敘事形態之探索
結構主義敘事學將語言學上的功能單位應用在敘事文本的創作與分析上,著力探索敘事作品大的類型上的深層結構,如神話故事、民間傳說,這點在著名結構主義學家普羅普的《民間故事形態學》中有詳細的理論方法。他推崇統一的術語系統和研究方法,所以在參考德國形態學的基礎上,使得敘事學也擁有了一套類似于數理科學和生物科學的嚴整的分類法。普羅普認為,民間神奇故事的功能項是有限的,在千變萬化的故事情節背后,其實有一套固定的“骨骼”,可概括為31個敘事功能。在這樣的敘事模式中存在著七種人物類型,即:英雄或者受害人、反面角色、協助者、救援者、公主和她的父親、送信人、假英雄。
角色的定位都是圍繞其功能展開的,所以,這里的“角色”并不同于傳統定義中的人物,他們并不以各自“性格”為區分標準,而是以自身起到的功能為區分,這種區分能幫助我們從新的視角理清故事的脈絡,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傳承了亞里士多德的“情節”中心論的,這也是結構主義者的核心觀點。他們認為情節才是一切,而情節又是由“行動”構成,所以,在結構主義視域下,角色便成了行動元,也就是行動的發出者,人物本身的性格反而不成為首要考慮的因素。
讓我們為《遠大前程》中的幾個主要角色定位:顯然,匹普是英雄,反面角色是郝薇香小姐,她選擇匹普成為自己報復的對象;協助者是逃犯馬戈維奇,是他給了匹普資助,幫助他成為一名真正的紳士;姐夫喬則是救援者,他讓匹普認識到了什么才是最珍貴的,虛幻的紙醉金迷的“遠大前程”遠不及真實的溫情溫暖人心;公主是艾斯黛拉,匹普深深地愛著她;送信人由律師賈格斯先生充當,最初是他為匹普帶來繼承一大筆財產的美好幻想,后來也是他為匹普帶來重要消息,揭開“資助人”的神秘面紗,打破了匹普“遠大前程”的幻夢;假英雄是倫敦里有權有勢的花心浪蕩子,與匹普爭奪“公主”艾斯黛拉,并于艾斯黛拉結婚。
同時,一個文本往往存在著多個故事。在這里,我們不談是否是因為狄更斯,即作者本人豐富的人生經驗和明確的創作目的,才構思出《遠大前程》這部展現了典型環境(英國1812年耶誕節前夕至1840年冬天)中的典型人物的佳作,僅就文本而言,《遠大前程》有多條故事線,幾個主要人物在《遠大前程》中都有自己的故事,比如被拋棄后陷入幾十年復仇計劃的郝薇香小姐、被郝薇香小姐收養調教成一柄報復男人利器的艾斯黛拉、因為自己妻子被調戲后和仇人發生爭執鋃鐺入獄的馬戈維奇……
普羅普就文本層次提出了術語“回合”,將一個文本中存在的故事數量、一個故事中存在的層次數量,都用“回合”作為其形態學意義上的計量單位。就前文論述,我們已經得知《遠大前程》中多個“角色”蘊含著多回合故事。這種外部層次間的回合是根據人物本身極具社會意義內涵的故事背景展開的,或許在文本中并沒有單獨展開,沒有和主角匹普發生直接聯系,但都契合亞里士多德所提出的“起始、中間、結尾”結構,是一條完整的故事線。但是,簡單認定為“多線并行”又是不恰當的,因為這些故事或階段性獨行,或階段性交織成網。在普羅普的故事形態視域下,我們根據其總結的六種回合方式為《遠大前程》定義文本結構,為《遠大前程》這座輝煌的文學宮殿復原一幅基礎的設計圖。
就故事展開而言,以匹普,即“我”為基點,將各個人物聯系起來,匹普和姐夫喬構成一個“回合”。郝薇香小姐,因被未婚夫背叛拋棄,陷入對男人深深的仇恨中,她選擇了艾斯黛拉作為向男人報復的工具,將艾斯黛拉教養得傲慢、冷酷,在第一次與匹普的見面中,艾斯黛拉便深深地羞辱了匹普,使匹普對自己現在的生活生出羞恥感。兩名“孤星”(《遠大前程》又譯名為《孤星血淚》),艾斯黛拉和匹普,因郝薇香小姐的“血淚”復仇糾纏在一起,三人又構成一條故事線,而匹普又因為自己好心救助的行為和馬戈維奇有了交集……
這是圍繞著匹普的幾條主要線索,我們在此基礎上理清《遠大前程》的建造結構。若要把整個故事概括為一個敘事句子,則可以是:匹普追逐遠大前程。匹普和其他六個功能角色的交集也都是服務于這個敘事句的,這是最基礎的建筑骨骼。喬的故事線幫助匹普完成對“遠大前程”的真正明悟,馬戈維奇這條故事線又和郝薇香小姐的復仇糾纏,因為匹普的誤會而構成一種追逐遠大前程過程中的明暗線,神秘資助人的“身份”揭開之際,才是馬戈維奇這條暗線揭開之時。所以將《遠大前程》比作建筑的話,應是一座高高聳立的城堡,兩個塔頂并立于同一方向,其中一個略高將另一個遮擋,使另一個若隱若現,其他小型的附屬建筑則林立于四周,遠觀則構成一座整體的建筑。
二、意蘊豐富的文學本體:《遠大前程》文本魅力之解析
通過前文中功能單元和故事層次的闡釋,我們已經可以看出《遠大前程》中無限生成的闡釋空間,因為完整的故事鏈條使得角色無論從哪個方面展開,都足以構成一個跌宕起伏的故事。亞里士多德強調“情節”,認為“人物”是次要的,“情節”才是故事的首要因素。關于這個問題,他曾在《詩學》中說道:“情節是悲劇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悲劇中的兩個最能打動人心的成分是屬于情節的部分,即突轉和發現。”所以,優秀的情節,已經為《遠大前程》做了有力的佐證。這是一部成功的敘事作品,其中情節所包含的突轉和發現每一個都那么吸引讀者注意又合乎情理:匹普突遇逃犯、匹普機緣巧合進入郝薇香小姐宅邸中、匹普受到神秘人的資助、匹普發現資助人的身份、匹普發現艾斯黛拉的身世、匹普發現自己姐姐殘疾的原因……
讓我們看一下文本中由“送信人”赫伯爾特揭開的郝薇香小姐的身世謎團:
“郝薇香小姐的爸爸很有錢,很高傲。他的女兒也是這樣。”
“……也許是跑馬場上遇到的,也許是跳舞會上相識的,你愛說哪兒都行——反正他來向郝薇香小姐大獻殷勤。”
“這個男人追求郝薇香小姐追得很緊,口口聲聲說是忠誠不二地愛她。我相信郝薇香小姐當時大概還沒有對誰用過多少情,可是她這情不用則已,一用便如決堤之水,不可收拾……那人處心積慮地施展手法,騙取了她的感情,把大量的錢財弄到了手。”
“結婚的日子定了,結婚禮服置辦齊全了,蜜月旅行籌劃好了,吃喜酒的請柬發出去了。可是臨到結婚那一天,新郎不到,卻寫了一封信來——”
郝薇香小姐身世的懸念從敘事文本的起始就開始了,不論是她怪異的言行還是裝扮,只需數句話揭開,就給讀者有了新的感受,也為她的“反派”角色提供了合理的行動成因。當然,在故事結尾,郝薇香小姐并沒有因為報復成功而感到喜悅和暢快,當她看著因為分離和背叛陷入痛苦的匹普和艾斯黛拉,終于發現,自己想要的并不是有人和她一樣的痛苦,所以她選擇用一場大火結束自己經年許久的仇恨。這種悲劇效果讓讀者也深深動容。
當然,在探索了結構主義為我們提供的故事文本“骨骼”層面,即情節鏈條層次上的分析后,我們也可以從文本本體出發,分析其“肌理”,這就涉及具體的創作技巧和語言加工手段了。1941年,美國學者蘭色姆出版了名為《新批評》的批評專著,梳理討論了20世紀20年代以來瑞恰茲、艾略特為代表的幾位“新批評家”的批評理論。此后,他在自己的論文集《世界的形體》一書中反復闡發了 “本體論”批評主張,為“文學作品”確定本體地位,拒斥文學以外的因素進入文學批評。
與傳統本體論不同,蘭色姆的本體論是將藝術的存在規定為世界的本體。他的本體論關注的是以異質性、生成性、偶然性為特征的本體存在。他在本體論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肌理說”,認為“一首詩是一種具有局部肌質的邏輯結構”,這種比喻得益于普羅普等人開創的跨學科傳統,尤其是普羅普所借鑒的生態學分類法,所以我們能從蘭色姆的理論中看到生物學的影子也就不奇怪了。前文之“情節”為邏輯結構,類似于骨骼,這是最基本的部分,若沒有則故事無支撐,肌質則是文辭手法。此后韋勒克和沃倫繼承他的本體論,在《文學理論》中言明了文學本體應研究哪些部分,這為我們分析《遠大前程》的“肌理”提供了一些方向。
我們在此重點分析《遠大前程》“意義單元以及作品形式上的語言結構、風格與文體規則”。《遠大前程》無疑是一部語言藝術極高的小說,作家在創作這部小說時,已經有了豐富的創作經驗,歲月的沉淀為狄更斯提供了足以信手拈來的創作素材,所以,這部小說無愧于“英國語言中最杰出、結構最為完美的小說”這一評價,為我們展現了作品形式中語言結構、風格以及文體上諸多閃光之處。文本中含有大量生動的比喻、夸張、細節描寫,在刻畫人物上,作者最擅長通過語言和細微的動作,鞭辟入里地展現人物性格,側面揭示角色的關系和處境,尤其是匹普和姐姐、姐夫的相處,寥寥數語生動而富有畫面感。
三、二元對立的哲學構思:《遠大前程》敘事主題之哲學
王蕾在《遠大前程》的序文中寫道:“《遠大前程》的故事始終貫穿著愛的主題:匹普對艾斯黛拉始終不渝的愛,匹普與赫伯爾特的兄弟情誼之愛,馬戈維奇對匹普畸形卻讓人起惻隱之心的愛都得到了細致的鋪敘;而最令我們感動的仍是喬那無私淳樸的愛……因虛榮一度迷失最終幡然醒悟的成長道路上,無處不見喬對匹普最誠摯的關愛。”顯然,文本中充滿了讓人感動的溫情瞬間。但是,在匹普個人的成長歷程中,這種愛是他最后幡然悟后才重新獲得的珍寶,在此之前,他迷失過、痛苦過。文本既勾畫了一名孤兒對“遠大前程”的追求之旅,同時也是一場心與靈的凈化之旅,在理想與現實的碰撞中,作家為我們揭示了最深刻的愛之哲理。
結構主義理論旨在剝去文學作品紛繁冗雜的外衣,從而揭示作品的深層意蘊。其中,二元對立是結構主義最重要的基礎與主線。通過找尋抽取存在對立關系的特征,深入剖析這些成對的概念,加深對其中每個觀念的理解。顯然,這種相互支撐、互為印證的二元對立關系,使得文學作品不斷臻于立體飽滿。
《遠大前程》的主題正是一對典型的理想與現實之對立。這種對立是階段性的展示,通過劇情的峰巒迭起,不停揭示理想/現實這對文本故事中所體現得最基本的二元對立中所囊括的多個層次和部分。首先,整個故事的主線是由匹普追求遠大前程展開的,在這場追逐之旅中,讀者會隨著匹普一起發現,遠大前程不過是一場虛幻的泡影——他的資助者是一名叫馬戈維奇的流放犯,他深愛的艾斯黛拉就是這個罪犯和一個女殺人犯所生,他心目中的庇護人郝薇香小姐是一個冷酷又可悲的復仇者,而在這個過程中,自己僅僅是個被報復的替身。也就是說,匹普理想的一切:理想中的“英雄自我”、理想中的“幫助者”、理想中的“愛情”……都盡數化為泡影。但在不同階段,又有另外的展示,比如在第一階段的鄉村生活中,理想與現實是階段性統一的:喬愛護他、體貼他,匹普也樂于跟隨喬學習,以成為一名鐵匠為理想;但緊接著,在遇到自己的摯愛以后,他的理想便與現實發生了對撞,代表“遠大前程”的金錢,讓他從一個跟姐夫學習打鐵、寄人籬下、整日被親戚冷嘲熱諷的窮學徒變成了闊少爺,他看似擺脫了現實的困境,人生得意,縱情歡樂,但是這些又是那么虛幻,既沒有為他贏得最初所渴望的佳人和愛情,也沒有填補他內心的那份自卑和空虛,反而使他染上了上流社會的惡習,在姐夫懷揣著熾熱的關懷與親情來倫敦看望他時,匹普覺得丟臉而不愿搭話,喬說:“你和我在倫敦坐不到一塊了……”
故事的結尾,恩人被捕、艾斯黛拉小姐另嫁他人,匹普的遠大前程徹底破滅。歷經千帆,匹普不僅沒有成為一個真正的紳士,反而背上了巨額的債務,最后幫助他解決這一切的不是他神秘的“資助人”,更不是郝薇香小姐,而是喬。最初的夢想以及最后夢想幻滅的種種經歷,讓匹普清醒、成長,使他重新認識到真正的遠大前程不在于財富和地位。他和摯友赫伯爾特夫婦一起,“日子過得很快活”,他終于鼓起勇氣,見到了自己一生的摯友、姐夫喬還有他的新妻子,“我哪怕加一千倍還你們的錢,還是不能報答你們的情分于萬一。”黃昏時分,他來到舊日的莊屋,與他一生的摯愛重逢,兩人重歸于好,“我們再也不會分離了” ,在此刻他終于明悟,愛才是真正的珍貴之物。
參考文獻
[1] 羅經國.狄更斯評論集[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2] 查爾斯·狄更斯.遠大前程[M].王科一,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
[3] 艾曉玲.《遠大前程》的敘事特征[J]. 四川大學學報,2000(1).
[4] 楊天地.狄更斯《遠大前程》主題思想評析[J].語文建設,2014(35).
[5] 任文林.狄更斯小說的敘事風格簡評[J].語文建設,2016(23).
(特約編輯 楊?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