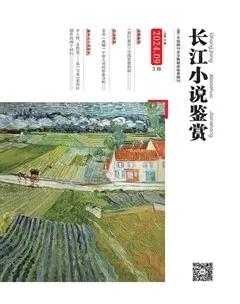阿Q的現代轉生:論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阿Q正傳》仿作
李龍琪
[摘? 要]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興起了一股《阿Q正傳》仿寫潮流。仿作者們一方面為阿Q設置了學生、富豪等摩登身份,讓他們從未莊來到都市,但其思想與行為卻與此前的未莊阿Q一脈相承;另一方面,注入了濃厚的時代特征,刻畫了戰時社會環境中各式各樣的阿Q變種。對《阿Q正傳》的仿寫得以在彼時蔚然成風,阿Q典型本身具有的高度的普遍性是不容忽視的前提。同時,戰時社會塑造民族主義的身份認同,需要借鑒阿Q這一批判性的文化資源。
【關鍵詞】 《阿Q正傳》? 仿作?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 魯迅
[中圖分類號] I106[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9-0039-04
早在1928年,錢杏邨就宣判了“阿Q時代”的結束。但是,在接下來的二十余年中,《阿Q正傳》的仿作不斷涌現,以創作的形式質疑了錢杏邨的判斷。在這些仿作中,阿Q轉生為小Q、亞Q、阿O等種種形象。比起在辛亥年間就被槍斃了的阿Q,他們所處的時代已經日新月異。但阿Q精神沒有隨辛亥革命遠去,而是融入了他們的血液和基因。這些新式阿Q同樣值得關注。但是,目前學界關于《阿Q正傳》仿作的相關研究尚不充分,僅對個別仿作進行了細讀,并未從宏觀的角度對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阿Q正傳》仿作進行整體觀照,也未交代為何《阿Q正傳》的仿作會在這一時期層出不窮。本文則試圖在整體梳理三四十年代《阿Q正傳》仿作的基本創作風貌的基礎上,結合時代的具體語境,探查這些仿作對魯迅原作的承傳與變異,進而思索此時《阿Q正傳》仿寫熱潮形成的動因。
一、從未莊阿Q到摩登阿Q:《阿Q正傳》仿作中的人物類型
魯迅原作中的阿Q尚是一個農民或流氓無產者,而仿作中的阿Q大多進了城,成為“城里人”。他們擺脫了農民阿Q的蒙昧狀態,擁抱了現代城市文明。仿作中常見的摩登阿Q有兩種:學生阿Q和富豪阿Q。
對學生阿Q的書寫在《阿Q正傳》的仿作中占相當大的比例,這些仿作多來自在校大、中學生發表于校園刊物上的文章。他們在仿寫《阿Q正傳》時,一般會自然而然地以校園生活為底本,以身邊的同學為模特。他們的仿寫情節較為簡單,模仿痕跡也比較明顯,基本是將阿Q的精神和事跡移到學生身上。有些學生阿Q繼承了阿Q式的“瞧不起”,如馬三郎筆下的女阿Q,穿著校服大搖大擺地去學校,仿佛自己是學生就高人一等,但到了學校,卻對老師同學極盡巴結;王士年塑造的學生阿Q成績好,就瞧不起成績不好的同學,自視為城里人,便瞧不起鄉村的同學。有的還繼承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蔡觀筆下阿Q的兒子小阿Q喜歡打架,打不過就喊別人“阿爸”,自稱是一種明哲保身的手段……這些接受了現代教育的學生阿Q學問遠在連名字都不會寫的老阿Q之上,但卻透出了老阿Q的精神底色。由此可見,阿Q精神并不會因代際更迭和文化水平提高而消失,受過新式教育的年輕一代身上依然存在阿Q的陰影。
在原著中,“不準革命”的阿Q死在了革命的第二天,窮困潦倒地終結了一生。有些《阿Q正傳》續寫者則試圖為阿Q創造翻身的機會。在仿作中,阿Q真正過上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歡喜誰就是誰”的上等人生活,成為上流人士。阿Q的發家史受到普遍關注。但在這些作品中,阿Q的“闊起來”不是靠他的“真能做”,而是靠各種不正當手段。在尤晨的《阿O正傳》中,阿Q的私生子阿O兒時當乞丐,后來,一架飛機在鎮上墜落,阿O趁機撿走飛機上的現金,成了億萬富翁。阿O的投機致富使他真正地凌駕于小鎮居民之上,連昔日與他打架的阿猴(類似于與阿Q龍虎斗的小D)也成了他的手下。但是,某天,阿O在與婦女搭訕時被暗殺。結尾的“阿O死了,但阿猴在微笑著”[1],暗示阿O之死是阿猴的設計。從阿O投機成為富翁,到阿猴暗殺并取代阿O,在此,革命的潛能沒有帶來正面的變革,反而催生了不擇手段、巧取豪奪的鬧劇。
闊起來的上等人阿Q與未莊的窮苦阿Q的思維方式并無不同。在一些仿作中,曾飽受欺辱的奴才阿Q終于爬到了主子的位置上,但他卻反過來加倍欺壓在自己之下的奴才。在聲笙《新阿Q傳》中,新阿Q曾是流浪漢,后來到了上海,靠與地痞惡霸勾結樹立起了權威。一次,他幫某公館的太太擺平了桃色糾紛,太太送他巨額酬報,他便用這些錢辦起了百貨商店。他把伙計當成牛馬,若伙計稍不合他心意,他便動輒打罵。他甚至將一個伙計折磨致死。高遠東曾將魯迅思想的內核概括為“相互主體性”。上述對富豪阿Q的書寫正表明了,“單向度的人之為人、主體之為主體并不能消滅主奴關系”,只有把“立人”的命題延伸到社會性的相互關系領域,“主體才能成為‘相互主體,社會才能成為人人為人的社會,真正消滅了主奴關系的現代主體化的新文明才可能出現。”[4]
二、劇變的時代與不變的阿Q:戰時社會中的“阿Q相”
三四十年代的《阿Q正傳》仿作者們力圖在對魯迅原作的借鑒中注入新的時代思考和現實關懷。因此,這些仿作不只限于阿Q身份的拓展,揭示無論男女老幼、貧富貴賤,都或多或少沾染了阿Q精神的遺毒,也不只停留在對原作亦步亦趨的模仿層面,而是一種“在新的文化、政治和語言背景下對前文本的再創作,是作品穿越時空,從一種接受語境到另一種接受語境的變遷”[5]。
從14年抗戰到3年解放戰爭,戰爭構成了這一時期最主要的歷史背景,救亡成為時代的主旋律。考察此時仿作者對阿Q故事的重述離不開戰時語境的參照。實際上,此時的很多《阿Q正傳》仿作中都有戰爭的影子,有的甚至直接傳達了仿作者的戰時思考與批判。
首先,在民族危亡之際,抗日救亡是上至國家政府下到每個國民不容推卸的責任,以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拒絕反抗顯然有悖民族大義。在國家政治的層面上,抗戰初期,輿論普遍對當局的不抵抗政策強烈不滿。有人借助對阿Q故事的重述,以形象性的小說形式表達辛辣的諷刺。在高慶豐《阿Q與唐吉訶德的會談》中,阿Q竟聲稱敵人進攻中國是為了將他們的萬千頭顱奉送中國。而敵人占領南京,并且還要繼續西進,是因為送禮要送到家。他還矢口否認中國將面臨亡國的危險,稱中國的失敗是敗中取勝和勝利的退卻。阿Q上述的荒誕言辭顯然脫胎于當局的“不抵抗”言論,當局不抵抗的阿Q主義者的面目在這篇作品中躍然紙上。
在個體層面,為一己私利拒絕承擔抗戰義務,沉浸在個人的小天地中而不去接觸殘酷的社會現實的人也被視作阿Q。對學生來說,一味鉆象牙塔、進研究室已是一種不合時宜的行為。林茂《小Q的故事》就講述了只顧讀書、不關心抗戰的小Q精神勝利法失效的過程。小Q從不參與社會活動,認為讀書之外的事都是國家的事,與學生無關。然而,“九一八”之后,他的夢想被當局的不抵抗政策斷送了。他決心不再安分守己,積極參加抗日的社會活動。但是,他還是看不慣同學們與反動的學校當局的對立,認為要采取阿Q的精神勝利法,做有涵養的學生,理解校領導的苦衷,即使學校開除學生也是因為學生自己的問題。然而,后來學校竟以參加社會活動、玩忽學業為名,將成績優異的小Q開除了。“孫子才敢開除我”[6]這類話從此失去了效力。作者講述小Q的故事,意在提醒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際,阿Q式的精神勝利不可取,要懷揣社會責任感,與中外反動勢力做實際的斗爭。
其次,揭露阻礙抗戰的現實黑暗勢力是戰時創作的重要主題之一,這一主題在彼時對《阿Q正傳》的再創作中亦不鮮見。有的作者以尖銳的筆觸揭露了戰時阿Q出賣國家、發國難財的卑劣行徑。阿Q“前世吃了假洋鬼子的虧,這一世他就想勾結真洋鬼子來搗亂”[6]。他一面逢迎外國權勢者,幫他們擺好“人肉的筵宴”[8],一面仗勢欺人虐待同胞,從中牟取巨額利益。《阿O起家傳略》詳細地描繪了“外形酷像阿Q”的阿O投靠侵略者大發不義之財的起家史。阿O本是王莊地痞,村莊被敵人占領后,他被任命為偽自治會會長。他精明能干,善于逢迎,加之善于運用各種肥己手段,他便很快發達起來。后來阿O“功成身退”,帶著血腥錢投入上海商界,靠主子的扶助賺得盆滿缽滿。抗戰勝利后,阿O帶著錢財出逃,不知所蹤。小說結尾的“但是阿O……——沒有下文?”[9]卻提醒人們警惕這種時代“弄潮兒”的再度出現。
最后,有些民眾對戰爭的目的缺乏正確的認識,正如在阿Q看來,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歡喜誰就是誰”,《兩個現代阿Q的故事》中的兩位現代阿Q對戰爭的理解與之并無二致。瘌痢阿毛是天津的一個裁縫,他聽聞我軍即將解放天津,便開始幻想娶銀行行長的三姨太為妻。小劉在濟南的銀行當茶房,聽說我軍即將接管濟南,他于是變得趾高氣揚,不再完成上司分配的任務,還把銀行的很多東西都搬到家里去了。可見,對于兩位現代阿Q而言,解放戰爭反對獨裁、爭取民主的目的與他們無關,他們只關心“純粹獸性方面的欲望的滿足——威福,子女,玉帛”[10]。也可看出,廣大民眾如果缺少“深沉的勇氣”“明白的理性”[11],對革命和戰爭抱有阿Q式的理解,以正義、民主、自由為追求的革命便難以實現其目的。因此,在戰爭中,啟迪民智,消滅群眾腦中的“思想敵人”同樣不容忽視。
曾有人指出,“許多批評家說,阿Q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然而我們試看看周圍,這種人卻多得可以。過去潛伏著的這種品性,在這個戰爭里都充分暴露出來了。”可以說,對于戰時“阿Q相”的發現與揭露,有力地證明了“魯迅所描寫的時代已經過去,是完全錯誤”[12]。也正如魯迅所言,“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并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13]
三、藝術與時代的合力:《阿Q正傳》仿寫熱的成因
盡管魯迅認為“永遠是炒阿Q的冷飯,也頗無聊”[14],但這絲毫不能澆滅人們仿寫《阿Q正傳》的熱情。值得追問的是:為什么對《阿Q正傳》的仿寫會在三四十年代蔚然成風?曾有學者指出,文本的傳播動力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文本自身的魅力,二是社會的需求。前者由文本的固有屬性決定,后者則是“文本在與流變著的時代背景中多種可變性條件遇合之后衍生出來的動力性因素”[15]。探察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阿Q正傳》仿寫熱潮,也可以從這兩個方面進行思考。
對文本自身而言,《阿Q正傳》能夠迅速地被經典化,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壇中贏得崇高贊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小說塑造了一個“說不盡”的阿Q形象。阿Q形象自誕生起就被指認為“中國人品性的結晶”[16]“中國的一切譜的結晶”[17],成為當之無愧的國民性典型。同時,正如羅曼·羅蘭曾認為法國大革命時也有過阿Q,阿Q的典型形象更是具有全人類的普遍性。由此,阿Q典型的高度普遍性使《阿Q正傳》成為一種“可以無限演繹和變形”“能夠不斷被再寫和再述”的“起源文本”[18],進而構成了《阿Q正傳》被不斷改寫的前提。正是由于無論何時何地、何種身份的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分有阿Q的基因,所以仿作者們的嘗試便順理成章。
但是,《阿Q正傳》的仿寫自三十年代開始才形成潮流,小說發表的最初十年中的相關仿寫作品卻甚少。僅從阿Q形象典型性的角度無法解釋為何在三四十年代《阿Q正傳》仿寫熱的原因。故此,彼時時代語境的催化作用應被納入考察范圍。
如前所述,戰爭構成了三四十年代最大的時代背景。“九一八”以來,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使抗日救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日漸洶涌澎湃,塑造民族主義的身份認同,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體塑形成戰時社會的迫切需要。作為“民族脊梁”的魯迅精神被視作重構戰時民族精神的重要資源。戰時社會對魯迅的推崇亦帶動了人們對魯迅作品的重視。如果說魯迅的精神和人格給予民族精神正面的建設作用,對國民性負面典型阿Q的形塑則為人們對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想象和反思提供了批判性的文化資源,在戰爭語境中“以反思性的愛國主義方式投射于民族主義意識的覺醒”。正如時人所說:“我們現今的國家社會,不能再容有阿Q這樣的人物”“為了抗戰,為了勝利,我們需要時時刻刻槍斃阿Q”。基于這種時代需要,《阿Q正傳》獲得了廣泛關注。也就不難理解,《阿Q正傳》的仿作為何在此時大量涌現。這些仿作者為阿Q改換了身份和時代背景,但卻保留了其精神內核,意在以文學創作的方式向人們展示:阿Q并沒有死,戰時社會中還存在著形形色色的“阿Q”。只有努力揭露并消滅國民性中的阿Q精神,才能求得抗戰的勝利。而解放戰爭期間的《阿Q正傳》仿寫的時代背景處于抗戰的延長線上,為了爭取建設嶄新的民族國家,國民必須具有良好的精神面貌,為此,同樣也要摒除阿Q式的國民劣根性。
四、結語
綜上所述,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阿Q正傳》仿作基本延續了魯迅原作“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的創作主旨。在仿作者筆下,無論長幼、賢愚、貧富,都能在他們身上發現熟悉的“阿Q相”。在跨越了身份和階層的同時,阿Q精神還穿越了時代。仿作者們敏銳地捕捉到了變動時代下的不變,成功刻畫了戰時社會環境下滋生的各種阿Q變種。彼時《阿Q正傳》仿寫熱潮的出現,一方面,印證了阿Q形象的持久魅力,對宣判阿Q已死的言論提出了有力質疑;另一方面,順應了戰爭中強大的民族主義時代思潮,為重塑民族精神、凝聚民族情感提供了助力。這些仿作的藝術水準雖難與原作比肩,但其借魯迅思想與現實對話,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復現”魯迅筆下人物的嘗試卻是難能可貴的。可以說,《阿Q正傳》的仿作者們正是以創作的形式接續、發揚了魯迅的思想傳統。
參考文獻
[1] 尤晨.阿O正傳[J].現代周刊(檳榔嶼),1948(109).
[2] 魯迅.“題未定”草(一至三)//魯迅.魯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3] 齊雯.阿Q別傳(續)[J].國風(上海1939),1939(3).
[4] 高遠東.魯迅“相互主體性”意識的當代意義[J].探索與爭鳴,2016(7).
[5] 陳紅薇.改寫[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21.
[6] 林茂.小Q的故事[J].青年知識,1940(12).
[7] 丁力.阿Q轉世[J].論語,1947(150).
[8] 魯迅.燈下漫筆//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9] 阿O起家傅略[J].人人周刊,1945(5).
[10] 魯迅.五十九“圣武”//魯迅. 魯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1] 魯迅.雜憶//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2] 周黎文,洪予.長篇漫畫:阿Q之再生[J].青年月刊(蘇州),1942.
[13] 魯迅.《阿Q正傳》的成因//魯迅.魯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4] 魯迅.360108致沈雁冰//魯迅.魯迅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5] 田義貴.經典文本的變遷與歷時傳播——以《紅巖》為例[J].社會科學戰線,2006(3).
[16] 雁冰,譚國棠.通信[J].小說月報,1922(2).
[17] 仲密.《阿Q正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1913-1983:第1卷.[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
[18] Julie Sanders.Adap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The New Critical Idiom)[M].Routledge, 2006.
(特約編輯 范? 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