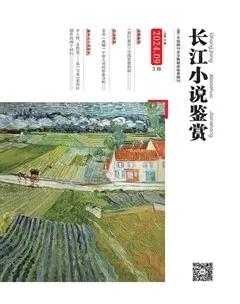家鄉、歷史、女性——張翎小說主題探究
徐靜
[摘? 要] 張翎,作為北美華文文學重要的作家之一,在加拿大旅居幾十年。身在異國他鄉,她用自己的小說創作表達了對家鄉的追憶、對歷史的回顧、對女性的關切。家鄉藻溪、歷史創傷、女性艱辛成為其創作的小說的三大主題,本文便對這些主題進行逐一分析。
【關鍵詞】 張翎? 家鄉? 歷史? 女性
[中圖分類號] I247[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9-0066-04
張翎的小說聚焦于家鄉、歷史、女性這三大話題,她筆下的故土藻溪是充滿原始生命力但也有些世俗的浙南小城,她對歷史的敘述是為了讓人們直面歷史中的創傷和災難,她塑造的女性在歷史沉浮中、在故土、在他鄉堅韌地生存,從她們身上,能看到藻溪的印記,能感受到歷史的厚重。
一、對家鄉的追憶
在張翎的小說中,我們常常能看到“藻溪”這個地名,許多故事也在此地展開。藻溪,溫州蒼南的一個小鎮,是張翎母親的故鄉,承載著屬于母親的故土記憶。張翎曾在采訪中提到,在她小時候,母親和其他長輩們不停地給她講述藻溪的種種趣事,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筆下,藻溪是一個原始蓬勃且又飽經滄桑的浙南小鎮,如同沈從文筆下的邊城,居住在這里的人們純粹善良,但也自私世俗。
1.原始純粹的藻溪生命力
藻溪鎮里有條“藻溪河”,《陣痛》開篇就提到這條河流不長也不寬,然而到了雨天,這條河流卻成了翻臉的悍婦,湍急洶涌。依水而建的藻溪鎮也被河水影響,充斥著奔流不息的原始生命力,這種生命力深深烙印在每一個藻溪人的基因中。《陣痛》中,上官吟春和月桂嬸一起,帶著剛出生的小桃,離開藻溪,來到溫州城,改名換姓,在一間小小的賣熱開水的鋪子里將小桃撫養成人,“只要活著,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你什么都能看見”[1]。這種生命力讓上官吟春成了勤奮嫂,讓小桃于炮火中生下武生,武生在午夜馬路上生下路得……
《雁過藻溪》中,末雁回到藻溪,安葬母親的遺體。在藻溪的山水滋養下,她漸漸逃離了一直禁錮她的兩座牢籠——母親和丈夫的冷漠。藻溪的日子是一種藏了頭掐了尾沒有因緣不問結果沒心沒肺的日子,愚昧簡單省心,甚至有些隱隱的快樂[2]。百川,是藻溪蓬勃原始生命力的集結者,他簡單直白,不顧倫理道義,和末雁(后文知道他們兩人是親姑侄)發生男女關系。在和百川相處過程中,末雁沉睡幾十年的生命力被喚醒,她可以和百川、靈靈,甚至和自己的前任越明開些世俗的玩笑,直面自己的欲望,她變得鮮活起來了。“末雁說完了,就暗暗吃了一驚,沒想到自己如此木訥的個性,到了藻溪,換了個地界,竟也變得伶牙俐齒起來。”[2]“越明,你去死吧,你老婆離老,還有幾里路呢。”[2]
蓬勃原始的生命力鐫刻在藻溪人骨子里,即使遠離家鄉幾十年,但只要一回到家鄉,這種生命力就會被喚醒,人們互相幫助,善良簡單,有著獨屬于浙南小鎮的溫情味道。“月桂嬸是下街的一個寡婦……上街下街誰家有事,都喊她過來幫忙——也算是接濟的意思。”[1]
2.自私落后的藻溪世俗性
與其他小鎮居民一樣,藻溪人或多或少帶有著世俗氣息,也有自私落后的一面。
《雁過藻溪》中,末雁的母親黃信月,原本是藻溪大戶人家的千金,從藻溪一路逃到溫州。但當信月嫁給溫州城的大官宋達文后,藻溪鄉人卻來尋求信月的幫助,無論是看病、找工作這種一家一戶的事情,還是需要化肥農藥災款的大事情,他們帶著鄉下的特產,怯懦地敲響信月家的后門,希望這個曾經被全鄉人傷害過的女人能夠不計前嫌,讓他們得到一些實際好處。
《陣痛》中也有這種世俗落后性。上官吟春誤以為自己懷的是日本人的孩子,投河自殺,婆婆呂氏為了救她和肚子里的孩子,先是找了道姑喊魂念經,然后才派人去叫郎中;除此之外,呂氏十分渴望一個男孫,呂氏第一次見到上官吟春的時候,她緊盯著的是上官吟春的腰臀,衡量著吟春的生育能力;呂氏可以忍受男孫生于亂世的簡陋,但絕不能接受吟春肚子里的是個女孩。
藻溪人身上的世俗性、落后性受到歷史、傳統、社會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毋庸置疑,他們的確有令人可恨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可悲。
二、對歷史的回顧
張翎的小說常常直面歷史,揭示在歷史沉浮中,人們(尤其是女性)最真實的、悲慘的生活狀態,這也形成了她小說主題的一大特色——創傷敘事。回顧歷史,我們總會自覺而不自覺地躲避那些血淚、掙扎、苦難,而張翎以一種可貴的勇氣向歷史發問,透過小說背后,我們能感受到歷史的厚重,能看到堅韌的人。
《金山》可以說是一部海外勞工的百年奮斗史,以艾米和歐陽云安的現代對話,再現了方氏一家從晚清到土改時期經歷的歷史風云,時代洪流的每一次漲潮都精準淹沒了方家。方元昌因過度吸食鴉片而死,15歲的方得法一夜之間承擔養家的責任,成了金山客,漂洋過海掙錢財,但金山并不是遍地金銀,金山伯也只在家鄉風光,對于金山來說,這些天朝子民是最廉價的黃種勞工,是“豬仔”苦力。他們忍受著海水的顛簸、封閉污濁的空間,背井離鄉,開啟了艱辛的人生新篇章。方得法不是個例,《金山》也不是虛構偽造。在晚清,曾有成千上萬的華工前往北美洲淘金、修建鐵路,他們變賣土地家產,籌措船費,拿著薄弱的工資,承擔最危險的工作。太平洋鐵路的每一個枕木下,都沉睡著一個中國勞工的亡魂。他們不懂得修建鐵路是為了什么,能帶來什么,他們只知道,等鐵路完工后,他們就可以得到一大筆工錢,寄回家鄉,如果錢夠的話,還能榮歸故里,娶妻、買田、蓋房。但當最后一顆道釘敲進枕木,加拿大政府揭開了排華反華行動的序幕。《華人入境條例》的頒發,人頭稅的增長,禁止華工親屬來加拿大……多少華工永埋在大洋東岸,孤魂無法安寧。
他們在大洋彼岸吃盡了苦頭,用筋肉、血淚換來的銀票一點點摳出來,將自己的思念和牽掛植根于銀票里,寄到此岸。然而時代變遷,日月更新,那頭吃了苦,這頭也不得歇,他們的家人在此岸也無法生存。他們的家人還是會經歷戰爭、饑荒,甚至因為家里有個金山客,成了別人的眼中釘。《金山》里,有專門盯金山客家人的土匪,六指和錦河便曾被土匪劫走,變賣田產,東拼西湊才被贖回。[6]
張翎的其他小說中也有對戰爭、“文革”等歷史事件的描寫,《陣痛》中,人物命運起伏,是時代交接更替的結果。趙夢痕,資本家的大小姐,家境優渥,摩登時尚,她從象牙塔里跌落,成為一名女工。抗戰,南下干部的兒子,他的父親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也十分風光,然而到了“文革”,也被審查打倒。更不必說勤奮嫂、小桃這種普通人,他們只能順著歷史的洪流,聽從歷史的安排。
這些被歷史裹挾著的人們,并不都只無奈地被歷史推著行走,也有挺立潮頭,想要改寫歷史的前進方向。《金山》中的歐陽先生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他作為一名教書先生,熱衷國事,批評時政,后來參與戊戌變法。作為歐陽先生的弟子,阿法也用自己的力量,試圖改寫歷史。在聽完梁啟超先生的演講后,他停止了如日中天的洗衣館生意,賣了兩個衣館,把絕大部分的錢捐給了北美的保皇黨派,希望大清國能夠再次興起。“大清國若是略為強壯些,你我何必拋下爺娘妻子,出走這洋番之地,整日遭人算計訛詐。”[3]他的兒子錦山,也從賣菜得來的錢中,時不時搜取一點,捐給革命。在他們身上,我們能夠感知到人們對時代的反抗,但歷史的車輪即使偏頗,最終還是會回到應有的軌跡中。
歷史是一堆灰燼,但在灰燼之中仍有余溫。張翎的小說,在對創傷的揭露下,讓我們看到了個體在歷史中的生命軌跡,這是值得被記住的溫熱。
三、對女性的關切
張翎深受家族女性生命韌性的影響,因此,作為一名女性作家,她自然而然更了解女性,更關注女性,更同情女性。在她的小說中,如《金山》《陣痛》,常常以一個女性的成長歷程為起點,衍生出幾代女性不同的成長故事,每一代女性都有著自己的困境和艱辛。
第一代女性是以麥氏和呂氏為代表的婆輩。作為封建時代的典型女性,她們遵守三從四德,始終維護男權社會的核心利益。丈夫在世時,她們最大的愿望就是為丈夫生出兒子、養活兒子。因此,麥氏為了治好放得善的病,將年僅13歲的女兒阿桃低價賣給了別家做婢女。丈夫死后,她們便成了家庭中的權威,她們的重心和依靠全部轉接到兒子身上,“大先生是呂氏手里的一只風箏,呂氏讓他飛多遠就是多遠,一寸不多,一寸不少”。[1]對于以呂氏和麥氏代表的婆輩來說,她們的困境就是家庭男性的缺失。方得善死后,麥氏只剩下阿法這一個兒子,但阿法遠在金山,幾十年才能回趟家,麥氏帶著對阿法的掛念熬完了自己的生命,而她死后,阿法也沒有機會來墳前祭拜。同樣,呂氏和她的兒子——大先生聚少離多,她死前也記掛著大先生,除此之外,她還掛念著未出生的孫子。事與愿違,大先生死在呂氏面前,吟春肚子里的是個女孩。
第二代女性是以六指和上官吟春為代表的母輩。她們從一個稚嫩的少女,轉變成了博大的、堅韌的母輩。她們的困境分為兩個部分,一方面,她們要忍受來自婆婆的壓迫,丈夫的無情。六指伺候麥氏28年,為了照顧麥氏,她和阿法不得不分離在大洋兩岸,在麥氏病重的時候,剜下自己的肉滋補麥氏。而阿法卻在大洋對岸找到了新歡知己——金山云,甚至想把她帶回開平,“阿賢是好人,不會容不下你”[3];吟春一開始就作為替代品被大先生關注,在呂氏仔仔細細打量過她的腰臀之后,被迎娶進了陶家,進入陶家之后,呂氏迫切地想要一個孫子,逼迫吟春扛起陶家的未來。至于大先生,當他誤以為吟春懷的是日本人的孩子之后,他怪罪吟春,說她是賤人,肚子里的孩子是賊種。另一方面,丈夫長期在外,她們的肩膀壓上了養家的重擔。六指嫁入方家時,她意識到從此刻起,她的命就不再是她一個人的了,而是要剁得細細碎碎,和方家所有人的命搟在一起,再也分不出你的我的他的了。[3]六指也的確將整個生命獻給了方家,生育三個兒女,撫養成人,為麥氏送終,守護著得賢居。吟春在大先生病倒之后,也明白了從今往后,她再也沒有指望了,只能一個人跪著爬著,一毫一寸地,把塌了的天再慢慢扛回去。[1]她帶著小桃,成為了勤奮嫂,改名換姓來到了溫州,在一間老虎灶中把陶家唯一的后人撫養長大。
第三代女性是以區燕云、貓眼、小桃為代表的年輕女輩,她們的困境主要是和丈夫之間的尷尬情感。區氏,是六指為錦河挑選的妻子,但錦河并不想和自己的妻子隔著山海,他心中最合適的妻子人選是阿喜,可亨德森太太拆破了這樁姻緣,他只能和區氏結婚,讓阿法早日抱上孫子。區氏只和錦河生活過幾個月,之后便再也沒有見過錦河。貓眼,作為錦山的妻子,和錦山也并不是兩情相悅。她從番攤館逃出來,將錦山作為救贖,緊緊抓住。錦山也只能好心收留她,“這一個男人從一開始就沒有喜歡過她,卻為了不叫她在街上餓死凍死”[3],即使當貓眼成了方家的主要經濟來源,錦山仍時不時提到她的過去,在夢中呼喚的依舊是桑丹絲。小桃,愛上了留學中國的越南學生——黃文燦。但黃文燦最終必須回到千瘡百孔的家鄉,懷著身孕的小桃只好嫁給她喜歡但又不喜歡的宋志成。
第四代女性是以延齡、武生為代表的更年輕的女輩。對于她們來說,家庭是最大的困境。延齡從小生活在父母的爭吵下,對那個拮據的家庭十分厭惡,因此她不斷地出逃家庭,在陌生的城市中感受自己的生命,然而,她的每一次逃離都以失敗告終,最終帶著艾米回到了沒有祖父和母親的家。武生,在得知自己的導師——布夏教授就是自己的親生父親黃文燦之后,無法接受她的生命是個遮天蔽日的謊言,和小桃大吵了一架,在杜克的寬慰下慢慢接受了這個事實。
四代女性都有著各自的隱晦和心酸,但不同代際的女性無法相互理解,反而彼此對抗,呈現出一種僵持的關系。麥氏和呂氏壓榨著六指和吟春,麥氏認為六指有六個指頭,是晦氣的象征,是六指搶占了阿法;呂氏則盯著吟春早日懷上兒子,讓陶家后繼有人。六指、吟春也和年輕女輩們僵持著。六指也像麥氏壓迫過自己那樣對待區氏和貓眼。她不承認曾經是妓女的貓眼是錦山的媳婦,即使在阿法破產、錦山受傷、錦河從軍后,寄回開平的銀票都是貓眼掙來的。六指也包辦了錦河和區氏的婚姻,然而對木訥的區氏極其不滿意。勤奮嫂和小桃也有著對抗,勤奮嫂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小桃身上,當小桃沒交算術作業時,勤奮嫂扇了小桃的臉,同樣,小桃無法理解母親的艱難和節省,因為“老虎灶西施”這個稱號給年少的她帶來了很多苦楚,被排擠在班級之外,在招生考試的面試環節,被考官們譏笑。在第三代女性和第四代女性之間也能看到這種僵持關系,得知身世的武生責怪小桃的欺騙,想對小桃嚷“我沒有求你生我”[1];貓眼顧不上青年時期延齡的自尊心和沖動,延齡也無法體悟貓眼養活一家人的難處,延齡出逃家庭,沒見到貓眼的最后一面;貓眼望著延齡的房間,叫一聲延齡之后便撒手人寰。
張翎筆下的女性帶著獨屬于自己的酸辛,孤獨地、艱苦地活在家鄉,活在異國他鄉。
四、結語
張翎的小說主題緊緊圍繞著家鄉、歷史、女性這三個大主題。在加拿大幾十年,她積攢的故土記憶排山倒海涌泄出來[4],在書寫家鄉時,張翎也重新來到了她記憶中的溫州藻溪。對家鄉的追憶離不開對歷史的回顧,戰爭、“文革”這些歷史創傷也深刻影響著浙南小城。回顧歷史時,張翎的視野不僅僅局限于故土,她的寫作疆域拓展到了廣州,描寫了兩百年前的華工生存境遇。對故土的追憶,對歷史的回顧都是通過女性展露出來,女性用不同于男性的姿態迎接著歷史,用更堅忍的態度反抗災難和創傷。自詡字匠的張翎,用她的文字鍛造著歷史長河中的隱秘角落,用女性的形象呈現出災難和創傷,重塑自己精神上的故土。
參考文獻
[1] 張翎.陣痛[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2] 張翎.雁過藻溪[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3] 張翎.金山[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
[4] 張翎.張翎作品集:長篇小說卷(全六冊)[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社,2021.
[5] 阮丹丹.情感·創傷·女性:論張翎的小說追問[J].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5).
[6] 陳姻吟.張翎小說《金山》中的華工書寫[J].新紀實,2022(10).
(特約編輯 范? 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