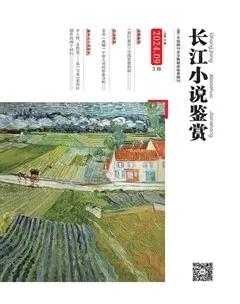“莫言”角色的符號形象與敘事功能分析
曹冠楚
[摘? 要] 本文從《生死疲勞》中的“莫言”這一作者自我虛構形象入手,通過語義分析法和符號學分析法研究其形象特點,并進一步借助結構主義分析方法,從具體語段中分類抽象出“莫言”形象的敘事功能,從中見出“莫言”形象的敘事價值。
【關鍵詞】 《生死疲勞》? 莫言? 符號形象? 敘事功能? 自我虛構形象
[中圖分類號] I247.5[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9-0070-04
一、人物符號形象分析
所謂人物符號學,菲利浦·阿蒙在《人物的符號學模式》一文中進行過詳細論述,并提出了分析人物的具體步驟:第一,確定話語中循環出現的詞語,包括行動與人物品質的區別性屬性;第二,將每個人物據此區別性特征進行分解;最后,確定其人物類型[1]。通過人物符號學模式分析,人物可以超越作品進入更廣闊的人物類型長廊。
莫言在創作《生死疲勞》時,為每個人物形象都賦予了特定的符號形象特征,這顯著體現在詞匯表達上。
詞匯對人物形象的顯示具體體現在《生死疲勞》中的顏色隱喻。文本中動用大量的顏色詞表現人物性格,即顏色隱喻,與中國臉譜顏色有一定關聯。藍臉對應一半“藍”和一半“紅”,藍意味著性格剛直執拗、桀驁不馴,文中藍臉的單干即體現這一性格與顏色隱喻,包括藍臉的后代藍解放、藍開放,甚至藍臉鬼卒,都符合這一顏色隱喻;黃瞳對應“黃”“黃頭發黃臉皮黃眼珠”,黃意味著兇暴,而文中黃瞳殺西門鬧正是符合這一顏色隱喻,此外黃瞳的性格與外貌皆與王黼類似,一定程度上說明莫言《生死疲勞》中的文學形象與文學史上的文學形象有所呼應;此外,西門金龍多用“綠”的顏色隱喻,秋香多用“黑”,都體現了《生死疲勞》中作者對用字用詞的雕琢,體現符號研究對文本中人物性格的揭示。
因此,本文借助人物符號形象分析的方法,通過窮盡式列舉與分類,從《生死疲勞》中找出作者形容莫言的詞匯,即行動與人物品質的區別性屬性,進行詞頻分析與分類分析,將莫言形象據此區別性特征進行分解,推求其文學形象與人物類型,從中看出莫言這一角色在文本中的價值傾向,也能為分析其敘事功能提供一定依據。
1.字、詞頻統計
從中刪去無意義虛詞與派生詞綴后,詞頻統計按頻率由高到低依次為胡編、好奇、忽悠、討厭、精力過剩,字頻統計按頻率由高到低依次為嘴、胡、編、鬼、厭、說、丑、奇、怪、壞。
“胡編”“忽悠”“嘴”“亂”都是形容莫言形象的滿口胡言,“好奇”“精力過剩”則是說明莫言形象的擅長向外探求,“討厭”“壞”等則是說明莫言形象的令人厭煩,從中預示莫言符號形象的大致趨向。
2.莫言符號形象分類分析
結合詞頻統計與字頻統計的傾向,本文將其行動與人物品質的區別性屬性劃分為以下幾類,共150個詞。
“湊熱鬧”“行為出格”“好奇”類,共計26詞左右,占比17.33%。這類詞大多帶有一種向外探求的傾向。《生死疲勞》作為第一人稱敘事的說書型小說,常受第一人稱敘事局限。第一人稱敘事即故事的敘述僅限于某一個人物看到了什么、經歷了什么,但一個人物的所見所聞有限,因而“莫言”這一人物的向外探求傾向便帶有一種特殊的敘事學意味,即敘事視野的延伸,這對于《生死疲勞》這部小說能否順利鋪展開情節至關重要。
“碎嘴”“令人討厭”類,共計21詞左右,占比14.00%。在向外探求的傾向下,“碎嘴”這一形象特點便順理成章。既然莫言承擔敘事視野延伸的功能,那么必然需要“言說”的機會,因此莫言在小說中總是以碎嘴的形象出現,由此自然地引發人們的不滿,這也是“令人討厭”“臉皮厚”等形象特點出現的緣由之一。此外,“碎嘴”中多有打斷別人的話、插嘴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莫言的話語亦形成了小說的復調,在眾人話語之外形成獨立話語體系。
“胡編亂造”“異想天開”“鬼怪”類,共計37詞,占比24.67%。這類詞大多帶有一種異于常人的傾向。胡編亂造、異想天開即指出莫言這一敘事者的不可靠。“不可靠的敘事者”是敘事學中重要的一個概念,這種不可靠同時與作者的“解構”目的相契合。因此,“不可靠的敘事者”“解構”將是莫言敘事功能的重要著力點,將放到第二部分詳細展開。
丑化類,共計32詞,占比21.33%。“邋遢貌丑”“油滑”“怯弱”“無能愚笨”都是對莫言形象不同程度的丑化,而文學史上被刻意丑化的人物譜系,既有莎士比亞的小丑形象,也有古典戲劇中的丑角形象,體現莫言這一形象的文學譜系價值。
綜合這一章節對莫言形象的字詞頻分析與符號形象分類分析,可大致概括出“莫言”這一角色的人物類型:“莫言”是一個總喜歡湊熱鬧、愛打聽、碎嘴又古怪的頑童丑孩兒。
與“莫言”形象這一人物類型相比,作者莫言小說中確實存在著大量丑角形象,甚至可以建構出莫言小說中丑角的人物譜系。《生死疲勞》中的“莫言”,《牛》中的羅漢,《白狗秋千架》中的白狗,《錦衣》中的王婆、王豹,《酒國》中的丁鉤兒,《民間音樂》中的三斜,都延續著莫言小說一貫的美學風格與丑角精神。
作者為何設置這類角色?言語行為出格的表面下存在著怎樣的敘事功能?這將在下一章節進行探究。
二、敘事功能分析
1.敘事者身份
研究莫言這一角色的敘事功能,首先要確定其敘事者身份。
1.1故事內敘事者、人物敘事者
莫言作為故事中的一個角色,與其他人物同處一個關系網之中,因此是故事內敘事者。
莫言在文中既是敘事者,也是人物,為人物敘事者,但參與故事的程度、在故事中的功能比較特殊。參與程度上,莫言是次要人物;而功能維度上,莫言既是觀察者之一,又是情節推動者、行動參與者。
1.2內隱敘事者轉向外顯敘事者
外顯敘事者往往喜歡用第一人稱“我”進行敘事,并直接或間接地面向敘述接受者說話,并帶有一定的話語與情感傾向。在前幾章節中,直接面向敘述接受者的是藍千歲與藍解放,直到最后一章中,莫言才從內隱敘事者轉向外顯敘事者:
那么,就讓我們的敘事主人公——藍解放和大頭兒——休息休息,由我——他們的朋友莫言,接著他們的話茬兒,在這個堪稱漫長的故事上,再續上一個尾巴。
而在此前,展示話語與情感傾向的始終是藍千歲與藍解放,如下面片段中藍千歲對過去幾次輪回轉世的情感態度:
我還想到我的朋友莫言的小說《養豬記》中那頭神通廣大的公豬——
老子就是那頭豬——大頭嬰兒回到他的座位上,氣勢洶洶但又頗為得意地說。
在這些片段中,外顯敘事者具有較強的自我意識,甚至“闖入”故事中,公開對人物和事件發表評論,這與作者向說書藝術的學習相關。而前幾章中的莫言顯然不具備這樣的自我意識,更多地作為故事中的人物與內隱敘事者出現。
1.3不可靠敘事者
不可靠敘事者意味著其敘述與隱含作者的敘述意圖不一致。如同樣是刻畫西門豬,“莫言”會莫須有地丑化西門豬的形象,而在隱含作者意圖中,西門豬在內的西門鬧各個轉世俱為豪杰。也正是這樣的不可靠敘事,塑造出“莫言”這一獨具意義的人物形象。
2.敘事功能
在敘述交流層次的區分中,莫弗雷德·雅恩從敘事文本交流過程出發,認為敘事文本的交流至少涉及三個層次,每個層次的交流都涉及自身的信息發送與信息接收者的解構,其敘述交流層次由外向內分為以下三層:第一層“作者→讀者”,第二層“敘述者→受述者”,第三層“人物→人物”[2]。
本文將《生死疲勞》的敘述分為敘述外圍與敘述內圍,敘述外圍即“敘述者——受述者”層,主要以虛構的自涉互文這一方式呈現;敘述內圍即“人物——人物”層,主要體現為情節推動者與滑稽丑角。
2.1敘述外圍:虛構的自涉互文
這里的互文指小說敘事者藍千歲、藍解放、莫言講述的故事,與“莫言”寫的《黑驢記》《養豬記》等小說構成互文關系,這里莫言的小說或起到補充情節的作用,或起到評點作用,或起到解構真實性的作用。但文本中提到的所有莫言所寫的小說,皆是作者的虛構,現實中的作者并未寫過那些小說,即虛構的自涉互文。
文本敘事中,藍千歲曾說:“嗨,我說這些話干啥呢?這些話讓莫言寫到他的小說里好了。”這里有一層暗藏的意思,即有的話能從藍千歲和藍解放口中說,而有的話只能借助莫言的小說談。那么究竟是什么話、哪些事情需要借助莫言的小說,莫言的小說又具有怎樣的敘事功能呢?這或許能通過以下對互文文本功能的分類探究中尋求答案。
作者用虛構的自涉互文這一方式,大致具有以下幾個功能。
一是將莫言作為視角承擔者,拓寬敘述視角。《生死疲勞》全篇第一人稱內聚焦敘事,具有敘事視角局限。敘述者只能講述自己的見聞,尤其在敘述者多為人化動物的基礎上,其見聞便更具局限性。作者應對這一局限的方法,一是按章節轉變敘述視角,再即借敘述者之口,通過引介莫言的小說進行有益補充。如在西門豬看不到的西門大院發生的情節,則由敘述者之口用莫言小說的內容進行補充:
莫言小說里說洪泰岳滿嘴燎泡,眼珠子布滿血絲。還說你藍解放躺在炕上,兩眼發直,不時哭泣,像一條切斷了腦神經的鱷魚。
除了情節這類感知性視角所觀察到的事,還有認知性視角對事件看法和評價的補充[3]。如莫言評價金龍和解放發瘋:
按照莫言小說里的說法,你藍解放是真瘋,西門金龍是裝瘋。
這里莫言小說的作用便不僅是對情節的補充,更是對所發生的事予以認知與評價。
二是借莫言的小說進行評點,這類互文基本位于一個章節的結尾,取法于古代說書藝術,如文本中《黑驢記》的評點手法。
三是構成不可靠敘事,由外顯敘述者進行真實性評判,形成文本張力。
譚君強《敘事學》中,對可靠與不可靠進行了具體類型分類,分為事實的、價值的、意識的等。這里莫言小說的不可靠敘事主要體現為事實性不可靠,通過對其不可靠敘事的揭示,體現藍千歲與藍解放兩位外顯敘述者的權威與可信任,如:“莫言那小子在他的小說中多次講述一九五八年,但都是胡言亂語,可信度很低。我講的,都是親身經歷,具有史料價值。”
此外,不可靠敘事者的身份方便魔幻現實主義書寫,如文本中對“太歲”的描寫。
綜合上述分析,回歸到前文的疑問:“究竟是什么話、哪些事需要借助莫言的小說來說?”一是藍千歲和藍解放看不到的,二是對故事中的人物進行評點的話,三是可信度低的話。由此,從文本表面浮現出的,是藍解放和藍千歲的說書人身份,《生死疲勞》實際上就是一部說書現場,呈現出“說書體”敘事的特點。
有學者指出,說書體敘事的一大特點在于“在一些劇目中借鑒說書人的角色,會設置專門角色進行引戲,即跳出戲外向觀眾介紹劇情、發表評論、渲染氣氛,增強同觀眾的交流共感”[4]。這類說書人角色在《生死疲勞》中體現在藍解放和藍千歲身上。兩人恪守說書人的本分,專注于講故事,并適時發表評論。但受制于故事內敘事者的這一身份,不便對部分人物進行點評,則借于“莫言”之口。藍千歲所說“這些話讓莫言寫到他的小說里好了”,前面的文本即是對藍解放行為的評價:
盡管你對這個同母異父的哥哥成見很深,但還是跟著他沾了光,如果沒有他,你能當上飼養班班長?如果沒有他,你能撈到第二年秋天去棉花加工廠當合同制工人的機會?如果沒有在棉花加工廠當合同制工人的機遇,能有你后來的官運?你落到今天這地步,不能怨別人,只能怨自己。
這一段話正是證實了前文的觀點,即說書人需要在講故事的過程中評點故事中的人物,但有些話只能借莫言之口才能無所顧忌。
實際上,在莫言的老家昌濰一帶,新中國成立后尤為盛行說書,特別是濰縣的沙灘說書場,可謂說書人云集之處。新中國成立后濰縣說書人收徒傳技,學徒學成后走街串巷,行走于各縣市之間,西至益都(今青州市),東至高密,在市井中廣有知音,在精神食糧短缺的時代受眾極廣。莫言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對說書藝術的吸收集中體現在《生死疲勞》這部小說中。
2.2敘述內圍:情節推動者
作為小說中一位濃墨重彩的次要人物,莫言這一角色體現次要人物的功能。主要分為以下兩種敘事功能。
一方面,作為行動元直接推動情節發展。莫言在杏花樹金龍解放發瘋、藍解放和龐春苗的相識兩大主要情節中起到關鍵性作用,如果不是莫言的推波助瀾,則情節無法順利推進。如杏花樹金龍解放發瘋情節中,莫言起到告知者的作用,莫言告知藍解放,藍解放才會發現西門金龍與黃互助的私情,才會引發一系列情節;又如在藍解放與龐春苗相識的情節中,莫言起到聯系者的作用。
另一方面,作為幫助者,為角色提供行為動力。格雷馬斯區分了行動元和角色這兩個不同概念,行動元是共同享有一定特征的一類行為者,諸如發送者與接受者、幫助者與反對者等,而角色則在不同的敘事作品中被賦予具體的特性。敘述話語中,不同作用的行動元作為中介,覆蓋整個話語,為角色提供動力。
在《生死疲勞》中,莫言經常作為幫助者這類行動元,為角色提供動力。這一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主要情節中。一是西門豬通過聽莫言讀《參考消息》而學貫古今中外,從而有知識解救刁小三。二是在藍解放和龐春苗被世俗拋棄、被權力威逼的情況下,為他們提供庇護所,從而使他們得以喘息與生存。三是莫言介紹藍解放參演電視劇,從而實現異地哭喪這一戲劇性情節。
2.3敘述內圍:滑稽丑角
作者莫言所創作的丑角人物與丑角精神為眾多學者發現并重視,如齋藤先生用榮格分析心理學的性格類別論來分析莫言《白狗秋千架》中的人物形象,王晴晴則從“文革”政治體制的角度分析《牛》“羅漢”這一角色體現的丑角精神。
本文從結構主義研究角度,從以下兩個方面抽象出《生死疲勞》中“莫言”這一角色的丑角精神。
一是插科打諢。文本中隨處可見莫言的插科打諢,即傳統戲曲中科諢的穿插。作者通過對其語言的巧妙修辭處理,營造出滑稽的場面,給人以愉悅的喜劇藝術享受。作者筆下的莫言喜歡把成語說殘,借以產生幽默效果:
“兩小無猜”他說成“兩小無——”“一見鐘情”他說成“一見鐘——”;“狗仗人勢”他說成“狗仗人——”。他一來龐春苗就樂了。
又如莫言向西門金龍討要劇中的角色,“哼唧”“巴眨著小眼”等,亦極具喜劇性,使讀者產生諧趣的審美體驗。
二是構成小說復調,體現為眾人皆醉我獨醒的人物狀態。
“莎士比亞筆下的弄人和小丑,其職能決不限于彈彈唱唱,插科打諢,更重要的是既在劇中,又時常超然劇外,以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通過夸張、荒誕、悖理的方式,道出真知灼見。”[5]《生死疲勞》中莫言這一角色亦與莎翁筆下的丑角類似,在瘋癲無狀、行為出格的表象下,具有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如文本中莫言突然說破西門豬的輪回身世。
此外,文本中對人物出場與介紹的描寫,體現莫言作為次要人物的功能特點。而作為用俗語間接評論的干預者,莫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聲音的代表,是眾人話語外的復調。
綜上所述,莫言不僅承擔著角色與行動元的劇內人物功能,推動情節發展,更是承擔外部敘事者的功能,是《生死疲勞》中重要的功能性人物。
三、結語
正如上文所言,通過人物符號學模式分析,人物可以超越作品進入更廣闊的人物類型長廊。莫言這一形象所體現的強烈的丑角精神,可與莫言其他文本中的丑角、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丑角、中國傳統戲曲中的丑角形象進行比較分析,從而確認其在人物類型長廊中的地位與價值,值得學界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 張寅德.敘事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2] 譚君強.敘事學導論:從經典敘事學到后經典敘事學(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3] 胡亞敏.敘事學[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
[4] 王晉華.《主角》的“說書體”敘事及其魅力[J].新文學評論,2020(2).
[5] 陸谷孫.莎士比亞研究十講[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特約編輯 楊?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