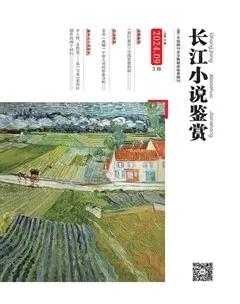以辛棄疾詞為例論王國維的評詞標準
劉芳
[摘? 要] 王國維在其《人間詞話》中,稱辛棄疾詞“堪與北宋人頡頏”[1],并對其不吝贊美之詞。反觀其評詞偏好,不難發現他更喜五代和北宋詞:“詞之最工者,實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對于南宋的詞作,他的整體評價并不高:“梅溪、夢窗、玉田、草窗、西麓諸家,詞雖不同,然同失之膚淺”。但他卻一反常態地對同為南宋詞的辛詞偏愛有加,這主要是因其評詞時,不單單將側重點放在詞作本身的文采上,還著眼于詞人自身的品格、詞作的整體風貌和自然真情上。由辛詞在《人間詞話》中不同于其他南宋詞地位的原因可觀:王國維評詞標準之中的“隔與不隔”,并非是絕對固定的對立兩極,而是可以根據創作實際進行調和兼容。
【關鍵詞】 辛棄疾? 《人間詞話》? 評詞標準
[中圖分類號] I206[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9-0101-04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表現出對五代、北宋詞人以及南宋詞人截然不同的態度,對前者他極力贊賞,謂之“北宋風流”,認為其詞風流韻致;對后者則持相反態度,認為其詞“渡江遂絕”,失去了詞本該有的韻味,乃至于他猜想“抑真有運會存乎其間耶?”[1]而在這涇渭分明的兩撥詞人的詞作中,辛棄疾詞卻遺世獨立,與眾不同,王國維稱其“堪與北宋人頡頏”,并將其區別于南宋其他詞作視之。本文將以《人間詞話》中對辛棄疾詞的評價為切入點,深入探討辛詞能夠在南宋詞中脫穎而出,并備受王國維青睞的具體表現以及內在原因,通過其特殊性來探討王國維是如何在批評實踐中巧妙化解“隔與不隔”和用典之間的矛盾,使其達到調和兼容,以此觀其評詞標準。
一、《人間詞話》中辛詞特殊地位的具體表現
從數量上看,在《人間詞話》的一百二十五則詞話中,有十四則與稼軒及其詞有關,從其占比以及出現的頻率不難看出,王國維對辛棄疾詞作具有頗多的關注。從《人間詞話》這十四則有關辛棄疾的評述內容上看,王國維不但對辛詞青睞有加,而且對其的觀照和評價也是多維度深層次的。一方面,有“與北宋人頡頏者,唯一幼安耳”這樣突破時代的拔高贊美。另一方面,又有其他多角度的評述,如在第四十三則稱:“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橫素波‘干青云之概,寧后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1]將目光放置在辛詞的性情、境界之上,不簡單拘泥于詞作是否易學易模仿之上。第四十四則:“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從后人模仿的視角去反照稼軒詞的豪放不群;第四十五則:“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1]以伯夷、柳下惠的高逸風韻和脫俗情懷作比,來贊美稼軒詞所表現出來的寬宏氣度和高雅情致;第四十七則:“用《天問》體作《木蘭花慢》……詞人想象,直悟月輪繞地之理,與科學家密合,可謂神悟”[1],以辛詞強調真實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性。
諸如以上的種種,或從正面和側面多維度欣賞,或以辛詞為引談文學見解的評述性文字,在《人間詞話》中比比皆是。由此可以見得,王國維對辛詞的喜愛溢于言表,重視之意亦不必多言,而他對南宋詞的整體評價和對辛詞評價的巨大差異,更是將辛詞放在了一個超越同時代的特殊地位之上。
二、《人間詞話》中辛詞具有特殊地位的內在原因
辛詞之所以能具有特殊地位,在眾多南宋詞作中脫穎而出,備受青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從辛棄疾本身人格出發,可看出其高遠人格對王國維的吸引力;其次,從“境界”觀照辛詞,可看其蘊含著《人間詞話》所追求的真“性情”;最后,辛詞雄偉壯闊的“氣象”,讓其詞區別于南宋詞,在《人間詞話》中具有超然的地位。
1.稼軒人格的“雅量高致”
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曾表現出對于創作主體人格的關注:“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極顯他對于詞人“人格”的推崇,且將之視為其作品優劣與否的重要因素。而在《人間詞話》的三十二則,王國維亦言:“永叔、少游雖作艷語,終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1]其中所提到的“品格”以及“淑女與倡伎”也指向了人格,由此可見,他始終將詞人的“人格”視為評斷詞作的標準之一。
觀《人間詞話》原文的第四十四則,稱:“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1]直述若缺少蘇軾與辛棄疾的博大胸襟,即使模仿得再相似,也如東施效顰,難以捕捉其詞中所蘊含的精髓。后續的第四十五則亦云:“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白石雖似蟬蛻塵埃,然終不免局促轅下。”其中的“雅量高致”,是將辛棄疾與姜夔劃分為兩類人的標尺。這二則的內容都對辛棄疾作了肯定的評價,且都涉及了他那高遠的“胸襟”以及寬宏的氣度。而王國維對于自己不喜的南宋詞人,諸如姜夔、吳文英、張炎、陳允平等,稱其詞作為:“面目不同,同歸于鄉愿而已。”[1]以“德之賊”貶低他們,更從側面印證了王國維將人格視為其評詞的重要標準之一。
觀辛棄疾詞作,其內容大多表現了他對于家國的熱愛和維護,對于建功立業的向往和追求,字里行間激蕩著他胸中那豪邁磊落的情懷,展現著他高遠、寬宏的胸襟和氣魄,正是因為他將自己的真摯感情注入作品,并加之自己人格魅力的渲染,才使得他的詞作不易模擬、難以企及,也讓王國維為之傾倒。
2.稼軒詞性情之“真”
《人間詞話》的第六則稱:“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1]王國維認為只有那些能寫出真實、具體的景物和情感的詞作,才能稱其為有境界。由此可見,王國維更加重視詞作作者的“喜怒哀樂”,以及由這樣的情緒激蕩出的真情實感。在書中的第四十三則,他評稼軒詞:“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也是以“境界”作為觀照。對于“境界”一詞的具體表現尚存爭議,但是“真”作為“境界”的前提這一結論是毋庸置疑的[4]。
圍繞這一“真”,《人間詞話》手稿本的第十七則云:“至南宋以后,詞亦為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其中的“羔雁之具”與“真”相悖,而王國維所強調和看重的“真”也在此更明確了其涵義,即是要求創作主體擺脫寫作時,以詞為“羔雁之具”的應酬心態,將詞作為言情、言志的媒介,去真實地、忠實地描寫所觀之景、闡發心中之情以及展示情景間的關聯,為讀者呈現觀感真實、情感真實的文字,將真實感情傾注于其中,做到“有境界”。而第六則所言的“真性情”,更具有主觀、個性的意味,其本身就指向了詞人內心之“真”。而王國維用“性情”作標準評價李煜時,稱其“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1],也從另一方面表現了“性情”與“真”之間密不可分的緊密關系。而在《人間詞話》中,王國維以“有境界”這樣的評價去看待稼軒詞,可見其詞中確實蘊含著“真”,且這種“真”滿足了他對于欣賞詞作中真實情感抒發的訴求。正因為如此,稼軒詞才在眾多南宋詞中獨樹一幟,備受王國維喜愛,具有特殊的地位。
觀辛棄疾的作品,確實在字里行間中透露出真性情。一則,辛棄疾的詞中所展露出的豪情是不加掩飾、直露無隱的,讓讀者對其感情的抒發更覺熾熱和強烈,在其自我排遣心中的惆悵時:“莫上扁舟訪剡溪。淺斟低唱正相宜”[2],坦率真誠;在其看到山河破碎,對此痛心疾首:“神州畢竟,幾番離合?汗血鹽車無人顧,千里空收駿骨。”[2]直言心中所想。二則,在他郁郁不得志時,也嘆:“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2]雖然不似前者淺露直白,但所抒發的感情并不假,是他從自身真切感受出發而傾吐出來的,表現的是他的真實情感,仍與“真”密切相關。稼軒詞所表現得如此種種的“真”性情和“有境界”讓《人間詞話》為其傾倒。
3.稼軒詞雄偉壯闊的“氣象”
《人間詞話》第四十三則中,王國維從氣象這一點出發進行評價,稱稼軒詞:“即以氣象論,亦有‘橫素波‘干青云之概”,這也是后世人摹稼軒詞學不到的精髓所在。這條評述將重點放在“氣象”二字上,此二字在書中并不少見,王國維常用其評價詞作,如在第十五則評述李煜詞時,在末句以溫庭筠和韋應物二人的《金荃》《浣花》作比來贊李煜詞,稱溫、韋二人詞“能有此氣象耶?”無獨有偶,在第十則中稱贊李白詞作時,王國維亦用:“太白純以氣象勝”[1],以“氣象”評之。這兩則中的“氣象”都是針對一位詞人及其詞作,除此之外,還有針對某類詞作,如第三十則舉《詩經》中《鄭風·風雨》、楚辭《九章·涉江》、秦觀《踏莎行》、王績《野望》中的幾句,以“氣象皆相似”進行評價。以上“氣象”,看似與“胸襟”頗為相似,好像與創作主體的人格息息相關,但由第三十則可看出,這種“氣象”更多地指向詞作本身[3]。劉鋒杰、章池將其概括為“作品的整體風貌與格局”確為妥帖。
王國維對稼軒詞作的整體風貌以“‘橫素波‘干青云”評之,這六字給人的直觀感受是雄偉壯闊的,也與辛棄疾詞作的自身風格契合。王國維以此作評,可見在其心中,一方面對辛詞的整體風貌予以肯定和欣賞;另一方面,則是對辛詞在南宋詞中的“獨超眾類”地位的肯定。以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為例,上闕“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展現了一幅遼遠開闊的南國秋景圖像,詞的下闕“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2]直述自己的憂愁和感慨,既能使讀者對詞風的豪闊有直觀的感受,亦能透過字里行間,從詞人直接傾吐的憂思中深入體會到泛化的哀痛。由此角度觀之,這首詞與《人間詞話》第十則所欣賞稱贊的李白之“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有極為相似之處。
由此觀之,辛棄疾詞這種豪放開闊的氣象與直陳內心郁結的整體風格,使其詞作不會因為重視營造雄偉壯闊的風貌而失去詞人本身細膩的情感,兩相融合得恰到好處,這也是辛詞在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中地位特殊的原因之一。
三、從辛詞的特殊性論王國維的評詞標準
上文分析了稼軒詞具有特殊地位的表現和其內在成因,下文將以辛詞去觀照《人間詞話》中的普遍理論和評詞標準。詞體發展到南宋時,與五代、北宋時期的詞作風貌已有所不同。辛棄疾身處這個時代,辛詞創作于這個時代,也就難逃時代的桎梏。而當王國維仍以品評五代、北宋詞人的標準去看待辛棄疾的詞時,就會遮蔽住辛詞本有的風采。故以辛詞的特殊性為入手點,來觀王國維《人間詞話》中含義模糊、概念沖突之處,則更能發現其評詞標準在具體的實踐中的調和轉圜。
辛棄疾是一位善用典故的詞人,他的作品《賀新郎·送茂嘉十二弟》《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都可稱之為用典的典范。但是反觀王國維一直以來的評判標準,都是立足于詞作的自然真情,用“隔與不隔”評之,其中對詞作用典持消極態度,認為用典易造成“真情感”和“真景物”的隔閡。如《人間詞話》第四十則評永叔詞“‘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則隔矣”[1]而被王國維以“不隔”標舉的詞作,也甚少出現事典和語典。由此可觀他對用典的態度。
如此說來,頻繁用典且以用典為長的稼軒詞無疑是“隔”的代表了,王國維對其的態度理應是抗拒不喜的,但是在手稿本的第五十七則卻評大量用典的《賀新郎·送茂嘉十二弟》為“語語有境界”的典型,對此種矛盾,筆者將引入稼軒詞的具體文本內容,通過分析和審美鑒賞,進一步探究王國維評詞時對這種矛盾的調和。
首先,由稼軒詞的章法結構觀之,像前文提到的兩首詞作,都具有一種以用典作為詞的開啟,以用典收束全詞的獨特抒情脈絡。兩首詞作分別用“千古江山”闡發興衰之感,以“人間別離”道出遇故人辭別之不舍,最后用“憑誰問”和“如許恨”兩句對全詞進行收束,收放自如,不因用典而阻礙詞人傾吐心中之情。
其次,稼軒詞所用的典故與其詞想要表達的感情是緊密相連、互不沖突的,換言之,正是因為用典,使得辛詞的情感更透徹地展現出來[5]。其詞中所提到的無法再尋覓到的英雄孫權、“尋常巷陌”中居住的劉裕和好大喜功的劉義隆以及揮師南下的拓跋燾等人,皆是“千古江山”的匆匆過客,而這些“過客”的典故其實是稼軒抒發心中真實情感的重要媒介,因此究其本質,這些典故運用的目的是“不隔”的。且這些典故的運用也讓作者所抒發的情感變得更加意蘊豐富,若將稼軒詞中的典故減少或者去掉,那么詞的整體就會失去靈魂,顯得空洞無趣。
最后,以辛棄疾自身經歷觀之,辛棄疾處于南宋這一時代,不得不受當時政治、文化生活的束縛。再加上稼軒作為“歸正人”的尷尬身份以及當時南宋朝廷的政治情況,使他無法將內心中報國無門的情緒和當朝統治者行事草率的擔憂直言出來,不得不用典來代替所指的時事,這也導致他的一些詞作只能徒留下“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2]一般的縹緲。這類詞作與稼軒用典之詞相比,雖然更有朦朧的美感,但是如果用“隔與不隔”的標準來看這類詞,反倒是前文所提到的運用典故作為抒情媒介以此來表達內心情緒、創造直觀情境的詞作更為“不隔”。簡而言之,當一位詞人能將運用典故置于對眼前之景、心中之情以及歷史之事和歷史“過客”的“忠實”與“真摯”上,并且使用典故已經是詞人當下抒發胸中情緒的不二之選時,那不管其詞的意蘊是婉轉迂回亦或者是開宗明義,都是“不隔”。
由上述可見,王國維在評價詞作時,其“隔與不隔”的標準并不是沒有轉圜調和的余地的,“隔”與“不隔”不是冰炭不相容的,其評價核心在于“忠實”和“真摯”,他所反對的是詞人的情感被典故所呈現的文字遮蔽住,因此在具體的評價實踐中,王國維并非執而不化,保守唯一標準為宗旨,而是會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通融調和。
四、結語
《人間詞話》中的辛棄疾可謂是個與眾不同的存在,他的詞以及他在王國維心中的地位,處處彰顯著他不同于南宋其他詞人的特殊性。稼軒雖生在南宋,但是卻能與王國維所喜愛的五代、北宋詞人連鑣并軫,這彰顯出稼軒在其心中與眾不同的地位。此外,稼軒詞以用典見長的特點雖然在整體上看來與王國維一直以來對詞作的評價理念相悖,但從稼軒詞的章法結構以及所展現出的情感方面觀之,其彼此是可以兼容的,而正是這一調和兼容,使得本來模糊的義界在對辛詞的批評實踐中走向明朗。總的來說,稼軒詞之所以能在王國維的評價中不同于一般南宋詞人群體,究其原因,與其人格的高遠、真摯自然的“性情”、壯闊雄偉的“氣象”等方面具有突出成就息息相關,這些特點深深地吸引著王國維,同時也揭示出了用典手法在王國維“隔與不隔”的評詞標準里是有一定調和,其重點在“真”和“忠實”之上,并非將其看作固定對立的兩極。
參考文獻
[1] 王國維.人間詞話[M].彭玉平,譯.北京:中華書局,2016.
[2] 辛棄疾.稼軒詞編年箋注//鄧廣銘,箋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 楊祖望.《人間詞話》中辛棄疾的超拔地位與成因——兼論王國維的評詞標準[J].河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1).
[4] 張瀟丹.論王國維《人間詞話》中境界之“真”[J].開封文化藝術職業學院學報,2022(9).
[5] 左卉婧.《人間詞話》中的辛棄疾詞批評研究[J].洛陽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1).
(特約編輯 楊?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