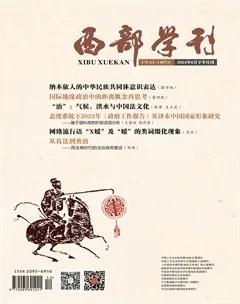國際地緣政治中的距離概念再思考
摘要:通過對地緣政治學位置、距離、區域三要素中最為關鍵而復雜的地理距離概念進行文獻梳理和定性分析,發現其具有模糊性、非同質性、不變性三個方面的不足,認為在國際地緣政治分析中使用“效應距離”概念來代替“地理距離”概念更為恰當,并給出了效應距離的計算公式及其在不對稱情況下的解決途徑。歸納出基于效應距離的國家地緣政治所應當追求的縮短本國核心地區到本國邊境地區的效應距離、謀求增加敵對國家到己方核心地區的效應距離和縮短本國到其他國家的效應距離三種戰略目標,以及實現這些目標的三類手段:大力投資建設國內的交通網絡、追求交通價值低的地理位置作為邊境和追求海洋的控制權。
關鍵詞:地緣政治;地理距離;效應距離
中圖分類號:D80;K901.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4)12-0035-12
Reconsidering the Concept of Distance in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s
Dong Shaozheng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most critical and complex geographical distance concept among the three elements of geopolitics, namely location, distance and region,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shortcomings of geographical distance in terms of vagueness, heterogeneity and invariance, proposes to replace the concept of “geographical distance” with the “effect distance” in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analysis as it would better align with practical needs, and provides the calculation formula for effect distance along with approaches to solving it in asymmetric situations. Finally, three strategic goals based on effect distance in national geopolitics are summarized along with three categories of means to achieve these goals. The three strategic goals are: reducing the effect distance from one countrys own core area to its own border areas, seeking to increase the effect distance from hostile countries to one countrys own core area, and reducing the effect distance from one country to other countries. The three categories of means to achieve these goals are: making a large invest in building domestic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pursuing geographic locations with low transportation value as borders and pursuing control of the oceans.
Keywords: geopolitics; geographical distance; effect distance
地緣政治學研究的是地理與政治之間的關系,核心理論是地理決定論,核心要素是包括位置、距離、區域等要素在內的通常視之為恒久不變的國家地理空間。中國古代多數王朝都實行“遠交近攻”的外交政策,就是基于國家間距離的戰略考量[1]。美國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持續了一百多年,開創這一傳統的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在著名的《告別詞》中指出,美國得以不卷入歐洲列強紛爭的前提條件就是美國獨居一方、遠離他國的地理位置出自“farewell address”“Our detached and distant situation invites and enables us to pursue a different course.”全文參見Advocate of Peace through Justice,Vol.82,No.4(APRIL,1920):120-121.。但實際上,在地緣政治學中,唯有距離這一因素最為關鍵而復雜。表面上看,兩地之間的距離是不變的,但人們可以通過各種交通工具使通行時間縮短,從而使距離的阻隔效應發生變化,故距離對使用不同交通工具與依靠兩條腿走路的人來說,遠近感覺既不一樣,實際效應也大有不同。特別是火車、飛機、輪船、火箭以及音速、光速概念出現以來,距離的阻隔效應大為降低,地理空間越變越“小”,地理距離越變越“近”,傳統地理因素對國家戰略考量的制約力大大減弱。陸俊元指出,在甲、乙兩個行為體之間地緣政治關系抽象模型中,位置、范圍和方向等屬性都失去了意義,唯有它們之間的距離成為其空間關系的唯一指標[2]。同時,對于現代國家而言,一方面,各國都希望能夠更方便地與他國往來,不遺余力地通過各種技術手段修建或改進交通與通信設施,試圖從時間上縮短空間距離;另一方面,彼此距離很近的鄰國之間又常常齟齬不斷,往往通過外交的、政治的、軍事的手段延長或阻隔彼此之間的空間距離,如修建隔離墻就是典型的延長空間距離的做法,又如劃定邊界都希望依托地理屏障而盡量阻隔兩國間的地理距離。這種主客觀在距離認識上的差異,一方面模糊了距離概念、限制了距離概念的應用,另一方面也對與距離概念相關的理論研究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需要我們重新評估國際關系中的距離概念,以使國家的對外戰略更加準確及時。事實上,海權論和陸權論這樣的經典地緣政治理論就是由于理論框架中無法容納技術和其他因素帶來的變化而逐漸過時的[3]。令人遺憾的是,雖然距離概念在國際地緣政治等領域的理論研究中被頻繁提及,在國際沖突和國際貿易的實證研究中也作為控制變量和獨立變量被大量使用,但是針對距離概念本身內涵變化進行的理論分析卻較為少見,對距離概念的認識也多有混淆之處,這與距離概念的應用廣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鑒此,本文擬從距離效應隨著時代科技進步而變化這一視角入手,辨析距離的尺度與效應兩重含義,對“距離”做出評估,提出“效應距離”這個概念,用以衡量和評估國家間“距離”概念的動態性、有效性,并闡述其性質與戰略意義。
一、關于國家間地理距離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國際關系中與距離概念相關的論述最早出現在軍事戰略領域,對距離在國家間戰爭的重要性和作用進行了討論。在兩千多年前的《孫子兵法》中,開篇的《始計篇》就指出代表地理條件的“地”是“兵者五事”之一,而衡量距離的“遠近”則是“地”的四個主要內容之一,《地形篇》也提到計算遠近是“上將之道”分別出自《孫子兵法》“始計”篇,“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地形”篇,“料敵制勝,計險隘遠近,上將之道也”。參見:諸子集成·孫子十家注.上海:上海書店,1986:1-2,176.。《孫子兵法》主要討論了距離在戰爭中的重要性。19世紀的德國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戰爭論》中用了三章的篇幅論述行軍,對距離造成的行軍困難作了詳盡的論述,甚至認為未來行軍速度還會進一步下降[4]。親身經歷過拿破侖征俄慘敗的另一位著名軍事理論家約米尼(Antoine-Henri de Jomini)更是直接指出大規模侵入和遠征“主要的困難就是由距離引起的”,他認為,從己方的作戰發起點到敵方的距離越遠,行軍和后勤保障就會越困難,被敵人迂回側翼的風險也越高,古代游牧民族的千里奔襲在近代已經不可重現[5]。總的來說,早期的軍事戰略研究在當時的技術背景下對距離在戰爭中的作用進行了詳細分析,將距離視為一種重要的制約因素。
從19世紀末地緣政治學的誕生一直到今天,國際關系中與距離概念相關的分析和研究在地緣政治學的框架下不斷出現。到20世紀50年代之前,是早期經典地緣政治理論流行的時代,學者開始將國家作為一個空間現象來描述和解釋,空間和位置在這些理論中具有核心地位[6]15。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認為國家最重要的特征是空間和位置,國家的成就依賴于兩者的相互作用[7]30。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將地理位置作為海權六要素之一,特別強調優勢的地理位置在于靠近敵人或攻擊目標[8]。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通過比較陸路和海路的機動性,論證心臟地帶的空間范圍及其重要性[9]。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用地緣政治學說論證國家對空間的需求,認為海權可以最有效跨越空間,陸權能贏得對空間的統治[7]30。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將地理位置作為影響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10]。在這些理論中,對空間和位置的進一步分析都離不開距離概念,這是因為對空間的描述和衡量依賴距離,地理位置的價值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與各個關鍵地區的距離,距離在此階段仍然被視為靜態的地理因素的一部分。
在20世紀50年代之后,地緣政治學的發展經歷了二戰后的低潮和70年代的復興,逐漸脫離了傳統的“中心—邊緣”范式,對地理因素的關注集中于地理環境與政治現實的互動模式上。學者們普遍認識到地理環境對政治現實的影響是變化的,斯普勞特夫婦(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開創了新的行為認知主義研究路徑[11-13],認為地理環境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存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地理環境是如何被決策者感知和理解的,二是地理環境是如何限制決策實施的。在環境、環境中的行為體以及這兩者間的互相關系中,特別強調了決策者對環境知覺的重要性Sprout的著作中稱之為“ecological triad”(environment, environed entities and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在認識論上,斯普勞特以地理因素決定程度的高低為標準,劃分了從環境決定論到其首創的認知行為論(cognitive behavioralism)的五種路徑,并且論證了認知行為論的合理性這五種路徑分別是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free-will environmentalism, environmental possibilism, environmental probabilism和cognitive behavioralism.。在認知行為主義路徑中,他們認為人所處的心理環境(psychological milieu)與行動環境(operational milieu)是不同的,前者依賴人對環境的主觀認知。簡言之,斯普勞特夫婦強調了人對地理環境的心理認知的變化性,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地理環境對政治現實的影響在不斷變化。
在斯普勞特夫婦之后,地緣政治框架下對包括距離在內的地理因素的研究集中在國際沖突領域。斯塔爾(Harvey Starr)在斯普勞特的環境可能論(environmental possibilism)和認知行為論基礎上建立了機會(opportunity)與意愿(willingness)分析框架,成為之后數十年內較為主流的分析框架[14]。在此基礎上,他認為距離既決定了對外政策的選擇范圍,又影響了國家對選擇范圍內某種政策的選擇意愿[15]。迪爾(Paul Diehl)提出了沖突研究中另一個被后來者廣泛使用的分類框架,將地理因素分為沖突的促進因素和沖突的根源兩大類,距離上的鄰近性兼有這兩種作用[16]。瓦斯克斯(John Vasquez)分析了距離、互動、領土這三種導致鄰國沖突多發的理論解釋,提出了距離解釋的不足[17]。在這一類的研究中,距離上的鄰近性(proximity)與國際沖突的相關性是研究的重點,研究者一般采用遠——近的兩分法來處理距離概念。
除了作為地理因素的一部分被納入分析框架,地緣政治框架下距離因素所產生的直接效應也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提出了重要的LSG(loss-of-strength gradient)理論,認為國家在一個地區能夠投射的力量隨著該地區與本土距離的增加而下降Kenneth Boulding在1962年出版的《沖突與防御:一般理論》一書中提出了“力量遞度損失”理論。轉引自[英]奧沙利文.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M].李亦鳴,朱蘭,朱安,等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1991:11.。奧沙利文也認同這一“距離磨損”理論,認為“一個國家在它的邊境之外施加強權,不管其目的如何,這個發動國的力量將隨著距離的延長而減弱”[18]。亨里克森(Alan Henrikson)在地理距離之外分別基于引力模型、邊界研究和文化建構三個領域的成果,總結了引力(gravitational)、拓撲(topological)和屬性(attributional)三種距離模型[19]。斯塔爾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使用地理信息系統(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將距離等空間數據作為自變量在國際沖突領域的實證研究中使用[20]。格萊第奇(Kristian Gleditsch)指出了國際關系實證研究中幾種處理距離變量方式的缺陷,并提出了一種用最小距離作為距離變量的數據庫[21]。羅布斯特(John Robst)等人將貿易和沖突同時作為因變量,用實證方法研究了距離對國際合作與沖突的綜合影響[22-23]。在這一類研究中,距離概念本身及其屬性開始得到關注和研究,其數據屬性也被發掘并且在實證研究中得到了廣泛應用。
國際關系中與距離相關的研究還出現在國際貿易和后來出現的地緣經濟領域,與距離相關的研究主要圍繞著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的應用。引力模型由廷伯根(Jan Tinbergen)等人在1960年代首先開始使用,認為兩國間的貿易流與兩國經濟總量的乘積成正比,與兩國間距離成反比引力模型基本形式為F=G*M1M2/D,與物理學中的萬有引力公式形式相似,其中F為兩國之間貿易流,M分別為兩國的經濟總量,D為兩國間距離,G為常數參數。90年代之前引力模型的主要相關研究參見:Edward E.Leamer,James Levinsoh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The Evidence[J].Working Papers,1994(4940):44-47.。一般認為,隨著技術進步和全球化進程的推進,距離的重要性應該逐漸下降,但是實證研究表明引力模型中距離的彈性并沒有變化,這種理論預期與實證研究結果的不符引起了不少關注,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經典公式采用的對數線性模型并不適合實際情況,有學者在模型中引入了交通基礎設施等新的變量后得出距離的重要性確實在下降,也有學者收集更大范圍的歷史數據重新驗證模型從而得出距離的重要性在最近幾十年實際在上升[24-26]。在這個領域內,不論是從模型的數學方法還是從理論上對距離作用的討論出發,理論預期與實證不符的距離難題(distance puzzle)仍然沒有得到完美地解決,表明現有的距離概念在地緣政治研究中確實有其局限性。
在國內,與距離概念相關的研究比較少見。在地緣政治領域內,國內的研究在層次上更加偏向于戰略分析,對地理因素的關注不多,深層機理探討有所不足[27]。與距離相關的論述集中于討論地理以及空間因素的重要性。沈偉烈和陸俊元都論述了地理和空間要素在地緣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28]。劉新華將空間距離作為地緣政治的六個地理要素之一并從影響力的角度論述了其作用[29]。在國際貿易領域,施炳展基于引力模型研究了地理距離對貿易流量的減少效應[30]。
在既有研究中,20世紀50年代以后對距離的認識從靜態轉為動態可以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進步。19世紀是科學方法開始進入人文學科的時代,例如,地緣政治學的誕生就深受“物競天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影響,那么物質的、客觀的地理環境被視為決定性的,甚至是宿命性的選擇因素也就不足為奇斯皮克曼是一個例外,他明確地反對地理決定論,但仍將距離作為面積和位置兩個因素中的不變量。參見:Nicholas J.Spykman.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I[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38(1):28-50.。從地理決定論的角度來看,距離的不變性其實是理論合理性的一部分。但是,以靜態的概念決定動態的政治現實本身就是一個悖論,直接從不變的地理環境出發建立的解釋國際政治的元理論必然是機械的,也是無法適應變化的。但是,在從靜態到動態的認識轉變過程中,既有研究在認識論上又出現了矯枉過正的傾向。斯普勞特以及后來斯塔爾等人建立的分析框架實際是在將人的知覺作為地理環境與政治現實的中介,由人的知覺的變化來容納地理環境對人類活動影響效應的變化[31]。這種研究路徑的價值無疑是巨大的,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也走向了地理決定論的反面,變成了認知決定論(科學性)。所以,在既有研究中才會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定性研究中距離概念的作用只在于區分遙遠和鄰近兩種不同狀態,甚至這兩種不同狀態中文化距離、心理距離所起到的作用還要凌駕于地理距離之上;定量研究固然天生地就要從物質主義本體論出發,但是其對距離的認識卻無法借鑒理論研究的成果,反而退回到了靜態的觀點,把距離等同于長度數據。所以,從物質主義本體論出發來研究距離概念、建立一種動態的距離概念,仍然是一個有待填補的空白。
二、地緣政治研究中原有“地理距離”概念的缺陷
“距離”(distance)不論在中文還是英語中都是一個常用詞,但是都包含了多重含義。在《漢語大詞典》中“距離”有三個義項:一是指空間或時間上相隔,二是指空間或時間上相隔的長度,三是指認識和感情方面的差距[32]。從中可以看出,物質意義上的距離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兩地間的地理距離(geographic distance),作為一種客觀尺度存在,通常用米、公里等長度單位來表示,例如,北京到紐約的距離是10 980公里;二是代表兩地間相隔的感受程度,用來衡量距離的效應,通常用主觀感受來表示。例如,北京到武漢的地理距離是固定的,但乘火車與乘飛機者的“遠”“近”感受顯然不一樣,乘普通慢車與乘高鐵的感受也不同,等等。
地理距離對國際政治產生影響的根本原因在于距離的長短決定了人員與物品流動和信息傳遞的難易,換言之,距離是一個基本的限制性條件。距離在經濟上同樣是一個重要的限制性條件,在一個國家的同一市場之內,交通閉塞的偏遠地區往往經濟發展落后。在不同國家之間,距離對外貿產生重要影響,而世界整體范圍內對外貿易額占GDP的比重已經接近30%[33]。蘇珊·斯特蘭奇在分析世界經濟的權力結構時直接將運輸體系作為四種次級權力結構之一[34]。雙邊貿易量隨著兩國距離的增加而減少是國際經濟學中最重要的經驗結論之一,實證研究表明平均距離每增加10%則雙邊貿易額下降9%。此外,距離在限制能力上的減弱還是推動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原因,雖然距離的效應在持續下降,距離在貿易上的重要性自1960年代以來仍然在增加。
綜合起來看,當前的國際地緣政治研究中使用的地理距離概念,有如下不足。
其一是模糊性。地理距離的模糊性體現在其表達方式中。不同地區在地球空間上不同的分布產生了地理上的距離,在幾何學中,這種地理上的距離應該是一個球體表面的兩點之間的球面距離,目前的重力模型設計與分析中基本都采用這種方法事實上地球并非一個正球體,地理距離的詳細計算公式,參見:衛宇.考慮地球曲率情況下兩點距離問題的求解[J].航空兵器,2008(3):7-12.。故用兩點之間的長度來表示距離是最常用的方式,但是兩個地區之間的距離用哪兩個點之間的距離來代表則是一個難以確定的問題,如中俄之間的距離,用北京與莫斯科或北京與海參崴之間的距離來表達差別就很大,而國際關系研究中關注的往往正是國家之間、國家與熱點地區之間的距離。且現實中的國家各自擁有廣袤的領土,是一個面而非一個點,而大國——國際政治領域的主要關注對象——還往往擁有更加廣闊的面積。所以在實際研究中,對于中國、美國和俄羅斯這種幅員遼闊的國家,從不規則的領土形狀中各自選出一個點,并且用連線長度來代表中美距離、中俄距離,是很難有客觀而統一標準的。目前將地理距離作為自變量的研究中,獲取地理距離數據主要有兩種主要方法:一是以兩國邊界之間的距離為準,二是以兩國的中心地點如首都間的距離為準,實際上這兩種方法都各有利弊[35]。前者如中俄邊界長達數千公里,東部與海參崴的距離或西部新疆與俄羅斯新庫茲涅茨克的距離,同樣的尺度會意味著很不一樣的內涵;后者如北京到莫斯科的距離與北京到越南河內的距離,同樣的尺度內也會有很不一樣的意味。彭秋蓮等提出的重力模型回歸分析,也證明了地理距離度量存在偏差從而影響了檢驗結論[36]。地圖是另一種表達距離的常見手段,但是地圖投影的選擇同樣是一個難題。地圖的優點在于不僅借助比例尺提供了兩點之間的空間距離,而且提供了距離與距離之間的比較。但是由三維的球體投影為二維的平面必然導致某些區域的形變,任何一種平面地圖與球面上地理景觀分布在幾何特性上都存在差異[37]。對于最常見的墨卡托投影,緯度越高的地區投影面積相比實際面積越大。麥金德就曾被批評有意使用墨卡托投影“掩蓋了‘樞紐地區和北美之間的真正關系”,“夸大了大英帝國的面積”[11]。距離概念的模糊性還表現在當前的地緣政治研究中,使用地理距離概念的時候往往將實際地理距離與感受地理距離效應這兩種含義相互混淆。例如,在討論距離重要性的研究中,一方面,通常認為隨著技術進步,距離的作用在變小,距離的重要性在降低,這是在使用距離的效用這一層含義;另一方面,卻往往用地理距離的數據來進行驗證,判斷國家之間鄰近與否也以地理距離數字為標準,這毫無疑問是在使用距離的尺度含義。使用不同的距離含義無疑會得出相矛盾的結論。距離的尺度與效用兩重含義之所以會混用,是因為距離的尺度與效用存在著一定的正相關關系,一直以來,兩地間距離尺度大也就意味著距離效用強。例如,中國與歐洲間的地理距離比中國與日本間的地理距離要長,那么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中歐相隔的程度都比中日相隔程度要大。但是這種關系只有在一般意義上的地理距離情況下才能成立,在很多時候地理距離相對較長反而距離的阻隔效應未必較強,例如,中國到西歐地區的距離比中國到里海周邊地區的距離要遠,但事實上中國到西歐顯然比到里海要更容易,因為中國與里海地區陸路近而難暢通,海路則要遠繞紅海、地中海、黑海;地理距離較短也有可能距離的阻隔效應巨大。例如,中國與印度雖然在地理上直接相鄰,但是陸路往來十分困難,在效應上中國和印度其實并沒有感覺很“近”。另外,如果兩個國家地理位置本身就有較大的面積,就難以得到這兩個地理位置之間的準確距離數據。
其二,地理距離在實際的比較操作中無法保持同質性。如果說對距離表達方法的討論只是對距離概念的精確性進行了質疑,那么距離所具有的非同質性則使得這一概念在進一步的分析中幾乎不具有可操作性。所謂距離的非同質性,是指地貌和氣候不同造成的距離上的不等價,也就是實際的自然的地理距離給人們所造成的距離效應是很不相同的,我們可以把它稱為自然距離或地形距離。地球上不同地區的地貌和氣候各不相同,同樣數字的自然距離或地形距離,在不同地區感受不一樣、發揮的效應也不一樣。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平原地區兩點間的實際距離與山區兩點間的實際距離,除飛機之外的任何交通工具所造成的效應是不一樣的,如同樣是100公里的距離,在阿爾卑斯山區、青藏高原與南俄草原、華北平原上的意義截然不同,在高緯度地區的冬天和夏天其意義也不一樣;二是山區或高原兩點之間的距離,下行與上行給人的感覺也是不一樣的,如從云南到西藏,和從西藏到云南,落差6 000多米,同樣距離的運輸,除了飛機之外的任何交通工具,來往難度與所耗時間都是不一樣的。而中印這種隔著喜馬拉雅山脈的鄰國與中蒙這種草原相連的鄰國相比,其距離顯然也不可一概而論。正是因為沒有人會認為丘陵地帶100公里的距離可以等同于平原地區100公里的距離,或者是高原上100公里的距離,地理距離在地緣政治上作為統一尺度的價值往往會大打折扣。
其三,不變性。人類在人員與物品流通方面克服距離限制依靠的是各種交通運輸方式,在信息流通方面克服距離限制依靠的是各種通信方式,付出的代價則是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付出的時間和經濟成本越高,則距離就越遠。所以在現代日常生活中,已慣常用時間距離來表示地理距離,諸如一小時車程、十分鐘步行路程等。當距離的效應被當作衡量距離更精確的手段時,我們會發現距離不再是一個靜態的尺度,而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因為科學技術進步使得人類的交通工具不斷得到改進,速度不斷得到提高。如馬車、汽車、輪船、火車、飛機的相繼出現,速度的不斷提高,時刻在改變著距離在人們心目中的效應,一小時在普通公路與高速公路的車程概念已大不一樣,一小時車程與一小時飛機航程更是不可同日而語。總的來說,運輸能力在運載量和速度方面的不斷提升代表著距離產生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不斷下降。由此可以看出,距離的效應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由科技水平所主導的,這就引出了舊有距離概念的第三個缺陷——不變性。地理上的距離長久以來被認為是不變的物質性因素,而距離的效應卻在不斷變化,以距離不變為前提進行戰略分析自然會得出不準確甚至錯誤的結論。雖然環境因素通過人們對其認知來影響態度和決策,但是限制性的環境因素發揮作用并不依賴于人的認知,甚至可能與其毫不相關。處在克勞塞維茨的時代,自古以來陸路運輸技術的進步并不明顯,所以也難怪他在《戰爭論》中諄諄教導6普里的距離就是一日行軍的極限,他甚至認為隨著軍隊規模增大與給養制度的完善,軍隊的行軍速度會更加緩慢[6]15。可是不到50年之后鐵路出現,德軍總參謀長老毛奇就發現“利用鐵路來運輸部隊,可以比拿破侖時代的行軍速度快6倍。所以作為一切戰略基礎的時空因素都必須作新的計算”[38]。不僅在戰術和作戰層面將距離視為不變因素會產生錯誤結論,在戰略和大戰略層面也是如此。喬治·凱南在討論美國安全形勢時認為“五十年前它對我們并不是很危險,今天,它使我們陷入巨大的危險之中”[39]。而他將這種變化歸咎于理想主義的法律——道德主義方法,未免有些以偏概全。美國絕對安全的基礎其實是美國與歐亞大陸的遙遠距離,但是正如保羅·肯尼迪認為美國的“不易受傷害性”隨著“超遠程轟炸機和洲際彈道導彈的問世”而消失[40],隨著二戰后科學技術的快速進步,這種距離的阻礙效應在快速下降,美國的絕對安全地位也就隨之一去不復返了。
顯然,在日常生活中,地理距離的以上三個缺陷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但在國家間關系上、在戰略決策方面,特別在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爭方面,如果使用固有的距離概念來面對高科技條件下的實際距離效應,就會得出嚴重脫離實際的結論或決策。因為距離是分析國家間地緣競爭必不可少的要素,一個國家追求地緣擴張有兩個方面的約束條件:即其他國家的地緣競爭和地理位置的維持成本。而分析這兩個條件都需要考慮距離。LSG(loss-of-strength gradient)是關于距離的著名理論,主要內容是以數學模型證明了國家在一個地區能夠投射的力量隨著該地區與本土距離的增加而下降[41]。那么對于一個地理位置而言,距離其他國家的遠近決定了國家間在此位置的力量對比,也決定了其他國家在此地維持統治所需要付出的代價。但是,如果使用原有地理距離概念來進行這樣的分析,就會發現在地緣政治的范疇內一切地緣競爭的結果都是固定的。對地緣競爭結果產生影響的因素基本都是地緣政治范疇之外的內容,如經濟發展對國力的影響、國際規范對戰爭和兼并的限制、文明的沖突與軟實力對治理成本的影響等。如果將考察范圍限定在地緣政治范疇之內,由于這些位置的地理環境是不變的,那么在兩國的國力和地理距離都不變的情況下,兩國在給定地理位置的力量對比和地理性質的維持成本也都固定了,兩國間的地緣競爭形勢也就固定了。顯然,這樣的地緣政治分析結果,與實際情況會產生很大差異,其價值將大打折扣。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威廉二世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希特勒,除了其他因素外,用固化的地緣政治眼光審視科技發展背景下的空間距離,從而對世界政治與軍事作出錯誤判斷,應該是一個重要因素。
既然地理距離是一個限制性的條件,用它來衡量地理位置間的遠近,嚴重忽略了距離效應在其中的作用,并有可能嚴重影響國家的戰略決策,特別是有可能造成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爭方面的決策失誤,那么就應該從克服距離的這種模糊性、不準確性出發去尋求更準確明晰描述距離效應的新概念或新方式。
三、效應距離的定義和性質
那么,究竟如何表達科技進步條件下所導致的地理距離效應不斷變化這一動態狀況呢?我們發現,現代運輸方式的運輸路線克服了上述地理距離的非同質性,因為無論是公路、鐵路還是管道、飛機,這些現代交通工具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抹平了不同地形地貌帶來的崇山峻嶺、河流湖海、高原平原等千差萬別,其運輸路線本身不會隨時變化,具有了很強的一致性,可以此為基礎來衡量距離的效應。而區別不同的運輸工具、載重量與運行速度,又使我們能夠更加精確地計算距離效應的具體數據,從而克服舊有距離概念的模糊性與不變性。因此,我們嘗試提出用“效應距離”這個概念來表達處在不斷變化中的地理距離及其效應,可以表述為如下公式:
有效距離=地理距離運輸能力
在這個等式中,地理距離就是距離的尺度,由地理實際決定,以實際數字的形式表達,在給定地理位置的前提下是一個作為分子的不變量。運輸能力則是代表兩地之間各種可行的運輸方式(包括交通工具、運載重量與運行速度)所具有的總運輸能力,既可以用噸位等重量單位,也可以用公里等長度單位,是一個沒有量綱的數字變量,與科技水平成正相關。二者的比值就是用于衡量距離的效應距離概念。對于給定的兩個位置之間,科技水平越高,則運輸能力越強,效應距離也就越小。從遠近程度上描述就是運輸能力越強,效應距離就顯得越短。以20世紀80年代的英阿馬島戰爭為例,從英國樸茨茅斯港出發到馬島橫貫大西洋距離是13 000公里,平均要航行21天。但英國組成的特混艦隊,包括兩艘航空母艦、兩艘核動力潛艇,及兩棲突擊艦、登陸艦、支援艦、補給船、醫院船、油船等近50艘艦只;征用民用商船近60艘,總噸位約68萬噸,其中包括4.5萬噸級的“堪培拉”號客輪、6.7萬噸級的“伊麗莎白女王二世”號大型豪華客輪(均改裝成大型運兵船),和1.8萬噸級的“大西洋運送者”號集裝箱船(改裝成運載20架鷂式戰斗機和其他軍用物資的小航母),軍民輸送艦只達70多艘,總噸位達百萬噸以上,與作戰艦艇的比例接近1∶1,在8 000海里海域上形成了一條川流不息的運輸線,先后載貨10萬噸、燃料油40萬噸以上,人員3.5萬,各種飛機95架[42]。另外,還有一個空軍大隊,包括C-130和Vc-10等大型運輸機600架次,累計出動飛機270架,飛行17 000多小時,由本土向阿森松島空運人員5 600多人、物資7 500余噸[43]。我們姑以一百萬噸運輸能力計算,其13 000公里海路的效應距離幾乎為零,雖遠猶近,英軍等同于在家門口作戰。反觀阿根廷,距馬島最近海岸只有約511公里,故戰前阿根廷總統加爾鐵里囿于地理距離的不變性,以為英國遠隔重洋,在萬里之外,鞭長莫及,如果勞師遠襲,其取勝的希望在“百分之一以下”[44]。嚴重低估了高科技海空運克服大西洋海路投送兵力的效應距離。阿方在“勞埃德”國際航運組織注冊登記的商船有495艘、234余萬噸,但戰時被征用的只有6艘,約4萬噸,[45]加上英軍奪占南喬治亞島后,即實施了對馬島周圍200海里的海、空封鎖,阿方從此不敢再動員組織運輸補給,阿方的戰時輸送能力幾乎為零,等于戰時阿方的效應距離仍然是511公里,雖近猶遠。馬島上雖有阿軍13 000人,背靠祖國,卻嚴重缺乏給養與彈藥,投降時已饑寒交迫。可以說,英阿馬島戰爭就是一個運用現代海空運輸能力大規模遠距離迅速投送強大力量從而大大縮短效應距離而取勝的典型戰例。
距離有空間、時間二個維度,可以分別稱之為空間距離、時間距離。兩地之間的空間距離是不變的,時間距離則是隨著交通工具運行速度的不同而變化的。比如,武漢到北京距離1 181公里,普客17小時車程,高鐵4小時車程,轎車12小時車程。故往往可以用時間距離來表達空間距離,因此,上述等式中,運輸能力除了用噸位表達外,也可以用運輸速度或時間來表達。比如,莫斯科到北京5 843公里,普通火車120公里/小時,其效應距離就是48.7小時;北京到莫斯科,如果是高鐵350公里/小時,其效應距離就是16.7小時。
效應距離的定義方式不僅結合了科技因素和地理因素,也避免了單純使用距離尺度概念的固有缺陷。以距離尺度為分子是地理因素的體現,兩個大面積地區之間的距離數據可以采用運輸里程代替,克服了地理距離數據難以統一的缺陷;在宏觀分析中,距離的模糊性可以容忍,因而效應距離的定義中沿用了距離的舊有概念作為分子。以運輸能力為分母是科技因素的體現,主流的公路、鐵路、水運、空運和管道這幾種物流方式在其基礎設施滿足運行要求的情況下,其運輸過程都基本滿足同質性的要求,不會因為不同的地形地貌而產生不同的時間與經濟成本,所以效應距離的概念克服了距離數據非同質性的缺陷。效應距離是與距離成正比,與運輸能力成反比的一個變量,克服了舊有距離概念不變性的缺陷。總的來說,效應距離概念既與距離的含義緊密相連,又解決了距離概念在模糊性和非同質性上的缺陷,還能體現距離概念中由技術因素主導的變化性,是分析距離概念的一個理想工具。
在效應距離的定義中,效應距離與科技水平成負相關,那么從國家中心主義的視角出發去考察國家間效應距離的時候,就必須面對一個新的問題:不同國家的科技水平是很不一致的。近代的歐洲曾經在科技上遙遙領先世界其他各國,而在今天世界的主要強國之間的科技水平也參差不齊,更不用說強國與弱國之間的科技差距了。舉例來說,19世紀初中國和英國之間雖然隔著同一片海洋,但是中英之間在海運技術上的差距是巨大的,英國擁有規模龐大的遠洋風帆船只和完善的導航技術,如果以英國的運輸能力為分母,效應距離顯然會較小;而以中國的落后運輸能力為分母,效應距離就會較大。那么在討論兩個技術水平不同的國家之間的效應距離時,應該以哪國的科技水平為準呢?這就引出了效應距離不同于距離概念的一個重要特性——效應距離的不對稱性。簡而言之,在A、B兩個技術水平不同的國家之間,從A國到B國的效應距離不等于從B國到A國的效應距離。在之前的例子中,從英國到中國的效應距離應該使用英國的運輸能力作為分母,由于英國的運輸能力較強,這個效應距離是較短的;從中國到英國的效應距離應該使用中國的運輸能力作為分母,由于中國當時的海運能力落后,這個效應距離是相對較長的。也就是說,效應距離是一個向量,雖然中英間的距離尺度數據不變,但是從中國到英國和從英國到中國的效應距離是不同的,這更好地體現了效應距離概念的準確性。具體可以表示為:
英國到中國的有效距離=中英之間的地理距離英國運輸能力
中國到英國的有效距離=中英之間的地理距離中國運輸能力
在和平時期這種效應距離不對稱的差距可能會非常小,在戰爭或者對抗時期這種不對稱的程度可能會大大增加。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對英國的貿易出口相當可觀,但是鴉片戰爭爆發時如果中國想將軍隊從海上運往英國則毫無實現可能。效應距離的不對稱程度在和平時期會縮小,其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和平時期的交通基礎設施是共用的。基礎設施的水平對交通運輸能力至關重要,然而像海港、機場、鐵路這樣的交通基礎設施在兩國之間的運輸路線上卻必須要共用,比如,從中國到巴基斯坦的海運路線除了要利用中國的港口,也必然要用到巴基斯坦的港口。固然有可能運輸路線上的一方基礎設施技術水平較為先進而另一方的設施較為落后,但是不論是從哪國出發,到另一國的運輸線路都必須利用雙方的基礎設施,那么在這方面的差距也就大大縮水了。其次是和平時期可以自由購買先進的交通工具,甚至可以購買技術。在和平時期經濟利益優先,先進的交通工具雖然只有科技發達的國家才能制造,比如,當前能制造大型干線客機并廣泛投入商業使用的也只有美國、歐洲的波音和空中客車兩家公司,但是和平時期技術落后的國家可以向技術先進的國家購買先進的交通工具甚至是交通技術,多付出一些經濟上的代價來換取交通運輸能力。事實上,擁有先進技術的國家也樂于出售先進的交通工具換取經濟利益,落后國家引進交通技術也并非全無可能。所以世界大部分國家無論技術水平強弱都可以向波音、空客等飛機制造公司購買到大型客機,而中國也成功引進并掌握了高鐵技術。
效應距離的不對稱性可以解釋距離概念在重要性上的變化。早在1968年就有學者指出,美國距離泰國—老撾邊境8 500英里,中國距泰國—老撾邊境不過450英里,但是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卻能運送四倍于中國的物資到達該地區,所以距離不再是決定利益相關性和能力的標準[46]。從效應距離出發來解釋,實際上是國家間效應距離在整體上隨著技術進步而縮小了。但是效應距離總體上在縮小并不代表距離概念的重要性在下降。一方面,距離對物品運輸的阻礙性質沒有本質性變化。現有運輸技術雖然相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仍然沒有實現通信技術那樣一步登天式的跨越。最快的空運速度也沒有超過音速,但是信息傳遞速度卻是光速。所以雖然距離對信息傳遞的阻礙已經近乎消失,但是地理距離對物品流動的阻礙仍然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效應距離的不對稱性保證了距離概念的重要性。
四、基于效應距離的大國地緣政治目標
如果用效應距離代替地理距離,就意味著在國力和地理距離都不變的情況下,一個國家可以通過減少效應距離的方式增強其在一個地理位置所能投射的力量,這樣計算得出的結果會與實際情況較為契合。那么,效應距離本身的變化也會成為國家地緣政治目標的一部分。具體地說,一個國家基于效應距離的地緣政治目標,應該包含如下三類。第一,一個國家應該追求縮短本國核心地區到本國邊境地區的效應距離。其目的在于和平時期促進經濟發展,戰爭時期便于調動兵力。這樣在邊境上就增加了己方所能運用的力量,有助于提高安全程度,同時也減少了本國在邊境地區的維持成本。我國在20世紀下半葉于邊境地區修建的戰備公路就是這樣一種設想。第二,一個國家也需要謀求增加敵對國家到己方核心地區的效應距離,這樣在邊境上就減少了對手所能施加的力量,增加了己方的安全。日本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俄國修建西伯利亞鐵路的暗中阻撓,正是出于這樣一種戰略考量。第三,一個國家還應該追求縮短本國到其他國家的效應距離。目的在于和平時期促進外貿,戰爭時期便于支援盟友。前文提及外貿一般隨著距離增加而下降,效應距離與地理距離成正相關,縮小效應距離也就促進了外貿發展,而戰時對盟友國家進行支援,自然也會希望效應距離越小越好。這樣做在敵對國家的邊境地區有可能增加己方所能投射的力量,這是在安全上防患于未然。而對于非敵對國家,根據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引力模型,兩國間的貿易流與兩國間距離成反比,這樣做可以促進國際貿易,增加本國權力與利益。
要達成以上三個地緣政治目標,至少有三種手段需要考慮。
第一,大力投資建設國內的交通網絡,尤其是通往邊境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可以有效縮短本國中心地區到邊境地區的效應距離。交通條件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前文已有論述,而國內交通網絡對軍事調動的意義也不容低估。在普奧戰爭中普軍獲勝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普魯士擁有5條通往波西米亞邊境的鐵路,而奧地利只有1條,使得普軍的調動比奧軍快一倍,用較少的常備部隊反而在戰場上形成了人數優勢[47]。俄國通過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將俄羅斯的亞洲邊境部分和歐洲核心部分連接起來,大大地縮短了到遠東地區的效應距離。“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建設以及與中國的聯通立即帶來了貿易的繁榮”[48]。實現這種戰略目標的主要手段是提升自身的運輸能力和開辟新的運輸路線。英國開鑿蘇伊士運河、美國建設巴拿馬運河,都開辟了新的運輸路線,縮短了到友好國家的效應距離,具有重大的經濟利益。抗日戰爭中中國在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之后失去了主要的外援通道,美國為了繼續對華進行援助,付出巨大代價開辟并維持了駝峰航線,這也是縮短到友好國家的效應距離從而支援盟友的典型。
第二,追求交通價值低的地理位置作為邊境。距離是削弱敵對國家力量的根本,而交通價值低的地理位置一般是交通困難的地形地貌,如戈壁、熱帶雨林等。在這一地區己方破壞交通基礎設施之后,對手的運輸能力很難在短時間提高,效應距離也就相對較遠。交通價值低的地理位置往往具有較高的安全價值,山脈就是兼具這兩種特點的典型地理位置,歷史上法國追求以比利牛斯山脈、阿爾卑斯山脈和萊茵河構成的“天然疆界”就遵循的是這個邏輯;各國間的陸地邊界大多都遵循的是這個原則;同時,這也應該成為劃定陸地邊界的一種戰略考量原則。換句話說,戰略要地往往恰恰是這種交通價值低的地方。如1884年,沙俄吞并了中亞戰略要地謀夫(Merv,今屬土庫曼斯坦的馬雷省),從謀夫到赫拉特的阿富汗西北大門洞開,情形誠如英國地理學家馬爾文(Charles Marvin)所言,如果俄國人進占謀夫,“我們將不得不接受俄國給兩個帝國劃定的邊界,而把威脅印度最好的地點讓給俄國”[49]。又如1898年,保守黨干將喬治·寇松(G N Curzon)出任印度總督,上任之初就制定了使西藏成為英俄之間夾層的戰略方針,并在1904年利用日俄戰爭的時機入侵了西藏,西藏從此逐步淪為英國的勢力范圍[50]。
第三,是追求海洋的控制權。效應距離的不對稱程度在戰爭和對抗時期會增大,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戰爭時期無法使用對手的運輸基礎設施,開辟和維護運輸通道的能力非常依賴于技術水平。戰爭中防止敵方利用己方的運輸基礎設施是重要的防御手段之一,歷史上鐵路軌距之所以有1 435毫米、1 520毫米等多個不同的標準,就是為了防止敵方使用己方鐵路,而戰爭中的雙方顯然也無法直接利用處于對方掌握之中的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所以戰爭時期后方到前線的運輸只能在新開辟的運輸路線上進行,而軍隊行軍過程中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是常態,這就完全依賴國家的相關技術水平。其二,軍事領域匯集了尖端技術,國家之間軍事技術的差距往往比民用技術差距更大,但是軍用技術卻很難擴散。最先進的技術會被迅速用于軍事領域,甚至可以說軍事目的才是技術發展的最大推動力。以飛機為例,技術含量最高的飛機肯定是軍用飛機,從運輸能力上看運載量最大的飛機也是軍用飛機。中國也許可以從美國波音公司購買B747這樣的客機,卻絕對無法從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手中購買到C130這樣的軍用運輸機。其三,在戰爭時期和軍事領域,運輸對經濟成本會更加不敏感。和平時期的運輸需要綜合考慮運量、時間和金錢成本,高技術手段所能達到的運輸能力上限有時并不經濟,比如空運這種高技術含量的運輸方式在總運量中占比較小就是因為空運昂貴的費用。但是在戰爭和對抗時期,經濟利益處于次要地位,達成政治目的才是終極目標,運輸能力的上限反而更為重要。例如,柏林危機期間蘇聯封鎖了柏林的水陸交通,美軍在近一年的時間里用空運的方式向柏林居民運送了211萬噸物資,顯然蘇聯在這里就過高估計了封鎖柏林對西方陣營造成的阻礙效應。所以在戰爭和對抗時期,效應距離對于強國而言還有不計代價進一步縮小的空間。而海洋地區是這種不對稱現象最顯著的地區,這意味著海權國家既可以增加敵對國家到本國的效應距離,又可以減少本國到敵對國家的效應距離。地球表面海洋面積占71%,而所有的主要國家都是沿海國家,海運至今也是大宗物資運輸的最主要方式,而掌握了海權的國家可以輕易掐斷對手的海上運輸能力,敵對國家到海權國家的效應距離可能會變得極大。與馬漢同時代的英國海軍中將菲利普·柯隆布(Philip Colomb)認為,當時的英國可以把海洋作為其領土,海上交通線作為其國內道路,敵國海岸線為其邊界[37]。這種說法對于當時握有絕對海權的國家而言并不夸張,掌握海權的國家投射力量的起點不會被國境線所限制,而是延伸到整個公海。英阿馬島之爭中阿根廷選擇開戰就是忽略了這種不對稱性,嚴重低估了戰時英軍跨越8 000英里海路投送兵力奪回馬島的能力[51],結果阿根廷到馬島的運輸線被英軍截斷,使得阿根廷到馬島的效應距離反而遠大于英國,完全無力支援馬島守軍,這是典型的實際距離與效應距離顯示巨大差異和后果的案例。
可以發現,后兩個目標及其實現手段對于不同的大國來說是互相排斥的,這就構成了大國間的地緣競爭。一個大國在追求第二個目標,增加其他國家到本國核心地區的效應距離時,必然阻止了其他大國追求第三個目標,反之亦然。一個大國追求交通價值低的地理位置為邊界,其鄰國就無法以此地理位置為邊界;一個大國追求海權,必然降低其他大國對海洋的控制力度。由于地理距離是固定不變的,那么競爭就體現在了運輸線和具有交通價值的位置上。以當前的人類社會的科技水平,海運仍然是大宗物品運輸的主流,這就決定了海權在大國地緣競爭中的主要地位。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追求以上三個基于效應距離的地緣目標的手段有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這是因為效應距離雖然具有非對稱性,但是它和地理距離也有正比關系。如果兩國之間增加一片緩沖地區,這既增加了敵對國家到本國的效應距離,其實也減少了本國到敵對國家的效應距離,相當于達成了第二個目標,卻背離了第三個目標。兩國海路間建造一條運河,如果不考慮運河控制權的話,其效應同時減少了彼此之間的效應距離,這相當于達成了第三個目標,卻背離了第二個目標。這些目標和基于地理位置的地緣目標同樣有矛盾之處。一個國家往往會追求控制高價值的地理位置,又會為了保護其安全進一步謀求其周邊的高價值地理位置,如此周而復始,歷史上的俄羅斯帝國就是這樣。而將距離因素考慮進來,在交通價值高的地區擴張領土其實是在減小敵對國家到本國的效應距離,不僅無助于提高安全程度,反而會惡化安全形勢。例如,俄羅斯將領土擴張到東北平原之后,實際上反而使其處于易受攻擊的地位,其在日俄戰爭中的失利就證明了這種地緣態勢的脆弱性。因此,一個國家在考慮本國戰略布局和對外政策框架時,不僅要兼顧效應距離的戰略意義與選擇,同時還有必要在目標之間分出輕重緩急,即超出國界,在更宏觀的區域層面劃分中心地區與邊緣地區之間的主次,以此為基礎決定國家地緣戰略目標的主次與先后。
五、結束語
著名英國政治地理學家杰弗里·帕克曾提到:“政治地理學家相信,權力自身是牢固地根植于世界的自然性質之中的。”[6]1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國家之間在地理上的間隔正是被視為這樣一種不變的自然性質。但是這種地理上的間隔被當作距離概念的全部之時,其模糊性、非同質性和不變性就顯示出了極大的局限性,以這樣的距離概念作為分析基礎,也必然會產生錯誤的推論。實際上,距離所產生的阻礙效應由于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而在不斷下降,以這種動態的距離效應作為距離尺度更加具有科學性。本文通過建立效應距離概念再定義了距離,不僅彌補了舊有距離概念的三種缺陷,而且能夠以效應距離的不對稱性為基礎,推導出國家對于效應距離的幾種戰略目標。這種再定義明確了每個國家都應該在效應距離上追求減少本國到他國的效應距離,而擴大他國到本國的效應距離,也證明了距離概念仍然是戰略分析中的重要一環。
參考文獻:
[1]劉向.戰國策: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90.
[2]陸俊元.論地緣政治中的技術因素[J].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5(6):7-12.
[3]SPROUT H,SPROUT M.Geograph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an era of revolutionary change[J].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60(1):145-161.
[4]克勞塞維茨.戰爭論[M].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2:429-454.
[5]約米尼.戰爭藝術[M].鈕先鐘,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113.
[6]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M].李亦鳴,徐小杰,張榮忠,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7]杰弗里·帕克.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M].劉從德,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
[8]艾·塞·馬漢.海軍戰略[M].蔡鴻干,田常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36.
[9]哈·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M].林爾蔚,陳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66.
[10]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M].俞海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1-37.
[11]SPROUT H,SPROUT M.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J].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57(4):309-328.
[12]SPROUT H, SPROUT M.Geograph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an era of revolutionary change[J].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60(1):145-161.
[13]HAROLD SPROUT.Geopolitical hypothesis in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J].World politics,1963(2):187–212.
[14]HARVEY STARR.“Opportunity” and “willingness as ordering concepts in the study of war[J].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1978(4):363-387.
[15]HARVEY STARR.Territory,proximity,and spatiality: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J].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2005(3):387–406,390,391.
[16]PAUL F.DIEHL.Geography and war:a review and assessment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J].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1991(1):11-27.
[17]JOHN A VASQUEZ.Why do neighbors fight?proximity,interaction,or territoriality[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95(3):277-293.
[18]奧沙利文.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M].李亦鳴,朱蘭,朱安,等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1:11.
[19]ALAN K HENRIKSON.Distance and foreign policy:a political geography approach[J].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2(4):437-466.
[20]STARR H.Opportunity,willingnes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reconceptualizing bord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Political geography,2002(2):243-261.
[21]KRISTIAN S GLEDITSCH,MICHAEL D WARD.Measuring space:a minimum-distance database and applications to international studies[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2001(6):739-758.
[22]JOHN ROBST,SOLOMON POLACHEK,YUAN-CHING CHANG.Geographic proximity,trade,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cooperation[J].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2007(1):1-24.
[23]YUAN-CHING CHANG,SOLOMON POLACHEK,JOHN ROBST.Conflict and tra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ic distanc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J].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4(4):491-509.
[24]DAVID T COE,ARVIND SUBRAMANIAN,NATALIA T TAMIRISA.The missing globalization puzzle:evidence of the declining importance of distance[J].IMF economic review,2007(1):34-58.
[25]BRUN JEAN-FRANOIS,CLINE CARRRE,PATRICK GUILLAUMONT P,et al.Has distance died? evidence from a panel gravity model[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5(1):99-120.
[26]SAMUEL STANDAERT,STIJN RONSSE,BENJAMIN VANDERMARLIERE.Historical trade integration:globalization and the distance puzzle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J].Cliometrica,2016(2):225-250.
[27]杜德斌,段德忠,劉承良,等.1990年以來中國地理學之地緣政治學研究進展[J].地理研究,2015(2):199-212.
[28]沈偉烈.關于地緣政治學研究內容的思考[J].現代國際關系,2001(7):57-61.
[29]劉新華.論地緣政治學的核心:地理要素[J].世界地理研究,2009(1):6-12.
[30]施炳展,冼國明,逯建.地理距離通過何種途徑減少了貿易流量[J].世界經濟,2012(7):22-41.
[31]羅伯特·杰維斯.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M].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3.
[32]羅竹鳳.漢語大詞典:下[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6101.
[33]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of GDP)[EB/OL].World bank group.(2023-03-28)[2024-01-20].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EXP.GNFS.ZS?end=2015&start=1960&year_high_desc=true.
[34]蘇珊·斯特蘭奇.國家與市場[M].楊宇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18.
[35]KRISTIAN S GLEDITSCH,MICHAEL D WARD.Measure space:a minimum-distance database and applications to international studies[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2001(6):739-758,741.
[36]彭秋蓮,陳春斌,劉衛民.談地理距離對加工貿易發展的影響[J].商業時代,2010(2):56-58.
[37]何光強,宋秀琚.地圖投影與全球地緣政治分析:一種空間認知的視角[J].人文地理,2014(2):113-122.
[38]鈕先鐘.西方戰略思想史[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290.
[39]喬治·F·凱南.美國大外交[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133-136.
[40]肯尼迪.戰爭與和平的大戰略[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174.
[41]BOULDING KENNETH E.Conflict and defense:a general theory[M].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2:246.
[42]葉燦.馬島戰爭40周年:這場現代化的島嶼爭奪戰帶來哪些啟示?[J].中國軍轉民,2022(9):76-80.
[43]郭兆東.馬島戰爭中英軍交通運輸保障與啟示[J].國防交通工程與技術,2004(3):1-4.
[44]LAWRENCE FREEDMAN.“The War of the Falkland Islands 1982”,in Foreign Affairs[J].Fall,1982(1):196-210.
[45]賈恒闊.馬島戰爭中英阿雙方戰爭動員的經驗教訓[J].軍事歷史,1994(1):10-12.
[46]WOHLSTETTER A.Illusions of distance[J].Foreign affair,1967(46):242.
[47]馬克斯·布特.戰爭改變歷史:1500年以來的軍事技術、戰爭及歷史進程[M].石祥,譯.北京:軍事誼文出版社,2009:164.
[48]彼得·弗蘭科潘.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M].邵旭東,孫芳,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256.
[49]CHARLES MARVIN.The russians at the gates of heart[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85:49.
[50]傅正.顛倒了的中心與邊緣:地緣政治學的善惡之辨[J].開放時代,2018(6):127-143,8-9.
[51]LAWRENCE FREEDMAN.The war of the Falkland islands[J].Foreign affairs,1982(1):196-210.
作者簡介:董紹政(1988—),男,漢族,湖北武漢人,博士研究生,單位為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研究方向為國際關系學。
(責任編輯:張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