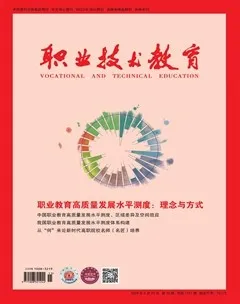省域高職院校分類發展的現實背景、框架設計與推進路徑
何超萍 虞凱


作者簡介
何超萍(1988- ),女,浙江農業商貿職業學院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高職教育管理(紹興,312088);虞凱(1985- ),男,浙江農業商貿職業學院副研究員,研究方向:高職教育管理
基金項目
2020年全國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教育部青年課題“分類視角下省域高水平高職院校差別化發展研究”(EJA200400),主持人:何超萍
摘 要 省域高職院校分類發展,不僅是推進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構建省域現代職教體系的重要舉措,更是政府優化管理,引導高職院校多樣化、特色化發展的有效路徑。本科院校分類評價已進入全面普及階段,但高職院校內部分類及分類評價尚未真正實現。對分類必要性、現狀及問題進行梳理,明確分類的原則和標準,搭建起“3×3+1”的“十宮格”省域高職院校三維分類框架,并以浙江為例,進行了分類運用。提出要轉變管理理念,加強政府宏觀引導,分層分類推進高水平高職院校建設進程;探索多維評價,構建分類評價指標體系,做到現實與未來聯動、共性與個性兼顧;合理運用結果,完善分類評價資源配置,激勵高職院校開展良性競爭;堅持特色辦學,在類型宮格與省域需求中追求高水平,為高質量分類發展提供內生動力。
關鍵詞 省域高職院校;分類標準;分類評價;推進路徑
中圖分類號 G718.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24)15-0061-08
高等教育多樣化發展已經成為國際共識。我國高等教育的規模已位居全球首位,高職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勢頭旺盛。黨的十八大以來,以教育治理現代化為目標構建高校分類發展體系成為從中央到地方的有力行動。據教育部統計數據,2021年,我國共有普通本科院校1238所,在校生1893.1萬人,本科層次職業學校32所,高職(專科)院校1486所,職業本專科在校生1603萬人[1]。面對這一龐大的體量和規模,亟需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高職教育分類發展體系,通過高職院校多樣化發展、特色化發展、高質量發展,從省域層面呈現出分類、錯位、高水平的發展態勢,有力推動了我國從高等教育大國向高等教育強國轉變。
一、省域高職院校分類發展的必要性
省域層面推動高職分類發展,是依據一定標準以及省域實際情況,通過科學分類,對省域內的高職院校劃分新的賽道,將各個高職院校從無序、混亂的競爭模式中解脫出來,引導高職院校開展合理、規范、有序的競爭,進而形成特色化發展的良性競爭循環。
開展高職院校分類,不僅是高職院校自身發展、提高社會認同度和適應性的需求,同時也是政府統籌管理、提高區域高等教育整體發展水平的需求。一方面,政府通過統籌管理,以合理的績效管理體制,激發院校的辦學積極性,引導域內高職院校通過提高專業特色、提升社會服務能力水平來達到分類發展。處于不同類型或同一類型不同向度的高職院校,既可以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還可以對照指標,填補空缺、錯位進取,逐步形成各居其位、各盡其職的區域高職教育布局結構。另一方面,學生和家長以及用人單位、區域內行業企業能夠依據高職院校所屬類別,對其人才培養特色和水平以及社會服務內容、能力及水平有更清晰、直觀的了解,進而作出理性判斷與選擇。
(一)外部因素:經濟社會發展及政府宏觀調控驅動
1.產業升級、制造業、新興產業發展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工作重點之一。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加快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途徑[2]。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需要與產業相匹配的多類型、高素質的技術技能型人才。因此必須從實際需求出發,把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同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結合起來,加快構建省域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培養更多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型人才。當前,省域高職院校發展水平與層次參差不齊,為滿足社會發展需求,亟需引導高職院校依據專業辦學性質差異進行特色化、差別化發展,以提高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的質量和精準性。
2.政府宏觀調控出臺的政策引導力度增加
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提出,要“建立完善的高等學校分類發展政策體系,通過分類設置、分類指導、分類支持、分類評估,引導高校科學定位、特色發展”。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提出要“推進高校分類評價,引導不同類型高校科學定位,辦出特色和水平”。從國家宏觀層面來看,系列政策的出臺表明了以分類管理、分類評價為政策工具,推進高校科學定位、特色發展日益重要并上升到了國家戰略決策高度。
(二)內部因素:扭轉不良發展現狀及主動應對不確定性競爭
1.扭轉高職院校發展同質化與兩極分化的現實需求
隨著“雙高計劃”等不均衡發展策略的深入推行,高職教育內部各院校間的發展形勢與規模的“馬太效應”也愈加凸顯。部分辦學綜合實力強、人才培養水平高的國家“雙高計劃”建設院校已比肩同類本科院校,正積極籌備升格職業本科;而另一部分新建高職院校或基礎薄弱的高職院校,因資源配置和政策支持不夠,還在維持正常運轉的生存線上努力掙扎。正因如此,高職院校為求得生存,爭得資源配置和生源,在專業開設方面逐漸貪大求全,許多院校雖名為行業院校,但在實際辦學方面逐步轉向了綜合院校,辦學特色和辦學重點不夠突出,辦學的同質性現象越加凸顯。因此,亟須通過分類差別化發展扭轉省域高職院校間的不良競爭。
2.主動調節應對即將到來的高等教育層次上移的沖擊
國際經驗表明,隨著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層次結構也會隨之變化。2022年,我國人均GDP已達到12741美元,將進入人均GDP 1萬美元向2萬美元邁進的時代,這一時期是高等教育層次結構調整的重要時期。結合英美日韓等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我國高等教育層次可能會有以下變化:專科比例縮減,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占比適當增加。有專家預測,到2035年,我國比較適宜的高等教育層次結構為:專科層次教育占比為30%~35%,本科層次教育占比為50%~55%,研究生教育層次占比約15%[3]。而教育統計公報顯示,2022年專科在校生人數占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比例為41.5%,因此面向2035年的專科層次學生占比可能會減少6%~10%。基于這一趨勢,高職院校分類特色發展,有利于應對高等教育層次結構變化帶來的沖擊。
二、高職院校分類發展的現實背景
(一)關于高校分類的已有研究
一是關于分類的內涵及意義。高校分類是高校或利益相關者遵循相關規律,選擇特定標準和方法,按照一定目的將高校劃分為不同類別的活動[4],是遵循高等教育發展規律和辦學規律的體現,有利于激發高校自主辦學主動性[5]。將高等教育系統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和層次,有利于人們更好地認識、研究及引導高等教育發展,確定高等教育系統中各子系統及各要素間相互關系[6],是實現高等教育均衡化發展的重要途徑,為實現學科專業特色發展提供現實可能,有利于解決高校與勞動力市場脫節分割的矛盾,同時也順應了世界高校分類管理的趨勢[7]。另外,對于政府及管理部門而言,高校分類發展,有助于高校進行理性的定位,引導同類型高等學校堅持有特色的、內涵式可持續發展[8]。
二是關于分類的角度及標準。高校分類角度眾多,潘懋元等在研究特色型大學的發展過程中,將我國的高等學校分為學術型、應用技術型和職業技術型[9]。李立國等以人才培養定位為基礎,將高等學校劃分為綜合研究型高校、特色研究型高校、應用通用型高校、應用技術型高校、應用技能型高校五類[10]。依據學位授予情況,美國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在2015年版的分類中,將高校依據學位授予情況分為7大類[11]。也有研究者按照3個類型標準和3個層次標準,經組合后從理論上把我國高職院校劃分為72種類型[12]。廣東省教育研究院搭建的廣東高校分類框架,縱向上分“型”:分為一流大學與高水平大學(一流大學、高水平大學)、應用型本科學校(引領型、提升型)、技術技能型院校(示范引領型、改革提升型、規范發展型)三型。橫向上分“類”:將高校劃分為綜合、理工、文科、農醫四個類別[13]。從這一分類框架來看,廣東高校可分為7型4類共28種類型。總的來看,高校分類發展已經得到研究者的廣泛認同,但對于高職院校的分類研究少,大多散見于或穿插在對普通高校的分類研究之中。已有關于高職分類的研究,分類方法以產業相關進行劃分,適應面和覆蓋面有限,而分類過多過細會失去分類原有的意義。
三是分類的政策梳理。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高校分類體系,實行分類管理.....引導高校合理定位”。自此,我國高等學校由以往的縱向分層建設為主階段,轉入橫向分類發展不同高等學校體系階段[14]。2014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首次提出了職業本科、專業碩士研究生的職業教育層次。2017年,在關于“十三五”時期高等學校設置文件中,教育部將高職院校整體劃分為一類,即“職業技能型”高等學校。
(二)高校分類的省域實踐
1.本科高校分類實踐
目前,已有多個省份探索開展省域高校分類管理。省域高校分類呈現出多種趨勢。一是針對本科院校進行層次分類。如北京將市屬公辦本科高校分為高水平研究型大學、高水平研究型大學(B類)、高水平特色型大學、高水平特色型大學(B類)和高水平應用型大學[15]。二是按照“人才培養定位及科研類型+專業集中度”進行分類。上海是最早開展高校分類管理的省市之一,按照人才培養主體功能和承擔科學研究類型等差異性,將高校劃分為學術研究、應用研究、應用技術和應用技能四種類型,按照學科專業集中度,將高校分為綜合性、多科性、特色性,再通過橫縱結合,形成了高校“十二宮格”,這一分類標準轉化為全國首個地方高等教育法規《上海市高等教育促進條例》的組成部分,為上海全面實施高校分類評價提供了法律保障。與上海相似,重慶將本科高校分為學術研究型、應用研究型、應用技術型三種類型以及學科專業綜合性、多科性、特色性三個類別的“類型+類別”的本科高校分類發展定位。浙江省在2016年將本科高校按主體功能分為研究為主型、教學研究型、教學為主型三類,根據學科門類、專業數量等分為多科性和綜合性,又在2019年根據學位授予層次及培養能力,將全省本科學校劃分為“具有博士生培養高校、具有碩士生培養高校、學士學位授予型高校和獨立學院”4類,并建立了4套對應的評價指標體系。
2.高職院校分類實踐
對照上海“十二宮格”指標要求,高職院校屬于應用技能型高校,并內部劃分為綜合性應用技能型、多科性應用技能型、特色性應用技能型三種。廣東自2017年起實施高等職業教育“創新強校工程”,將省屬高職院校根據建設層次劃分為ABC三大類別,建設目標和任務也有差異化指導意見,并以此為依據,構建起三套考核指標體系。浙江省從2020年開始試行高職院校綜合督導評估,全省所有高職院校通用一套考核體系,即將全省高職統分為一個類型。江蘇省從2019年開始實施省屬高校年度綜合考核,以是否為“高水平高職院校建設單位”為分類標準,將省屬高職分為“高水平高職院校”和“其他高職院校”兩類[16]。
(三)高職院校分類的問題
1.高職院校分類關注度不足,研究成果較少
一是頂層設計不足。政府對高職分類發展的關注不夠,現有政策文件除《關于“十三五”時期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意見》外,尚未有正式的國家層面針對高職院校分類的文件。二是研究成果較少。從已有研究和省域政策實踐層面來看,目前針對高校分類發展、分類管理的研究及政策文件,大多著眼于對省域內的本科院校進行分層分類管理評價,而對高職院校缺乏有針對性的分類研究。三是職業本科學校分類發展引導不足。作為高等教育領域的新事物,職業本科學校自2019年以后新生并逐步發展壯大,但目前整體數量在高等教育中占比還很少,因此在本科院校的分類管理、分類發展、分類評價體系中,難以兼顧職業本科學校的發展特色指標,職業教育類型屬性未得到應有體現。
2.高職院校缺乏細化分類,評價考核引領力有待提升
與普通本科院校相比,高職院校分類發展落實的范圍小,實踐層面缺乏科學的分類標準,高職院校內部類型的區分度不夠清晰。在開展高職院校考核評價的省份中,除廣東、上海等少數省份有高職內部類型劃分外,大多數省份都將省域內高職籠統劃歸為一類,缺乏細致的分類,且評價指標體系缺乏賽道區分度,大多為同一套考核指標,即綜合排名評價,對學校的專業辦學性質、開設專業、服務面向等辦學特色體現不足,對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院校也缺乏差別化認知,評價的公平性不足,評價的激勵機制和反饋機制的效用發揮有限,導致高職院校群體難以走出辦學層次本科化、專業開設綜合化、辦學體量擴大化的發展誤區。
三、省域高職院校分類發展的框架設計
省域高職院校分類發展不能機械地依靠院校自然形態進行被動、消極地“分類”,而是需要政府層面基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特點以及職業教育類型特征和發展規律,重視并適應院校多樣性差異,全面統籌不同院校辦學實際,做到院校分類全覆蓋。
(一)省域高職分類的原則
一是注重分類的科學性。推進省域高職院校分類發展,必須構建起科學合理的高職分類框架。而框架構建的關鍵環節是明確分類的標準和依據。要增強標準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明確分類的內涵和指向。標準應以定量標準為主,定性標準為輔。要避免“為分類而分類”、將分類指標劃分得過多過細,導致出現大量類型沒有對應院校的空白分類情況。
二是考慮歷史延續性及現實可行性。需要堅持現實與邏輯相統一原則,既要尊重省域高職教育的現實布局,也要遵循高職教育類型發展的內在邏輯。分類要充分考慮已有的發展秩序,如國家和省級層面的高職重點校、示范校、“雙高”校建設,這既是對以往發展政策的接續與利用,也尊重了院校的發展實際,且具有顯著的便捷性與可行性,同時也是獲得科學性與公信度的重要做法。
三是保持和促進高職院校的多樣性。分類不是為了排名次,而是為院校發展提供更加自由寬松的環境,避免重復建設、同質化的惡性競爭,實現院校發展的個性化。合理的分類要以促進和提升院校的多樣化發展為原則,幫助院校依據自身發展情況選取合適的發展賽道,在同類型院校中爭創高水平。
四是堅持橫向分類縱向分層相結合[17]。已有的高職院校發展秩序,以縱向層次劃分為主,橫向分類的實踐較少。但僅注重縱向層次劃分,容易導致高職院校發展的同質化、單一化,難以實現多樣性特色化發展。因此,對省域高職院校的分類,既要做到對院校的不同類別進行劃分,也要對同一類別院校不同發展階段層次進行劃分。
(二)省域高職分類標準及三維分類框架
總體來看,雖然各省高校分類各不相同,但在實際的分類過程中,各種分類標準和方式組合運用,在不同中又有相通之處。即本質上是從學科構成和辦學類型兩個基本維度出發,將高校細分為不同類別,再將以上兩個基本維度兩兩組合[18],得到本省所需要的類型“宮格”。基于以上規律,構建有區分度且簡潔直觀的分類框架可以從三個維度展開。
維度一:按照人才培養層次進行縱向分層。當前國家層面大力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構建完整的現代職教體系、打破職業教育專科層次“天花板”、落實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要求,發展職教本科成為省域層面完善職業教育體系的重要做法之一。按照人才培養層次將高職院校分為本科層次高等職業學校、專科層次高等職業學校。
維度二:按照院校辦學專業性質進行橫向分類。省域高職的舉辦主體及隸屬關系多樣,在吸取普通本科高校分類經驗的基礎上,以辦學的專業性質為標準,按照相似相近、科學簡化的原則,將高職院校劃分為綜合類、理工農醫類、文科類三大類,以此建立同類或相似相近類高職院校可比較的基礎。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科層次高等職業學校全國僅33所,平均每個省擁有1~2所,且大都處于新建階段,因此,為避免無意義的過度分類,目前僅對專科高職進行內部橫向分類,待本科層次高等職業學校發展到一定成熟階段再進行內部橫向分類。
維度三:按照建設層次劃定專科高職首次發展階段。受發展基礎、辦學特色、環境和政策等多方因素影響,各高職院校的發展階段也有較大差距。為了引導同類型、同階段的院校進行科學、健康、可持續的競爭,需要對專科高職進行縱向發展階段的劃分。從尊重現狀、延續歷史政策和便于操作角度而言,按照高水平高職院校建設層次,對專科高職進行縱向再分層,以此作為首次確定專科高職院校所處發展階段的依據。目前,國家層面的高水平院校建設計劃主要是2019年12月發布的國家“雙高計劃”。同時,全國大部分省在國家“雙高計劃”的引領下開展了省級層面的高水平高職院校建設項目。如浙江省2020年公布了省高水平職業院校和專業(群)建設名單,包括15所省高水平職業院校建設單位以及20所高水平專業群建設單位。因此,按照建設層次將省域高職院校劃分為“國家高水平階段、省級高水平階段、規范發展階段(未納入國家及省級高水平院校建設項目)”三個層次。其中,首次確定的“國家高水平階段”包括了國家高水平專業群建設單位,首次確定的“省級高水平階段”涵蓋了省級高水平專業群建設單位,同屬國家和省級兩個層級的,按就高層次計算。見表1。
(三)以浙江為例的省域高職分類運用
2023年,浙江省在建設高教強省方面動作頻出,通過召開高層次推進會、出臺專門政策等舉措,分層分類推動不同類型高校特色化高水平高質量發展。浙江省目前有高等職業院校51所,其中本科層次2所,專科層次49所。按照專業辦學性質,專科層次49所院校包含綜合類21所、財經類9所、理工類10所、農業類2所、師范類2所、體育類1所、醫藥類1所、藝術類2所、政法類1所,院校的層次類型分布具有普遍代表性。從建設層次來看,國家高水平高職院校(含高水平專業群建設院校)15所;省級高水平高職院校(含省高水平專業群建設院校)35所,其中含國家高水平高職院校9所;未納入國家及省級高水平建設項目的其他院校10所。
按照省域高職院校三維分類框架,浙江省高等職業院校分類見表2,其中,職業本科類2所;專科層次,國家高水平階段:綜合類5所、理工農醫類3所、文科類7所,省級高水平階段:綜合類13所、理工農醫類7所、文科類4所,規范發展階段:綜合類3所、理工農醫類3所、文科類4所。
從表2中可以看出,全省51所高等職業院校被分在了“3×3+1”的“十宮格”中,依照分類的三個維度,各個院校均有分類落腳點,做到各有所歸。以浙江農業商貿職業學院為例,學校辦學專業性質為農業類院校,省級高水平專業群建設單位,按照分層分類維度,學院從屬于省級高水平階段的理工農醫類院校。
四、省域高職院校分類發展的推進路徑
(一)轉變管理理念,加強政府宏觀引導,分層分類推進高水平高職院校建設進程
僅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由發揮來推動高職院校的發展,極容易引發高職院校產生一定程度錯位與混亂,只有“自生秩序”與“分類引導”有機結合[19],才能推動高職教育平穩有序發展,因此宏觀科學的政府引導對高職院校分類發展極為重要。
1.轉變重分層的管理理念
高職分類不是劃定院校身份高低等級,而是要凸顯培養不同類型職業技能人才的辦學導向。要在以往重層次、劃等級的政策引導基礎上增加橫向分類,按照相似相近、科學簡化的原則,將專科層次職業學校劃分為綜合類、理工農醫類、文科類三大類,并建立對應類別的評價指標,以此建立同類或相似相近類高職院校可比較的基礎,避免院校盲目追求高層次而走向同質化辦學的歧途。
2.完善省域頂層制度設計
一方面,省級政府需要更新或制定省級層面的職業教育法實施細則(即《省級職業教育條例》),為省域高職分類發展提供制度保障。以浙江省為例,1991年出臺了《中等職業教育條例》,至今已30余年,內容條款早已不符合現實需求,且該條例只限于中等職業教育,對于高等職業教育沒有涉及。因此,各省應當在吃透新《職業教育法》精神的基礎上,結合省域發展實際,出臺有針對性的《省級職業教育條例》。目前,山東省已經走在前列,修訂后的《山東省職業教育條例》將在2024年5月1日起施行。另一方面,要基于《省級職業教育條例》,出臺對應的發展規劃、政策標準等配套制度,可參考《廣東省高職教育“創新強校工程”》,劃定高職教育發展的宏觀框架,引導各類型高職院校錯位發展,優化省域高職教育布局結構。
(二)探索多維評價,構建分類評價指標體系,做到現實與未來聯動、共性與個性兼顧
為避免使用同一套發展目標和評價標準,考核辦學基礎和辦學規模相去甚遠的幾十所高職院校,需要政府部門科學劃定省域內高職院校發展的目標與檔次。通過制定出臺每類院校的特征、發展目標和具體要求,與學校實際情況對照進行發展績效考核評估,并通過分類管理政策及指標框架的引導,推動高職院校在框架內主動尋求特色發展。
1.設定“國際先進水平階段”評價指標,引導鼓勵國家高水平階段院校發展
“雙高計劃”提出,到2035年,一批高職學校和專業群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按照這一要求,在專科層次高職院校的評價指標中增加“國際先進水平階段”相關內容。該階段主要圍繞“專業設置深度對接區域優勢產業鏈、擁有大批行業專家大師組成的教師團隊、建設廣受師生認可的國際一流課程、形成培養世界一流杰出技能人才的特色模式、產教深度融合命運共同體運行有效、建成國際先進水平的實驗實訓室”[20]等幾方面構建評價指標。要說明的是,該階段評價指標為面向2035年遠景目標,僅作為國家高水平階段院校今后10年的發展目標引導,暫不列入院校目前的實際類別劃分中。
2.評價指標既要考慮共性也要突出個性
評價高職院校,既要對學校的基本職能情況進行評價,也要對院校的專業辦學性質差異加以考慮,既要圍繞“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四大基本職能設置評價指標,也要對“辦學聲譽特色”加以區別評價。因此,分類評價指標不能過于共性化,這樣既為不同類型學校預留特色發展空間,又保證了同一類型中不同院校具有同向度的可比性。比如,浙江農業商貿職業學院作為一所農業類院校,相較于其他類型院校,該校在服務鄉村全面振興方面具有顯著優勢;但另一方面,學生就業方向為涉農領域,在“畢業生薪酬”方面的評價指標中,初期階段的薪酬標準很難與其他類型畢業生相比較。因此,在分類評價中應適當考慮有專業性質區分的考核指標,需要針對院校類型,在相關指標中設置不同比例的滿分標準或者分數權重。
3.單獨構建職業本科學校的評價指標體系
2021年11月,教育部辦公廳出臺了《本科層次職業學校本科教學工作合格評估指標和基本要求(試行)》,要求“教學條件基本達標,教學管理基本規范,教學質量基本保證”,達到本科辦學標準的“及格線”。但從高質量可持續發展角度來看,省域層面對職業本科學校的引導力度不足,針對職業本科學校的年度考核評價體系還不完善。各省可以在參考本科教學工作合格評估指標的基礎上,適度提高建設標準,突出強化職業屬性,并結合省份特點,單獨設立一套省域職業本科學校的評價指標體系,以推進職業本科學校盡快從初創期過渡至平穩辦學期[21],為省域現代職教體系的完善發揮應有作用。
綜上所述,省域層面應當設立“職業本科、綜合類、理工農醫類、文科類”四套評價指標。可以參考“雙高計劃”的實施意見設定相關指標,并根據省域實際情況,設立核心指標和特色項目,用以凸顯不同專業性質院校的辦學特色。同時,每一套評價體系還需要在指標難度上細化分層,劃分出國際高水平階段、國家高水平階段、省級高水平階段、規范發展階段考核要求,由此搭建起符合實際的高職院校分類評價體系。
(三)合理運用結果,完善分類評價資源配置,激勵高職院校開展良性競爭
只有高職院校按照自身所屬賽道的考核指標進行提升和發展,才能達到調整高職教育結構、引導省域內高職科學定位、特色發展的目的。而高職院校對所屬類型的認同并努力的外部環境,就是對應類型背后所標榜的政策條件、資源配置。也只有將類型及考核結果與政策條件和資源配置相掛鉤,才能推動院校朝著類型考核指標引導的發展方向前進。
1.以資源配置政策落地分類評價考核結果
目前各省域運用分類評價結果的目的主要有考核問責、激勵選拔、診斷改進三種導向。總的來看,各省分類評價結果運用雖然有不同導向,但各類導向都附帶以資源配置作為結果運用的砝碼,加大了將評價結果落到實際的力度。因此,在高職院校分類評價中也要做好相關的資源配置,建立健全評價結果的實踐運行機制,從財政撥款、建設項目遴選、院校辦學獎懲等方面逐步配套完善,既要運用好財政資金,又要結合政策激勵,為引導省域高職院校在同類院校序列中開展良性競爭,實現以評促建的目的打下“強心劑”。如將同類院校的年度考核結果分為“優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個等級,在申報下一輪省級“雙高計劃”時,設定近三年考核至少1次優秀的,方可參與遴選;也可以將評價考核結果與某一個或幾個專項財政撥款相掛鉤,按照考核結果進行一定差額的比例下撥經費;還可以運用多重導向相結合的方式落地考核結果,即,同類型不同等級的高職院校賦予不同等級的財政經費,同時發展檔次可以根據年度分類考核結果動態調整,如三年內考核2次“優秀”的,可以提升1個檔次,考核“不合格”達到2次的,需要降低1個檔次,以此形成“規范發展階段”向“省級高水平階段”看齊,“省級高水平階段”向“國家高水平階段”看齊,“國家高水平階段”向“國際高水平”看齊的良性競爭氛圍。通過諸如此類的資源配置形式將分類評價考核結果落地。
2.注重考核評價的公平公正
考核評價結果的運用,是引導和激勵各類型高職院校分類發展、特色發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一環,也是政府對高職院校分類管理的有力抓手。因此,對省域高職院校的分類考核評價,需要利益相關者和第三方專業機構共同參與,以保證評價結果達到公平、公正、公開的目的。行業企業作為利益相關者參與評價,主要可以在學生實習基地建設、實踐實訓教學等方面發揮作用。同時,穩妥謹慎選擇第三方評價機構,應當由政府牽頭,結合省域高職院校分類發展實際,確定和選擇機構。為保證評價的科學性與權威性,第三方評價機構在完成評價后,教育主管部門應及時對該機構評價工作的及時性、專業性與公正性進行“再評價”[22]。
(四)堅持特色辦學,在類型宮格與省域需求中追求高水平,為高質量分類發展提供內生動力
要實現高職院校分類特色化發展,需要不斷提升高職院校的辦學質量,以滿足學生多樣化的教育需求,同時應對生源減少、教育層次上移的發展趨勢。需要在自身所在的類型賽道中不斷追求高水平、高質量發展,通過調整目標定位發展策略、強化關鍵辦學能力等手段,增強發展的內生動力。
1.目標定位與發展策略差異化
一方面,高職院校要根據自身實際情況,明確在“十宮格”中的類型、層次及定位,在省域范疇和自身類型定位中激發特色,追求高水平和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面對激烈的競爭,難以實現全面高水平高質量發展,需要在堅持特色化、差別化辦學中尋求突破,緊密結合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和需求,在改革中形成具有院校“標簽”特色的產教融合模式、專業品牌和人才培養模式。如浙江農業商貿職業學院,辦學綜合排名在省內高職院校中處于中后段,難以比肩省內頭部的綜合類高職院校辦學水平。但同時,學校也是省內唯一一所“農”字頭高職院校,學校應當在發展目標和策略上加以調整,通過錯位發展,突出農業辦學特色,培養符合區域農業農村發展所需的知農愛農新型人才。
2.加強高職院校關鍵辦學能力建設
關鍵辦學能力是“一個在實踐中產生的概念”[23],對于高職院校而言,關鍵辦學能力是學校高質量分類發展的核心要素和可持續發展動力。首先,要持續完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體系,發展定位及目標深度聚焦于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其次,各類型院校要基于自身所屬類型賽道,打造一批優質專業的課程開發、師資培養、教學改革等主題的基地和平臺,并以基地平臺為依托,在課程、教材、實踐項目、信息化等教學資源建設方面達到示范引領水平;第三,推進產教深度融合,通過建設市域產教聯合體等新型產教融合平臺,推動建設行業企業的新技術新標準,及時有效地融入教育教學活動中;第四,加大人才引進力度,通過內培外引、改善人才待遇等多重舉措,匯集人才資源,打造專家大師集聚的高水平師資團隊;第五,深挖院校自身辦學特色,主動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積極對接新業態新職業要求,創新社會服務內容形式,開展“社會所需、院校所能”的高質量社會服務和科技服務工作。
參 考 文 獻
[1]教育部.2021年教育統計數據——全國基本情況[EB/OL].(2022-12-30)[2024-03-30].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2021/quanguo/.
[2]李芃達,姚進,馬春陽,等.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N].經濟日報,2023-03-09(001).
[3]李立國,趙闊,杜帆.經濟增長視角下的高等教育層次結構變化[J].教育研究,2022(2):138-149.
[4]陳厚豐.中國高等學校分類問題研究[D].長沙:湖南大學,2004.
[5]史秋衡,康敏.探索我國高等學校分類體系設計[J].中國高等教育,2017(2):40-44.
[6][17]潘懋元,陳厚豐.高等教育分類的方法論問題[J]高等教育研究,2006(3):8-13.
[7]張旺,龍柯.“雙一流”建設背景下高校分類發展的依據及實踐路徑[J].教育評論,2018(1):3-7.
[8]杜彬恒,王瀟晨.回顧與展望:中國高校分類問題研究20年——基于CiteSpace知識圖譜的分析[J].高等建筑教育,2019(1):1-10.
[9]潘懋元,王琪.從高等教育分類看我國特色型大學發展[J].中國高等教育,2010(5):17-19.
[10]李立國,薛新龍.建立以人才培養定位為基礎的高等教育分類體系[J].教育研究,2018(3):62-69.
[11]王茹,高珊,吳迪.美國2015版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介紹[J].世界教育信息,2017(9):41-43.
[12]李海貴.我國職業類高校分類體系研究[D].長沙:湖南大學,2016.
[13]廣東省教育研究院.廣東省高等學校分類建設框架與標準體系研制報告[EB/OL].(2018-02-23)[2024-03-30].https://gdae.gdedu.gov.cn/gdjyyjy/yjcgd/202008/80a69ea8a04048e8a5573b38ddf62ebe.shtml.
[14]陳偉.省域高等學校分類發展:政策邏輯與實踐路徑[J].教育發展研究,2020(3):1-7.
[15]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領導小組.關于印發《北京市屬公辦本科高校分類發展方案》的通知(京教組發[2020]4號)[Z].2020-05-09.
[16]謝永華.江蘇省高等職業教育差異化分類考核研究[J].江蘇高職教育,2020(3):45-49.
[18]張艷國.科學用好高等教育分類評價重要方法[J].中國大學教學,2023(4):67-75.
[19]陳厚豐,李海貴.我國職業類高校分類初探[J].職教論壇,2015(33):11-16.
[20]劉松林,賴韻臻,陳琳.國際先進水平高職專業群的特征、要素與建設路徑[J].現代教育管理,2023(10):116-128.
[21]何超萍.合并轉設背景下職業本科高質量發展的應然價值、現實問題與推進策略[J].教育與職業,2023(4):64-69.
[22]劉曉,王露瑩.“雙高計劃”高職院校辦學評價:理論審視與現實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2(5):139-143+200.
[23]周保平,孫琳,馬培安.職業學校關鍵辦學能力提升的現實意義和政策語境分析[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23(21):28-32.
Realistic Background, Framework Design and Promotion Paths of the Classified Development of Provincia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e Chaoping, Yu Kai
Abstract? The classified development of provincia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build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but also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government to optimize management and guide the diversified and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of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comprehensive popularization, but the internal class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not been really realized.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necessity,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classification, clarifies the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of classification, sets up the 3-dimensional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of “ten grids” provincia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th “3×3 + 1”, and takes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for class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It is proposed to change the management concept,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s macro-guidanc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a layered and classified manner; explore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build a classified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and achieve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and take into account both commonalities and individuality; reasonably use the results,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classified evaluation resources, and encourag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engage in healthy competition; adhere to distinctive school-running, pursue high levels in the type grid and provincial needs, and provide endogenous impetus for high-quality classifi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provincia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promotion paths
Author? He Chaoping,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Zhejiang Agricultural Business College (Shaoxing 312088); Yu Kai, associate researcher of Zhejiang Agricultural Business Colle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