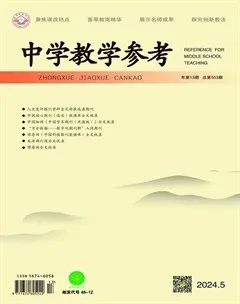筆底蘊“春秋” 凡語見至情
劉志軍
[摘 要]歸有光的散文《項脊軒志》感情至深,為后世傳誦。在閱讀和教學時,可以嘗試借助“春秋筆法”來尋找新的切入點,從詞語的打磨、內容的安排和情感的褒貶等角度解讀文本,探尋《項脊軒志》中尋常話語背后的精微意蘊,從而更好地領略文言散文獨特的意趣,提升閱讀審美品位。
[關鍵詞]春秋筆法;《項脊軒志》;文言散文;解讀
[中圖分類號]??? G63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058(2024)13-0004-03
“春秋筆法”由孔子開創,由司馬遷發揚光大,廣泛地應用于后世的文學作品創作中。文法作為“春秋筆法”的第三種樣態,與經法、史法并列,具有“尚簡用晦”和“一字褒貶”等特點,在文學作品中體現在字詞的精妙運用、事件的精心選擇和情感的含蓄表達上。
明代文學家歸有光對司馬遷和《史記》推崇有加,后世評論者也頗認為歸氏作品得《史記》之神,如黃宗羲“震川之所以見重于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本文嘗試從“春秋筆法”的角度來賞析歸有光的散文代表作《項脊軒志》,探尋文言散文獨特的意趣,為文言散文的閱讀和教學尋找新的切入點。
一、斟酌推敲,追求用語簡約之佳境
司馬遷對微言大義的簡約文風是激賞的,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他評價屈原的作品“其文約,其辭微”,而他的《史記》其實也處處流露出“微言大義”的風格。歸有光的《項脊軒志》全文約八百字,分前后兩部分,成文時間相差了十多年,記述了其書齋“項脊軒”在十幾年間的變化,以及若干與這間書齋有關的人和事。如果不是言辭簡約、蘊意豐富,這樣的文本效果是無法產生的。短文要想言簡義豐,就要重“煉字”。且不說文中“借書滿架……珊珊可愛”這段膾炙人口的描寫,單是一些看似尋常的遣詞,也能讓人深感歸有光對文約辭微境界的用心追求。
講老屋之破,歸有光用“雨澤下注”。“注”雖是很常見的動詞,用在此處卻極為貼切。在屋內都能感受到大雨如注,可見房屋破敗成何等模樣,相比“漏”“滴”“流”這些動詞,“注”的力度更到位,并使得相關形象更突出。
對母親和祖母,歸有光充滿了深深的懷念。同樣是睹物思人,情感的表達卻不盡相同。歸有光自幼失恃,母親留給他的印象應不會很深,關于母親的往事只能通過旁人轉述得知,這種間接的體驗對情感的沖擊是有限的,故歸有光寫“余泣”;而祖母卻不同,她不僅與歸有光相伴時日較長,還對其充滿愛憐和期待,故歸有光“瞻顧遺跡”時“長號不自禁”。一“泣”一“號”,盡顯個中的情感強弱之別,毫不做作地道出了真實的人間親情。
除動詞的推敲外,歸有光在名詞的取舍上也頗費匠心。在“諸父異爨”后,“庭中始為籬,已為墻”,從“籬”到“墻”,似乎只是隔斷的材質發生了變化,但實際上這一字之變,卻蘊藏歸有光難以言說的辛酸和無奈。用竹籬來隔斷,雖然“隔”但并未真的“斷”,可以聞其聲、見其人,甚至可以隔著竹籬傳遞東西,“隔籬呼取盡余杯”,竹籬兩邊的人依然可以暢通地交流。而“墻”則完全不同,聞聲不見人,是生人還是熟人,墻那端的人在做什么都無從知曉;在墻的這邊說話,還會擔心隔墻有耳。本來是不分彼此的一家人,有了“籬”已經產生了距離,而一堵“墻”無異于在一家人之間豎起了厚障壁。
“項脊軒”在文中有多個稱法,從一開始的“舊南閣子”“老屋”到“軒”再到后來的“室”“南閣子”,也并非歸有光隨意為之。我們發現,當歸有光稱它為“軒”的時候,正是他在里面焚膏繼晷用功苦讀之時,或者是記述祖孫、夫妻之間的美好情景之時。而“舊南閣子”只是對家里一間普通小屋的稱呼。還沒有成為書齋時,它當然只能被稱為“舊南閣子”;而后文中寫妻子死后“室壞不修”“復葺南閣子”則是在告訴讀者,此時這間屋子已經不復如往昔——人生的坎坷經歷讓書齋的主人失去了年輕時的雄心和傲氣,也讓“項脊軒”失去了作為書齋的功能或意義。
二、量體裁衣,營造平中見奇的妙境
《項脊軒志》短短數百字容納諸多的人、事、物,這離不開歸有光對日常瑣事的用心選擇和妙手剪裁。文本時間跨度達十余年,可寫的內容太多太雜,但歸有光卻能將內容安排得簡潔而熨帖。看似信手拈來的場景描寫、隨意排布的順序,實則匠心獨運。
“項脊軒”的破舊之態可寫之處很多,而歸有光只選取了一個下雨的場景,就把如杜詩中“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的情形呈現了出來,讓讀者身臨其境。家道中落的場景可寫之處同樣很多,而歸有光選取了“東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雞棲于廳”的生活場景,看似煙火氣十足,實則狼狽不堪。這句話提及的“犬”“客”“雞”極具典型性,“雞”“犬”在中國古代常連用,如“雞犬不寧”“雞犬升天”“雞飛狗跳”。東家的犬為何要對著西家叫?因為犬的領地意識很強,若有不熟悉的人路過,它便自然叫起來了。要知道,犬在古代大多用于看家防賊。本在同一個庭院里,卻戶戶養犬,一家人相互提防了起來。“廳”是建造在建筑組群縱軸線上的主要建筑,常作為正式會客、議事或行禮的場所,是我們平時常說的“上得了廳堂”中的“廳堂”。它是顯示主人身份和地位的地方,理應整潔、雅致、大氣;如今卻被雞占領,凌亂、污濁之相可見一斑。那為何要寫“客逾庖而宴”呢?“庖”即廚房,孟子曾說“君子遠庖廚”,可見廚房在古人眼里是粗俗的人待的地方,家里的主人一般極少踏足其間,更何況是尊貴的客人呢?而此時的歸家,由于大家庭已分割成若干個小家,原本的大廚房也變成了若干個小廚房散落在庭院里,客人要來赴宴,還必須穿過廚房。這樣的情形對飽讀詩書、接受孔孟思想熏陶的歸有光來說是無法忍受的。“羞惡之心,義之端也”,這種羞恥心應該也是歸有光想要通過科舉改變自己和家族命運的動力吧。
再看祖母探望歸有光的場景描寫。歸有光和祖母相伴多年,從祖孫的關系來看,祖母對這個孫兒是愛護有加的。歸有光沒有選擇寫常見的噓寒問暖,而選擇寫祖母來軒中看望自己讀書,突出了祖母曾經的大家閨秀、如今的沒落家族守護人的形象。祖母說“久不見若影”并非表示見不到孫兒,而是表示知道孫兒獨自關在斗室里足不出戶,不愿過多地打擾,言語之間充滿了心疼;離開之時“以手闔門”,生怕外人來打擾;且自言自語時,既說出了歸氏家族不景氣的現狀,又表明了把希望寄托在眼前這個爭氣的孫兒身上。僅此還不夠,祖母甚至拿出了她祖父在宣德年間上朝用的象笏——這物件絕不是一件尋常的物品,可以稱得上是傳家寶。祖母拿出來給孫兒,并且說“他日,汝當用之!”。這里,祖母對歸有光考取功名已經不只是期許了,她認為這近乎是定論了,只是時間的問題。祖母對歸有光有如此期待也暗合了歸有光的心思,所以這個場景也成了有關祖母的諸多往事中最讓作者難忘的。
在這篇文章中,歸有光先后提到了與自己有密切關系的四位女性——老嫗、母親、祖母和妻子。作為一篇以“項脊軒志”為題的散文,所記之物、所敘之人必然都和這個書齋有關。看一下歸有光是如何將這四位女性和這個書齋聯系起來的:從老嫗寫起,用“嘗居于此”來表明此書齋與老嫗之間的關聯,在成為書齋之前的若干年中,這里曾經是老嫗的住處。這位老嫗是祖母的婢女,又做了兩代人的乳母,得到了祖母的關愛。愛屋及烏,歸有光對“項脊軒”及對老嫗的情感,究竟是哪個影響了哪個,還真是很難說清。母親對于歸有光來說,也許只剩下一個模糊的影子,畢竟母親去世時,他還是一個兒童。那么怎么把已經去世多年的母親和現在的書齋聯系起來?還是通過老嫗。“室西連于中閨,先妣嘗一至”,老嫗告訴歸有光他的母親當年曾到這個地方看望嗷嗷待哺的女兒(歸有光的姐姐),由此引起了歸有光對母親的懷念。而寫祖母時,歸有光選擇了自己在書齋里讀書時“大母過余”這一事件,直接寫出祖母對這個酷愛讀書的孫兒的疼愛和期望。至于妻子,則寫她“時至軒中”紅袖添香,而這個書齋也成了夫妻交談的一個話題。
在寫前三位女性時,歸有光并沒有完全按時間的順序來寫,他巧妙地安排了老嫗這一人物的出場,從屋子寫到生活在其中的人,再借此人之口引出已故的親人。寫離當下近的人時用直接描寫,寫離當下遠的人時用間接轉述,既要言不煩,又合乎情理。
三、詞含褒貶,臻于言近旨遠的至境
“春秋筆法”最大的特點就是“一字褒貶”,在《春秋》中,褒則稱字,貶則稱名,常用一字寓意褒貶。而在后世的文學作品中,“一字褒貶”常指作者用極其簡單的字詞來表達深刻而豐富的含義和情感。在《項脊軒志》中,這類字詞也有不少,卻容易被讀者忽略。特舉幾個例子來闡述。
(一)“項脊軒”
在讀這篇文章時,我們往往會忽視這個書齋名稱的由來和用意。歸有光為什么不把這篇文章題目命作《老屋志》《南閣子志》呢?從文章所記內容來看,“項脊軒”應該是作者把南閣子修葺并改造成自己的書齋后所取的名字,以此來命名便烙上自己鮮明的印記,而如果是“老屋志”“南閣子志”的話則無法表明這間屋子和自己的關聯。
古代文人對自己的書齋十分看重,故對書齋取名也特別用心,如陸游的“老學庵”源自劉向《說苑》中的“師曠老而學猶秉燭夜行”。有的書齋名表現了主人為學的態度,如張溥的“七錄齋”就是其讀書勤于手抄的寫照,蒲松齡的“聊齋”則告訴我們在小說創作中生活是源頭活水……但“項脊軒”呢?“項脊”即“項脊涇”,在今江蘇昆山市(一說太倉市),為歸有光先祖居住地。歸有光并沒有在該地居住,為何要將其作為書齋名?歸有光擁有這個書齋時,還是一個刻苦讀書、尚未成家的少年郎,他給自己取了一個號——“項脊生”,可見“項脊”二字在歸有光心中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歸家曾經是當地的大戶,也曾經有人擔任過朝廷命官,而到了歸有光祖輩父輩那里,家道不幸中落,甚至到了“諸父異爨”的分崩離析的境地;而歸有光自小就受到激勵,渴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光耀門楣,重振歸家基業,恢復先祖榮光。對歸有光來說,“項脊涇”這個地名代表著歸氏家族曾經的輝煌和榮耀。看似平平無奇的地名,卻寄寓了年輕的歸有光的雄心壯志,寄托著他對未來無盡的希望。
(二)“神”
歸有光在原文(第一次成文)敘事的最后部分,說“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這句話看上去充滿了封建迷信的色彩,讓很多讀者莫名其妙。歸有光為什么要寫項脊軒有神靈的庇佑?神靈又為何要庇佑這間小小的書齋?這也許是古人的一種信仰或思維方式,但從中我們可以發現,歸有光是不希望這間書齋被“火災”這樣的災禍損毀的,因為“項脊軒”對他來說不僅是一間小書齋,記錄了他的讀書時光;更是一個精神家園,承載了他的宏圖偉愿。歸有光感受到冥冥之中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保佑他,這讓他堅信自己就是一塊讀書的料,也是歸氏家族振興的希望所在。因此,與其說這里寫得魔幻,不如說寫出了歸有光對自己功成名就的信心和對美好前途的憧憬。
(三)“坎井之蛙”
《項脊軒志》中,歸有光模仿司馬遷的“太史公曰”,寫了一段“項脊生曰”,以表達自己的心志。此段文字在教材中被刪除,原文如下:
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坎井之蛙何異?”
歸有光先用蜀女清和隆中諸葛孔明兩個古人的例子,闡明能成大事業者一開始也會“昧昧于一隅”,無聲無息不為世人所知曉,但這并不會影響他們將來的成就。然后寫自己在“項脊軒”這個敗屋中發奮勤學的情形。最后用“人知之者,其謂與坎井之蛙何異”作結,表面上看這句話有自嘲的意味,將自己身處斗室比作“坎井之蛙”。然而,正是因為有了兩位古人做榜樣,所以歸有光才不會甘于“昧昧于一隅”,他希望能和清與諸葛孔明一樣,有朝一日出人頭地,大放異彩,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給那些以為他是“坎井之蛙”的人以有力的回擊。歸有光用委婉的方式,表達出如陳涉“燕雀安知鴻鵠之志”般的不屑,展現出“少年心事當拏云”的決心。
(四)“吾妻”
在不同的回憶文章中,歸有光對他的第一個妻子(《項脊軒志》中的“妻”)有不同的稱呼,如“魏氏”“先妻”“孺人”等,而在《項脊軒志》里,他連用了幾個“吾妻”,這又有何區別呢?“某氏”是古代對已婚女子的官方稱謂,適用于人物傳記;“先妻”只是交代了妻子已經亡故的事實;“孺人”明清時為七品官的母親或妻子的封號,也用作對婦人的尊稱。
而“吾妻”則截然不同,“妻”表明了身份,“吾”強調了是自己的。此時,歸有光的妻子魏氏已經亡故數年,她死的那年親手種植的枇杷樹都已經亭亭如蓋了,但歸有光在敘述相關事件時依然用“吾妻”,似乎魏氏并不曾離開他,而依然像以往那樣,和他卿卿我我,相伴相守,時而“從余問古事”,時而“憑幾學書”。可以說,這樣的美好時光永遠地留在了歸有光的記憶里。正因為如此,當我們讀到“庭有枇杷樹”這段文字時,總免不了唏噓動容。假如將這里的“吾妻”換成“魏氏”或“孺人”,歸有光便成了一位旁觀者,一位客觀的敘事者,沒有了你儂我儂的深情,文章也就很難直擊人心。
“春秋筆法”這個古老的概念,歷經數千年后,其內涵和外延都得到了豐富和拓展。歷代文人憑著自己對它的理解,在傳承中不斷創新發揚,將它體現在各自的文學創作中。文言散文的魅力在于“文”(意蘊),也在于“言”(詞語),兩者不可分割。作者通過某些文字技巧或藝術手法,將“文”融入“言”中,又用“言”來傳遞“文”。而讀者在閱讀文言散文時,如果能從“春秋筆法”的角度進行思考,也許就能透過字詞讀出一些新的意蘊,產生新的感悟。這對文言散文的閱讀和教學而言,是一種有意義的嘗試。
(責任編輯??? 農越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