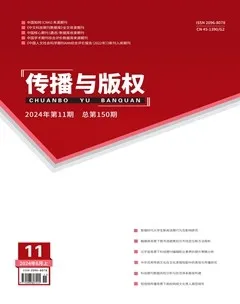高校慕課制作與傳播中的著作權問題
[摘要]當前,以慕課為基礎的線上線下混合教學模式已成為主流,但是,相關主體在慕課制作與傳播的過程中,仍存在一系列著作權問題尚未解決。文章通過界定慕課的作品類型,進而討論高校與教師等多方主體之間的著作權歸屬爭議及侵權責任承擔問題。囿于條款限制和原創(chuàng)者保護的要求,教師在慕課制作中使用他人作品,可能無法以合理使用主張抗辯。因而,為降低交易成本,兼顧原創(chuàng)者和教育提供者雙方利益,文章建議引入法定許可制度,以支持在線教育的發(fā)展。
[關鍵詞]高校慕課;在線教育;著作權;合理使用;法定許可
大規(guī)模在線開放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簡稱“MOOC”,即“慕課”)是以開放教育資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為基礎,以現(xiàn)代數(shù)字技術為支撐的新型教育模式[1]。截至2024年初,中國已上線慕課數(shù)量超過7.68萬門,學習人次超過12.77億[2]。調(diào)查顯示,77%的受訪者認為慕課的教學效果和受眾面都優(yōu)于傳統(tǒng)課堂教學[3]。然而,教師在慕課制作與傳播的過程中仍存在一系列著作權問題亟待解決。例如,涵蓋教師、高校和平臺多方投入的慕課視頻,著作權歸屬于誰?此外,在線模式提高了慕課制作的資源依賴性,教師在慕課的制作過程中使用他人作品是否需要征得原創(chuàng)者同意?在尚未征求同意的情況下,侵權責任應當由誰承擔?文章擬對上述問題展開討論,并探究激勵作者創(chuàng)作和促進在線教育蓬勃發(fā)展的利益平衡方案。
一、慕課的作品類型界定
作為教師講授、學校或?qū)I(yè)攝制團隊錄制,最終發(fā)布于在線平臺的慕課,通常情況下應是口述作品和錄像制品的結(jié)合。教師的授課內(nèi)容可構(gòu)成口述作品,課程錄制者則作為錄像制作者享有鄰接權。但是,在符合特定條件的情況下,課程整體將作為視聽作品獲得著作權法保護。
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將“授課”納入口述作品范疇。慕課制作的在線性并沒有剝離其授課的本質(zhì),慕課的授課內(nèi)容即為教師獨立構(gòu)思并以口頭形式表達的作品,屬于口述作品范疇。第二,在司法實踐中,部分法院主張慕課是由聲音配合畫面組成的整體,應構(gòu)成視聽作品。但是,文章認為,課程錄制者對慕課的錄制,并未體現(xiàn)其獨創(chuàng)性表達,無法達到視聽作品的創(chuàng)作高度,不構(gòu)成視聽作品。相關受眾針對課程錄制者拍攝機位的選擇、鏡頭畫面的切換及不同素材的剪輯存在穩(wěn)定的預期,且多名達到相同技術水準的錄制者拍攝相同的課程內(nèi)容,差距并不會過于顯著[4]。例如,北京法院在針對春晚錄制的獨創(chuàng)性判斷中指出,編導、攝像等人員按照其意志所能作出的選擇和表達非常有限,由此決定了“春晚”所具有的獨創(chuàng)性不足以構(gòu)成電影作品,應作為凝聚了一定智力創(chuàng)造的錄像制品予以保護。基于此,創(chuàng)作空間的有限性導致課程錄制者獨創(chuàng)性表達的匱乏,而獨創(chuàng)性表達的匱乏決定了慕課無法達到視聽作品的創(chuàng)造性高度。但是,當慕課存在腳本設計、鏡頭切換選擇、創(chuàng)造性剪輯的情況下,慕課的制作構(gòu)成獨創(chuàng)性表達,該課程整體也應被界定為視聽作品享有著作權。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辦案指引》中曾指出,要認定某一作品構(gòu)成電影作品,需要拍攝者在攝制上以分鏡頭腳本為藍本,注重鏡頭的切換,采用蒙太奇等剪輯手法制作成片。腳本的設計一方面能夠反映拍攝者在拍攝之前進行過獨創(chuàng)性構(gòu)思,使拍攝行為擺脫了機械錄制的范疇;另一方面則否定了口述作品所要求的“即興”特征。鏡頭切換是拍攝者在其意志支配下的選擇、編輯和處理,體現(xiàn)了拍攝者的個性化表達。蒙太奇等剪輯技巧則在素材的選擇和加工上體現(xiàn)了創(chuàng)造性。因此,符合上述標準的慕課并不是口述作品和錄像制品的結(jié)合,而應整體作為視聽作品享有著作權。
二、慕課著作權歸屬及其侵權責任
(一)慕課屬于一般職務作品
文章認為,無論作為口述作品還是視聽作品,慕課應屬于一般職務作品,著作權歸屬于授課教師,高校有權在其業(yè)務范圍內(nèi)優(yōu)先使用。作品要被認定為一般職務作品,需要符合兩項特征:其一,作者與單位存在雇傭關系;其二,創(chuàng)作目的是完成單位交付的工作任務。對慕課而言,教師與學校之間的雇傭關系無可否認;而混合式教學模式的常態(tài)化則肯定了在線教學屬于教師的工作范疇。
自2020年起,基于實際教學需要,在線教學技術不斷發(fā)展,“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成為常態(tài)。截至2022年3月,中國高校教師利用慕課開展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的比例已從2019年的34.8%提升至84.2%[5]。教育部2020年發(fā)布的《高等學校慕課建設與應用指南(試行)》中也指出,我國目前存在三種主流的混合教學模式,其中包括:基于慕課的混合式課程、基于SPOC的混合式課程、基于“MOOC+SPOC”的混合式課程。混合教學模式的常態(tài)化使慕課制作日益成為教師日常教學工作的組成部分,大部分高校都將慕課納入教師的工作總量認定范疇。清華大學首次上線慕課時就曾提出,針對在線課程,按照普通課程的三倍課時認定教師的工作量[6]。因此,雇傭關系和工作任務兩項特征決定了慕課應被認定為一般職務作品,著作權歸屬于教師本人。值得注意的是,倘若教師在慕課制作過程中利用了高校的物質(zhì)技術條件,則慕課可構(gòu)成法定型特殊職務作品。但是,大部分慕課都是在正常教學環(huán)境錄制,并輔之以簡單剪輯,并未利用高校的資金、設備、技術資料等[7],因此不構(gòu)成特殊職務作品。法院的判例也支持這一觀點。比如,凱路通著作權糾紛案中,法院指出,公司雖為原告提供了食宿、電腦、麥克風及教材,并對涉案11套慕課進行剪輯,但與工程設計、產(chǎn)品設計圖、計算機軟件等作品相比,涉案視頻對單位的資源和技術的依附程度較低,故不屬于特殊職務作品。除法定型特殊職務作品外,《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第十八條第二款規(guī)定,特殊職務作品還包括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或合同約定著作權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享有的職務作品。因此,在教師與學校進行特別約定的情況下,慕課將構(gòu)成約定型特殊職務作品。
此外,在線教學平臺不能基于其輔助功能享有慕課著作權。研究指出,在線教學平臺功能的有用性對用戶的學習效果有顯著正向影響[8]。但是,在線教學平臺所提供的課后討論、隨堂測試等功能,均屬于市場化產(chǎn)品,并非平臺運營方創(chuàng)造性的體現(xiàn)。因此,在合同沒有特別約定的情況下,在線教學平臺并不享有慕課的著作權。
(二)慕課侵權責任承擔主體的判定
在慕課教學過程中,為保障教學質(zhì)量,教師使用他人作品不可避免。但是,對他人作品的使用極有可能為教師或高校帶來侵權糾紛。關于慕課侵權責任的承擔主體,在實踐中,不同法院的判決存在不一致性。例如,在“硬筆書法課程案”中,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教師和教育機構(gòu)共同實施了侵權行為,應當共同承擔侵權責任。在“英文教材案”中,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教育機構(gòu)通過電子數(shù)據(jù)的形式轉(zhuǎn)化了原著作權人創(chuàng)作的教材內(nèi)容,應由教育機構(gòu)承擔侵權責任。根據(jù)《著作權法》第十八條的規(guī)定,一般職務作品由作者本人承擔責任,特殊職務作品則存在兩種不同情況:第一,利用單位的資源和技術創(chuàng)作的法定型特殊職務作品,應由單位承擔責任;第二,經(jīng)過當事人約定形成的約定型特殊職務作品,責任承擔則完全取決于當事人的約定。因此,在通常情況下,作為一般職務作品的慕課視頻,由教師自行承擔責任;利用高校的物質(zhì)技術條件形成的特殊職務作品,由高校承擔責任。但是,高校與教師特別約定形成的約定型特殊職務作品,責任主體則較為模糊。規(guī)則制定之初,即有學者指出,允許雙方當事人通過合同約定由工作單位取得職務作品的著作權,容易引發(fā)一系列問題[9]。
筆者調(diào)查全國26家高校發(fā)現(xiàn),有62.0%的高校與教師通過合同約定慕課著作權歸屬于高校。可見,慕課通常為約定型特殊職務作品。如前所述,約定型特殊職務作品的責任承擔,完全取決于當事人之間的約定。本次調(diào)查的26所高校中,慕課合同中關于責任承擔的條款存在以下兩種情況。明確約定侵權責任由教師承擔(占比28.6% )。未約定侵權責任承擔主體(占比71.4% )。
第一,侵權責任完全由教師承擔的約定,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我國《著作權法》融合了作者權體系作者中心主義的理念和版權法體系重視投資人收益回報的需求。針對法定型特殊職務作品,《著作權法》規(guī)定,作者享有署名權,其他權利歸屬于單位,并由單位承擔責任,是典型的肯定投資人經(jīng)濟貢獻和激勵作者創(chuàng)作投入兩種價值取向權衡的結(jié)果。但是,涉及約定型特殊職務作品,上述約定卻引發(fā)了著作權取得和侵權責任承擔之間的錯位,打破了立法者的平衡安排,代之以投資者利益傾向性,對創(chuàng)作熱情無疑是嚴重的打擊。信息分享可以很容易,但是,要創(chuàng)造出新穎而有用的信息,依然很難[10]。雖然數(shù)字技術減少了創(chuàng)作重復性、機械性的一面,但是其本質(zhì)上并沒有使創(chuàng)作變得更容易。任何寫出生動詩行的人,必定都揮汗如雨[10]。因此,文章認為,打破當事人約定的不平衡性,恢復產(chǎn)權制度的創(chuàng)作激勵功能,確有必要。高校提供的慕課合同通常為格式合同,有學者指出,交易風險分配是否合理是判定格式條款效力的關鍵步驟[11]。約定由教師承擔侵權責任的條款,將責任承擔風險完全轉(zhuǎn)移給教師,該責任分配已達到“不合理”程度。因此,該條款應被認定為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不合理地減輕自身責任、加重對方責任”的條款,教師有權主張該條款無效。
第二,在本次調(diào)查的26所高校中,有71.4%的高校在與教師簽訂的慕課合同中,對侵權責任完全未作約定,這反映國內(nèi)高校和教師著作權意識的缺失。文章認為,法定型特殊職務作品的規(guī)定是更加符合立法目的,強調(diào)利益平衡的合理安排。其在重視投資者利益回報的同時,兼顧了原創(chuàng)者的熱情激勵。因此,在合同未約定侵權責任承擔主體的情況下,應遵循法定型特殊職務作品的立法規(guī)定,侵權責任由高校承擔。
三、慕課制作的合理使用認定分析
慕課教學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使用他人作品。但是,無論根據(jù)我國現(xiàn)行法律制度,還是合理使用的概括性條款,教師在慕課教學中使用他人作品,均不能以合理使用主張抗辯。司法實踐中,合理使用的抗辯理由通常也不被法院所接受。
首先,教師在慕課教學中使用他人作品不符合我國《著作權法》關于合理使用的時空條件、對象范圍和數(shù)量限制的規(guī)定,不屬于合理使用范疇。第一,《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規(guī)定,合理使用限定于課堂教學。而課堂教學在空間上限定于校園范圍內(nèi),在時間上始于上課,終于下課。美國《TEACH法案》也規(guī)定,個人只有在現(xiàn)場課堂教學、傳輸知識的過程中,才有權表演、展示他人作品。但是,慕課一方面不囿于教學地點的限制,另一方面具有全天候教學特征,不符合合理使用的時空條件。第二,課堂教學合理使用的對象限于“教學科研人員”,但國內(nèi)主流的十家慕課平臺中,只有上海交通大學的“好大學在線SOPC”平臺僅向在校學生開放,其他所有平臺都既面向在校學生,也面向社會公眾。大部分法院的判決也指出,在線傳播方式導致慕課面向不特定社會公眾,遠超高校教學的學生范圍,不能構(gòu)成教學性合理使用。例如,在《霧雨電》侵權案中,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將他人作品放在網(wǎng)站上供公眾閱讀,不符合合理使用。在“小鵝通”案中,溫州市鹿城區(qū)法院認為,該視頻可供公眾查看,即使被告和其他案外人在獲取涉案課程視頻后用于學校課堂教學或者研究使用,也不構(gòu)成合理使用。第三,慕課的“開放性”特征與合理使用條款中“少量復制”的要求相悖。基于“平等、開放、共享、協(xié)作”的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產(chǎn)生的慕課知識共享模式,其傳播程度和影響力度遠遠超過了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當將慕課發(fā)布于在線教育平臺后,作品的傳播范圍很難受到控制,無法符合“少量復制”的要求。Coursera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只有31.6%的平臺用戶是在校學生及研究者,而這些學生將以在校生身份免費獲取的教學資源與非注冊用戶分享,有違“合理使用”原則[12]。
其次,即使根據(jù)《與貿(mào)易有關的知識產(chǎn)權協(xié)議》規(guī)定的“三步檢驗法”及美國“四要素檢驗法”判斷,教師在慕課制作過程中使用他人作品也不構(gòu)成合理使用。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在“關于對《XX醫(yī)療手冊》案的答復”中指出,可根據(jù)“三步檢驗標準”認定是否構(gòu)成合理使用。如果復印的份數(shù)非常之多,則不得準許這一復印,因為它與作品的正常利用發(fā)生抵觸。在傳統(tǒng)教學環(huán)境下,囿于技術條件的限制,“復印”的傳播數(shù)量十分有限,而網(wǎng)絡傳播的便利性必然導致在線課程內(nèi)容的傳播數(shù)量遠超“復印”所及,難以構(gòu)成合理使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充分發(fā)揮知識產(chǎn)權審判職能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和促進經(jīng)濟自主協(xié)調(diào)發(fā)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借鑒了美國“四要素檢驗法”。可見,我國在適用《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規(guī)定的概括性條款“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的其他情形”中,可以將“四要素檢驗法”作為借鑒。但是,“四要素檢驗法”明確要求認定合理使用需考慮使用行為的性質(zhì)和目的,而慕課平臺的營利性卻與使用目的的正當性相背離。在美國法院有關合理使用的案件判決中,有90%以上將非商業(yè)性使用作為合理使用的判斷標準之一[13]。《TEACH法案》也指出,營利性的慕課不能以“合理使用”為由主張侵權抗辯。當前,國內(nèi)十家主流慕課平臺主要營利模式包含認證收費、公證評估、會員服務、招聘參考、廣告分成、版權合作六種[14]。在國際三大慕課平臺中,Coursera和Udacity都在版權協(xié)議中列舉了多種營利方案。盡管高校等教育機構(gòu)本身不具有營利性,但是其與慕課平臺合作時,合作性質(zhì)也可能出現(xiàn)異化。例如,皮爾森虛擬大學教育公司在與大學的合作協(xié)議中約定,大學可以取得慕課平臺的6%—15%的現(xiàn)金收入與20%的總利潤[15]。泛濫的營利性平臺進一步僭越公立教育的“政府本位”(Government-based),對其原有的利益純粹性造成一定沖擊[16]。
最后,除條款適用的不適當性外,文章認為,認可慕課教學合理使用,也不利于被利用作品原創(chuàng)者的創(chuàng)作激勵。合理使用制度將作品控制權和補償獲得權同時從原創(chuàng)者手中剝離,在減少創(chuàng)作者在數(shù)字形式上自治范圍的同時,又打消了原始創(chuàng)作者一個潛在的收入來源,對數(shù)字時代的原創(chuàng)發(fā)展是較為嚴重的打擊。因此,教師在慕課教學中使用他人作品,不能以合理使用制度主張抗辯。
四、降低授權成本的制度建議:法定許可的引入
(一)引入法定許可的必要性
版權法永恒的困境是決定權利人專有權的止境和公眾獲取作品自由的起點,以達成謹慎的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平衡[17]。著作權保護不足將會挫傷被利用作品原創(chuàng)者的創(chuàng)作積極性;但過度的產(chǎn)權保護,卻有可能阻斷公眾獲取知識的途徑。因此,法律在激發(fā)被利用作品原創(chuàng)者創(chuàng)作熱情的同時,也應當為慕課教學中的資源利用提供適當?shù)脑S可空間,不宜全面禁止。第一,平臺的營利性不足以掩蓋慕課的教育本質(zhì),也不足以否定在線教育具備的傳道授業(yè)價值。在此基礎上,慕課在消弭地區(qū)教育資源差距方面也發(fā)揮了關鍵作用。據(jù)統(tǒng)計,截至2023年5月,國內(nèi)慕課平臺共向中西部高校提供19萬門慕課及其他在線課程服務,幫助中西部地區(qū)高校開展混合式教學446萬次,參與學習學生達4.9億人次[18]。其公益性質(zhì)不容忽視。
第二,復雜的許可模式會給教師施加過多版權負擔。根據(jù)OCLC的研究報告,一門慕課版權清理時間高達380小時[19],而慕課制作中的侵權責任往往由教師承擔。學者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為了回避授權難題,2/3的教師選擇放棄對既有版權資源的利用[20]。此外,相較傳統(tǒng)教學,在線課程的時長更短,受眾注意力更加分散。因此,慕課往往需要整合更多的圖片、文字及音像資料,以提高教學質(zhì)量。據(jù)統(tǒng)計,線下100分鐘的課堂內(nèi)容錄制成慕課通常為50—70分鐘[21]。資源集合型創(chuàng)作模式提升了教師的作品利用需求,課程制作的版權負擔進一步加重。
與龐大的資源需求相對應的,是市場中單個知識產(chǎn)權都由廣泛的個人攥在手里。因而,僅以教師與原作者之間的私人談判實現(xiàn)版權許可將導致慕課制作中版權許可的交易成本攀升。市場需要盡量促進有限資源的合理配置,以提升資源運轉(zhuǎn)的效率,產(chǎn)生更大的經(jīng)濟效益[22]。而交易成本的內(nèi)耗將帶來負值的合作剩余,使交易雙方均無利可圖,無疑是市場銷效率低下的表現(xiàn)[23]。因此,法律需要對資源加以引導,引入富有效率的交易機制,使創(chuàng)作成果在產(chǎn)權保護的前提下,仍能夠順暢地流動,實現(xiàn)原創(chuàng)者權利保護和在線教育發(fā)展之間的平衡。
(二)慕課教學的法定許可:具體制度設計
法定許可是兼顧教育產(chǎn)業(yè)發(fā)展和被利用作品原創(chuàng)者創(chuàng)作激勵的有效制度安排。《日本著作權法》第35條規(guī)定:在學校等教育機關(以營利為目的而設立者除外)中任教者,為教學目的使用時,可在必要的限度內(nèi),復制已公開發(fā)表的作品,教育機構(gòu)的設立者應當向著作權人支付補償金。我國可參照日本在《著作權法》中增加:為制作在線課程,可以不經(jīng)著作權人許可,在視頻中使用已發(fā)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樂作品或者單幅的美術作品、攝影作品、圖形作品等,但應當按照規(guī)定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24]。有學者指出,數(shù)字時代真正的難題,并不是在根據(jù)財產(chǎn)權獲得收入補償?shù)姆矫妫窃谟谒鼈冑x予了太多控制的這一事實[25]。法定許可制度的引入,在慕課教育領域,引導創(chuàng)作者的控制權為教育公平讓步。一方面降低了使用人付款中流入交易成本的比例,減少了交易中的純粹摩擦,消除了教育提供者的版權許可之困;另一方面以補償金激勵原作者持續(xù)創(chuàng)作,并將流入創(chuàng)造者的收入最大化,是權利配置的合理安排。
法定許可需與便捷的補償金支付機制相配套。第一,建議設立網(wǎng)絡教育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由該組織負責收取并支付報酬[26]。集體管理組織的建立將原有的“個別收費”更改為“一站式支付”,便利大規(guī)模、廣泛性的資源利用。第二,營利性慕課平臺應作為補償金支付主體。教師雖為作品的實際利用者,但營利性慕課平臺卻是教學視頻經(jīng)濟收益的獲得者。此外,平臺的營利性是阻卻合理使用抗辯適用的重要原因。具體而言,教學平臺應在慕課發(fā)布后一個月內(nèi)向集體管理組織支付費用,集體管理組織受到費用后應立即向權利人轉(zhuǎn)付。補償金額可參照《教科書法定許可使用作品支付報酬辦法》的規(guī)定確定。針對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由集體管理組織收取補償金后提存,5年內(nèi)仍找不到著作權人的,該補償金用于集體管理組織自身建設。
五、結(jié)語
權衡公益與私權的關系是著作權立法的基本考量。投資者經(jīng)濟回報和作者創(chuàng)作激勵之間的有效權衡是慕課著作權歸屬認定的關鍵。 互聯(lián)網(wǎng)和其他數(shù)字技術已經(jīng)構(gòu)建了一個充滿協(xié)作與交互的美麗新世界, 其內(nèi)在的邏輯和動力與傳統(tǒng)的財產(chǎn)權約束存在明顯的不一 致性。在許多情況下,如果堅持資源必須歸個人控制,就會阻撓這種新技術范式的希望。因此,法律摒棄高昂的私人談判成本,引入更有效率的許可方案,以實現(xiàn)教育公平促進和原創(chuàng)者保護之間的利益平衡,則是符合經(jīng)濟效益的更優(yōu)選擇。
[參考文獻]
[1]梁九業(yè).MOOC教育模式下著作權合理使用問題研究[J].電子知識產(chǎn)權,2019(09):36-43.
[2]農(nóng)村教育發(fā)展中心.中國慕課服務國內(nèi)12.77億人次應用規(guī)模成為世界第一[EB/OL].(2024-01-31)[2024-04-10].https://mp.weixin.qq.com/s/r5l1TUN0EsmHshlWOBnEnw.
[3]ALLEN E,SEAMAN .J Changing Course:Ten Years of Tracking Onlin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EB/OL].[2024-04-10].http://www.onlinelearningsurvey.com/reports/changingcourse.pdf.
[4]王遷.論體育賽事現(xiàn)場直播畫面的著作權保護:兼評“鳳凰網(wǎng)賽事轉(zhuǎn)播案”[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6(01):182-191.
[5]中國青年報.世界慕課與在線教育聯(lián)盟秘書長汪瀟瀟:在線教育實現(xiàn)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共享.[EB/OL].(2024-03-01)[2024-04-10].https//mp.weixin.qq.com/s/307KtxQh4vImT04CZvr1JQ.
[6]何雋,喬林,林思彤.MOOC平臺的著作權風險及對策[J].中國遠程教育,2019(04):60-66.
[7]王遷.著作權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8]楊根福.混合式學習模式下網(wǎng)絡教學平臺持續(xù)使用與績效影響因素研究[J].電化教育研究,2015(07):42-48.
[9]劉春田,劉波林.論職務作品的界定及其權利歸屬[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0(06):61-69.
[10]莫杰思.知識產(chǎn)權正當性解釋[M].金海軍,史兆歡,寇海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
[11]馬一德.免除或限制責任格式條款的效力認定[J].法學,2014(11):146-153.
[12]王麗霞.摭談慕課教育版權合理使用制度的建構(gòu)[J].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7(05):30-34.
[13]WALLACE M W.Analyzing Fair Use Claims:A Quantitative and Paradigmatic Approach[J] .University of miami Entertainment & Sports lau Review,1994.
[14]韓梅,李佳玉.MOOC盈利模式研究[J].科技與出版,2015(05):9-13.
[15]丹尼爾爵士,丁興富.大規(guī)模開放在線課程的發(fā)展前景:對由相關神話、悖論和可能性所引發(fā)困惑的深層思考[J].開放教育研究,2013(03):42-55.
[16]馮曉青.知識產(chǎn)權法前沿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
[17]張鐵薇,張琨.著作權權利限制視角下突發(fā)事件時期高校信息化教學的法律治理模式[J].黑龍江高教研究.2022(09):91-99.
[18]慕課西部行發(fā)展報告專欄|慕課西部行發(fā)展報告編寫組:邁向公平之路:慕課西部行發(fā)展報告.[EB/OL].(2024-02-21)[2024-04-10].https://mp.weixin.qq.com/s/ve-uDwY5ywpB_bmwAXHDww.
[19]蔡卓衡,丁志亞.我國MOOC發(fā)展中的版權問題研究[J].河北法學,2017(07):181-187.
[20]張云麗.美國高校圖書館開展MOOC版權服務的實踐及啟示:以杜克大學圖書館為例[J]山東圖書館學刊,2014(06):95-100.
[21]戰(zhàn)德臣,徐曉飛,張龍.深度理解高校慕課指南,建好線上線下混合課程[J].計算機教育,2021(10):1-6.
[22]考特,尤倫.法和經(jīng)濟學:第六版[M].史晉川,董雪兵,等,譯.上海:格致出版社,2012.
[23]GORDON W J,BAHLS D.The publics right to fairuse:Amending Section 107 to avoid the“fairuse”fallacy [J].Utah Law Review,2007(03):619-622.
[24]鄭重.慕課背景下日本教學性權利限制制度的改革及啟示[J].知識產(chǎn)權,2020(03):76-85.
[25]萊斯格.思想的未來: 網(wǎng)絡時代公共知識領域的警世喻言[M].李旭,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26]鄭重.慕課背景下日本教學性權利限制制度的改革及啟示[J].知識產(chǎn)權,2020(03):76-85.
[作者簡介]林玥(1999—),女,廣東廣州人,暨南大學法學院/知識產(chǎn)權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