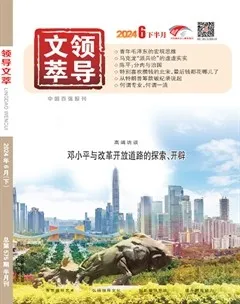蔡元培的兼容與能容
趙淑荷
北大的風景
1917年1月,深冬的北京。新年剛過,蔡元培獨自一人,來到前門外煤市街的一家旅館。這位點過翰林、做過總長的先生,剛剛出掌北京大學,此刻踱步在房間外的長廊上,靜靜等待著什么。
這是他第三次來找一位故人。
多年前,蔡元培與陳獨秀在上海曾有革命之誼。若不是陳獨秀出手相救,蔡元培可能會葬身于自己親手所制的炸彈之下。如今,蔡元培三顧茅廬,懇請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希望這位文辭快厲的文學革命旗手,能為北大最腐敗最官僚的一科帶去強勁的“新青年”之風。
蔡元培既然選中陳獨秀,自然是明確支持新文化運動,但與此同時,蔡元培也并不拒斥傳統國學的血脈。
不久后,西裝革履的胡適和留著辮子的辜鴻銘同時出現在校園,各教自己的學問,堪稱北大一景;信古派的學者黃侃,上課時突然罵起對面教室的疑古派錢玄同,“錢聽了也滿不在乎,照樣講課”。
不僅新舊兩派同處一堂,就是在新派人士當中,各有主張的學者教授,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如李大釗,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如劉師培,在北大也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蔡元培解釋:“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余地。”
如果梳理蔡元培的個人史,我們會發現,能在北大種下兼容與自由之種子的人,非蔡元培莫屬。晚清革命志士多為新知識階層,曾作為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做到了翰林卻轉而干革命的,唯蔡元培一人;而這位留德留法,半工半讀,鉆研西方學問的新派留學生,年少時卻受宋儒理學影響至深,廣泛閱讀西方書籍,他能反思儒學弊端,甚至在自己的婚姻中超前地實踐男女平等思想。
由此可見,蔡元培有著非凡的開闊思維和批判精神,因此能夠接受截然相反的兩種文化并存,決不因自己所推崇的,而貶低他人所信仰的。
“兼容并包”思想在學校體制上的體現,則是蔡元培從國外帶回的評議會制度。他提出“教授治校、民主辦校”,讓有學問的人管理做學問的事。北大不僅兼容不同學術觀點,也在兼容大家對學校管理的不同意見,此時北大形成“為學術而學術”的宗旨,成為純粹的學術研討之所。
北大的歷史,乃至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歷史,要從蔡元培這里重新開始寫了。
愛因斯坦會來的
在蔡元培的心中,北大應該是什么樣的呢?
1916年,蔡元培應黎元洪邀請回到北京,于年底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當時的北大,雖得一新學堂的皮子,卻還是舊社會的里子,權貴之子在此浪蕩三四年混得一紙文憑,校工對學生稱“老爺”行禮,學生對師長則如官級之間,遞“呈文”,傳“手諭”。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來到北大。校工向新校長鞠躬,蔡元培脫下帽子,也回以鞠躬,此后日日如此。一場教育改革——從形制到理念——正在北大校園里,緩慢而堅韌地生出根芽。
蔡元培最為痛恨將大學視為為官致富之道的觀念。大學斷然不是一個給權貴子女來混一紙文憑好去做官的“養成資格之所”,也不應該是培養實用人才的“販賣知識之所”,而應該是學者自由成長的地方,“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蔡元培在自述中回憶,“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他稱這根本的兩科,為“本科”。又因為文理兩科為根本,所以“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干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愿往別種機關去的”,這就又有了“學術”。
我們對現代大學的基本認知,在蔡元培的建設下,已初見雛形。
正因這份對“研究”的看重,蔡元培不僅在國內延攬名家,而且廣邀世界學術巨擘來北大講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他不計代價地“三邀愛因斯坦”。他深感興趣,決心無論花多少錢,都要請愛因斯坦來北大講學。三次受邀后,愛因斯坦答應了北大的請求,最終卻因為當時北大方面不懂“合同”之事,而愛因斯坦只認“契約”,錯過了時機,終未成行。
然而經此一役,外界都已了解,這時的北大已經是一所能容納相對論的大學。一流大學的使命是探究時空真理,這一認識,至今沒有改變。歷史記載,愛因斯坦最后沒來。但是當時人們都那樣相信,愛因斯坦會來的。
你我在何處安身
在教育上求索不止的蔡元培,一直面臨著一個比相對論更難解的問題。
在思想層面,孔教被駁倒,綱常被打破,假如人們不再信仰延續幾千年的規范,在這之后,國人的精神應在何處安放呢?蔡元培試圖為自己、為社會,尋找到一個能填補空白的精神定位。
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學會以“以美育代宗教說”為題發表演說,這一思想也成為他最著名的一個主張。
若只有“美育”二字,它似乎只是教育領域的一個方針,因蔡元培還提及了“宗教”二字,“美育”就被賦予了通往心靈與現世的超越性意義。
蔡元培說的“美”,更像一種“善”,或者,美是通往善的途徑。這并非一種樸素的善良,而是具有啟蒙色彩的人文關懷。美育代宗教,其實質是以科學理性替代愚昧宗教,審美行為凸顯了人的主動性,人能夠自由選擇、自由發展信仰,而無需臣服于什么,乃千年所未有。
蔡元培以一種美好的未來眼光,構想著他心目中那個強健而和美的社會。他規劃了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并行的格局,從公立的胎教院和育嬰院到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健全人格得以長成;提出“五育并舉”的方針,希望通過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塑造合格的共和國民。
教育之為救國,在此意義盡現:“造成完全人格,使國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謂愛國。”為美育振呼的蔡元培,成為當時中國最為赤誠的烏托邦建造者。
只是,以非關利害之心做著攸關國家生死的大事,這對矛盾,在他執掌北大的十年間不斷顯現,而在1919年的5月達到頂峰。
彼岸的烏托邦
學者胡元倓曾以八個字評價蔡元培:有所不為,無所不容。
無所不容,自然指的是蔡元培最著名的兼容并包思想,以及他寬厚的老好人性格;有所不為,大抵是說蔡元培的“不合作”,他不允許自己成為理念的附庸,也不肯在時代的洪流中被裹挾著前行,每每以辭職表達自己的態度。
蔡元培創造了一個奇跡。馮友蘭當時在北大讀書,回憶稱:“僅僅兩年多時間,蔡先生就把北大從一個官僚養成所變為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把死氣沉沉的北大變成一個生動活潑的戰斗堡壘。”
然而,這十年時間,他七次辭職,實際工作時間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慚悚”。
不是在寫辭職信,就是在投辭職信的蔡元培,內心被一個念頭擾動:在那樣的時代,烏托邦是不存在的。他心中那個單純治學的學術天堂,唯有在彼岸,而當時的中華民族,尚未蹚過這條深深的河。
如今,一個新的時代,從北京大學出發,朝向門外的中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