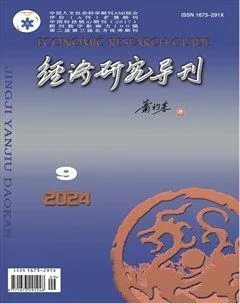試論智慧養老服務中的政府責任
沈思源
摘? ?要:政府在智慧養老服務中履行職責,是現代服務型政府的職能乃至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個縮影。政府主導下的智慧養老服務具有現代老齡化社會治理的特征,是老齡化社會治理的一條新路徑。當前,政府在履行智慧養老服務責任中存在諸多碎片化問題。從實踐上看,應當完善智慧養老服務中的政府責任體系,關注智慧養老服務的制度政策建設、資源整合以及監管機制建設等問題。
關鍵詞:智慧養老;政府責任;老齡化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D669?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4)09-0088-04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日益嚴峻。截至2023年年底,全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9 697萬人,占總人口的21.1%,其中65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1 676萬人,占總人口的15.4%[1]。人口結構老齡化與現有社會經濟體制的不協調給社會平穩運行帶來諸多挑戰,比如對社會保障體制形成壓力、帶來公共安全隱患、對傳統文化造成沖擊[2]。尤其是養老需求在數量和質量上急劇增長,已然是政府和民眾關注的重點問題。
為了更好地滿足日益增長的養老需求,人們開始尋求更加高效便利的養老方式。近些年,互聯網、大數據等新興技術的迅速發展,為人們帶來了智能化的生活方式,人們的思想和行動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養老模式也發生了嬗變,在這個過程中“智慧養老”應運而生。智慧養老可以說是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時代產物。智慧養老服務的運行需要整合多個養老服務供給主體和多種養老資源,其構建和推行依靠個人力量只能是舉步維艱,需要國家行使公權力才能實現。
智慧養老服務體現了服務型政府著力解決民生問題、保證人民的養老權利的特點。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整體性治理有機結合,以高效精準地滿足老人的養老需求為目標,可以說是今后老齡化社會治理的重要路徑。而政府作為構建智慧養老體系的重要社會力量,在構建良好的國家與民眾關系中具有推動作用,是維護社會秩序和提升老齡化治理成效的必備條件。正因如此,智慧養老是老齡化社會治理可能的新路徑,以“國家—社會”關系理論為基礎,論證政府在智慧養老中履行職責的必要性,檢視智慧養老中政府責任的實踐,進而提出智慧養老中政府責任的優化路徑,以期為智慧養老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思路和對策。
二、智慧養老:老齡化社會治理的一條新路徑
既有的關于老齡化社會治理的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將老齡化視為“問題”,形成了對于老齡化社會治理的認知偏差,導致了老齡化社會治理的困境[3]。智慧養老模式正是采取積極的態度應對老齡化進程,并將傳統與現代結合,進而成為老齡化社會治理的一條可能路徑。
(一)智慧養老是老齡化社會治理理念轉變的體現
楊善華認為,可能通過人為的干預改變影響人口老齡化的兩個核心因素,即總和生育率和老年人生理上的衰老,那么也可能通過干預改變人口老齡化進程[4],也就是采用干預方法積極應對老齡化,保障老年群體的生存發展權益。老齡化社會治理理念轉變主要在兩個方面:其一,家庭結構和功能的變遷使得養老服務逐漸由“家庭”走向“社會”。養老服務的社會化要求政府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向全社會提供養老服務,使養老服務成為一種“公共”服務[5]。享受養老服務已成為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內容,政府為民眾提供養老服務不再是人道主義的社會救濟,而是公民的養老權利保障。其二,老齡化的社會治理長期處于碎片化的狀態。老齡化的碎片化治理表現在養老政策、服務供給主體以及資源碎片化和分散化,各部門專注于自己的職能和職責。碎片化的治理模式不僅降低了政策效能,也削弱了制度供給能力,這是整合機制不完善的結果。智慧養老正是利用大數據技術將養老服務供給主體、資源和制度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在一起,避免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沖突,從而實現養老資源的高效利用和養老服務質量的提升,進而有效驅動老齡化的社會治理從“碎片化”邁向“整體性”。整體性治理不僅僅是智慧養老的內在機制與碎片化問題的解決對策,更是老齡化社會治理的內在要求和深層內核。政府通過整體性治理解決碎片化治理困境,更好地為民眾提供養老服務,實現養老權利的有力保障。
(二)智慧養老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治理的結合
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下,“4-2-1”抑或“4-2-2”已成為現代中國家庭結構的重要特征,這些少子化和老齡化的家庭結構削弱了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供給能力。在家庭結構變遷的同時,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隨之興起,代際關系也發生了變化。有學者認為,在現代化進程中,孝的主導性已經式微,但其社會底色沒有變[6]。家庭功能和孝道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發生了變遷,對現代社會有了新的回應并在當今社會發揮作用。傳統家庭文化對家庭凝聚力、代際關系具有很強的約束力,并在未來的家庭結構和家庭功能的變化中表現出極強的韌性,使家庭養老持續作為中國養老中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智能時代的到來,大數據技術能夠為政府治理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信息,是其與整體性治理的重要連接點,有效驅動養老服務邁向整體性治理[7]。智慧養老和老齡化社會治理都不是孤立的制度或實踐,而是多元主體和多元資源協調共治的有機構成。將智慧養老視為一個整體,以整體性和可持續性作為切入點和落腳點,而政府作為主導者,承擔起老齡化治理的治理主體,整合自身資源和內部聯動機制,從制度政策機制上打破碎片化的治理困境。最終實現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家庭、個人等多個主體參與養老服務供給,構成多元共治格局,進而促進老齡化社會治理。
(三)智慧養老是老齡化社會治理的重要路徑
首先,智慧養老是大數據驅動社會治理的重要實踐形式。大數據驅使國家治理的組織結構和決策過程轉型,賦予國家或政府新的角色[8]。大數據對國家治理理念、治理范式和治理手段的革新具有重要影響,進而成為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路徑。同時,大數據技術也是智慧養老的重要技術支撐,在提供養老服務的過程中可以通過智慧平臺的信息交流,實現老齡化社會治理主體的有效參與和養老資源的有效整合。其次,智慧養老擴大了老齡化社會治理的參與力量。老齡化治理是政府、社會組織、家庭、個人等多元社會主體的治理,也是多元社會治理主體共同參與的治理。參與主體多元化是智能時代老齡化社會治理區別于傳統老齡化治理的一大特征,而智慧養老的本質就是協調多元老齡化社會治理主體,整合養老資源和信息。不同的社會治理主體結合自身優勢資源在不同治理階段發揮作用。最后,智慧養老豐富了老齡化社會治理形式。老齡化社會治理中已有社區養老、機構養老、醫養結合、日間照料中心等多種形式,這些老齡化社會治理形式積極應對老齡化,但是都存在其固有的缺陷,不能滿足養老需求的多元化。在此基礎上,老齡化治理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深化,結合現代互聯網信息技術,探索和發展智慧養老模式對老齡化社會治理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三、智慧養老中政府履責的實踐檢視
智慧養老模式是大數據技術和養老產業結合的產物,在其運作過程中,大數據技術促進現有的制度和政策革新,以有效提高資源利用率和服務質量,但這需要政府根據社會與經濟的發展,以超越個體和職能部門的視野進行整體性治理。
(一)智慧養老制度仍需不斷完善
規范的智慧養老制度體系是養老服務供給主體行動的基礎和依據。構建規范的制度體系意味著契約關系的形成,制約著訂立契約雙方的行動,一方面,養老服務供給主體要遵守國家的各項規章制度;另一方面,政府要履行職責維護好供給主體和服務對象的權益,規范市場機制,確保智慧養老的良好運作。實際上,當前我國智慧養老還處于探索階段,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印發了大量的規范性文件,比如,2017年,工業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衛生計生委印發《智慧健康養老產業發展行動計劃(2017—2020年)》;2015年,國務院印發《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按照我國立法法的相關規定,這些智慧養老政策只屬于“其他規范性文件”的范疇,而不屬于法律,即目前智慧養老在法律方面仍需進一步完善[9]。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存在城鄉差異、區域差異,社會基本養老保障制度陷入碎片化的困境,這樣的碎片化現象在智慧養老中也同樣存在,也表現出區域差異和城鄉差異。智慧養老是傳統養老模式智慧化的模式,其發展與智慧社區、智慧醫療等建設密切關聯。比如,上海市、杭州市這樣的新型智慧城市,其智慧平臺、智能技術、大數據等與智慧養老密切相關的體系構建走在全國前列,而社會經濟基礎較差、信息技術發展較為落后的農村和西部城市,智慧養老的建設和推廣舉步維艱,這樣的情況還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不管是智慧養老法律的完善,還是智慧養老政策的碎片化,必須要政府履行職責才能得到有效改善。
(二)養老服務供給主體碎片化
目前智慧養老服務體系構建尚未完善,存在養老服務供給主體碎片化的問題。多元主體參與治理是現代社會治理的特征,但是協調機制不完善導致了碎片化的困境,進而造成資源利用率低和協調成本高等問題。智慧養老中養老服務供給主體碎片化主要表現在科層制和社會分工精細化的安排下,養老服務呈現條塊式分化。一方面,養老服務供給需要科層制體系內各級政府的協調和參與,要進行自上而下的縱向動員。專業分工背景下的職能部門進行自上而下的養老服務供給有效地提高了管理效率,但是各部門按其獨立的職責分工參與養老服務供給,形成了養老服務供給“條條”分割的特征。另一方面,養老服務供給是建立在政府權力的地區劃分基礎之上,因而各個地區都是獨立的養老服務供給主體。政府權力的分散化實際上就決定了養老服務供給的碎片化,進而構成養老服務供給的地區分化,形成明顯的“塊塊”劃分現狀。比如,2017年工信部、民政部等部門制定的《智慧健康養老產業發展行動計劃(2017—2020年)》,盡管文件中制定了總體目標和重要任務,但是對于各部門的具體職能、任務以及實施細則并無具體的制度和程序設計,因而容易導致“多頭管理”的局面或“權力死角”的困境,進而降低了政策效能、養老供給效率和質量。
(三)養老服務資源分散化
事實上,養老服務供給過程中的主體協調與資源整合是同步的。主體的協調更多的是科層制內部權力的轉移,而資源整合則相對復雜,由于地區、行業等因素存在差異。與養老供給主體碎片化相對應,現有養老服務資源呈現分散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智慧養老資源分散在不同部門。比如,衛健委主要負責制定和落實醫養結合政策,并承擔老年醫療健康、疾病防治、心理健康等工作;人社部門主要負責養老服務人員的專業化培訓、資格審核、人才隊伍培養等工作;殘聯涉及到殘障老人的權益保障、扶助殘障老人平等參與社會生活等工作。精細化分工背景下涉及養老服務供給的職能部門根據其專業化職責制定相應的政策制度,進而造成一系列的行政沖突,難以實現資源有效整合與統一服務供給。其二,智慧養老資源分散在不同地區。從實踐層面看,各部門的養老服務資源最終要落實到地方政府。政府權力分散化下,不利于養老服務資源的有效利用和最優配置,導致養老資源分散化,無法實現跨域整合資源、共享資源。
四、智慧養老中政府責任體系的完善之道
智慧養老是智能時代提升養老服務質量的重要方式,要想不斷發展和推行并成為老齡化社會治理的重要路徑,需要不斷完善政府責任體系,加快制度政策建設,加快協調理念落到實處以整合養老資源,并加快監管機制建設,以實現養老服務的高效優質供給。
(一)加快智慧養老的制度政策建設
首先,由于我國養老法律的缺失以及養老政策碎片化導致智慧養老服務運行中存在一系列的行政沖突。相關職能部門應該進一步構建智慧養老政策的規范化路徑,為智慧養老運作提供制度依據,以提高智慧養老的服務質量和效率。基于此,應該經過調研分析后先制定智慧養老發展過程中可能涉及到的關鍵性法律,然后根據實踐的基礎啟動立法程序,完善智慧養老法律制度。其次,我國智慧養老政策存在碎片化的現象,為了提升養老服務的規范性和有序性,政府應該重視智慧養老的頂層設計,加快體系化建設。就目前我國的智慧養老政策而言,整合各項政策應從兩個方面進行。其一,應明確各級政府與職能部門之間的權責。在養老服務供給過程中,職能部門與政府之間存在“權責分立”甚至出現“避責”的現象,導致基層政府創新缺失、權威流失、被動回應等嚴重后果,并引發鏈式反應[10],不利于老齡化的社會治理。其二,應細化具體的實施準則。經過最高權力的決策制定出的制度政策,其意義在于執行過程中能夠落到實處改善民生。政府在推動智慧養老規范化與法制化的過程中,應制定相關的實施細則,確保養老服務供給能夠有序進行。
(二)加快智慧養老的服務資源整合
高效協調智慧養老服務供給主體是整體性治理的思想前提,而整合多個養老服務供給主體的資源是將協調思想落到實處,整合的目的在于打破空間和地域的限制。智慧養老在資源整合過程中充分利用大數據技術,具有較強的技術主導傾向,使養老資源的整合缺乏社會基礎。養老服務資源的整合主要是在兩個方面:其一,加強各職能部門之間的資源整合。將民政部門、老齡辦、衛健委等的養老服務資源有機整合,尤其是信息資源,將信息數據在大數據平臺上進行整合和共享,打破傳統信息壁壘,促進各部門之間高效聯動,提高資源利用率。其二,加快社會組織之間的資源整合。社會組織作為智慧養老服務的重要主體,具有協同社會資源的特點。政府與多元社會組織共同參與老齡化社會治理,以多元協同參與為基礎的運作,有利于實現養老資源的整合。在此過程中,政府與多元社會組織分享老齡化社會治理的權力,形成協同共治的模式,進而整合各社會組織的優勢資源。比如,整合醫療衛生資源、社工資源、文化娛樂資源等,共同為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娛樂等多元化服務,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質量。
(三)加快智慧養老的監管機制建設
智慧養老在保障基礎養老服務的基礎上,提供更加精準化、智慧化和個性化的養老服務,以更好地構建服務型政府。但是在提供養老服務的過程中,不能脫離政府的監管。因而,政府應通過政策制定,充分發揮引導與監管的作用,保障養老服務供給的效率和質量。政府可以結合老年人的需求、服務對象認同度、服務質量反饋等信息構建智慧養老服務的監管體系,明確服務標準,實現智慧養老服務規范化,以提高智慧養老服務的效率和滿意度,使民生得到改善。此外,政府還應該加快完善服務人員從業制度和服務標準、信用管理體系以及服務糾紛處理機制,有力保護智慧養老中老人的合法權益,促進老齡化社會治理的成效。
五、結束語
人口老齡化日益嚴峻,養老服務供給不足,養老需求日益增長,急需探尋新的養老模式。智慧養老是大數據、互聯網等新興技術與整體性治理理念的有機結合,政府在其中起主導作用,有力推動了養老服務智慧化發展,提升了養老服務效率和質量。這種創新模式無疑是治理人口老齡化的有效路徑,但是現有的制度整合機制不夠完善,導致了制度不規范、養老服務主體及其資源碎片化。這些問題僅依靠個體力量是無法解決的,必須要政府承擔起責任進行整體性治理才能夠有效改善,進而有力保障民眾的養老權利。
參考文獻:
[1]? ?中華人民共和國202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2024-02-29)[2024-03-05].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2/content_6934935.htm.
[2]? ?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視角下的中國人口老齡化[J].中國社會科學,2011(3):121-138,222-223.
[3]? ?胡湛,宋靚珺,郭德君.對中國老齡社會治理模式的反思[J].學習與實踐,2019(11):81-91.
[4]? ?楊善華.“責任倫理”主導下的積極養老與老齡化的社會治理[J].新視野,2019(4):73-77.
[5]? ?魯迎春,陳奇星.從“慈善救濟”到“權利保障”:上海養老服務供給中的政府責任轉型[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6,17(2):76-84.
[6]? ?翟學偉.“孝”之道的社會學探索[J].社會,2019,39(5):127-161.
[7]? ?杜春林,臧璐衡.從“碎片化運作”到“整體性治理”:智慧養老服務供給的路徑創新研究[J].學習與實踐,2020(7):92-101.
[8]? ?王向民.大數據時代的國家治理轉型[J].探索與爭鳴,2014(10):59-62.
[9]? ?粟丹.我國智慧養老模式的法律特征及其制度需求:以智慧養老政策為中心的考察[J].江漢學術,2018,37(6):50-59.
[10]? ?倪星,王銳.權責分立與基層避責:一種理論解釋[J].中國社會科學,2018(5):116-135,206-207.
[責任編輯? ?劉? ?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