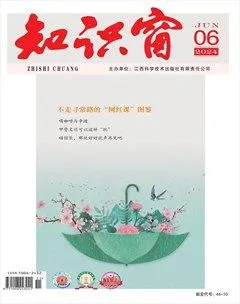方言種種
彭妤
這是屬于情感的方言
前不久,一段用浙江省瑞安方言進行演講的視頻在網絡上“走紅”。在瑞安一中的高三成人禮上,學生代表李超慧堅持全程用老家方言上臺演講,原因只有一個:他的媽媽不會說普通話,而他的演講是說給媽媽聽的。“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風”,在回蕩著李超慧方言的禮堂里,能完全理解那些方言的或許只有他和媽媽。但那又怎樣?天南地北的網友都表示聽懂了,依靠的不是耳朵,而是真情。
這是屬于文藝的方言
有說給一個人聽的方言,就有說給很多人聽的方言,它常常出現在書卷里、熒屏上。上海作家金宇澄用上海方言寫就小說《繁花》,王家衛導演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也首選“滬語版”。茅盾文學獎組委會對小說《繁花》的授獎詞是:金宇澄遙承近代小說傳統,將滿含文化記憶和生活氣息的方言重新擦亮,反復調試,如鹽溶水般匯入現代漢語的修辭系統,如一個生動的說書人,將獨特的音色和腔調賦予世界,將人們帶入現代都市生活的夾層和褶皺,亂花迷眼,水銀瀉地。觀眾評價電視劇《繁花》:“不看‘滬語版,就相當于去重慶的火鍋店點清湯鍋底。”
這是屬于國學的方言
方言不僅能寫書,還可以用來讀詩。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老師劉媛常年堅持一項教學新體驗。在每學期大學語文課開課時,面對來自五湖四海的大一新生,劉媛都會鼓勵他們用家鄉方言讀一讀“國風”。因秋季開學是在二十四節氣的白露前后,他們便常常從《秦風》“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讀起。這些年,僅《蒹葭》,劉媛就聽過滬語版、蘇州話版、紹興話版、寧波話版,甚至還聽過猶如“加密通話”的溫州話版。劉媛坦言,她無意在課堂上做方言調查,對音韻學更是一竅不通,甚至個人的研究方向都不是中國古代文學。之所以如此樂此不疲地讓新生用方言讀“國風”,除了個人趣味之外,她是真心希望那些學中文的學生,能在南腔北調中聽一聽“風”從哪里來,詩從哪里來,中國從哪里來。
這是屬于傳承的方言
有人說方言,也有人學方言。在主持各類節目時,汪涵在各種方言之間轉換自如,方言既是他的主持秘籍,也是他的特有標識。自己模仿和學說之后,汪涵最希望當下的年輕人有繼續講方言的意愿,了解方言背后深厚的文化支撐。他認為保護語言的多樣性就像保護物種多樣性一樣急迫,他決心保護、傳承方言。2015年起,他自掏腰包,發起了進行方言調查與保護的“響應”計劃,“響應”即“鄉音”。汪涵受聘擔任中國語言資源保護研究中心顧問后,又極力促成我國首座實體語言資源博物館——中國語言資源博物館建設。“最起碼若干年之后,能有一個博物館,你愿意走進去的話,能聽到100年前、500年前,跟你同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祖先,是用這樣的語言來表達他當時的喜怒哀樂的。”汪涵說,“如果我們沒有保護方言的意識,100年后的人類將無法聽到今天的聲音。”
這是屬于民族的方言
講到學說方言這件事,有個名字永遠繞不過去——趙元任。他是蜚聲海內外的“雜家型”大師,一生學會并精通33種中國方言,去全國各地都會被當地人誤認為本地人。女兒問趙元任為什么研究這些,他笑答:“因為好玩兒。”哪里是因為好玩,趙元任學遍全國各地的方言,是為了設計官方標準國語時做到盡可能均衡,建立簡便一致的系統發音。
從1927年起,趙元任奔波全國各地,展開了中國第一次最系統的方言調查,出版《現代吳語的研究》。這部中國首次用現代語言學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成為現代漢語方言學誕生的標志。此后多次調查研究,趙元任還發表了《國語羅馬字的研究》。這篇趙元任自己口中的“草稿”,比當時任何一份拉丁字母都要完善,最終成為漢語拼音的基礎。隨后,“走到中國哪里都是‘老鄉”的趙元任編寫了各種教材,全力推廣國民學說普通話,被譽為“中國語言學之父”。可以說,每個學習漢語的人,都在享受趙元任先生的研究成果。
方言,是有聲的韻腳,也是無形的賡續。鄉愁記憶、地域符號、泥土基因、情感密碼……這些形容都不足以注解方言真正的奧義。在那些割也割不斷、堵也堵不住的語句流淌中,方言的河流,涌動之處是唇齒間,發端之源在血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