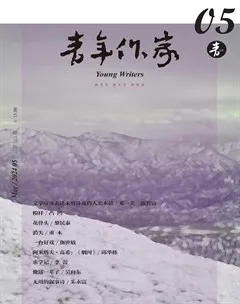紀念一段消失的生活
重木
弗洛伊德在其著名的文章《憂郁與哀悼》中區分了這兩種存在狀態,哀悼指的是通過一系列程式化的紀念方式,對失去的人或物進行恰當的送別,由此得以接受他者的離開或消失;但憂郁卻源自這一過程的失效,從而導致我們把失去的他者內化到自己體內,最終導致原本投注在他者身上的憤怒轉向了自身,由此造成了自我攻擊。憂郁既是一種存在狀態,也是一種氤氳不去的氛圍,而它的產生往往源自生活中的創傷,這樣的創傷有時會是災難級別的,有時可能只對特定的個體才有強烈的沖擊。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不得不處理人生與生活中諸多的創傷,而如何擺脫或是走出憂郁,就成為《消失》中好幾個人物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寫《消失》或許可以說是為了紀念一段消失的、無名的生活,有的人可能熬了過來,遺忘傷口,繼續往前;有的人則不斷地被舊日的陰影纏繞,創傷無法愈合,最終導致繼續生活的可能都在不斷衰竭。《消失》中陳寒的個人遭遇是特殊的,但他面對的困境和問題則具有普遍性,尤其對當下的我們來說,如何處理好舊日的傷口成為每個人的必修課,因此我想通過不同的角色去探索不同的選擇與可能性,而且或許恰恰是這些差異化的選擇才讓未來變得值得期待。
《消失》是2023年初寫的,對于我自己而言,或許也可以看作是某種自我療愈的企圖。在這之前,我已經有快兩年的時間沒再寫小說,既因為忙著其他事情,也因為對于寫小說這件事產生了猶疑,尤其是對于我自身是否還必要的懷疑。從大學時開始寫小說,被一股強大的渴望與好奇驅使著,所以動力似乎源源不斷,但伴隨著我開始研究理論,就漸漸地意識到,曾經通過構建小說而企圖理解和思考的問題,如今可以通過哲學研究而更加清晰且條理化地探索,寫小說對于我似乎逐漸成為一個非必要的選擇,而曾經那股強勢的內驅力似乎也在不斷地消失,所以最終停了筆。《消失》是這漫長輾轉思考中的產物,幾乎是自然而然地就寫了,只是因為我對自己所虛構的這個叫“陳寒”的生活——尤其是在他遭遇這么多創傷之后的選擇和如何繼續生活下去——產生了強烈的好奇,這股好奇讓寫小說再次變得可能。
這些問題對于我自己來說,似乎暫時依舊還處在過程之中,但好像也沒那么重要了。而在災難之后,我漸漸發現,寫小說作為一種行動,或許依舊可欲且意義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