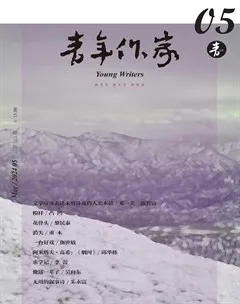求學記
我在村人的靈魂里長大
我的村莊叫河村。河村是山東省高密縣姜莊鎮東北方向的一座村莊。河村的村后就是人工河膠萊河。河村只有一所小學——河村小學。河村小學坐落在村中心的東西大路和南北大路交叉的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從我的父輩們有記憶開始,村里就有一座寺廟,在膠萊河的南岸邊。后來這座廟就成了河村的小學學校,我的父親和大姑父他們都是在這座廟里讀完的小學。1976年,這些廟磚和一些墳磚建起了河村小學。至今,河村小學的屋山的青磚上,還刻著“1976年建成”的字樣。1980年代后期的河村小學,校舍是平房。整個校園空曠靜寂,高高的青磚墻與外面的農田和人家隔開。
讀小學之前,我上了一年的育紅班,育紅班就是學前班。育紅班設在河村小學的校園里面。那一年,小學老師家的玉米堆放在校園里,成了山,我們這些學前班的小孩就幫她剝玉米皮,那座小山像是永遠也干不完的苦役。
我的小學語文老師叫王秋玲。每次期中或期末考試,我翻到語文試卷的最后,看到作文題的得分,都是“30+3分”或者“30+4分”。讀小學時,小姑是學校圖書室的管理員。她從圖書室里出來,帶上門,把小開本的莎士比亞讀本、《紅蕾》等雜志拿給站在校門口的我。這是我最早接觸書刊。
1991年我開始讀初中,讀的是鎮一中——姜莊一中,期中、期末的成績,我都排在前三名。那時候,都是發紅色紙的光榮榜,排出前一百名,發到每個同學的手中。紅色的光榮榜,高高地貼在學校教學樓的屋山上。
女生宿舍的床,是兩層的通鋪。一開始,我睡在一層,面向北墻。晚上的時候,我趴在床上,點著蠟燭看書。后來,我搬到了二層,靠南窗。夜晚的時候,窗外下雪了,我斜靠在床上,映著月光下的雪看書,用“映雪”“刺股”的故事激勵著自己。早上,我很早就起床了,教室的門還沒有開,我就站在路燈下看書。班里教室的鑰匙是阿成拿著。阿成低著頭走過來了,我也就進了教室。晚上的時候,我會在教室里看書到最晚。教室的門關了,我就換一間還亮著燈的教室。阿成鎖上門,低著頭往南走了。很奇怪的就是,男生宿舍是在北面。阿成往南面去干嗎呢?難道是去上廁所了?每天早上我看到的阿城,也是從南面走來。南面是校門口的方向。他是在外面租房子住嗎?那個時候,學生哪里有這個錢?他可能就是去上廁所了,或者去散步了。我的近視眼,就是那時候得的。我的眼睛近視了,同桌孫英把她的一副近視眼鏡借給我戴,那時候我們不知道這樣是會把眼睛戴壞的。戴了很短的一段時間,我就去鎮上的眼鏡店配了眼鏡,檢查有沒有散光。
有一天,坐在我身后的阿成遞給我一個筆記本。上面粘著貼畫,是當時流行的電視劇《射雕英雄傳》的人物貼紙,翁美玲演黃蓉,黃日華演郭靖。阿成是有些像郭靖:傻傻的、憨憨的、敦敦實實的。筆記本上面寫著:做我女朋友,可以嗎?我不想談戀愛,也不想阿成做我的男朋友,我給他回復:我現在只想好好學習。
大約初二時,有一天,幾個同學錯落地圍坐著聽我唱歌。大家認為我的聲音好聽,推舉我做了文藝委員。每天早晨,早自習前,我站在講臺上,領著全班同學唱歌。有一次,我正在講解《讓我們蕩起雙槳》的歌詞,班主任兼數學老師張老師鼓著掌從窗外走進了教室。張老師個子高,身材比較魁梧,白色面皮,然而他總是沉默的,最多抿嘴一笑。一次,在學校的作文競賽中,我得了一個硬殼筆記本。我一句話不說地拿給他。我覺得這次獲獎是他培育的結果。他坐在講臺后面的椅子上,沉默地接下,什么也沒說。
課堂上,老師問大家的理想。我站起來說:“我想當作家。”班里那個總是跟我競爭的女孩阿巧說,她想當警察。那時,學校里組織的作文競賽,我得到的方格作文本、硬皮筆記本、筆等獎品堆滿了一抽屜。我把那個抽屜鎖了起來,那是少女時期我最神秘的一個抽屜,我總是夢見它。一直到我離家讀大學、讀研究生,有一次父親告訴我,夜里家里進了小偷,我那個抽屜被撬開了。我回去時發現,鎖孔被損壞得厲害。那個抽屜,再也鎖不住我的夢了。
我人生的第一筆稿費有五塊錢,是讀初中時獲得的。學校里組織演講比賽,我演講的題目是《我的家鄉》。那篇演講稿,被縣城廣播臺選中。我拿著匯款單,同學玉珍陪著我去郵局取稿費。但是郵局告訴我,還需要身份證。我懶得再跑一趟,那五塊錢稿費,算是捐給了郵局。那時我對錢沒有啥概念,又不愿意費事。讀小學時,六一文藝匯演,我就發現了口紅的秘密:涂在嘴唇上,很漂亮。一只口紅就可以讓一個女孩子瞬間變美。后來我讀張愛玲的書,她說她用第一筆稿費買了一支口紅。她的嘴唇,永遠都是紅艷艷的。
李蕾這個名字,是小姑給我取的。她的名字是“秀霞”。霞和蕾,都是女孩子的名字。鄉間的女孩子,名字取得隨意,小姑給我取名字的時候,或許也沒想這么多。我的乳名是蕾。十三歲時,我寫著“蕾”字,覺得這個字字形結構太局促了、筆畫太多了,太女孩兒化了。于是,我改成了“磊”字,希望自己光明磊落、大氣。二姑父、四姑父,都是我當時就讀的姜莊一中的老師。我請他們兩位陪著我到鎮上的派出所改了名字。
我還保留著一張“家庭通知書”,時間是1994年7月21日,初三的課程結束時。數學老師兼班主任徐老師在上面,用鋼筆寫下了對我的評語:該生思想端正,學習認真刻苦,成績優秀,能嚴格遵守紀律,對班級工作認真大膽,望更加努力!如今,這些墨跡有些斑駁,但還能辨識清楚。徐老師個子不高,走路的時候目光堅定地看著前方。早自習的時候,他給全班同學念他喜歡的汪國真的詩。
后來,父親讓我考中專。我是數學課代表,我去徐老師辦公室交全班同學的作業時,他跟我說,他很后悔讀了中專,讓我一定要考高中。其實,不管徐老師怎么說,我是一定會考高中的,一定要讀大學的。這一點,從我在河村的少女時期開始就沒有猶豫過。望著河村一望無際的田野,我只覺得孤單。我研究每一只花生殼的內紋,光滑的內壁布滿紫色泛藍的紋。多數的花生都是兩粒,然而有的是三粒,鼓鼓的,歪著脖,很神氣。花生殼的外表像麻袋一樣。正生長著的芝麻籽在成熟之前是白色的、嫩嫩的。我研究剝掉粒的玉米骨,上面鑲嵌著一個一個空缺的窩,那正是它被剝掉的牙齒。我看著大蔥的花苞在干裂的土地上生長,直到一根根花穗撐破皮,仰天招搖。我看著秋天的豆莢炸裂,豆粒掉入土壤。我看著一片接一片的綠色的小麥苗,它們每年都這樣。我走在花生地里,半截褲腿被打濕。我摘棉花上的蟲子,我害怕蟲子,就用一片綠葉裹著蟲子,然后殘忍地把它一撕兩半。我太孤單了,我要離開農村。
我只報考了高密一中,沒有填報其他學校。當時為什么只填報了高密一中?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當時信心十足,我只要這個,我可以,我肯定可以。當時的我,沒有患得患失,沒有猶豫不決,沒有給自己留下后路。那一年,我15歲。
1995年,我初中畢業。離開校園的那一天,全班同學在一個教室里面,圍著一圈桌子,分成兩列,阿成舉起啤酒杯跟我碰杯,他淚流滿面。
從姜莊一中考入高密一中的學生一共有八人。能考上這所高中是全市尤其是農村孩子的榮耀。我考入了高密一中,我的遠航從這里揚帆啟程。
讀高密一中時,平日的考試成績,我是班里的前五名,有時是前三名。大約高二時,一次數學考試,同桌張捷拉過我的試卷對我說:“給我抄抄。”“抄吧。”張捷從家里給我帶了兩個韭菜盒子,鼓鼓的肚腹,兩面煎得金黃油光,一看就很香。她給我,我說那她也要吃我的爐包(我從家里帶的,媽媽給我做的)。她不要。我說那我也不要。她說:“不要算了。”我有著農村孩子的自尊。張捷的父親在高密縣城的一家工廠做科長,高考前,他去北京出差,到北京的書店里給張捷買了模擬試題。試卷垂下張捷的課桌。我沒有跟她說:給我看看。我是否暈染了河村人、河村男人、鎮上男人的沉默?高考前,張捷每天帶一個雞蛋到教室吃。有一天,她跟我說,她媽媽說每天也給我煮一個。我把錢給她。有一次她說:“有一個雞蛋破了,還你一個。”她有著縣城孩子的主動。高考前夕,我還是學習委員,有一次,班主任巡邏到我的面前,對我說:“你考上北師大,沒有問題。”北師大,我才不要考。我在心里想。然而,北大還是南大,我心里是沒有譜的,也就是說,沒有具體的設想。
1998年,我參加高考。那一年,是可以在查分機上查分數的。那個7月,我來到高密縣城,在查分機上查到了我的分數。645分,只比本科錄取線高出了兩分。“啊——”我沖出了人群。我的身后,聽到一個不理解的女聲,“過了本科分數線,還不高興!”那天下著小雨。我沖進了小雨。一個人坐在臺子上,發呆。
誰也沒想到,我會考得這么差。班主任、班里的同學們、河村的人們、我的父母、弟弟妹妹。大姑說,要不去濟南查查分數,別把檔案弄混了。我一個人躲在房間里傷心,家人誰也不敢過來安慰我。
我看了省內的大學,我的分數可以填報煙臺師范學院、聊城師范學院。我選擇了煙臺師范學院,因為在海邊。我選的是中文系。我語文好,我想當一個作家。我想過是否復讀一年再考。但是,有可能一年后考的分數,還不如現在的。而且加入復讀的大軍,游擊戰一樣地復讀,讓我覺得很怪異。我決定,讀大學期間考研。張捷平時的成績不如我,她考上了中國政法大學。
為什么我的高考沒有考好?我想可能有各種因素。我當時就讀的高密一中,實行素質教育。這在山東省是開先河的。高考前一個月,學校放假了,讓同學們自習。我當時不會自學。因此,那一個月抓瞎了。還有,高考前,我的母親出了車禍。我父親醉酒后,開著他的三輪車,把我的母親翻到了溝里。母親胸前的幾根肋骨斷了。我去鎮醫院陪伴了母親幾天。我的情緒低落,這是否影響到了考試?
也可能是我的作文沒有寫好,因為我沒有從我的真心所感來寫。那年高考的作文題目是《一件令人羞愧的小事》。我本想寫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真事兒:我剛上高中時,語文老師郭老師極為欣賞我的習作,給我的一篇作文寫評語:好久沒有讀到這樣的文章了,驚訝在于此,驚異在于此。郭老師給全班同學讀了我的這篇“作文”。但這篇文章,是我抄的。我羞愧極了。一個晚自習,郭老師把我叫到教室外,鄭重地讓我當學校幼林文學社的社長。郭老師的臉長長的,很嚴肅。我想到,那篇我抄的作文,我覺得自己沒有寫作能力。于是,我沉默地拒絕了。如果我把這件事兒寫在高考的作文中,一是有道德上的羞恥感,二是擔心萬一閱讀老師給我判零分。于是,我放棄了這樣一個寫作設想,胡編了一篇。胡編的作文,邏輯肯定是不通的。這道作文題目,我肯定是得了低分。
26年來,這件事一直沉重地壓在我的心頭。2021年5月,我為了寫作而回顧往事,聯系上了郭老師。交談之中,我才知道,他平日里只閱讀西方經典和中國古代經典。“文學之路很難走,除非像莫言、余華、閻連科、陳忠實、賈平凹等人,有長久旺盛的創作生命力,對眾多作家來說,寫作生命是有限的。中國古典文學成就更高。改革開放之后現當代文學多借鑒西方現代派,總能在莫言、余華、格非、劉震云、陳忠實等人的身上看到馬爾克斯、福克納、卡夫卡、肖洛霍夫的影子。”他說道。
那么,我一入學時,他就那么高看我的作文,我的特質真的很優異?我跟他談起當年他請我做文學社社長,對他表示感謝。但他不記得這事了。然而我始終沒敢告訴他,那曾藏在我心里26年的秘密。
自考達人大妹
1993年春天,我正讀初中二年級,我的父親蓋好了現在我家住的那座房子。住進這座新房子,我和大妹睡一個房間。她聽了父親的話考取了中專,是她愿意委屈自己成全別人。大妹覺得,家里不能三個人都上大學,父母負擔不起。弟弟是家里的兒子,大妹覺得弟弟是一定要上高中的。她天然地自覺服從兒子優先的安排。于是,她決定不考高中。她讀初中時的成績不如我,也不如弟弟,但是也不過就弱那么一點而已。以她的聰明和成績,是完全可以考上高中的。
大妹讀的中專,叫山東銀行學校,專業是經貿英語。這所中專學校委托高密一中作為培訓點。因此,大妹讀中專時,和我同處一個校園。我開始讀高三時,大妹開始讀中專的第一年。我們的教學樓,在校園的正中心。而大妹的學校,在校園東面角落里的一隅。1991年我讀初一時,開始學英語,學校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英語教材。大妹比我小兩歲,她也是從初一開始學英語的,也是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1997年,新標準英語這個版本的新教材,山東省是示范點,小學三年級的學生開始用這套教材上英語課。但是,山東省當時缺少小學英語老師,于是招了兩批中專生,讓他們學英語,以后當小學英語老師。高密市招了兩批,96級一批,97級一批,共100人,稱為“96英”“97英”。大妹2000年中專畢業。山東省2001年開始普遍使用新標準英語的教材。
2001年之前,對于中專畢業生,政府包分配工作。2002年開始,中專畢業生自主擇業,也就是政府不再包分配。但是,即使在2001年之前,也不是所有的中專畢業生都包分配工作。像大妹讀的中專班,有40個人,70%的人通過了崗前考試,走上了小學英語老師的工作崗位。剩下的30%的人,有兩種選擇方式。一種是,第二年再參加崗前考試;另一種是進工廠。大妹的同學,有的就進了工廠。第二年如果還沒通過崗前考試,那么國家不再負責分配,連進工廠也不負責安排了。大妹中專畢業后,被分配到姜莊小學。這所小學是鎮上唯一的小學,其他的小學都是村小,即姜莊鎮下屬的村莊的小學。大妹在姜莊小學做小學英語老師,一干就是十年。大妹讀中專時就開始自考專科。自考的途徑是:買書,學習,參加考試。一共要考九門,一次報兩門。每次考試,她都是一次性通過的。當時全班同學都在老師的鼓勵下參加了自考,但是很多人中途放棄了。大妹一直堅持了下來。到2000年中專畢業時,她就剩下口語交際這一門沒有過了。這門她是參加工作后去濰坊考的,考了兩次才通過。2002年,大妹拿到了山東大學自考專科的畢業證。
2000年,大妹每月領到手的工資接近300元。到2004年,大妹每月領到手的工資是700元。
大妹每月領到300元時,交給父親200元。她懂得照顧父親。2004年,大妹23歲,參加了全國成人高考,考了語文、政治、英語三門,考上了山東師范大學的函授本科。大妹跟父親說:“我不給家里交錢了,我的錢要用來交學費。”大妹上函授本科,半年交一次學費,一次交2000多元。這筆錢,大妹要攢好幾個月。同時,2004年大妹結婚了,她的心開始轉向了她的小家庭。每年寒暑假,大妹都去濰坊商校參加山師大函授班的上課,由山東師范大學派老師來給她們上課,考試通過才能畢業。2007年,大妹讀完了函授。
2010年,大妹通過考試,應聘了處于高密縣郊大王莊的高密實驗學校。大妹來到了縣城的邊緣。如果要當初中英語老師,需要考中學老師的資格證,大妹沒考。這所小學當時要成立心理咨詢室,于是派大妹去學心理咨詢。2012年,大妹考取了三級心理咨詢師。二級心理咨詢師就可以開心理咨詢室了,大妹不考了,她覺得心理學太深奧了,是要解決人的心理問題的,她沒有這方面的志向。2012年,大妹還考取了計算機證,為此她通過了四門計算機科目的考試。計算機證,評高級教師時才有用。大妹不參加高級教師評定,計算機證對她沒用。看到別人考,她也跟著考。
2014年,大妹憑自己的實力,調入高密東關小學。東關小學是高密縣城最大的幾所小學之一,也就是幾所重點小學之一。就這樣,大妹進了城。大妹調入這所小學,還有一個原因,這所學校離家近,方便照顧兒子。大妹調入東關小學時,學校里正缺少語文老師和班主任,于是大妹就做了語文老師和班主任。在高密縣城以及之下的小學,老師們基本是全能,學校里缺少什么科目的老師,他們都可以干。大妹各個年級都教,但是她主要是教五六年級。在鎮上教小學時,大妹感到輕松,因為鎮上小學的學生都是農村的孩子,農村的孩子樸實聽話。縣城里的孩子主意多,家長們無論是金錢、社會地位還是人脈也都更有能耐,因此有些孩子不聽話。大妹明顯感覺出來,縣城里的孩子比鎮上的孩子靈精,因為他們從小見的世面多一些,精神舒展得多。
大妹自考專科和函授本科,只是想提高自己的學歷。她的學歷,在她評職稱時派上了用場。2021年大妹晉升為中級教師。中級教師分三個檔共11級,大妹是11級,最高級是1級。全國的小學、初中、高中的教師的職稱是通用的。晉升高級教師時,分配給小學的名額少,而且小學教師多,因為小學是最初級的教育,上小學的孩子最多,所以需要的教師多。高級教師的職稱,分配給高中老師的名額最多。對中級教師的評定,國家層面傾斜于鄉鎮的小學,為的是讓鄉鎮小學的教師能安心于教學崗位。如果大妹一直待在大王莊那所小學,她2016年就能評上中級教師了,也是因為那所小學的老師少,評職稱相對容易。雖然中級教師的名額基本上是按照每所小學的教師人數的比例來分配的,例如,10個老師就給一個名額,20個老師就給兩個名額,但是老師多的小學,競爭非常激烈。東關小學老師很多,大妹覺得在這里很難評上高級教師,她想以后再換一所教師人數少的小學,以便能在退休之前評上高級教師。在目前這所小學,許多老師在退休之前都評不上高級教師。而評上高級教師,退休金就會領得多。
前幾年,我在大妹家的書房里,看到了她就職的高密小學的歷年考評表,她都是優秀,每一項都是A。那些評語,自然都是寫得循規蹈矩,是我這樣的自由分子有些不以為然的,然而她就那樣扎扎實實地生活在她的縣城。
二妹的獨立人生
我的二妹,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了村東的西劉村一戶姓張的人家撫養。二妹出生的那一年,是1985年。當時還在實行計劃生育。父親想生兒子的心還不死,只有把二妹送出去,他才有機會生兒子。我的叔叔為了生兒子,也是這么干的。
這戶姓張的人家只有一個兒子,是我的小學同學張軍。從小學三年級開始,西劉村的小學遷入我們村,他進到我所在的班級讀書。每次考試,他都是考倒數第一名,成績是個位數。
把二妹送給這戶人家,是二外祖父選定的。二外祖父的村子和張姓人家的村子,隔著一條河相望。這條河就是膠萊河的東端,從河村村后的膠萊河河段一直往東流淌。一天,趁著河村播放露天電影,二外祖父和父親把二妹抱出了河村。二外祖父趕緊去通知張姓人家來領孩子,父親趁人不注意把用小花棉被包裹好的二妹輕輕放在橋頭上。張姓人家從橋頭上把二妹抱起,對著橋畔的人大聲說:“我撿了一個孩子。”那個橋頭,修得高高的。比河村的橋頭,要高得太多。我小時候看那個橋頭,簡直就是一個山頭、一個碉堡。橋頭上,是神秘的森林。我時常,就沿著河邊,踩著河邊的灌木叢延伸出來的青草,往西走,走回河村的家中。
收養也算二胎。二妹的養父母因此被罰了款。二妹讀育紅班時,小姑在她們村的育紅班當音樂老師。那時候,由學生的家長管老師午飯。有一次,小姑到二妹家吃飯,二妹包了餃子給小姑吃,那時候二妹已經會做飯了。小姑對二妹很親近。
1990年代河村擴建了校舍,河村成為學區,附近的西劉村、王干壩、老屯等村莊的學齡孩子來到河村小學讀小學。從小學一年級開始,二妹即來到河村讀書。她也跟著在河村小學當音樂教師的小姑學跳舞。六一的排演,她蹲在前面一排的正中間,臉龐上涂著粉紅色的胭脂,一只手揮舞著一把粉紅色的扇子。
不是張家的親生女兒這件事,二妹剛讀小學時心理上受到的影響比較大。那時,她的屁股后面總有小孩跟著起哄說,她不是親生的。她就回家問。張氏夫婦安慰她道,別聽他們亂說。為此,她一直有心理陰影。遇到想不明白、不開心、不順利的時候,她就想,如果生活在親生父母的家里,自己的生活軌跡就不是這樣了。她產生了一種深深的被遺棄的感覺,并反復地想,“我的父母為什么不要我了呢?是我哪里不好嗎?我哪里不好呢?”但是,她慢慢告訴自己,生活就是生活,沒有如果,這就是命。
張軍人實誠,沒有壞心眼。他初中沒有上完,就輟學了。二妹乖巧懂事,張氏夫婦很疼她,比對他們自己的兒子還好。養父張發展從來沒有打過她,張軍有時候還挨張發展的皮鞭。二妹小的時候,張氏夫婦不讓她下地干活,她就待在家里做飯。二妹做的飯,一家人喜歡吃,她就很開心。這可能也是她后來讀書期間選擇去飯店打工、開小飯館的原因。
二妹讀小學二年級時,張發展在地里種樹,不小心把同村的站在一旁的劉村長的腿弄傷了。劉村長得理不饒人,要求他賠償,二人吵了起來。張發展的脾氣有點暴躁,一拳揮在了劉村長的胸口。鎮上派出所和黨委都派人來到了西劉村,要拘留張發展。張發展一介農民,親族中也沒有手握權力的人,他陷入了一籌莫展之中。沒有辦法,張發展就帶著二妹,來到了河村陳支書家,請求陳支書幫一下忙。陳支書是我的大姑父。當時,他做河村支書已經十幾年了,跟鎮上的這些人以及鄰村的村干部都很熟,便調解了此事。
經過了這件事,二妹還不是很確定她和父親的父女關系。她在河村讀小學時,小姑帶著她,去家里吃過兩次飯。她最后確定張氏夫婦是養父母,是因為一張紙。初一時,她閑著沒事翻家里的抽屜看到的。上面有父親寫的字,寫著她的出生年月日(1984年臘月十九),還寫著放了20多塊錢在里面。河村的同齡女孩李華是她的好朋友。她跟李華開玩笑說,李華不是親生的,李華傷心地哭了,二妹也跟著哭了起來。這張紙,她偷偷拿到了學校,夾在一個本子里,那個本子卻丟了。
初中,二妹讀的也是姜莊一中。我們姐弟四人,讀的都是姜莊一中,是姜莊一中的傳奇。因為,我們都成績優異,呈梯隊式。當大妹入讀姜莊一中時,學校里的老師就贊嘆而驚訝地跟她說:“啊,你是李蕾的妹妹呀。”
考高中時,二妹考上了高密二中。二中在夏莊鎮上,不在高密縣城里。二妹和弟弟,是同一年參加的中考。弟弟考上了高密一中,二妹沒有考上。
讀高中時,趁二妹放假回家,父親去她家,為了認她這件事。她偷偷聽見大人們在說,她正上高中,面臨高考,不要影響她,暫時不告訴她。等她大了,再告訴她。其實,那會兒,她早就知道了。大人們還說,等她結婚了,兩家都走動著。也是那時候,她慢慢想開了這件事。
二妹感覺化學和物理太難學了,所以高中分文理科時她沒有選理科。二妹晚一年入的小學,因此二妹和弟弟是同一年考的大學。二妹考上了天津財經大學,學財政專業,這個文科專業是這所大學的一本。
高考結束后,二妹在鎮上的飯館打工。
讀大學時,到了周末二妹就做家庭教師賺一些錢。暑期,她和當時的男朋友開了一個飯館,就開在天津財經大學的不遠處,是臨街的一間門頭房。從小寄人籬下,二妹很早就學會了經濟自立。二妹讀大學時,我去天津找她玩,她和男朋友做了水煎包給我吃。坐在河邊,我問她:怪父親嗎?我希望她能理解父親。二妹幽幽地不多說話。
本科畢業后,二妹考上了南京財經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專業是區域經濟。
二妹讀研究生時,張氏夫婦不富裕,而且要還以前欠了別人的錢,因此二妹沒再開口跟張氏夫婦要過錢。她考的公費,也不用花什么錢。當她打算買一臺電腦時,跟父親借了5000元。二妹跟父親有得聊,跟張發展說幾句就沒話了。父親跟二妹說,她的養父不同意父親把二妹認回。在河村及臨近的村子,家里多數都是由男人主事。二妹研究生畢業前,到西安實習。她的一個初中男同學,在西安做服裝生意。這個男同學,讀高中時是藝術生,大學讀的西安服裝學院,取得了一個專科學歷。兩人戀愛并結婚了。這個男同學,性格大大咧咧的。二妹文靜中帶點羞澀,不過自己很有主見。結婚的事,二妹沒有告訴父親。二妹結婚那天,弟弟給她打了好幾個電話,她都沒有接,因為她擔心她的養父母會多想。那時候,弟弟跟二妹的關系是最親近的,因為二妹只比弟弟大一歲多,兩人相當于同齡人,而且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兩人就是同學,初中也是同學,后來讀高中、大學、研究生畢業及至參加工作,兩人都是同步的,就一直有著共同的語言。為了生弟弟,父親把二妹送到了別人家寄養,因此,弟弟天然地對二妹有著一份愧疚,雖然這不是由他造成的。
二妹研究生畢業后,留在了西安工作,進了一家民營企業——某經濟研究院。這幾年,二妹和幾個同事從這家研究院辭職,合伙開了一個工作室。二妹她們開的這個工作室,做技術規劃,相當于智庫,做跟經濟相關的項目。時間上面比在研究院時自由,收入也要好一些。二妹這就是自由創業了。她一路上追求經濟自立,摸索出了跟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的方法。二妹時常在各地跑。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她劃出她的足跡:陜西省、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有一次,父親過生日,二妹給他寄了生日禮物:紅色的毛巾,中央點著紅點的大饅頭。父親查出得了癌癥之后,沒有告訴二妹。家里的人,也都沒有告訴二妹。我打電話告訴二妹。她是父親的女兒,應該讓她知道。“我出不了錢。我需要給養父母養老。我哥哥在農村,有個兒子,我嫂子身體不太好。我不能讓我的養父母知道,我跟父親走得太近。”二妹說道。
二妹生了一個兒子。有了孩子,她懂得了,父母都是愛孩子的,于是她徹底理解了父母當年出于無奈而被迫做出的選擇。她認識到,父母兒女情是一種緣分,她跟她的養父母有這種緣分。父母沒有把她接回家,她也理解了,她覺得與父母已經相認這就可以了。她的養父母至今不知道她已經和父母姐弟相認這件事。
父親把二妹送給了張姓人家收養,再也沒有把二妹接回家。父親說:“人家給你養了這么大,不會給你了。”我怪父親,沒有把二妹接回家。我認為,給二妹的養父母一些錢作為酬謝就可以了。后來,我忽然意識到:父親有四個兒女,在河村他的同齡人里,這是極少數。其他人多數都是有兩個孩子。當我問起這個事情時,父親說,“在哪兒還不一樣?要回來,四個孩子我更養活不了。”叔叔的二女兒一出生就被送到了姑祖母家養著,長到一歲時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我問父親為什么不這么操作呢?父親說,如果這樣,張氏夫婦更不要二妹了。其實,還有一個原因,熱情的嬸嬸是擅長處理人際關系的,所以,她可以走近姑祖母,讓對方幫她代養一年女兒。而母親和父親都是不擅長處理人際關系的,否則,他們可以請膠萊河北村的外曾祖母給養著,以后還可以接回家。但是,或許,父親當時想的就是需要把二妹送給別人,這樣才有可能繼續去生個兒子。
陳支書說,如果我父親把二妹要回來,會增加父親的經濟負擔;我父親只養三個孩子,這三個孩子就可以給他養老了。在鎮上計劃生育辦公室工作的三姑批評我的那個想法:孩子與養父母產生了感情,感情是可以用錢換的嗎?
讀北郵的弟弟
2005年,弟弟考上了北京郵電大學,讀的是當時最熱門的通訊專業。當時最熱門的理科專業有兩個,一個是通訊,一個是計算機。那時,中國的手機業務剛興起了不到五年,似乎人人都需要配一部手機,用手機打電話代替了座機。跟著人隨身移動的手機,保證了人的隱私。誰能想到,16年后的今天,微信正在逐步代替手機撥打電話和發送短信的功能。
2005年,我正在北師大讀研究生三年級。弟弟讀大學的第一年,住宿在昌平。2000年代,北京市里的多所重點大學在昌平建立分校,這是擴招的體現。我送弟弟到昌平。在北京郵電大學昌平分校的校門口的窗口處,我幫弟弟辦理繳費等各種手續。站在校門口的一個女老師厲聲對我說,“讓他自己做。”那時,我天然地對弟弟有保護之情。北師大和北郵,只隔著一條馬路。出了北師大的西門,過一條單行的馬路,就可以進入北郵的校園,所以我們姐弟見面非常方便。
小時候,我們姐弟三人去村后的膠萊河畔摘野棗。在家門口的小胡同里,弟弟讓我背著他。他不讓大妹背他。我就彎身背上他。到了膠萊河邊,他掛在我的脖子上,我伸手去摘野棗吃。紅紅的棗、綠綠的棗,核硬硬的,皮甜甜的,棗樹的刺自然是扎人的。
20世紀90年代初,家里只有兩本書,一本是《紅樓夢》,一本是《三國演義》。我趴在炕上看《紅樓夢》,弟弟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看《三國演義》。他的記憶力很好。他把《三國演義》從頭到尾記得滾瓜爛熟。他自信地跟我說:“你指到多少頁,我知道講的是什么內容。”我就用細竹枝挑開某頁,他果然回答無誤。
少年時代的弟弟,是個坐得住的孩子。家里有一臺收音機,他拆開,再組裝起來。同時,他也是一個孤獨的孩子。他總是拉著我跟他玩。我不會,也沒時間。因此,他坐在堂屋的水泥地面上,左手一顆黑色棋子,右手一顆白色棋子,左手走一步,右手再走一步,最后贏家是他,輸家也是他;左手摸一張撲克牌,右手摸一張撲克牌,最后,左手形成一套撲克牌,右手形成一套撲克牌,他再分別從3、4……一直洗牌到K、A、2、小王、大王,最后贏家是他,輸家也是他。
暑假里,我們女孩在家門口玩跳繩、丟毽子、丟手絹,男孩們在東西方向的村中心大街上玩打陀螺,弟弟總愛一個人在家里學習。奶奶趕他到大街上玩,笑著對他說:“太老實了,以后找不到媳婦。”
很多時候,我注意不到弟弟的存在。我和妹妹睡在西廂房的雙人床時,我不知道弟弟睡在哪里。或許是跟父母睡在東廂房的大炕上。有時候夏天,他就睡在正面(客廳)臨時搭建的鐵板床上。弟弟雖然是男孩,可是并沒有在家里受到優待。
在我小的時候,每一個河村人都想生養男孩,如果一直生的是女孩,他們就會一直不甘心,一直堅持著、想著法兒地生下去。我的父親為了生一個兒子,東躲西藏,因為他覺得,生兒子是自古以來流傳的觀念,是傳宗接代。但是我的父母,在落實到日常生活的行動上,并沒有表現出重男輕女。父親總是說,對我付出的最多,因為我是家里的第一個孩子,家里資源都優先供我使用了,而且我從小愛學習,我的父親就盡著我。讀中學時,我的成績就是優異的,這也讓父親在親戚們面前總是笑著夸獎我。另外父親認為,我的性格跟他像——倔強。
弟弟讀本科的學費,是他自己申請的國家助學基金,每年貸款5500元。弟弟本科畢業時,這筆錢他不能夠還上,因此,他只拿到了畢業證,沒有拿到學位證。多年后他還上了貸款,他才拿到了本科的學位證。本科畢業前夕,弟弟收到了華為公司的offer。考研究生之前,弟弟也猶豫過,他認為,與其繼續在學校里學可能用不上的東西,不如早一天工作。同時,他想到,如果保送得不理想,就自己考。最終,弟弟考取了清華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弟弟告訴我,他用了20根筆芯,這就是他考上清華的秘訣。
弟弟碩士研究生畢業時,他的女朋友繼續留在北京郵電大學讀博士。弟弟畢業后去了小家電的龍頭企業美的工作,先是在廣東佛山,后來調去了總部安徽合肥。有一次在北京,弟弟給我講全球的家電消費市場,他先分析世界的形勢,再分析中國的情況。這讓我對弟弟有了更多的了解,雖然他來自鄉村,卻有全球的視野。他的女朋友畢業后去了廣州的一所大學當老師,弟弟進了廣州的一家風險投資公司工作,二人在廣州定居了下來。工作之外,弟弟和他的幾個朋友操作了兩家公司以創業板上市。弟弟眼睛很小,然而上揚著自信的光芒。弟弟剛考上清華要去深圳分部讀一年時,他的一些物品放在了我租住的房子里,我看到了他的一個筆記本,上面寫著“山高我為峰”。弟弟實現了階層的躍升,36歲之前,他買了汽車,買了學區房。那年除夕,弟弟請父母在日本料理店吃飯,照片上的弟弟自信滿滿。
我自己的追問
我經常想,為什么一個農民家庭,能夠出四個大學生?互相的激勵,可能是一個原因。例如,我在2015年評副編審之前,需要經過六門計算機考試,看到妹妹已經過了四門,因而受到鼓舞。“你能過,我也能過。”就是這么一個心理。
我們都遺傳自母親的智商。母親是遺傳自外祖父那邊的智商。外祖父的智商是遺傳自他的外祖父那邊。87歲的外祖父沒有上過學堂,然而他跟我講起祖輩的經歷以及其中的道理,清明得很。外祖父的祖上,是體面人,有文化,有產業,受尊重。我的高外祖父是醫生,曾去青島坐堂行醫。高外祖父的父親,養了九匹馬,他總要比鄰居多養一匹以顯得自己尊貴。高外祖父的父親家里的土地非常多,當地的官員走到他的宅第前,都要落轎,進門去拜見一番。外曾祖母的外祖母家,有三個兒子,家里有大車、馬車,土地多,牛馬騾子多。秋收完了,到了冬天,外祖父的母親的舅舅們,就套上高高的馬車,拉著外祖父的母親和她的三個姊妹,去他們家過冬。這姊妹四人,去舅舅家住著,一住就是一個冬天。我手里有一張四姊妹的合影。四姊妹都是小腳,都穿著泛光的華麗套服,梳著油光整齊的發髻,每個人手里都拿著一本書,可見她們的父輩非常重視對她們的教育。
母親只上了四年學,可是母親是聰明的。幾年前,我在室內擺了一個帳篷,可是我不會撐開,母親一撐就開了。我讀小學時,冬天,在家里的神灶前,墻上掛著一盞煤油燈,母親在燈下給我講解語文課的題目。神灶就是我的書桌,我趴在上面寫作業,母親依在我的身旁,那是我童年記憶里溫馨的一幕。
從我們小的時候到長大成人,母親從來不議論人是非。母親知道大地上一年四季莊稼的收成以及天空中的流云。母親是與大地、莊稼、動物和流云打交道的,而不是和人。我們姐弟幾個,受到母親的影響,無論在學校讀書時還是參加工作后,不參與人事的糾紛,而只是致力于自己的求學、按照自己的心意開拓工作、追求自己心中的夢想。
我的爺爺的成分是貧農,他的一生在為全家人操持中度過了。然而,我的曾祖父是富裕中農、上中農。也就是說,我的祖父的父輩祖輩和我的外祖父的父輩祖輩都是體面人,差不多是當時的鄉紳階層,尤其是外祖父那邊。到了祖父、外祖父這一代,算是家道中落了。可是,他們的基因、聰明才智遺傳了下來,到我這一代,我們姐弟四人憑著參加高考,也算是再次使得“家道中興”吧。
我的父親體格健壯,我們姐弟四人遺傳了父親的體質,身體的底子都好,意志力也是好的。
我的父親一生與土地打交道。在我的少年時期,他都是背著一個噴霧器在田野里為莊稼噴灑農藥,在蘋果園里為蘋果樹噴灑農藥。他完全不戴防護措施,那些農藥迎風而來隨風而去,傷害到了他的身體。我想,這可能是他晚年患癌的一個原因。我的父親一生遠離權力。我的大姑父是村支書,大姑父的父親也做過村支書,我的叔叔和四個姑姑都自覺不自覺地靠近了大姑父和他的家族。而我的父親,沒有為了謀取利益,而去走近大姑父,走近陳家,這是因為他天生耿直,他不愿意也不會去求人,他沒有媚骨,不會屈膝,不指望權力以及權力者能給他帶來什么好處,他也不會向權力以及權力者屈服,他一輩子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志安排和承擔他自己的人生以及他的幾個孩子的人生。我的母親,也絕對不會為了家人的利益而去走近權力者。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也遺傳了我的父親和母親的這一特點。
在我們姐弟的求學階段,我的父親和母親從來沒有向我們講述和抱怨過生活的艱辛,這使得我們有一個安穩的心境投入學習。在我們的求學階段,我的父親和母親不怎么安排我們下地干活,也不怎么安排我們做家務,這使得我們的時間都投入到學習之中。讀中學的暑假,我在院子里學習,父親為了讓我安心學習,就安排大妹牽著牛下地。我是河村的第一個女大學生,也是河村李氏家族里的第一個大學生,我的前面沒有榜樣。我之所以學習能一直領先,跟我的父親對我這方面的照顧是分不開的。
我的父親和母親從來沒有強迫我們做任何事情。我的父親以為,我讀了中專就可以早畢業早工作早有收入,然而我想考高中,我的父親沒有提出一句反對。我考上了高密一中,春節時母親兄弟姊妹六人組成的六個家庭在外祖父的家里聚餐,父親興高采烈地夸耀高密一中多么好。我不好意思了,跟親戚們說,二表哥考上的平度一中和高密一中一樣都是各自縣最好的高中。
我天生好學。小學同學趙娟對我的回憶是:有一次,她看到我在幫母親燒火做飯,手里拿著書在看,火滅了我都不知道。
父親兄弟姐妹六人,他們的下一代,大表哥是家族里的第一個孩子,然而大表哥不討家族人的喜歡。我是家族里的第二個孩子,第一個女孩,而且我從小就學習優秀,而且大概在大人們看來我溫和而有理智,同時又有愛讀書的孩子的超脫寧靜的氣質——有一次,我安靜地坐在小姑家客廳的板凳上,她仰慕地看著我說:“到底是讀書的人,氣質真好。”姑姑叔叔們都喜歡我。我是家族里最受寵愛的孩子。初中畢業的暑假,小姑騎著一輛自行車,我也騎著一輛自行車,她帶我去縣城的新華書店給我買書,我選了《新華字典》和《蘇菲的世界》,那是我第一次去高密縣城。我讀高中時,三姑有一陣在縣城醫院學習,她多次用塑料袋裝好了飯菜帶到我的教室里給我,還帶我到那所醫院轉悠著玩。我考上了大學,父親讓我去跟二姑借錢。二姑拉開抽屜,問我要多少。上大學前夕,開棉被廠的大姑送了我一床白色印花的絲棉被。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從草叢里捉螞蚱、從槐樹上捕知了、從雨后的槐樹下摳幼蟬、從梧桐樹上摘木耳、從草叢中拔野鳶尾、從土溝里挖鬼子姜;在河邊抓蜻蜓、在河水里游泳、在夜晚的草叢里抓螢火蟲、在棉花地里摘棉花遇到一只蟲;走在花生地里打濕褲腿、鉆到村口的蘑菇棚里去玩、在路上遇到一條蛇和一只蜥蜴、在夜晚的屋檐下看到一只壁虎和燕子在屋梁上壘窩;聽著村中心的大喇叭播放著《歌聲與微笑》、看著家里房檐下放出聲音的廣播、在鄰居家看的電視劇、沿著家里的屋墻朝天開著大朵花的蜀葵、家里和村里的雞牛鵝騾子、村里的石磨、和弟弟妹妹父親興致盎然地打撲克牌……這些鄉村生活的場景,時不時地就會閃入我離鄉后的眼簾和夢境中,這些人事物景都開發了我和弟弟妹妹的心智和情懷。
【作者簡介】李蕾,曾用名李磊,山東高密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碩士,文學編輯;非虛構“高密河村往事”系列發表于《新史學》《山東文學》《滿族文學》等刊;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