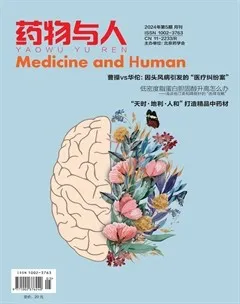曹操vs華佗:因頭風病引發的“醫療糾紛案”
宋飛濱?陳芋屹?吳劍坤


周末在家重溫前些年的熱播劇《軍師聯盟》,又看到了華佗被曹操誅殺的片段(這次被虛構成要謀害曹操),忍不住為華佗惋惜。惋惜之余,作為醫務工作者的我突發奇想,想以小說的形式和大家聊聊曹操和華佗之間因頭風病引發的“醫療糾紛案”。
前記
現在,讓我們把歷史的時鐘回調到東漢末年。時值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久經禍亂的劉協(漢獻帝)沒能守住正統,只得眼看大權旁落曹操,后者則是順勢挾天子以令諸侯,成為一方霸主。
這曹操做事也是不惜力,親持軍政,日夜操勞,導致頭風痼疾反復發作,逐漸加重。聽聞華佗醫術高超,曹操便多次召見華佗入府診病—可是,華佗都一一推脫掉了。據歷史記載,華佗是以思家歸鄉及妻子生病為理由而拒絕診病的,但曹操卻非常不滿,將之招捕入獄;又有民間傳言,華佗希望為曹操進行開顱手術,但曹操疑心很重,認為華佗是想謀害自己,由此起了殺心。無論何種緣故,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華佗最終以枉死獄中為自己的人生寫下了“遺憾”—不僅所著醫書未能留傳后世,而且也催生出了所謂的“醫療糾紛案”。
后人評析,如果華佗能夠幸免此難,祖國傳統醫學或許另有新篇章。畢竟,彼時“建安三神醫”已聞名天下:仲景擅長內科諸病,一部《傷寒雜病論》影響至今;董奉醫德高尚,留下了一段杏林佳話;而華佗精通內、外、婦、兒各科,通曉養生、方藥、針灸、心理等治療手段,業已游歷天下,踏遍國土山河,臨床行醫經驗更為豐富。然而,歷史沒有“如果”,華佗也終究無法逃過歷史的宿命。
正文
那么,什么是頭風病?曹操到底有沒有頭風病?如果有,是什么類型的頭風病?是什么因素引發的?應該如何治療?歷史的真相到底如何呢?……別急,諸位看官且往下看。
明代綜合性醫書《醫林繩墨》論述:“淺而近者,名曰頭痛;深而遠者,名曰頭風。頭痛卒然而至,易于解散也;頭風作止不常,愈后觸感復發也。”由此可見,頭痛與頭風在發病部位、發病特征等方面相近,而在發病持續時間、發病深度等方面又有所區別。
所謂頭風,又名腦風或首風,發病部位常位于頭部一側,或兩側,或全部;發病表現多為跳痛、重痛、脹痛、針刺樣痛,嚴重者可出現頭痛欲裂、痛不欲生的感受;發病持續時間從數分鐘到數周不等,發病病程可長達數十年,疼痛難忍,纏綿難愈。沒錯,這與現代醫學中的緊張性頭痛、偏頭痛等原發性頭痛相近似;而現代考古學為揭示曹操頭風病的真相,更增添了最直接的證據。
2006年,河南安陽西高穴村發現了一座東漢時期的大墓,經過3年的考古搶救性發掘,于2009年,最終國家文物局認定河南安陽高陵墓墓主人即為魏武王曹操。自高陵墓出土的除了金、銀、銅、鐵、晶、玉、陶漆等傳統文物外,尚有一件特殊文物—慰項石。慰項石是一種石枕,具有導熱強、傳熱快的顯著特點,通過灌澆熱水給石枕加熱,主人將脖頸枕于其上,可以快速起到疏經通絡、松弛肌肉、緩解頭痛的作用。慰項石的發現,側面證實了曹操患有頭風病的基本事實,同時也佐證了曹操在殺死華佗之后可能用于治療頭風病采取的方法。另外,曹操遺骸存有多個累及牙髓的齲齒,暴露的牙洞在受到刺激時,可直接觸發頜部三叉神經引發劇烈頭痛,這也直接證實了曹操所患頭風病即為現代醫學三叉神經痛的真相。
現代醫學所稱的三叉神經痛,以一側面部三叉神經分布區內反復發作的陣發性劇痛為主要特點,表現為驟發、刀割樣、燒灼樣難以忍受的劇烈性疼痛,甚至風吹亦可發病,且常年纏綿難愈。這與正史記載曹操發病時的情形十分吻合:曹操常年在外征戰、風餐露宿、操心勞神,故而飲食失節、作息失律、情志失調,此皆是頭風病的誘發因素,以致氣血逆亂、經絡阻滯、腦失所養、不通則痛而發病。
后世中醫醫家根據頭風病不同的臨床表現,又將之分為5種辨證分型:
(1)肝陽上亢證,癥見頭脹痛,面紅目赤,耳鳴如蟬,心煩口干;
(2)痰濁上擾證,癥見頭重痛,或有目眩,惡心食少,痰多黏白;
(3)瘀阻腦絡證,癥見頭刺痛,痛如錐刺,痛處固定,經久不愈;
(4)氣血虧虛證,癥見頭綿痛,神疲乏力,面色晄白,心悸寐少;
(5)肝腎陰虛證,癥見頭空痛,目干心煩,時輕時重,腰酸腿軟。
并且,根據這5種辨證分型,分別對應給出了天麻鉤藤飲,二陳湯、溫膽湯、半夏白術天麻湯,通竅活血湯、血府逐瘀湯,四物湯、四君子湯、補中益氣湯,明目地黃丸、六味地黃湯等不同經典方劑。此外,中醫亦有針刺、推拿、按摩、放血等治療方法,為治療頭風病增添了新的手段。
后記
查閱文獻可知,近現代的中醫大家如張子琳、王為蘭、朱良春等,在臨床上多有應用中藥經典名方散偏湯治療偏頭痛、血管緊張性頭痛—尤其是三叉神經痛覆杯即愈的案例。對于散偏湯,2022版《中國偏頭痛中西醫結合防治指南》亦做了推薦。于是,筆者根據患者在臨床上的辨證,多次嘗試應用散偏湯加減治療三叉神經痛或偏頭痛,皆如原文所言,“毋論左右頭疼,一劑即止痛”,無不應驗。
為循其處方出處,筆者重新拜讀了清代名醫陳士鐸所著《辨證錄》,自序部分內容頗為傳奇,自述此書源于岐伯仲景,并非自己所寫,甚為謙虛。書中所論述內容非常精辟:以散偏湯為例進行方解,其用川芎一兩為君藥,循肝膽經上行頭目而活血行氣、祛風止痛;白芍五錢平肝氣、疏肝血,與郁李仁一錢、白芷一錢助川芎散頭風,又添香附二錢、柴胡一錢以開郁疏肝利膽,白芥子三錢以利氣消痰,共為臣藥;且郁李仁藥性主降,可防川芎升散太過,兼為佐藥;甘草一錢可調和滯氣,為使藥。再結合前文,風寒邪氣侵襲頭側膽經,肝膽相表里,膽經郁滯則肝經氣滯,發病為偏頭痛。因此,散偏湯采取肝膽同治之法,諸藥合用,可解風寒郁滯。肝膽盡舒,頭風盡消,頭痛自愈。
思考
隨著治療的規范,目前臨床上鮮有類似曹操與華佗這種“醫療糾紛”的案例。然而,由于用藥劑量失當引起的不良事件仍時有發生,對此我輩中醫藥人應該高度重視。比如,在散偏湯一方中,川芎的使用劑量達到一兩,依據1979年國家中醫處方用藥劑量單位改革統一標準,此處一兩換算成公制約為31.25 g,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20版)規定川芎3~10 g的用量有較大的出入。
面對復雜的臨床病情,中醫在為患者開具處方—尤其當處方所涉中藥用量很多時,多依據傳統經方用量、行醫經驗積累、患者個體差異等綜合做出判斷,而不會單純依靠法定劑量,因而可能與藥典存在較大的分歧。在這種背景之下,對于無法明確權責的中藥醫療糾紛,是直接歸咎于用量與藥典不符,還是考慮用其他方法深入界定,以使得臨床用藥更加安全很關鍵;而這一切都有待學術各界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