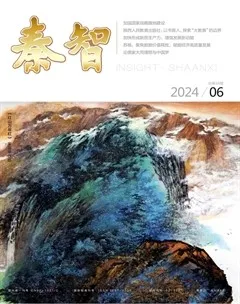《民法典》中居住權消滅的要素探究
[摘要]《民法典》僅就居住權的消滅規定了兩種情形,當事人能否通過意定方式確定居住權的消滅情形、居住權的消滅是否沿用登記生效模式均無明確規定。意思自治原則是居住權領域的核心與基石,通過體系解釋與目的解釋的方法,能夠明確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約定居住權消滅的情形。登記生效制度能夠有效保障交易安全及居住狀態的穩定,故居住權的消滅應在辦理注銷登記之后發生。
[關鍵詞]居住權合同糾紛;居住權消滅;意思自治;登記生效
[DOI]:10.20122/j.cnki.2097-0536.2024.06.007
居住權是《民法典》物權編新增的用益物權種類,回應了“住有所居”的時代需求。意思自治是居住權領域的核心與基石,《民法典》明確居住權的正向設立需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或通過遺囑作出單方意思表示,但就居住權的消滅僅規定了因居住期限屆滿或居住權人死亡而注銷的情形,而未明確居住權的消滅是否沿用登記生效模式。在審判實踐中,當事人之間就居住權消滅產生糾紛時,難以直接適用《民法典》中的相關法條進行認定。
一、案例概述
原告蔣某、被告宋某甲原系夫妻,生育宋某,現已成年。2021年12月13日,兩原告及被告簽訂《居住權協議》,約定被告宋某甲有權居住上海市靜安區某房屋(以下簡稱“系爭房屋”)直至身故,但如被告再婚或未經原告書面同意,有除被告外的其他人居住系爭房屋(護工除外),雙方均有權解除協議,注銷居住權。2021年12月14日,原、被告在系爭房屋上設立居住權并辦理登記手續。2021年12月27日,原告蔣某與被告宋某甲登記離婚。2022年,原告認為有案外人實際居住使用系爭房屋,故起訴要求解除雙方簽訂的《居住權協議》并注銷登記。后經法院調解,原、被告達成調解協議,約定解除《居住權協議》,被告配合原告辦理居住權注銷登記。
原告、被告簽訂書面的《居住權協議》,對居住人、住宅位置、居住期限、居住條件和要求均予以明確,同時約定了合同的解除條件。該合同系雙方自愿簽署,未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應認定為有效。后雙方在系爭房屋上辦理了居住權登記,整個過程符合《民法典》的規定,至此應認定居住權設立。原告認為被告未能按照合同約定的居住要求使用房屋,故訴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注銷居住權,被告亦當庭表示同意解除。本案的關鍵問題是《居住權合同》解除之時,能否發生居住權隨之消滅的法律后果。
二、居住權消滅的意定之爭
《民法典》第三百七十條第一款規定:“居住權期限屆滿或者居住權人死亡的,居住權消滅。”居住權的消滅是否僅限于這兩種法定情形?當事人能否通過意定方式使得居住權消滅?顯然通過文義解釋已無法得到答案,需適用體系解釋和目的解釋進行綜合認定。
(一)體系解釋
體系解釋是通過和借助體系展開的解釋方法,就解釋標準而言,則是使得解釋結論符合體系的要求[1]。《民法典》第十四章全篇用作規定居住權的相關內容,可先將居住權的消滅置于這一局部體系進行分析。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條規定:“居住權人有權按照合同約定,對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權,以滿足生活居住的需要”。這一條文對居住權進行定義,明確權利的來源系“合同約定”,權利的范圍系“對他人住宅的占有、使用”,立法目的系“滿足生活居住的需要”;權利系由法律行為創設,本條明確創設居住權的法律行為系合同,即雙方意思一致,這從根源上即賦予居住權意思自治的基調。三百六十七條、三百六十八條及三百七十一條,進一步明確居住權的設立應以當事人合意或單方遺囑為前提,居住權的相應要素亦由雙方約定;對于設立的限制僅有書面要式及登記設立兩條,均為形式限制,并不涉及居住權的實質內容;而無償設立雖未被規定為一般原則,但可由當事人約定排除。足見意思自治乃居住權的核心與基礎,從根源上即賦予當事人民事范圍內的自由,這一原則應覆蓋居住權設立至居住權消滅的整個過程。
將居住權消滅置于《民法典》這一整體體系中,亦可發現意思自治乃《民法典》的重要價值理念。《民法典》作為典范性法源,開放出了法律行為的準法源地位,具有落實私法自治之憲法基本權利的意義;在構成維度,《民法典》的規范分析表明,意思表示系成立法律行為的先行機制[2]。作為《民法典》的新增內容,居住權的立法精神應與《民法典》保持高度一致,意思自治原理應貫穿居住權領域的始終,除去正向設立,亦應延伸至逆向消滅。
(二)目的解釋
目的解釋是以法律規范目的為根據,闡釋法律疑義的一種解釋方法[9]。從目的解釋的維度分析,需探究居住權的源流及其立法背景。居住權最早出現在羅馬法中,其立法目的是把一部分家產的使用權、收益權等贈予給妻子或者奴隸,解決居住與生活困境[3]。而歐美國家的法律,則主要將居住權用于婚姻家庭領域,賦予其“社會性”與“倫理性”[4]。可見居住權制度承擔了家庭保障的基本功能,為特定群體在特定情形下設定房屋的占有、使用權益,與婚姻家事、遺囑繼承、婦女與未成年權益保護等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內容緊密相關。
再看我國關于居住權的立法過程,最早關于《物權法》的征求意見稿曾提出保護婦女、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的居住權利,具體指向父母、離婚后暫未找到居住場所的前夫或前妻以及保姆;后雖在草案中將居住權載入,然而在正式法律出臺時又剔除。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居住問題呈現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點,需要居住保護的群體已遠遠不止這三種,以房養老、分家析產、離婚后財產糾紛及需保障自身居住權的房屋贈與等問題層出不窮。我國法律沒有關于居住權制度的規定時,司法實踐只能在欠缺法律支撐的情況下,通過符合司法理念的裁判規則實現居住權的目的,但當《民法典》在物權編內設立了居住權這一制度后,就為婚姻家庭、繼承、未成年人保護等可能對居住權有所需求的法律或者《民法典》其他各編打開了立法配套的通道[5]。
由此可見,居住權最早的起源即在婚姻家庭領域保護特定主題的居住權益,在我國的立法目的是滿足多元化的居住需要。在法律實務中,居住情況以及居住需求往往錯綜復雜,只有遵循當事人的意思表示才能真正將居住問題解決,發揮這一制度的核心作用。
(三)意定邊界
《民法典》特別明確了居住權系用益物權的一種,意思自治與物權法定的關系需審慎對待。居住權作為特殊的用益物權,不同于房屋租賃,其具有居住保障的性質,這一性質系法律規定,不能由當事人約定排除,居住權消滅的條件同樣受到相應限制。在一些特殊案件中,居住權人在他人房屋上設立居住權并同意給予對方一定的居住補償,當未能按約定給付錢款時不能僅以違反居住合同的約定而認定居住權消滅,特別是合同雙方存在親屬關系的時候。
三、居住權消滅的生效條件
(一)法律解釋的困境
前文已經論述當事人可通過意定方式使得居住權消滅,然而本案中,系爭房屋上設立的居住權自何時消滅,自雙方當事人協商一致解除《居住權協議》之時,還是辦理注銷登記之后,還需進一步探究居住權消滅的生效條件。《民法典》第三百七十條第二款規定:“居住權消滅的,應當及時辦理注銷登記”,從文義上無法判斷注銷登記手續究竟是居住權消滅的生效條件,還是僅僅起到登記公示作用;第三百六十八條明確規定:“居住權自登記時設立”,居住權的設立采用登記生效制度,居住權的消滅是否必然沿用這種模式,亦未可知。
另外,《民法典》物權編在《通則》部分第二百零八條第一款的規定:“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應當依照法律規定登記”;第二百零九條又進一步明確:“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經依法登記,發生效力;未經登記,不發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這兩條法律規定,明確了不動產物權的變動以登記為生效要件,而但書條文又給予了部分不動產物權變動未經登記即可生效的空間,例如土地承包經營權及地役權的設立。居住權的消滅能否包含在第二百零九條的但書條文之內,需綜合考量。
(二)登記生效的優勢
首先,需探究的是登記生效制度所保護的法益。登記生效制度是指物權的變動,除了意思表示之外,還需進行登記,以保證交易的安全和穩定。與登記生效制度相對的是登記對抗制度,即意思表示可引起物權的變動,登記公示僅產生對抗善意第三人的作用,更強調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時將未能公示引起的不利后果歸咎于當事人自己[6]。前文已討論過居住權的立法目的,以解決多元化的居住需求為根本,無償設立的原則更體現其為解決“社會性居住”問題,而非滿足投資性居住的需求。在此情況下,居住狀態的穩定無疑優先于權利變動的自由,故登記生效制度是更好的選擇。
其次,應考慮的是居住權消滅的法律后果。居住權是物權的一種,天然地具有絕對性和排他性,一處住宅上不可能同時存在兩個互相排斥的居住權,故居住權一旦消滅即意味著該住宅回到可以設立居住權的狀態。居住權的設立需登記手續,若居住權的消滅不進行登記,則后續需設立居住權的雙方無法判斷上一個居住權到底是何狀態,不利于房屋的使用和居住穩定的保障。若居住權的消滅條件已經成就,而未辦理居住權注銷登記,當事人仍可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確認居住權消滅并配合辦理注銷手續。
(三)登記對抗的特殊性
登記對抗制度是指物權變動無需登記即可生效,但未經登記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我國法律明文規定,可適用登記對抗制度的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地役權、動產抵押權及動產浮動抵押,而此類權利有其特殊性,地役權多存在于農村土地之上,主要發生在兩個權利人之間,一般不涉及第三人[7]。土地承包經營權亦是如此,農村地區的村民交往較為密切,相對于登記制度,熟人之間的信息交換更為便利,交易相對人亦可通過對方是否具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判斷其是否享有土地承辦經營權[8]。居住權消滅顯然均不具有上述權利的特征,故其適用登記對抗制度并不合適。
綜上,居住權消滅仍應沿用登記生效模式,即辦理注銷登記之后才能生效。
四、結語
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協商一致解除《居住權協議》,法院在調解協議中不僅就協議解除的問題予以確認,還將辦理注銷手續及房屋交接事項一并處理,尊重當事人意思表示的同時,也保證居住權消滅的徹底實現。
參考文獻:
[1]車浩.法教義學與體系解釋[J].中國法律評論,2022(4):103-119.
[2]姚明斌.民法典體系視角下的意思自治與法律行為[J].東方發現,2021(3):140-155.
[3]周枏.羅馬法原論(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4]申衛星.視野拓展與功能轉換:我國設立居住權必要性的多重視角[J].中國法學,2005(5):77-92.
[5]陳藝穎,吳秋月.居住權入典的理論證成及立法檢討——以《民法典》第366條至第371條為中心[J].民商法爭鳴,2022(1):34-48.
[6]李永軍.我國物權法登記生效與登記對抗模式并存思考[J].北方法學,2010,4(3):38-42.
[7]王利明.關于物權法草案中確立的不動產物權變動模式[J].法學,2005(8):3-9.
[8]江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精解[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
[9]李林太.從公法性角度對勞動法律關系重新定義[J].貴州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05(2):58-60.
作者簡介:趙錦鈺(1994.2-),女,漢族,山西大同人,碩士,法官助理,研究方向: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