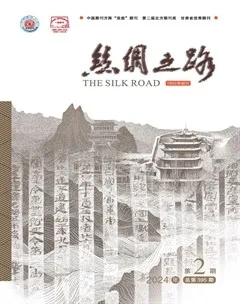絲綢之路游藝文化交流場所研究
叢振 金天
[摘要] 絲綢之路自漢時開通以來,便是我國同西域物質(zhì)、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此后經(jīng)過數(shù)百年的發(fā)展,到唐代時,更是進入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時期。西域文化和中國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留下了燦爛的寶貴文化遺產(chǎn)。在絲綢之路繁榮的背景下,中外游藝文化的交流頻繁開展,而中外游藝文化交流中的各類場所也自然為絲綢之路游藝溝通交流提供了物質(zhì)基礎(chǔ)。通過對絲綢之路游藝文化交流場所進行研究,能夠反映出唐宋時期中原地區(qū)對經(jīng)絲綢之路而來的異域游藝文化的喜愛與重視,也從游藝交流的角度側(cè)面說明了絲綢之路對于我國古代各階層人民的日常生活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關(guān)鍵詞] 絲綢之路; 西域; 游藝文化; 游藝場所
[中圖分類號] G812.78? ? [文獻標(biāo)識碼] A? ? [文章編號]1005-3115(2024)02-0016-09
文化傳播與交流在人類的發(fā)展歷程中始終存在。自漢代以來,東啟中原、西至歐陸的古絲綢之路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與互鑒的過程中,始終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沿途的農(nóng)耕文明、綠洲文明、海洋文明在絲綢之路的串聯(lián)下,共同造就了繁榮的人類文化瑰寶。但由于古代技術(shù)的限制,各文明間物質(zhì)與文化的交流往往伴隨著遙遠(yuǎn)的距離和漫長的旅途。在漫長的絲綢之路行程中,來往的使節(jié)、商人們無疑需要一種方法來消遣旅途的孤獨與艱辛。而游藝在旅人的生活中,無疑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為絲綢之路旅人們活躍氣氛、獲得愉悅的難得之法。可以說,只有在參加游藝活動的時候,他們才能暫時忘掉旅途的勞累與離鄉(xiāng)的寂寞,享受那一刻的感官快感與精神愉悅。正因為絲綢之路上游藝活動的不可或缺,西域的諸多游藝也隨著這些異域旅人們的腳步,一路相伴而來。
不論是絲綢之路沿途的旅人,還是絲綢之路起點長安城中的居民,在進行游藝活動時都需要一定的場所。為了使絲綢之路游藝文化交流場所研究更加全面具體,更加突出各階層、各文化元素的不同與交流融合,本文將其劃分為三個層次,并在每一部分選取較有代表性的具體場所進行分析,從而通過不同層面來了解游藝文化的傳播、交流過程,以期更加全面生動地敘述絲綢之路游藝文化傳播中的游藝交流場所,并深入思考不同游藝場所對游藝文化交流的作用與影響。
一、絲綢之路游藝文化研究綜述
“游藝”最早見于《論語·述而》:“志于道,據(jù)于德,衣于仁,游于藝。”[1]這是孔子對弟子們的行為規(guī)范做出的具體要求。他認(rèn)為學(xué)生們應(yīng)當(dāng)樹立遠(yuǎn)大理想,做事要符合道德規(guī)范,對萬事萬物要有仁愛之心,活動要在“禮樂射御書數(shù)”六藝之內(nèi)進行。不難看出,此時的“游”與“藝”二字是分開來理解的,并不是我們當(dāng)今所理解的娛樂、游戲的含義。在古代,“游”與“遊”是兩個不同的字,在陸地上活動,如“遊戲”“游覽”等,“游”與“遊”可以通用;而在水中活動,如“游泳”“浮游”等只能用“游”[2]。隨著歷史的推進,二者的含義才逐漸合一,“游藝”一詞逐漸開始包含游玩、游樂的含義。朱熹在解釋孔子之言時認(rèn)為:“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shù)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yīng)務(wù)有余,而心亦無所放矣。”[3]這說明到了南宋時,游藝已經(jīng)有了玩物適情、消遣娛樂之意。同時,游藝也逐漸成為古代儒家的一項重要的修身養(yǎng)性的手段,大大豐富了古人的精神世界。
但中國古代的正史資料中,并無對游藝的系統(tǒng)性專門記載,只是零星附屬于正史之“藝文志”“禮志”“樂志”等史料中,當(dāng)然也沒有對此的專門研究。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思想的傳入與中國社會思想的變革,對于“游藝”一詞的理解也逐漸通俗化、大眾化,并開始進入研究者的視野。近代第一個將游藝作為單獨的分類進行研究的是楊萌深先生,他所著的《中國游藝研究》一書資料豐富,分類詳盡,系統(tǒng)地敘述多種傳統(tǒng)游藝活動的歷史淵源與流變,為我們研究古代游藝提供了范本參考。楊先生在《中國游藝研究》中認(rèn)為:“游藝就是游戲的藝術(shù),并沒有含著什么深奧的意義。其詞或源于孔子‘游于藝(論語述而)一語。”[4]從此,“游藝”一詞的現(xiàn)代含義便與游戲、玩耍、娛樂活動有了緊密聯(lián)系。臺灣學(xué)者陳永平更是將其準(zhǔn)確定義為:“悠游、沉浸、涵泳在各項游戲、娛樂,或藝術(shù)(技藝、才藝)領(lǐng)域之中,可以讓人們以娛懷取樂、消閑遣興,達到放松、調(diào)適身心、增加生活樂趣為主要目的的一種精神文明活動。”[5]而本文所討論的游藝,也大抵相當(dāng)于現(xiàn)代定義的游戲、娛樂等利于身心的文娛活動。
古代的絲綢之路并沒有我們當(dāng)今的便捷交通手段,漫天的黃沙、極寒與酷暑、缺水缺糧、強盜襲擾等困難時刻威脅著來往路上的每位商旅。而游藝活動所帶來的短暫快樂,便成為撫慰來往商旅內(nèi)心孤獨苦悶的一劑良藥。或在奔波的駝背上,或在歇腳的驛館里,來自各地各民族的游藝相互交流、相互借鑒,又經(jīng)由他們帶到絲綢之路沿線各地,使絲綢之路成為名副其實的“游藝傳播之路”。
文明間的互動必然伴隨著文化的交流,早在漢代時,西域諸如雜技之類的游藝活動就經(jīng)由絲綢之路傳入了我國。《后漢書·西域傳》記載:“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吐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6]2920而源起于中原的諸多游藝形式,也通過絲綢之路不斷向西傳播。現(xiàn)存最早的關(guān)于圍棋理論的著作是1899年發(fā)現(xiàn)于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中的北周手抄本《棋經(jīng)》,可見經(jīng)絲綢之路傳來的圍棋也是西域比較受歡迎的游藝活動之一。
不管是百戲、雜技之類的體力游藝,還是博戲、弈棋類的智力游藝,都需要在一定的游藝場所才能進行。游藝場所是承載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空間基礎(chǔ)與載體,是人們參與游藝時不可缺少的物質(zhì)基礎(chǔ)。可以說,正因為有著多種多樣的、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的游藝文化交流場所的存在和不斷發(fā)展,絲綢之路游藝文化的發(fā)展傳播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廣闊的傳播與影響范圍。
二、統(tǒng)治階層游藝文化交流場所
統(tǒng)治階級是社會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物質(zhì)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zhì)生產(chǎn)資料的階級[7]。在我國古代漫長的封建社會時期,統(tǒng)治階層的范圍大致是封建王朝的王公大臣及其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群體。相較于社會其他階層,統(tǒng)治階層往往擁有花費大量人力財力物力所建造的游藝場所,而宮廷便是其中的代表。
宮廷或說宮苑,是帝王及皇族們起居和工作的場所。《周易·系辭》中說:“上古穴居而野處,后世圣人易之以宮室。”[8]宮廷是中國古代彰顯統(tǒng)治者權(quán)威的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其規(guī)模宏大、建筑考究,給人以強烈的精神與感官沖擊。宮廷不只是統(tǒng)治者工作和居住的場所,在閑暇之余,統(tǒng)治者們往往會進行各種各樣的游藝活動以充實個人生活。宮廷類的游藝交流場所中進行的活動多以觀賞性游藝文化交流為主。例如漢代時,宮廷宴會上就出現(xiàn)了大型百戲表演的場景。張衡在《兩京賦》中,托漢武帝時期之故事,寫其所處時期的百戲表演盛況:
烏獲扛鼎,都盧尋橦,沖狹燕濯,胸突鋸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爾乃建戲車,樹修旃,倔僮程材,上下翻翩,突倒投而跟掛,譬隕絕而復(fù)聯(lián)。[9]
文中提到的 “都盧尋橦”“跳丸”等活動,都帶有明顯的與外來文化交流的痕跡。此后,宮廷逐漸作為重要的游藝交流場所,被統(tǒng)治階層所喜愛。如《后漢書·陳禪傳》中提及:
安帝劉佑水寧元年(120),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主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于庭,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6]1685
中外的統(tǒng)治者們都喜歡在宮廷中舉行游藝活動,或為愉悅身心,或為招待賓客。如《法苑珠林》中就記載了“王玄策出使天竺時所見五女戲雜技”一條:
又王玄策西國行傳云:王使顯慶四年至婆栗阇國。王為漢人設(shè)五女戲,其五女傳弄三刀加至十刀。又作繩伎,騰虛繩上,著履而擲。手弄三仗刀楯槍等種種關(guān)伎。雜諸幻術(shù),截舌抽腸等。不可具述。[10]
這是天竺統(tǒng)治階級在宮廷中為中國使者舉行百戲表演的記載,生動展現(xiàn)了絲綢之路游藝文化交流的手段和場景。同樣,中國統(tǒng)治階級也接受了這樣的游藝交流。《舊唐書》中載唐睿宗接待婆羅門進獻的場景:
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于極鋸刀鋒,倒植于地,低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植于背下,吹篳篥者立其腹上,終曲而亦無傷。又伏伸其手,兩人躡之,施身繞手,百轉(zhuǎn)無已。[11]
這種宮廷與宮廷之間的游藝文化交流表明了宮廷這一場所不僅起到了簡單的提供一個觀賞百戲類游藝活動的場地作用,更是一處承載游藝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質(zhì)載體,沒有場所這一物質(zhì)載體,游藝文化交流就無從談起,可見宮廷對游藝文化交流傳播的重要作用。
頻繁的中外文化交流帶來的不僅僅是西域的游藝文化項目,還帶來了西域的游藝文化場所的特征,并影響到了中國的游藝文化場所建筑結(jié)構(gòu)。中國古代的代表性宮廷建筑,如未央宮、大明宮都是木質(zhì)結(jié)構(gòu)建筑。而與此相對應(yīng)的則是地中海地帶的埃及、羅馬、波斯、美索不達米亞等文明的磚石結(jié)構(gòu)建筑。在絲綢之路開通后,具有鮮明異域特色的諸多游藝活動伴隨著物質(zhì)文明的交換紛至沓來,并衍生出了新的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特色的游藝項目。在交流碰撞中,它們也帶來了獨具域外鮮明特色的建筑傳統(tǒng)與風(fēng)格,并且影響了中國古代宮廷的建筑風(fēng)格,使得宮廷游藝文化交流場所也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中產(chǎn)生了具有鮮明中外文化交流的場所特征。
宮廷游藝活動與宮廷這一游藝場所相輔相成的關(guān)系,是經(jīng)得起仔細(xì)推敲且有充分史料支撐的。王振鐸曾考證在秦咸陽宮殿遺址中可見中柱或“都柱”的設(shè)置,這種建筑風(fēng)格似乎并不僅僅是結(jié)構(gòu)上的需要,而是受到了域外文化的影響,秦咸陽宮殿這種高臺建筑與埃及、西亞的金字塔、觀象臺都有著相似的四棱臺(椎)幾何形體[12]。同時,中外美術(shù)界早已公認(rèn),漢代中原雕刻的新因素是張騫從西域引入的[13]。除此之外,麟德殿是唐代皇帝舉行大型宴會的地方,以數(shù)座殿堂高低錯落結(jié)合在一起,大殿的東西兩側(cè)又有亭臺樓閣襯托,其建筑造型風(fēng)格豐富多樣,這種建筑方式在唐代敦煌壁畫中亦可以見到[14]。可見唐代宮廷場所的設(shè)計也跟游藝活動一樣受到了西域的影響。而在西域的宮廷與建筑設(shè)計中,也能發(fā)現(xiàn)諸多中原文化的影子。如法國學(xué)者莫尼克·馬雅爾認(rèn)為,高昌古城是整體仿照唐都長安的平面圖建立起來的,而沿城池北墻則有一座仿照中國宮廷而建造的王城 [15]。
除觀賞性游藝之外,宮廷中還有可供統(tǒng)治階層親身參與的場所。馬球是深受唐代統(tǒng)治階層喜愛的一項游藝活動,唐代的諸多宮苑中,都有馬球場的存在。如“尚食內(nèi)苑、紫云閣之西有凝陰殿,殿南有凌煙閣。貞觀十八年太宗圖畫功臣之像二十四人于閣上,帝自為贊詞,褚遂良題額。又有功臣之閣在凌煙之西,東有司寶庫。凝陰殿之北有球場亭子”[16]。其中提到“球場亭子”,表明此處有一處球場,還有觀賞馬球用的觀賞亭。而當(dāng)有外國使節(jié)來訪時,唐代統(tǒng)治階層也會邀請他們一起參加馬球活動。如唐中宗時,有一場著名的馬球比賽就發(fā)生于宮廷內(nèi)的梨園之中:
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園亭子賜觀打球。吐蕃贊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請與漢敵。上令仗內(nèi)試之。決數(shù)都,吐蕃皆勝。時玄宗為臨淄王,中宗又令與嗣虢王邕、駙馬楊慎交、武秀等四人,敵吐蕃十人。玄宗東西驅(qū)突,風(fēng)回電激,所向無前。吐蕃功不獲施,其都滿贊咄,尤此仆射也。[17]
對抗的雙方分別是吐蕃使臣與唐廷官員。前幾輪比賽中,吐蕃使者皆取得了勝利。在被動情況下,當(dāng)時還是臨淄王的李隆基挺身而出,運用自己高超的馬球技巧,幫助唐方取得了勝利。顯而易見的是,這場著名的馬球比賽背后,不僅折射出馬球交流的諸多信息,還折射出了馬球場這一游藝場所的諸多信息,如參賽雙方來自不同區(qū)域,賽前必先充分溝通比賽規(guī)則和評判勝負(fù)的標(biāo)準(zhǔn)以及場地是否熟悉適合等。這既是絲綢之路馬球游藝文化交流的生動體現(xiàn),又是絲綢之路游藝文化交流場所的生動展示。
三、社會公共組織游藝文化交流場所
這里所討論的社會公共組織,指的是相對于統(tǒng)治階層專用場所的,具有一定官方或半官方性質(zhì),但更多面向大眾的社會組織或群體,一般包括寺院、官衙,或城市中的專門機構(gòu)等。此類組織的服務(wù)對象范圍較廣,既包括政府官員、教職人員,也涵蓋了百戲藝人和市民群眾。這些群體既可擔(dān)任游藝活動的組織者,也可以是其中的參與者。此處以寺院為例,探討中國古代公共場所中進行的游藝文化交流。
寺院是佛教僧侶及信徒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但以寺院為中心衍生出的廟會、戲場等場所又體現(xiàn)著一定的世俗特征。因而,流行其中的游藝活動往往誕生于宗教文化,但發(fā)展于世俗生活,并最終通過世俗游藝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因此,在寺院、戲場、廟會等場合進行的游藝活動,既不是完全的宗教儀式,亦非純粹的民間娛樂,而是一種有機融合宗教信仰與世俗生活的復(fù)合文化產(chǎn)物。
魏晉以降,佛教在中國本土得到了廣泛傳播,一方面是由于其本土化改造趨于完善,另一方面則出于當(dāng)時民眾無法逃避現(xiàn)實戰(zhàn)亂,因而寄情于超然世外的宗教文化的客觀需要。這種強烈的情感需要也促使當(dāng)時的僧侶更多地使用世俗化的方式,如詩歌、琴棋書畫、雕塑、茶道、變文等技藝來吸引信眾[18]。這種對于佛教的信仰則自然地物化為寺院文化的繁榮,《洛陽伽藍(lán)記》中甚至記載了孝文帝之時“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19]37。
隨著數(shù)量的增加與規(guī)模的擴大,寺院的功能與作用也逐漸超出了一般宗教場所的范疇。早期,許多寺院為了慶祝佛教節(jié)日,往往設(shè)有專門用于慶祝節(jié)日的場所。但隨著佛俗與民俗的深入融合,寺院周邊也逐漸演化出廟會這一時令性節(jié)慶場所(或稱集會)。如唐時流行的佛誕節(jié),最初是為紀(jì)念釋迦牟尼的誕生而設(shè)立的,慶祝形式也僅限于施齋、浴佛、抄念經(jīng)典等傳統(tǒng)的佛教儀式。但隨著信徒人數(shù)的增長、娛樂需求的增加以及更多教俗文化的交流,百戲演藝也逐漸融入慶典流程之中。《杜陽雜編》 載:
十四年春,詔大德僧?dāng)?shù)十輩于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四月八曰,佛骨入長安,自開遠(yuǎn)門安福樓,夾道佛聲振地,士女瞻禮,僧徒道從。上御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沾臆……競聚僧徒,廣設(shè)佛像,吹螺擊鈸,燈燭相繼。又令小兒玉帶金額白腳呵唱于其間,恣為嬉戲。又結(jié)錦繡為小車輿以載歌舞。如是充于輦轂之下,而延壽里推為繁華之最。[20]
此段描述的便是著名的唐懿宗“迎佛骨”事件。可以看到,在整個慶典過程中,除了“士女瞻禮”“僧徒道從”等基本佛教儀式之外,還出現(xiàn)了“吹螺擊鈸”、小兒“呵唱于其間”等歌舞表演。這充分說明了當(dāng)時宗教活動與世俗娛樂之間存在著相互融合的現(xiàn)象,而這種教俗文化的交織也就意味著廟會的出現(xiàn)。廟會往往吸引著眾多的僧侶、信徒以及普通群眾前來參與、娛樂,同時這種大型的人員聚集又為百戲藝人和貨郎商販提供了豐富的客源,寺院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成為一種大眾化的娛樂場所。《洛陽伽藍(lán)記》卷1“長秋寺”條載:
長秋寺,劉騰所立也……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獅子導(dǎo)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緣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于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19]43
上述即為長秋寺“行像”日廟會時寺院表演“獅子舞”與“吞刀吐火”“緣幢上索”等幻術(shù)雜技的場景。而這次表演也吸引了大量群眾前來觀看。
廟會中的雜技幻術(shù)大都自西域傳來,如上文提到的獅子舞,據(jù)周泓考證,大致于南北朝時期由西域傳入中原,這一時期亦出現(xiàn)了“漢人制作或扮獅”的現(xiàn)象[21]。獅子原產(chǎn)于西域,中國本土的獅子多源于絲綢之路西方諸國的進獻或贈送,后由西域胡人扮演獅子進行舞蹈,創(chuàng)制了獅子舞這一游藝活動。《新唐書·音樂志》記載,獅子舞自龜茲傳入中原,并對舞獅演員和道具進行了描述:“龜茲伎……設(shè)五方獅子,高丈余,飾以方色。每獅子有十二人,畫衣,執(zhí)紅拂,首加紅襪,謂之獅子郎。”[22]《通典》中亦有對獅子舞道具和舞姿的詳細(xì)記錄:
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師子摯獸,出于西南夷天竺、師子等國。綴毛為衣,像其俯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拂,為戲弄之狀。五獅子各依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樂,舞抃以從之,服飾皆作昆侖像。[23]
不難看出,此時的獅子舞仍然帶有明顯的異域色彩。但隨著其在廟會等世俗場所的普及與在演出過程中不斷進行的本土流變,獅子舞(亦可稱為舞獅)也中和了中西文化的不同因素,最終演變?yōu)榉现性貐^(qū)審美的形態(tài),為宮廷與民間所喜聞樂見。諸多唐詩如白居易《西涼伎·刺封疆之臣也》和元稹《西涼伎》中,都曾描寫過精彩絕倫的獅子舞表演。
除了中原地區(qū)的寺院廟會之外,在西部的敦煌地區(qū),人們也會在節(jié)慶時于寺院中進行游藝活動。S.4625《燃燈文》載:
每歲元初,靈巖建福;燈燃合境,食獻傾城;福事已圓,眾善遐集。其燈乃神光晃耀,炯皎而空里星攢;圣燭耀明,朗映而靈山遍曉。銀燈焰焰,香油注玉盞霞開;寶火煒煒,素草至金瓶霧散,千龕會座,儻然創(chuàng)砌琉璃;五閣仙層,忽蒙共成卞壁。遂使鐵圍山內(nèi),竟日月而通祥;黑暗城中,迎光明而離苦。[24]
每到上元節(jié)的夜晚,敦煌地區(qū)的人們便會前往寺院、佛窟通過燃燈的形式來祈愿。《燃燈文》中漫山遍野的燈火,正是當(dāng)時敦煌寺院節(jié)日熱鬧景象的最好反映,亦可借此窺見上元燃燈在敦煌以及更西地區(qū)的傳播。由此可見,寺院作為中國古代的公共組織場所,在絲綢之路游藝文化的交流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四、非正式游藝文化交流場所
非正式的游藝場所,不同于節(jié)令性的大型活動地點,多指的是不受時間、地點、條件制約,較為隨意、方便的娛樂場所。對比與統(tǒng)治階層及社會工作組織的大型游藝場所,此類場所往往規(guī)模更小,耗費人力物力較少,但卻具備著純粹的民間性,更能體現(xiàn)中西游藝文化交流的廣泛性、深入性。此處將選取瓦舍這類游藝場所,以更為具體地剖析非正式游藝文化交流場所的特征。
唐宋之際,伴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繁榮發(fā)展與市民階層的不斷壯大,在一些都市內(nèi)出現(xiàn)了服務(wù)于市民的商業(yè)性質(zhì)游藝場所,俗稱“瓦舍”,又名“瓦子”“瓦肆”。瓦舍之內(nèi)用于表演歌舞游藝的場所名為“勾欄”,或“勾肆”“邀棚”,勾欄內(nèi)設(shè)戲臺、戲房、神樓等。據(jù)記載:“每座瓦舍中都有勾欄,臨安北瓦有勾欄十三座。而小瓦子恐怕就只有一個勾欄撐持場面,故而勾欄有時也與瓦舍互為同義詞。勾欄的原意是欄桿,由于大型瓦子內(nèi)有不止一個游藝場所,各個場子四周以欄桿圈圍起來,成為一個演出的場子,另一層用意則不外乎防止有人趁機看白戲。”[25]勾欄作為瓦舍中主要的演出場所,其演出內(nèi)容多以音樂、歌舞等內(nèi)容為主,其中的歌舞有許多便來源于絲綢之路上的文化傳播。如宋元祐年間(1068-1094)的“諸宮調(diào)”,是宋朝紅極一時的音樂形式:“將唐宋以來的大曲、詞調(diào)、纏令、纏達、唱賺、傳奇以及北方流傳的民間樂曲按聲律高低,歸人各個不同的宮調(diào),敷衍成文而人曲說唱。”[26]33但像諸宮調(diào)這種音樂的形成,經(jīng)過嚴(yán)格的考究應(yīng)該是出現(xiàn)在宋之前。“經(jīng)比較,宋、金、元代流傳的諸調(diào)其性質(zhì)與體裁同唐代變文相似,發(fā)展到以琵琶等樂器伴奏的‘彈詞,又與胡曲發(fā)生一定的關(guān)系。無獨有偶,在中國西部地區(qū)敦煌遺書中也發(fā)現(xiàn)了可稱為諸宮調(diào)的3個寫卷,以及黑城佛教遺址問世的《劉知遠(yuǎn)諸宮調(diào)》。”[26]34這則史料證明,早在唐代,東西方的音樂藝術(shù)交流便已經(jīng)漸趨形成了諸宮調(diào)的雛形。而瓦肆作為其演出的主要場所,也承擔(dān)了文明交流的重要作用。
除音樂歌舞之外,瓦舍還有許多其他的娛樂活動也源起于絲綢之路上的游藝文化交流。例如在我國深受喜愛的“皮影戲”與“傀儡戲”,就與西域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生經(jīng)》卷3中記載,應(yīng)國王之約,“即以材木作機關(guān)木人,形貌端正,生人無異;衣服顏色,黠慧無比;能工歌舞,舉動如人”[27]。此處指印度與西域流行的木傀儡。在我國唐代,西域各地已盛演傀儡戲。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26號墓中曾清理出彩繪木俑和絹衣木俑70多件,另外,還有木馬殘腿、木俑手腳200件。這充分證明在唐代東西方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中,傀儡戲這一游藝在西域各地飽受關(guān)注。到了宋代,瓦舍中的皮影戲、傀儡戲表演更是有了長足發(fā)展,并在原有基礎(chǔ)上演變出了新的形式。宋代耐得翁《都城紀(jì)事》有載:“弄懸絲傀儡、杖頭傀儡、水傀儡、肉傀儡。”[28]另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載:“崇觀以來,在京瓦肆技藝有……藥發(fā)傀儡……影戲……弄喬影戲……不以風(fēng)雨間,諸棚觀戲人,日日如是。”[29]此處的“影戲”,即以平面傀儡取影,亦為傀儡戲的一種主要演藝形式。
除皮影戲、傀儡戲表演的形式是中外交流的結(jié)果之外,其表演的內(nèi)容也與通過絲綢之路的中外游藝文化交流密切相關(guān)。據(jù)史料記載,古代印度常用影戲的手法進行表演,其中最古老的戲劇名講述了羅摩與西多的故事,叫作“都墨伽陀”。除此之外,還擅長表演猴王“安家陀”的故事,因此,在古印度影戲也常被稱為“皮猴戲”。此故事當(dāng)從印度《羅摩衍那》史詩中的猴王“哈努曼”蛻變而出[30]。胡適先生在《〈西游記〉考證》一文中曾提及:“有一部專記哈奴曼奇跡的戲劇,風(fēng)行民間。中國同印度有一千多年的文化上的密切交通,印度人來中國的不計其數(shù),這樣一樁‘偉大的哈奴曼故事是不會不傳進中國的。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反映中印及周邊國家猴行者的根本。”[31] 由此看來,中國版的“美猴王”故事內(nèi)容,多少受到來自印度的皮影戲內(nèi)容的影響。據(jù)此可知,中國的游藝文化在同其他國家交流的過程中,不斷地兼收并蓄、取長補短。而瓦舍這種非正式游藝文化場所的出現(xiàn)和快速發(fā)展,不僅吸收了他國的優(yōu)秀游藝文化,更衍生出屬于自己的文化產(chǎn)品。
五、結(jié)語
場地場所是絲綢之路游藝文化交流中必不可少的基礎(chǔ)。它不但保證了游藝活動的開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游藝文化的交流與傳播。綜上所述,統(tǒng)治階級耗資大、占地廣的游藝場所不但代表了當(dāng)時的最高審美,也間接引領(lǐng)了整個社會的娛樂風(fēng)向。而社會公共組織類游藝場所則給統(tǒng)治階層之外的諸多民眾提供了世俗的、大眾的、開放的公共普適性游藝場所。非正式游藝場所雖從規(guī)模和檔次上都無法與前兩類場所相比,但它的確是廣大民眾最為喜聞樂見的、最常前往的游藝文化場所。其承載了最廣大民眾的娛樂休閑需要,在大多數(shù)時候它們是普羅大眾愉悅身心、放松心靈的寄托之所。
各類不同屬性的游藝場所源源不斷地吸引著諸多游戲者參與到各色中外游藝活動中來,從而使他們成為了各類游藝場所中游藝文化的參與者、傳播者,甚至是發(fā)展者和創(chuàng)新者。古代中原民眾在接受、學(xué)習(xí)并享受異域傳來的游藝活動時,也同樣將中原游藝場所與之創(chuàng)意性結(jié)合,從而在不知不覺中實現(xiàn)了文化的兼容并蓄。其中的許多創(chuàng)意最終通過漫漫絲路,反向影響了西域游藝活動的發(fā)展。通過對上文中三類游藝場所盛況的列舉分析,我們也能夠看到唐宋時期中原地區(qū)對經(jīng)絲綢之路而來的異域游藝文化的喜愛與重視,也從游藝交流的角度側(cè)面說明了絲綢之路對于我國古代各階層人民的日常生活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在今后的研究中,將游藝文化交流場所作為一個單獨的研究對象與客觀主體,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展示更為立體、飽滿的絲綢之路游藝文化形象,以便于更加深入地了解絲綢之路這一偉大的歷史之路。
[參考文獻]
[1]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述而[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85.
[2]左民安.細(xì)說漢字1000個漢字的起源與演變[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389.
[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述而[M].北京:中華書局,1983:94.
[4]楊蔭深.中國游藝研究[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1.
[5]陳正平.唐詩所見游藝休閑活動之研究[D].臺中:私立東海大學(xué),2006:6.
[6]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2920.
[7]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8.
[8]王玉德.中國宮廷文化集觀[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2.
[9]蕭統(tǒng)編,李善注.文選[M].北京:中華書局,1977:48.
[10]釋道世著,周叔迦、蘇晉仁注.法苑珠林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3:107.
[11]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1043.
[12]王振.張衡候風(fēng)地動儀的復(fù)原研究(續(xù))[J].文物,1963,(04):1-20.
[13]常青.西域文明與華夏建筑的變遷[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38.
[14]朱永春,朱永和.中國建筑[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8.
[15]莫尼克·馬雅爾.古代高昌王國的物質(zhì)文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95:94.
[16]宋敏求.長安志[M].臺北: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34.
[17]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5:53.
[18]李斌成等著.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8:376.
[19]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lán)記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20]王仁裕等撰,丁如明等校點.開元天寶遺事(外七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32.
[21]周泓.古代漢地之部分西域文化考溯[J].湖北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2018,(06):42-57.
[25]歐陽修等撰.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470.
[23]杜佑.通典[M].北京:中華書局,1988:3718.
[24]黃征,吳偉.敦煌愿文集[M].長沙:岳麓書社,1995:528.
[25]虞云國.水滸尋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227.
[26]王潔慧.絲綢之路上的音樂藝術(shù)研究[M].北京:中國商務(wù)出版社,2020.
[27]李強,柯琳.民族戲劇學(xué)[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532.
[28]馮雙白,等.圖說中國舞蹈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51.
[29]孟元老撰,侯印國注.東京夢華錄[M].西安:三秦出版社,2021:130.
[30]黎羌,柯琳.東方樂舞戲劇史論[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9:130.
[31]胡適.胡適古典文學(xué)研究論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