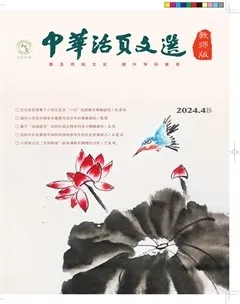“重疊共識”的構建:小學生社會公德教育改革策略探析
摘 要:縱觀當前小學生社會公德教育體系的構建,在參與者、內容、評價功能等方面存在著偏差。本文借鑒羅爾斯的“重疊共識”理念,分析小學生社會公德教育對“重疊共識”的訴求及原因,從而依據“重疊共識”理論,探析小學生社會公德教育的改革路徑。
關鍵詞:社會公德教育 重疊共識 改革路徑
一、研究背景
“重疊共識”起源于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理論。在當今理性且多元的社會中,構建和實現一種以理性主義為主導,具有高度包容性的“重疊共識”,成為解決現代多元化民主社會的穩定性和一致性問題的突破口。在現代社會,個體的意識越來越凸顯,要達成群體思維的高度一致是極其困難的,況且現代社會的共享氛圍也與此背道而馳,因此,達成一定的重疊共識既是對爭議問題的探討,又是對“臨時協定”的深化。羅爾斯啟發我們,在基本社會公德問題上的一致是社會穩定所必須的,同時也是能夠達到的。這對多元社會的對話方式、生存方式、思考方式等諸多方面都是一種非常有益的思考,它為解決現代多元社會所面臨的社會公德教育難題提供了深刻的見解和基本思維框架。
同樣地,“重疊共識”理念在當代教育領域也具有一定的現實借鑒意義。在社會公德的主體和內容多元化的時代,社會公德教育的難度增加,以單一主體對學生實施教育已經無法實現高質量的教育目標。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時代過早地帶領學生進入信息世界,魚龍混雜的社會信息更是使得學生容易進入思維誤區,由此,對于社會公德的教育范圍也變得豐富多元。從已有的研究來看,學術界對于社會公德的探究較少,主要從學科和管理視角將德育融入對小學生的日常教學中,而對于系統化的“社會公德”的研究尚存空白,缺失一種成熟的理念為社會公德體系的構建提供支撐。而“重疊共識”的構建價值在于本著整合和吸納多種合理有益價值理念的初衷,促進社會公德教育體系的完善與發展,從而推動小學生社會公德的形成與發展。
二、當前小學生社會公德教育對“重疊共識”的訴求及原因分析
1.社會公德教育參與者的缺失
大眾普遍認為,學校承擔著對小學生進行社會公德教育的主要責任。然而,實際上參與社會公德教育的主體范圍相對更小,通常僅限于教育行政的工作人員和部分專業的權威專家。家長、教師、學生、社會上的人都沒有在社會公德教育方面擁有參與權和話語權。換句話說,僅在針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時,教師才被授權了極其有限的權力。社會公德教育的實施,往往依賴政府政策的制定或指引,再由學校自上而下地貫徹實施,而在實施過程中的真正成效又會因種種原因而大打折扣。可以說,被動地進行社會公德教育也是教育主體的一種缺失。多數學校都未能將社會公德的教育作為小學生教育工作的重點,而是將其作為日常工作。因此,教師未能主動地在社會公德方面加以重視自己的行為規范,更無法將社會公德教育融入特定的道德教育工作中。而家長由于自身缺乏社會道德意識,對社會道德教育的關注不夠,一直未能參與到道德教育改革中,家長素質的參差不齊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孩子接受的道德教育質量無法保障,甚至存在對于社會公德的誤區。學生也由于身心發展的程度有限,難以主動形成自己的社會道德意識。因此,有人認為,家長、學生和社會人士在道德教育改革中的作用并不顯著,被剝奪了達成共識機會的權利。
2.社會公德教育內容的零碎單一
首先,社會公德教育的內容是單一的。在當代,德育的重要職責常常被視為對核心價值觀的教育,主要涉及思想、政治、道德、法律、心理健康等教育領域,具有強烈的主流思想傾向性。集中討論核心價值觀會形成一種誤解:只有達成共識的價值觀才是合適的。而這樣的結果無疑會使德育趨于同質化。核心價值觀的主流價值思想固然是社會需要大力推崇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將所有的社會價值理念和社會公德內容模式化、固定化。單一思維統領群體的時代已經過去,多元的時代需要多元的思維碰撞才能得以延續。假如社會對公共道德的解讀過分單一,那由此所形成的“共識”勢必會因為深度觀點的沖突而最后走向瓦解。
其次,社會公德教育的內容是零碎的。社會道德教育一直是現代公共生活中多元道德價值的體現。然而,在小學德育系統內,社會道德教育的領地過于狹小,除了《道德與法治》課程教學,社會道德教育幾乎未設置專門的主題教育活動。在我國的小學生守則中,社會公德也沒有直接體現,而是抽象模糊地融合在“愛國愛黨愛人民”和“明禮守法講美德”中。我國當前的小學生社會公德教育內容還是過于零碎,缺乏獨立系統的社會公德教育主題。
3.社會公德教育評價體系功能的缺位
德育評價是一個包含多元價值的建構活動,德育評價作為德育過程中的重要環節,應該體現多元主體的“視域融合”。
然而,從當今小學生的社會公德教育評價體系中,不難發現評價體系功能存在缺位。首先,當前“分數優先”的教育觀在社會之中仍占主導地位,雖然學校也會進行公德評比等活動,但多數情況下并非真正實施,缺乏有效的監控和評估措施;其次,經學者研究發現,對于小學生的品格評價仍以班主任為主導,缺乏其他教師的全面評估。學生之間或自我評價在實際中往往難以起到關鍵作用,班主任的個人觀點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學校對學生的道德評級。這種做法顯而易見是有失公允的,小學生對社會公德的理解和價值追求只能被限制于教師個人的價值理念內,即使學生互評對價值追求的“視域”有一定的擴展作用,但是或許會因為缺乏“重疊共識”導致彼此價值理念上的紛爭或者是學生互評流于形式,沒有得到教師的認可,失去實質上的意義,無法實現價值追求的“視域融合”。
三、“重疊共識”理念下小學生社會公德教育改革路徑
1.協同引導:養成公德意識
社會公德教育參與者的缺失導致了“重疊共識”主體的狹隘化,由此擴展共識的主體即社會公德教育的參與者成為優化小學生社會公德教育改革路徑的重要突破口。要實現“重疊共識”的構建,教師需要將學校、家庭與社會三方面的力量聯合起來。
首先,學校根據其等級設定公共行為準則,并組織一些相關的活動。學校是學生日常生活和學習的主場,也是培養公民道德認知的關鍵場域。對學生的道德培育方法主要可以分為三個環節:首先是公德標準,學校的領導團隊需根據政策需要,制定相應的標準并構建一套完整的小學生社會公德標準系統;其次是文化氛圍,校園環境是影響學生行為意識的隱性教育的重要因素,學校的校訓及校風所蘊含的深厚文化是隱形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最后是公德活動,學校需要針對學生道德認知發展的階段設計新穎的主題活動,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其次,家庭層面需要強化公德認同,參與公德實踐。家庭教育具有針對性、終身性、感染性,這是學校教育不可替代的。中國傳統的家庭教育理念重“私德”而輕“公德”。因此,家長應該立即改變舊的理念,正確理解公共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強化對公共道德的認同,給予公共道德教育足夠的重視,并在日常生活中以自己的社會公德意識和示范效應引導孩子參與到公共道德的實踐中。作為孩子的“第一任教師”,家長應在日常生活中以自身的社會公德意識及榜樣示范引導孩子參與公德實踐。
最后,社會層面需要支持公德實踐。根據愛普斯坦的交織影響領域理念,家庭、學校和社區被視為孩子受教育和社會化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意味著,公德教育不僅需要學校和家庭的參與,還需要社區主體的介入。社區可以在道德實踐中對學校和家庭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具體為為道德實踐活動提供場地、物資等資源,情感支持為對道德實踐活動的參與者提供鼓勵、引導等。
由此,學校、家庭與社會三方面參與到小學生社會公德教育中來,擴展了共識的主體,家校社以不同的角度在小學生社會公德教育中承擔了各自的任務,在不同的主體視角中遵循“相互承認”的思維方式,求得“同”的共識,構建“重疊共識”下的公德意識。
2.多元認同:拓寬德育內容
社會公德教育內容的零碎單一是缺乏“重疊共識”構建的結果。因此,教師構建合理的“重疊共識”,加強多元認同,才能豐富社會公德教育內容。
首先,“重疊意識”的構建需要有主流思想下的身份認同作為前提。伯林賽亞的多元文化理論主張,如果個人不融入集體且建立嚴謹的認同——也就是對自身身份的認可和肯定,會在被強迫同化的過程中失去自我。然而,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并不等于文化的單調性,它是在堅守公共價值的基礎上,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和不同之處。每個個體都有不同的價值觀,“重疊共識”的構建需要形成多元認同。每個人都不能僅僅局限于自己的道德觀,而應當互相尊重各自的價值追求,在面臨價值觀的沖突時尋求共同和平衡的地方。這需要我們彼此理解、接納,甚至互相學習、借鑒,逐漸建立一個廣大群體都能接受的利益協調的共識,實現“視域融合”。在小學生社會公德的教育中,教師借鑒皮亞杰和科爾伯格創建的認知性道德發展模式,根據道德判斷力的“三種水平和六個階段”制成道德發展量表,要求學生根據已有的發展水平確定教育內容,運用沖突的交往或圍繞道德兩難問題的小組討論等方式,創造機會讓學生接觸和思考高于他們一個階段的道德理由和道德推理方式,引導學生在尋求新的認知水平之中不斷提高道德水平,同時達到“重疊共識”的境界。為拓寬社會公德教育內容,教師可以借鑒魏賢超提出的“主體參與道德教育模式”,即社會、學校、教師和家長要在教育中積極組織學生參與活動,引導每個學生以主體身份直接參與班級、學校、家庭和社會各個領域的事務,主動接受班級、學校、家庭和社會的變革和發展,從而使學生在參與中受到教育、獲得發展,通過主體參與拓展社會公德教育內容。從宏觀上看,學校層面的社會公德教育應該引導學生以社會公民的身份直接參與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經濟、社群、政治與文化領域的生活、活動及其變革中去,從而接受社會生活的全面影響與全面教育,獲得主體性素質和主體性道德的全面、整體的發展。從微觀上看,學校中的一切教育活動與過程,都應該從學生身心發展的特征、需要與規律出發,重視學生學習與發展過程中的主動性、能動性、積極性、自主性與創造性,從而促進學生主體性素質和主體性道德素質的發展。由此,社會公德教育內容就增加了多元性,也能夠為更多人所接受、認可。
3.協商對話:完善評價機制
社會公德教育評價功能缺位的主要原因是評價主體的一元性,無法達到價值追求的“視域融合”。教師要實現從一元評價主體到多元評價主體的轉型,打破單純依靠教師評價的缺陷,即要倡導家庭和社會尤其是和被評價者協商對話,以構建真實有效的多元評價體系。
教師要提高學生德育評價的參與度,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學生自評是目前最為欠缺的內容,教師應鼓勵學生自我反思、自我對話、自我剖析,通過自評活動及時反映學生的道德發展需要。教師要將學生納入德育評價主體范圍,使其學會傾聽與交流,開展師生、生生之間的協商對話,并通過平等尊重的情境獲得個體認同感,進而在雙向認同的基礎上增進多元化的評價標準。其次,多維度的評價方式也十分關鍵。學校可以將形成性評價與過程性評價有效融合,創新道德情景設計與模擬,在各種活動中將社會公德的考核融入進來,將理論考核轉化為實操展示,提升社會公德教育的實際效能。最后,教師要充分發揮評價機制中“道德榜樣”的示范作用,利用評價機制給予社會公德優秀的學生表彰,借助榜樣力量助推校園道德文化建設。另一方面,為了多樣化評價主體,教師可以邀請第三方機構參與到學校社會公德教育的過程中來,形成家校社三方育人共同體,借此推動社會公德教育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參考文獻:
[1] 侯倩、李濤、劉中合《“重疊共識”視閾下大學生創業價值觀教育探究》,《高教學刊》2021年第25期。
[2] 嚴從根《“重疊共識”的“重疊共識”:德育改革的合理性訴求》,《全球教育展望》2009年第7期。
[3] 周敏《家校社共育背景下小學生社會公德教育策略研究》,貴州師范大學2022年碩士論文。
[4] 雷月榮、趙雪《第四代評價理論視角下我國德育評價的現實困境與突圍之策》,《教育理論與實踐》2023年第1期。
[5] 趙鳳琴《小學生社會公德教育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研究》,魯東大學2015年碩士論文。
[6] 楊曉《族群歸屬和身份認同的意義:以賽亞·伯林的文化多元論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學海》2021年第1期。
[7] 楊威、謝丹《羅爾斯“重疊共識”理念及其價值內蘊探微》,《學術交流》2020年第8期。
[8] 仲建維《德育評價應超越量化取向》,《教育研究》2014年第5期。
(樂佳萱,2002年生,女,漢族,浙江舟山人,大學本科,研究方向:小學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