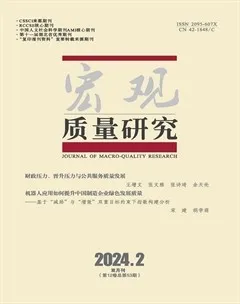企業(yè)對外直接投資如何影響出口產(chǎn)品質量
華岳 鄭文卓 肖皓



摘 要:提高國際雙向投資水平,推動產(chǎn)業(yè)競爭力提升是中國實現(xiàn)高水平對外開放和加快建設貿易強國的內在要求。本文依托全球價值鏈理論框架,基于2005-2013年中國工業(yè)企業(yè)和海關貿易微觀匹配數(shù)據(jù),深入探討中國企業(yè)OFDI影響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效應和機制。匹配-雙重差分和工具變量分析結果表明:中國企業(yè)進行OFDI顯著提升了出口產(chǎn)品質量,結論通過了一系列穩(wěn)健性檢驗。機理分析和機制檢驗表明,企業(yè)OFDI主要通過中間品進口效應、自主創(chuàng)新研發(fā)投入效應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推動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異質性分析顯示,當投資主體為小規(guī)模企業(yè)、非國有企業(yè)、高管理效率企業(yè)、一般貿易企業(yè)以及高市場化程度地區(qū)企業(yè)時,OFDI會導致更大幅度的出口產(chǎn)品質量提升。本文為理解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的互動關系提供了來自企業(yè)層面的新證據(jù),為如何利用資本要素和投資舉措促進貿易高質量發(fā)展提供了政策啟示。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出口產(chǎn)品質量;中間品進口;企業(yè)技術創(chuàng)新
一、引言
當前世界正經(jīng)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思潮抬頭,疊加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等因素,國際市場需求呈現(xiàn)斷崖式下滑態(tài)勢。國內方面,價值鏈低端鎖定、出口產(chǎn)品質量偏低等困境使得出口貿易面臨復雜、嚴峻的形勢(劉啟仁和鐵瑛,2020)。因此,出口產(chǎn)品提質升級成為從根本上促進企業(yè)出口競爭力轉型升級,從而實現(xiàn)全球價值鏈高附加值環(huán)節(jié)延展的關鍵舉措(許家云等,2017)。貿易強國建設被置于中國“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實現(xiàn)高質量發(fā)展的重要位置,如何有效提升出口產(chǎn)品質量成為極具緊迫性的研究議題(盧盛峰等,2021)。
現(xiàn)有針對推動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的研究較為豐富(Bas和Strauss\|Kahn,2015; Crinò和Ogliari,2017;Fan等,2018),眾多研究從企業(yè)生產(chǎn)率(Amiti和Khandelwal,2013)、企業(yè)自主創(chuàng)新(宋躍剛和鄭磊,2020)、中間品貿易自由化(Fan等, 2015)、人民幣匯率(余淼杰和張睿,2017)、企業(yè)股權激勵(湯超等,2023)等視角探究了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決定因素與機理。推動“雙循環(huán)”的順暢運行需要高水平對外開放與高質量發(fā)展有機結合。作為挖掘東道國市場潛力、規(guī)避貿易壁壘與維護全球化貿易及分工體系的有效方式,對外直接投資(以下簡稱OFDI)迎來歷史性增長契機,隨著中國“走出去”戰(zhàn)略的深入實施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大力推進,2023年中國全行業(yè)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1478.5億美元,居全球第二,存量近3萬億美元,居全球第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yè)選擇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參與到國際市場的競爭中,進行全球化戰(zhàn)略布局,據(jù)商務部統(tǒng)計,當前境內投資者在全球190個國家和地區(qū)共設立境外企業(yè)4.7萬家,覆蓋超過80%的國家和地區(qū)。國內外大量研究證實了企業(yè)OFDI對企業(yè)生產(chǎn)率(Li等,2017)、企業(yè)創(chuàng)新(Desai等,2009; 黃遠浙等,2021)、企業(yè)加成率(毛其淋和許家云,2016)和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楊連星和羅玉輝,2017)等方面有顯著影響。其中,對外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互動關系問題一直是國際貿易與發(fā)展經(jīng)濟學領域研究的熱點和重點,也有研究初步證實了企業(yè)OFDI對出口強度存在影響(蔣冠宏和蔣殿春,2014)。隨著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不斷深入,企業(yè)的國際競爭優(yōu)勢并不單純取決于出口規(guī)模(Fan等, 2018)。近年來,部分研究從出口技術復雜度(楊連星和劉曉光,2016)、出口產(chǎn)品多元化(楊汝岱和吳群鋒,2019)、出口增加值(徐國祥和張正,2020)等角度探討OFDI的出口效應。然而,在我國立足新發(fā)展階段,倡導“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高水平對外開放背景下,上述研究均未涉及OFDI與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關系,已有的少量相關研究(余靜文等,2021)也并未在統(tǒng)一的理論框架下系統(tǒng)探討OFDI影響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微觀機理。
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研究視角方面。在中國經(jīng)濟面臨“三重沖擊”、外貿需求下滑的現(xiàn)實背景下,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和加快實現(xiàn)出口貿易高質量發(fā)展是現(xiàn)階段的重要研究議題。本文通過嚴謹?shù)囊蚬R別方法穩(wěn)健揭示了OFDI對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影響,一方面拓展了OFDI在開放視角下的經(jīng)濟效應評估;另一方面也證實了利用資本要素和投資行為促進貿易高質量發(fā)展的合理性。第二,理論框架與機制分析方面,本文立足全球價值鏈的統(tǒng)一理論框架,從中間品進口、自主創(chuàng)新研發(fā)投入、逆向技術溢出三個層面探討OFDI對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影響渠道,為充分理解“從國際投資到國際貿易”這一重要議題提供了基于價值鏈環(huán)節(jié)和技術創(chuàng)新的新視角和新證據(jù)。第三,本文結合規(guī)模經(jīng)濟理論、產(chǎn)權理論和區(qū)域市場分割等理論,充分揭示了企業(yè)OFDI的出口產(chǎn)品質量效應在企業(yè)規(guī)模、所有權、管理效率、貿易方式、所在地區(qū)市場化程度等維度上的差異,進一步擴展了本文的研究廣度,為相關政策的精準制定提供了具有針對性的參考證據(jù)。
本文后續(xù)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第三部分介紹研究設計與數(shù)據(jù)來源;第四部分評估OFDI的出口產(chǎn)品質量效應,并對微觀機制進行實證檢驗;第五部分是拓展性分析;第六部分總結全文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在全球價值鏈的理論框架中,生產(chǎn)分工對象從最終商品擴展到價值鏈各環(huán)節(jié)上的中間產(chǎn)品(Antras和Chor, 2022)。作為比較優(yōu)勢理論和產(chǎn)業(yè)分工理論的繼承和擴展,全球價值鏈理論強調生產(chǎn)流程中各國從事的特定環(huán)節(jié)所能實現(xiàn)的貿易收益,明確指出對于價值鏈各環(huán)節(jié)的比較優(yōu)勢和規(guī)模經(jīng)濟進行分析的重要性。因此,對于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探討,不能忽視出口產(chǎn)品制造過程的中間環(huán)節(jié)與中間產(chǎn)品。此外,全球價值鏈理論還重點關注產(chǎn)品制造周期中各環(huán)節(jié)所產(chǎn)生的附加價值,據(jù)此將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區(qū)分為高端、中端和低端,而決定企業(yè)全球價值鏈位置和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一項核心要素即為企業(yè)技術創(chuàng)新水平,反映在生產(chǎn)要素使用比率與效率層面,即為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或勞動密集型生產(chǎn)模式的區(qū)分(呂越等,2018)。綜上所述,本文以全球價值鏈這一理論框架為依托,基于中間品投入視角(包括中間品質量和種類)和技術創(chuàng)新視角(包括自主創(chuàng)新與技術溢出)對企業(yè)OFDI影響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理論機制進行分析。
在全球價值鏈分工模式下,參與OFDI的中國工業(yè)企業(yè)較多承擔的是制造、加工和組裝等環(huán)節(jié),因而需要大量進口中間品。現(xiàn)有研究已經(jīng)證實,進口中間品在企業(yè)最終出口產(chǎn)品質量中的作用愈發(fā)重要,近乎等同于資本和技術(馬述忠和吳國杰,2016)。OFDI的中間品進口效應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進口中間品的質量效應。隨著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與消費品質升級,消費者對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產(chǎn)品的需求大幅提升,更優(yōu)質的中間品是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的前置性因素(Bas和Strauss\|Kahn,2015)。當前,國產(chǎn)中間品尤其是關鍵零部件的質量相比同類型發(fā)達國家產(chǎn)品質量存在一定差距,難以滿足企業(yè)高質量生產(chǎn)所需;另外,即使國內廠商具備高質量中間品的生產(chǎn)能力,但生產(chǎn)成本卻遠超進口中間品(張杰等,2015)。因此,企業(yè)OFDI的進口中間品質量效應一方面直接促進最終出口品質量升級,另一方面降低生產(chǎn)成本,優(yōu)化企業(yè)資源配置,間接地對出口產(chǎn)品質量產(chǎn)生積極效應(Halpern等,2015)。二是進口中間品的種類效應。企業(yè)可選擇中間品多元化程度的提升能夠有效降低企業(yè)進口中間品的成本(Goldberg等,2010),從而可將節(jié)約的資金配置到研發(fā)投入中,以促進出口產(chǎn)品提質升級(許家云等,2017)。同時,OFDI是企業(yè)獲得差異化資源(如能源型中間品與關鍵零部件)的重要渠道,進口類型更豐富的中間品有助于企業(yè)進一步優(yōu)化中間品投入組合,對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尤為關鍵(王雅琦等,2018)。此外,鑒于消費品種類多樣化會增大消費者效用,東道國多樣化的進口中間品與國內中間品的有機融合也被證實能帶來“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應(Halpern等,2015)。本文據(jù)此提出研究假說:
假說一:企業(yè)OFDI能夠通過中間品進口提升企業(yè)出口產(chǎn)品質量。
對外直接投資加劇了國內企業(yè)產(chǎn)品與國際市場同類產(chǎn)品的競爭,可能刺激企業(yè)增加研發(fā)資金投入、強化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進而推動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該效應可從兩個方面展開分析:一是直接激勵效應。企業(yè)進行OFDI后會極力促使產(chǎn)品在東道國競爭中脫穎而出,而最直接的手段則是加大自主創(chuàng)新研發(fā)的投入,增強自主創(chuàng)新研發(fā)能力,進而提升技術水平與核心競爭力,這一過程也被Desai等(2009)研究利用發(fā)達經(jīng)濟體數(shù)據(jù)所證實。二是間接促進效應。對外直接投資規(guī)模的擴張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貿易開放度的提升,這將引致大量同類型國外產(chǎn)品進入國內市場,進口競爭壓力倒逼了企業(yè)開展技術創(chuàng)新,為維持市場競爭力與市場份額,企業(yè)會主動增強其研發(fā)強度,從而加快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步伐(毛其淋和許家云,2019)。另一方面是母國市場深化效應,母國企業(yè)OFDI帶來的進口創(chuàng)造效應迫使國內該行業(yè)企業(yè)設法競相提高研發(fā)創(chuàng)新水平與生產(chǎn)效率以保證其市場占有率,從而提高母國國內產(chǎn)品質量階梯。母國市場深化有利于出口比較優(yōu)勢的提高與中國全球價值鏈的升級,毋庸置疑會對出口產(chǎn)品質量起到積極作用。本文據(jù)此提出研究假說:
假說二:企業(yè)OFDI能夠通過自主創(chuàng)新研發(fā)投入提升企業(yè)出口產(chǎn)品質量。
OFDI是跨國企業(yè)通過全球布局,以挖掘和吸收先進知識技術和管理理念,并提升出口企業(yè)產(chǎn)品質量的重要手段。發(fā)展中經(jīng)濟體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也被技術地方化理論和技術創(chuàng)新產(chǎn)業(yè)升級理論等經(jīng)典理論加以證明。實踐中,逆向技術溢出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點:一是模仿學習效應,根據(jù)知識技術的外溢性與非競爭特征,企業(yè)通過OFDI方式識別東道國技術優(yōu)勢,學習其生產(chǎn)工藝或模仿其制造流程,進一步吸收東道國新技術并內化于自身產(chǎn)品中,由此帶來產(chǎn)品附加值的提高,為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提供有力保障(鄧悅和蔣琬儀,2022)。二是上下游關聯(lián)效應。首先是東道國上下游關聯(lián)效應,投資母國企業(yè)通過綠地投資或跨國并購方式與東道國上下游關聯(lián)企業(yè)建立合作關系,這不僅有利于追蹤東道國優(yōu)勢產(chǎn)業(yè)上下游領域的技術發(fā)展動態(tài),還增大了近距離接觸到技術網(wǎng)絡與一線市場的可能性(黃遠浙等,2021),更重要的是有益于汲取前后向產(chǎn)業(yè)部門垂直技術溢出以及先進的經(jīng)營理念,為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提供了豐富的知識源。其次是母國上下游關聯(lián)效應,母國企業(yè)與東道國子公司暢通便捷的知識互聯(lián)互通渠道決定了子公司從海外獲取的有價值的知識會迅速傳遞回母國,在此基礎上,母公司進一步與國內上下游企業(yè)交互合作,那么知識技術無疑會再次交融整合,成為企業(yè)出口產(chǎn)品質量提升的重要驅動力。本文據(jù)此提出研究假說:
假說三:企業(yè)OFDI能夠通過逆向技術溢出提升企業(yè)出口產(chǎn)品質量。
三、研究設計與數(shù)據(jù)來源
(一)模型構建
由于不同企業(y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存在先后順序,本文構建交疊雙重差分模型并進行估計:
qualityit=β0+β1ofdiit+∑βkcontrolkit+μj+ηt+λp+εit(1)
式中,因變量qualityit表示i企業(yè)第t年的出口產(chǎn)品質量。解釋變量ofdiit表示i企業(yè)在第t年是否進行了對外直接投資,即將2005-2013年進行OFDI的企業(yè)作為處理組(以首次投資為處理發(fā)生時點),從未進行OFDI的企業(yè)作為控制組。本文感興趣的估計系數(shù)β1可以識別企業(y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決策對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沖擊。controlkit為影響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控制變量集合(k代表控制變量個數(shù));ηt為年份固定效應,μj為行業(yè)固定效應,λp為省份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企業(yè)出口產(chǎn)品質量(qualityit)。本文參照Khandelwal等(2013),將產(chǎn)品異質性納入框架,使用回歸反推方法對出口產(chǎn)品質量進行測算,具體測算方法如下:
n國消費者在第t年對中國企業(yè)i生產(chǎn)產(chǎn)品m的消費量為:
式中,qintm代表在第t年企業(yè)i對第n國出口產(chǎn)品m的數(shù)量;pintm表示在第t年企業(yè)i對第n國出口產(chǎn)品m的價格;ηintm代表在第t年企業(yè)i對第n國出口m產(chǎn)品質量;Ent為第n國第t年消費者支出;Pnt為第n國第t年價格指數(shù),σ為不同種類產(chǎn)品間的替代彈性,參照Melitz(2003)經(jīng)典模型框架關于消費者CES效用函數(shù)的設定,令σ>1。將式(2)兩邊分別取對數(shù),通過轉化可以得到式(3):
lnqintm=δnt-σlnpintm+εintm(3)
式中,δnt=lnEnt-lnPnt,代表出口目的國與時間二維虛擬變量,控制國家-年份固定效應。εintm=(σ-1)lnηintm為殘差項,包含出口產(chǎn)品m的質量信息。同時,本文在式(3)中還加入企業(yè)所在省份實際GDP以控制產(chǎn)品水平特征差異的影響。另外,考慮到產(chǎn)品質量與產(chǎn)品價格之間可能存在內生關系,本文借鑒王永進和施炳展(2014)的做法,對式(3)進行工具變量估計,并對殘差項進行變形化簡,定義企業(yè)i在第t年對第n國出口的m產(chǎn)品質量為:
為進行企業(yè)層面加總以及跨期比較,將質量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得到出口產(chǎn)品質量指標:
式(5)中,maxqualityintm代表在所有年份全部企業(yè)出口到所有出口目的國的產(chǎn)品質量中的最大值,minqualityintm則為相應的最小值,按式(6)進行加權加總處理,即可得到企業(yè)出口產(chǎn)品質量指標:
式(6)中,νintm表示企業(yè)i在第t期出口到第n國產(chǎn)品m的價值量,Ω是企業(yè)i在第t年出口產(chǎn)品的樣本集合。
2.核心解釋變量:企業(yè)是否進行對外直接投資(ofdiit):在樣本期內,如果企業(yè)i在第t年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ofdiit取值為1,否則為0。
3.控制變量:包含企業(yè)規(guī)模(lnysel),采用企業(yè)銷售額的對數(shù)進行衡量;企業(yè)管理水平(manage),采用企業(yè)主營業(yè)務收入與平均資產(chǎn)總額的比值衡量;企業(yè)年齡(lnage),采用企業(yè)當年所處年份減去開業(yè)年份后加1取對數(shù)來衡量;勞動生產(chǎn)率(lnlabor),選取企業(yè)總產(chǎn)值與年均就業(yè)人數(shù)比值的對數(shù)表示;資本密集度(lnkint),選取企業(yè)固定資產(chǎn)凈值與年均就業(yè)人數(shù)比值的對數(shù)衡量;企業(yè)利潤率(profitr),采用營業(yè)利潤與企業(yè)銷售額的比值表示;融資約束(fincon),采用企業(yè)利息支出與固定資產(chǎn)的比值表示;政府補貼(lnsubsidy),采用企業(yè)獲得的政府補貼的對數(shù)表示。
(三)數(shù)據(jù)來源
本文微觀企業(yè)層面數(shù)據(jù)主要來源于2005-2013年中國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與海關進出口數(shù)據(jù)庫。首先,借鑒Brandt等(2012)的做法整理中國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并進行以下處理:剔除工業(yè)總產(chǎn)值、中間投入、應付職工薪酬、銷售額、從業(yè)人員、資本存量、固定資產(chǎn)等重要信息存在不大于0或缺少值的企業(yè);剔除明顯違背“通用會計準則”的樣本企業(yè),如總資產(chǎn)小于流動資產(chǎn)、固定資產(chǎn)凈值的企業(yè);剔除職工人數(shù)不大于8人的企業(yè);剔除非國有企業(yè)的主營業(yè)務收入小于500萬元的企業(yè)。其次,參考余淼杰和張睿(2017)的做法對海關進出口數(shù)據(jù)進行處理,以從微觀層面準確測算企業(yè)出口產(chǎn)品質量;最后,依次按照企業(yè)名稱和年份、郵政編碼和電話號碼后七位組成的十三位數(shù)字進行匹配,并刪除重復樣本。由于初級品、資源品的產(chǎn)品質量主要由自然資源決定,因此在HS8分位數(shù)據(jù)轉換為HS6分位數(shù)據(jù)后,將數(shù)據(jù)與SITC編碼對應并進行轉化,剔除掉初級品和資源品,并剔除以中國為出口國的樣本數(shù)據(jù)。相關控制變量數(shù)據(jù)主要來源于中國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為了消除樣本離群值的影響,本文對連續(xù)變量進行了1%的縮尾處理。各國家和地區(qū)的國內生產(chǎn)總值和研發(fā)投入支出等數(shù)據(jù)均來源于聯(lián)合國商品貿易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庫(UN Comtrade)和世界銀行數(shù)據(jù)庫。相關變量描述性統(tǒng)計匯報于表1。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結果
1.雙重差分估計結果
表2報告了基于雙重差分模型的估計結果,第(1)列僅考慮核心解釋變量ofdi,第(2)列加入了企業(yè)補貼類別的控制變量(政府補貼),第(3)列進一步納入了反映企業(yè)基本面的因素作為控制變量(企業(yè)規(guī)模、企業(yè)管理水平、企業(yè)年齡),第(4)列進一步控制了反映企業(yè)生產(chǎn)結構和經(jīng)營狀況方面的因素(勞動生產(chǎn)率、資本密集度、企業(yè)利潤、融資約束),第(1)~(4)列均控制了年份、行業(yè)和省份固定效應。初步估計結果顯示,本文重點關注的核心解釋變量ofdi的系數(shù)均為正,顯著性水平均一致,說明與未進行OFDI的企業(yè)相比,進行OFDI企業(yè)的出口產(chǎn)品質量更高,即企業(y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決策顯著提升了出口產(chǎn)品質量。具體來說,進行OFDI的企業(yè)與未進行OFDI的企業(yè)相比,其出口產(chǎn)品質量提升了均值(0.322)的5%~14.3%。
2.平行趨勢檢驗
雙重差分估計結果的有效性需要平行趨勢假定予以支撐,即企業(yè)進行OFDI前,處理組企業(yè)與對照組企業(yè)的出口產(chǎn)品質量應具有共同趨勢。圖1繪制了95%置信區(qū)間下的平行趨勢圖,結果表明在企業(yè)進行OFDI前,處理組和對照組企業(yè)出口產(chǎn)品質量已存在顯著趨勢差異,即未通過平行趨勢檢驗。可能的原因是企業(yè)的自選擇行為,即企業(yè)是否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決策并不是隨機的,而是企業(yè)基于自身勞動生產(chǎn)率、規(guī)模、利潤率等因素進行選擇的結果(蔣冠宏和蔣殿春,2014)。因此,為克服選擇性偏誤導致的估計結果偏差,本文進一步采用傾向得分匹配(PSM)選擇與進行OFDI企業(yè)最有可比性的企業(yè)作為對照組,再使用雙重差分法得到更可靠的估計結果。
3.樣本匹配
本文選取勞動生產(chǎn)率(lnlabor)、企業(yè)利潤率(profitr)、出口密集度(exportr,以出口交貨值與企業(yè)銷售額比值衡量)、企業(yè)年齡(lnage)、企業(yè)規(guī)模(lnysel)、資本密集度(lnkint)等匹配變量,以OFDI作為分組變量分年計算傾向得分,并采用“一對三近鄰匹配”方法進行逐年匹配,為進行OFDI的企業(yè)匹配到盡可能相近的從未進行OFDI的企業(yè)作為對照組。表3報告了匹配后匹配變量在處理組和對照組的均值差異,結果表明通過平衡性檢驗,進一步證明選擇的匹配變量與匹配方法是有效的。
(二)基準回歸結果
表4報告了基于PSM\|DID方法的基準回歸結果,于第(1)~(4)列逐步加入企業(yè)層面控制變量。可以看到,核心解釋變量ofdi的估計系數(shù)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企業(yè)進行OFDI對出口產(chǎn)品質量提升具有積極效應。通過對比可以發(fā)現(xiàn),表4第(4)列結果與表2第(4)列結果(0.020)在維度上的差異較小,說明企業(yè)自選擇等問題固然存在,但實際并未給估計結果帶來重大偏誤,表2中的(非PSM)DID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本文同時進行了一系列穩(wěn)健性檢驗,包括工具變量分析、更換自變量及因變量測度、排除金融危機影響、控制行業(yè)和地區(qū)差異化趨勢、剔除外資企業(yè)等,結果均保持穩(wěn)健,限于篇幅,具體回歸結果未進行展示。
(三)動態(tài)效應分析
上文結果表明,企業(yè)進行OFDI在平均意義上有利于推動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需要進一步考慮的是,OFDI影響產(chǎn)品質量這一效應的演進趨勢如何,特別是中長期提升效應是否仍然存在?本文使用目前雙重差分中應用較廣泛的事件分析法進行動態(tài)效應檢驗(張子堯和黃煒,2023),考察OFDI對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影響在時間維度層面的演進特征。為此,本文將式(1)擴展為:
式(7)中,Dγyear為企業(yè)OFDI年度虛擬變量,當企業(yè)處于進行OFDI后的第γ年(γ=0,1,2,3,4,5,6,7,8)時由于本文的時間跨度為2004-2013年,并且處理組的識別是從2005年開始的,因此這里最長的滯后期為8期。,Dγyear取值為1,否則為0。ofdiit×Dγyear的估計系數(shù)φγ反映企業(yè)進行OFDI后的第γ年對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影響。其他變量含義同式(1)。
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包含所有控制變量的第(3)列結果顯示,交叉項估計系數(shù)除企業(yè)進行OFDI當年不顯著之外,其余年份均顯著為正,并且總體而言交叉項估計系數(shù)呈遞增趨勢,這表明OFDI對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提升效應存在一年的時滯,之后提升作用開始顯現(xiàn)并且提升程度呈上升趨勢,由此確認了企業(yè)進行OFDI具有促進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的長效機制。OFDI對出口產(chǎn)品提質升級不存在即期影響,但促進作用隨時間不斷增強這一結果可能存在如下兩點原因,其一,根據(jù)機理分析,企業(yè)進行OFDI后,不論是獲得東道國的中間品資源,還是吸收先進知識技術,又或是在競爭環(huán)境中自主增大研發(fā)投入,都需要內部學習、處理與轉化的過程,同時又受到既定合同與訂單的約束,其推動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的效果不太可能于當年立刻顯現(xiàn)。其二,從企業(yè)生命周期視角來看,對處于初創(chuàng)期和成長期的企業(yè)來說,學習國外技術知識與制造工藝、引進高質量中間品是其生存和成長的重要動力;而隨著企業(yè)向成熟期不斷邁進,其自主創(chuàng)新研發(fā)能力逐漸增強,逐步與國內外同類企業(yè)及上下游企業(yè)等主體建立長期合作關系,從根本上為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提供穩(wěn)定支持,在內外部規(guī)模經(jīng)濟的作用下可能導致OFDI的出口產(chǎn)品質量效應得到持續(xù)放大。
(四)影響機制分析
正如機理分析中所述,企業(yè)進行OFDI可能通過進口中間品效應、自主創(chuàng)新研發(fā)投入效應、逆向技術溢出效應三種渠道影響出口產(chǎn)品質量。基于此,本文引入進口中間品質量(imquality)、進口中間品種類(lnimtypes)、研發(fā)創(chuàng)新密集度(rdint)、通過OFDI獲得的國際技術溢出(lnspill)作為機制變量。關于進口中間品質量,本文借鑒施炳展和曾祥菲(2015)的方式進行測算,其推算過程和模型與前文測算出口產(chǎn)品質量基本一致;關于進口中間品種類的數(shù)量,已有研究認為越高質量的產(chǎn)品需要更多種類的中間品,因此中間品種類一定程度上可以代理生產(chǎn)技術復雜性指標(Bloom等,2018);關于企業(yè)研發(fā)創(chuàng)新密集度,本文使用新產(chǎn)品銷售額與企業(yè)銷售額的比值表示;關于企業(yè)進行OFDI獲得的逆向技術溢出,根據(jù)楊連星和劉曉光(2016)對國際技術溢出效應的界定,以中國OFDI獲得的國際R&D資本存量衡量OFDI的國際技術溢出。因此,借鑒宋躍剛和鄭磊(2020),利用Lichtenberg和Potterie(1998)的構建方法,根據(jù)省份OFDI存量權重加權得到省級層面對外直接投資獲得的國際R&D資本存量,進一步根據(jù)企業(yè)OFDI次數(shù)比重加權加總得到企業(yè)進行OFDI獲得的國際技術溢出(取對數(shù)衡量)。
由表6中第(1)列與第(2)列的估計結果可知,ofdi與ofdi×imquality、ofdi與ofdi×lnimtypes的估計系數(shù)均顯著為正,說明中間品進口效應(包括進口中間品質量效應與進口中間品種類效應)是OFDI提升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重要途徑。OFDI成為企業(yè)更多地引入國外高質量、多元化中間品的關鍵渠道,助力企業(yè)實現(xiàn)培育出口產(chǎn)品質量競爭優(yōu)勢的目標。表6第(3)列中ofdi與ofdi×rdint的估計系數(shù)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OFDI通過自主創(chuàng)新研發(fā)投入效應優(yōu)化出口產(chǎn)品質量,提高研發(fā)創(chuàng)新能力是解決當前中國企業(yè)出口產(chǎn)品“低質和低附加值”問題的重要舉措,也是對外直接投資企業(yè)提升核心競爭力,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的關鍵抓手。從表6第(4)列可以看出,ofdi與交互項ofdi×lnspill的回歸結果均符號為正且統(tǒng)計顯著,說明企業(yè)吸收逆向技術溢出同樣是OFDI促進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的一個有效途徑,是OFDI企業(yè)邁向產(chǎn)業(yè)價值鏈中高端環(huán)節(jié)的重要驅動力。綜上,表6的實證結果基本證實了中間品進口效應、自主創(chuàng)新研發(fā)投入效應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均是OFDI對企業(yè)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產(chǎn)生積極效應的作用渠道,驗證了機理分析中提出的3項研究假說。
五、拓展性分析
(一)企業(yè)規(guī)模異質性
不同規(guī)模企業(yè)的OFDI行為和生產(chǎn)管理模式存在明顯差異,基于規(guī)模經(jīng)濟理論,大規(guī)模企業(yè)憑借其雄厚的資本基礎和資源優(yōu)勢,能夠在生產(chǎn)規(guī)模、市場拓展及風險管理方面展現(xiàn)出較強的競爭力;而小規(guī)模企業(yè)可能依靠其更強的創(chuàng)新意愿、決策過程的迅速以及對市場變化的敏銳感知,以更專業(yè)化的經(jīng)營方式規(guī)避規(guī)模較小的風險,以提升其在目標市場中的競爭地位。據(jù)此,本文考察不同規(guī)模企業(yè)進行OFDI的出口產(chǎn)品質量效應的異質性。設置虛擬變量size,若企業(yè)營業(yè)收入小于樣本企業(yè)營業(yè)收入中位數(shù),則賦值為1,否則為0。
回歸結果參見表7第(1)列,交互項ofdi×size估計系數(shù)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相較于大規(guī)模企業(yè),小規(guī)模企業(yè)更有可能通過OFDI實現(xiàn)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首先,基于資源基礎視角,小規(guī)模企業(yè)面臨的資源約束迫使其在OFDI活動中更加注重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優(yōu)化配置,以期通過技術吸收和創(chuàng)新實現(xiàn)出口產(chǎn)品質量提升。其次,大規(guī)模企業(yè)雖然在資本和資源上具有優(yōu)勢,能承擔更大的投資項目并利用其規(guī)模經(jīng)濟來降低成本,但其在組織結構和決策流程上的復雜性往往導致反應速度較慢,創(chuàng)新能力的發(fā)揮受限;小規(guī)模企業(yè)由于其組織結構的靈活性和決策過程的敏捷性,能夠更快速地吸收東道國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jīng)驗,加速知識的內化過程,從而促進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提高。最后,小規(guī)模企業(yè)往往采取更明確和專注的市場定位策略,更加注重特定目標市場的深耕,通過OFDI加強在細分市場的定位和品牌建設,從而在出口產(chǎn)品質量上獲得競爭優(yōu)勢。
(二)企業(yè)所有權異質性
產(chǎn)權理論強調所有權結構對企業(yè)行為和經(jīng)濟績效的影響,國有企業(yè)和非國有企業(yè)在目標設置、運營效率和資源配置上存在本質上的差異。國有企業(yè)由于政府干預和多重目標(如社會目標)的存在,可能在追求經(jīng)濟效益和出口產(chǎn)品質量提升方面相對受限,其決策過程可能更加注重政策導向而非市場效率。相比之下,非國有企業(yè)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市場機制下,可能更加注重效率和創(chuàng)新,以提升競爭力和產(chǎn)品質量。據(jù)此,本文試圖進一步從考察不同所有制企業(yè)OFDI出口產(chǎn)品質量效應的異質性,設置虛擬變量state,若企業(yè)所有權屬性為國有企業(yè),則賦值為1,否則為0。
估計結果報告在表7第(2)列,結果顯示交互項ofdi×state估計系數(shù)在5%水平上統(tǒng)計顯著且符號為負,表明OFDI的出口產(chǎn)品質量提升效應在國有企業(yè)更弱。對此,可能的解釋有三點:第一,對外投資目標不同。國有企業(yè)更多的是承擔國家戰(zhàn)略性任務和社會責任,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首要目標可能并非是經(jīng)濟性盈利。因此,非國有企業(yè)相較于國有企業(yè)可能具有更強的技術革新意識與核心競爭力提升意識,更趨向于將資本投入到高附加值產(chǎn)業(yè)中,帶來更強的出口產(chǎn)品質量提升效應。第二,研發(fā)創(chuàng)新積極性不同。非國有企業(yè)資本更具流動性、管理體系更靈活、創(chuàng)新愿望更強烈,這決定了其在研發(fā)創(chuàng)新活動方面更具有活力與動力。而國有企業(yè)往往處于市場壟斷位置,面臨的外部市場競爭壓力相對較弱,易出現(xiàn)創(chuàng)新惰性。第三,東道國制度約束強度不同,國有企業(yè)由于其政府背景,OFDI可能會受到投資東道國政府部門更嚴格的制度性限制,而非國有企業(yè)在“走出去”時能更靈活、自由地應對東道國的制度門檻,從而支撐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
(三)企業(yè)管理效率異質性
基于資源基礎理論和企業(yè)邊界理論,企業(yè)的資源和能力是其獲得持久競爭優(yōu)勢的基礎。管理效率作為一種重要的組織能力,會影響企業(yè)資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進而影響企業(yè)的競爭力和市場表現(xiàn)。同時,管理效率高的企業(yè)能夠更接近效率邊界,即以較低的成本實現(xiàn)較高的產(chǎn)出效率,高效的管理能力促使企業(yè)在進行OFDI時,能夠更加精準地識別和利用國際市場機會,優(yōu)化全球價值鏈布局,提升產(chǎn)品質量和創(chuàng)新能力。為考察不同管理效率企業(yè)OFDI對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異質性影響,參考Eisfeldt和Papanikolaou(2013)的做法,以管理費用代理管理效率,人均管理費用越低,則意味著企業(yè)管理效率越高。根據(jù)行業(yè)管理效率中位數(shù)將樣本分為高管理效率企業(yè)與低管理效率企業(yè),設置管理效率虛擬變量mef,若樣本為高管理效率則賦值為1,否則為0。
表7第(3)列匯報了相應的異質性檢驗結果,發(fā)現(xiàn)相對低管理效率企業(yè),高管理效率企業(yè)OFDI對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提升效應更為明顯。可能的解釋是,管理效率越高,企業(yè)越善于結合內部管理經(jīng)營情況與外部動態(tài)市場環(huán)境做出充分與合理的資源配置決策,從而在海外市場更好地吸收逆向技術溢出、準確選擇與自身產(chǎn)品生產(chǎn)或設計過程匹配效率更高的進口中間品投入、提振自主創(chuàng)新成果轉化效率,進而對出口產(chǎn)品質量產(chǎn)生更明顯的正向影響。
(四)企業(yè)貿易方式異質性
全球價值鏈理論強調了企業(yè)如何通過參與全球生產(chǎn)網(wǎng)絡來提升競爭力。一般貿易企業(yè)通過OFDI融入高端價值鏈環(huán)節(jié),從而提高出口產(chǎn)品的質量和增加附加值。相比之下,加工貿易企業(yè)更側重于利用成本優(yōu)勢,參與全球價值鏈中的特定環(huán)節(jié),其OFDI可能更注重尋求成本方面的優(yōu)化。基于此,考慮到從事不同貿易方式的企業(yè)在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依據(jù)貿易方式將樣本企業(yè)劃分為一般貿易企業(yè)與加工貿易企業(yè),設置貿易方式虛擬變量trade,并以加工貿易企業(yè)為基準,若企業(yè)從事一般貿易則賦值為1,否則為0。
由表7第(4)列中的回歸結果可知,交乘項ofdi×trade估計系數(shù)顯著為正,這表明與加工貿易企業(yè)相比,從事一般貿易企業(yè)的對外直接投資顯示出更有效的出口產(chǎn)品質量提升效應。對此,可能的原因有三個方面:首先,技術創(chuàng)新意識方面。一般貿易企業(yè)更高概率參與高附加值產(chǎn)品生產(chǎn),其制造流程中更多地涉及研發(fā)創(chuàng)新與技術升級。然而,不論是進料加工還是來料加工貿易企業(yè),主要以低成本優(yōu)勢參與全球價值鏈低端環(huán)節(jié),因此創(chuàng)新意識相對較弱。其次,帶動相關產(chǎn)業(yè)發(fā)展方面。一般貿易往往處于產(chǎn)業(yè)鏈最終環(huán)節(jié),更有能力通過“走出去”帶動更多相關產(chǎn)業(yè)尤其是國內零部件等中間品所在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并反作用于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提升,形成良性互動。而加工貿易作為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中某單一環(huán)節(jié),在帶動相關產(chǎn)業(yè)發(fā)展方面作用微弱,提升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空間有限。最后,提質目標方面,與加工貿易企業(yè)擴大加工業(yè)務訂單的目標不同,大部分一般貿易企業(yè)為了提高其品牌認可度,以爭取到更大的市場占有率,會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競爭,并立足企業(yè)實際設定逐步提升產(chǎn)品質量的目標。
(五)企業(yè)所在地區(qū)市場化程度異質性
基于區(qū)域市場分割理論,在大國經(jīng)濟體中,不同地區(qū)的資源稟賦、產(chǎn)業(yè)結構、開放程度、制度環(huán)境等因素會顯著影響該地區(qū)的市場化水平,從而影響企業(yè)的經(jīng)營策略和績效。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qū),企業(yè)面對的是更加成熟和完善的市場機制、更加規(guī)范的法律環(huán)境和更加開放的經(jīng)濟政策,這會共同促進企業(yè)提升市場競爭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使得這些企業(yè)更有可能利用國際資源和市場機會來提升出口產(chǎn)品質量。考慮到OFDI對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影響可能會因市場化程度差異而存在異質性,根據(jù)王小魯?shù)龋?021)計算的各年各省份市場化指數(shù)中位數(shù),將樣本企業(yè)所處省份分為高市場化水平地區(qū)與低市場化水平地區(qū)進行異質性考察。設置市場化程度虛擬變量market,若該省份市場化程度高于中位數(shù)則取值為1,否則為0。
回歸結果參見表7第(5)列,交互項ofdi×market估計系數(shù)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相較于低市場化地區(qū),高市場化地區(qū)的企業(yè)更有可能通過OFDI實現(xiàn)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可能的原因是,區(qū)域市場化水平越高,越有益于培養(yǎng)成熟的要素市場,具備更優(yōu)質的營商環(huán)境,從而能夠更充分地發(fā)揮市場在要素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高市場化還能從一定程度上壓縮商業(yè)活動中的尋租空間,使得企業(yè)尋租成本增大,從而有利于企業(yè)將更多的要素資源用于自主研發(fā)創(chuàng)新和市場經(jīng)營活動,降低資源的錯配與扭曲,增大OFDI對企業(yè)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促進作用,這與毛其淋和趙柯雨(2021)的研究結論相呼應。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采用2005-2013年企業(yè)層面微觀數(shù)據(jù),系統(tǒng)分析了中國企業(yè)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結果發(fā)現(xiàn):第一,企業(yè)OFDI對于出口產(chǎn)品質量具有顯著的提升效應,這一發(fā)現(xiàn)通過了一系列穩(wěn)健性檢驗。第二,在全球價值鏈理論框架下,中間品進口效應、自主創(chuàng)新研發(fā)投入效應、逆向技術溢出效應是推動OFDI提升企業(yè)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重要渠道。第三,小規(guī)模企業(yè)、非國有企業(yè)、高管理效率企業(yè)、一般貿易企業(yè)和高市場化程度地區(qū)企業(yè)進行OFDI會表現(xiàn)出更大的出口產(chǎn)品質量提升效應。這表明對外投資對于出口貿易的影響在企業(yè)性質、管理狀況和空間地域等多維度層面存在差異。
在當前外部需求不振、貿易環(huán)境復雜多變的形勢下,以對外直接投資促進貿易質量升級,已成為中國企業(yè)提升國際競爭力,破除價值鏈“低端鎖定”的重要舉措。本研究的政策啟示包括:首先,實現(xiàn)高水平對外開放和加強貿易強國建設,不可忽視對外直接投資在其中的關鍵作用,政策層面,對外可更加積極地進行雙邊投資及多邊投資協(xié)定洽談,對內可制定政策激勵有條件、有意愿的企業(yè)參與或擴大海外投資。其次,從本文機制研究結論來看,在繼續(xù)加強國際技術交流合作,吸收前沿技術知識的同時,要更加注重自主研發(fā)投入和創(chuàng)新人才培育,持續(xù)提升價值鏈各環(huán)節(jié)上的附加值。同時,應繼續(xù)深化中間品貿易自由化改革,深度嵌入全球產(chǎn)業(yè)鏈,鼓勵企業(yè)進口高質量和多元化的中間品。最后,應差別化制定OFDI激勵政策,更多地挖掘大規(guī)模企業(yè)、國有企業(yè)和加工貿易企業(yè)通過OFDI提升出口產(chǎn)品質量的潛力,促進企業(yè)改進管理效率、優(yōu)化資源配置,并通過建設全國統(tǒng)一大市場等舉措進一步提升重點開放城市和區(qū)域的市場化水平。
參考文獻:
[1] 鄧悅、蔣琬儀,2022: 《工業(yè)機器人、管理能力與企業(yè)技術創(chuàng)新》,《中國軟科學》第11期。
[2] 黃遠浙、鐘昌標、葉勁松、胡大猛, 2021:《跨國投資與創(chuàng)新績效——基于對外投資廣度和深度視角的分析》,《經(jīng)濟研究》第1期。
[3] 蔣冠宏、蔣殿春, 2014:《中國企業(yè)對外直接投資的“出口效應”》,《經(jīng)濟研究》第5期。
[4] 劉啟仁、鐵瑛, 2020:《企業(yè)雇傭結構、中間投入與出口產(chǎn)品質量變動之謎》,《管理世界》第3期。
[5] 盧盛峰、董如玉、葉初升, 2021:《“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了中國高質量出口嗎——來自微觀企業(yè)的證據(jù)》,《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第3期。
[6] 呂越、陳帥、盛斌, 2018:《嵌入全球價值鏈會導致中國制造的“低端鎖定”嗎?》,《管理世界》第8期。
[7] 馬述忠、吳國杰, 2016:《中間品進口、貿易類型與企業(yè)出口產(chǎn)品質量——基于中國企業(yè)微觀數(shù)據(jù)的研究》,《數(shù)量經(jīng)濟技術經(jīng)濟研究》第11期。
[8] 毛其淋、許家云, 2016:《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如何影響了企業(yè)加成率:事實與機制》,《世界經(jīng)濟》第6期。
[9] 毛其淋、許家云, 2019:《貿易自由化與中國企業(yè)出口的國內附加值》,《世界經(jīng)濟》第1期。
[10] 毛其淋、趙柯雨, 2021:《重點產(chǎn)業(yè)政策如何影響了企業(yè)出口——來自中國制造業(yè)的微觀證據(jù)》,《財貿經(jīng)濟》第11期。
[11] 施炳展、曾祥菲, 2015:《中國企業(yè)進口產(chǎn)品質量測算與事實》,《世界經(jīng)濟》第3期。
[12] 宋躍剛、鄭磊, 2020:《中間品進口、自主創(chuàng)新與中國制造業(yè)企業(yè)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世界經(jīng)濟研究》第11期。
[13] 湯超、祝樹金、王梓瑄, 2023:《股權激勵、風險承擔與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宏觀質量研究》第4期。
[14] 王小魯、胡李鵬、樊綱, 2021:《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shù)報告(202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5] 王雅琦、張文魁、洪圣杰, 2018:《出口產(chǎn)品質量與中間品供給》,《管理世界》第8期。
[16] 王永進、施炳展, 2014:《上游壟斷與中國企業(yè)產(chǎn)品質量升級》,《經(jīng)濟研究》第4期。
[17] 徐國祥、張正, 2020:《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如何影響出口增加值——基于我國-東道國(地區(qū))產(chǎn)業(yè)結構差異的視角》,《統(tǒng)計研究》第10期。
[18] 許家云、毛其淋、胡鞍鋼, 2017:《中間品進口與企業(yè)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基于中國證據(jù)的研究》,《世界經(jīng)濟》第3期。
[19] 楊連星、劉曉光, 2016:《中國OFDI逆向技術溢出與出口技術復雜度提升》,《財貿經(jīng)濟》第6期。
[20] 楊連星、羅玉輝, 2017:《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全球價值鏈升級》,《數(shù)量經(jīng)濟技術經(jīng)濟研究》第6期。
[21] 楊汝岱、吳群鋒, 2019:《企業(yè)對外投資與出口產(chǎn)品多元化》,《經(jīng)濟學動態(tài)》第7期。
[22] 余靜文、彭紅楓、李濛西, 2021:《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產(chǎn)品質量升級:來自中國的經(jīng)驗證據(jù)》,《世界經(jīng)濟》第1期。
[23] 余淼杰、張睿, 2017:《人民幣升值對出口質量的提升效應:來自中國的微觀證據(jù)》,《管理世界》第5期。
[24] 張杰、翟福昕、周曉艷, 2015:《政府補貼、市場競爭與出口產(chǎn)品質量》,《數(shù)量經(jīng)濟技術經(jīng)濟研究》第4期。
[25] 張子堯、黃煒, 2023:《事件研究法的實現(xiàn)、問題和拓展》,《數(shù)量經(jīng)濟技術經(jīng)濟研究》第9期。
[26] Amiti,M.and Khandelwal,A.,2013,Import Competition and Quality Upgrading,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95(2):476\|490.
[27] Antras,P.and Chor,D.,2022,Global Value Chain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5:297\|376.
[28] Bas,M.and Strauss\|Kahn,V.,2015,Input\|trade Liberalization,Export Prices and Quality Upgrading,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95(2):250\|262.
[29] Bloom,N.,Manova,K.,Van Reenen,J.,Sun,S.T.and Yu,Z.,2018,Managing Trade: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the US,NBER Working papers.
[30] Brandt,L.,Van Biesebroeck,J.and Zhang,Y.,2012,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97(2):339\|351.
[31] Crinò,R.and Ogliari,L.,2017,F(xiàn)inancial Imperfections,Product Quality,and 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4:63\|84.
[32] Desai,M.A.,F(xiàn)oley,C.F.and Hines Jr,J.R.,2009,Domestic Effects of the Foreign Activities of US Multinational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1(1):181\|203.
[33] Eisfeldt,A.L.and Papanikolaou,D.,2013,Organization Capital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Expected Returns,The Journal of Finance,68(4):1365\|1406.
[34] Fan,H.,Li,Y.A.and Yeaple,S.R.,2015,Trade Liberalization,Quality,and Export Pric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97(5):1033\|1051.
[35] Fan,H.,Li,Y.A.and Yeaple,S.R.,2018,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10:28\|49.
[36] Goldberg,P.K.,Khandelwal,A.K.,Pavcnik,N.and Topalova,P.,2010,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Evidence from India,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5(4):1727\|1767.
[37] Halpern,L.,Koren,M.and Szeidl,A.,2015,Imported Inputs and Productiv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5(12):3660\|3703.
[38] Khandelwal,A.K.,Schott,P.K.and Wei,S.J.,2013,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mbedded Institutional Reform: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er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3(6):2169\|2195.
[39] Li,L.,Liu,X.,Yuan,D.and Yu,M.,2017,Does Outward FDI Generate Higher Productivity for Emerging Economy MNEs?-Micro\|level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6(5):839\|854.
[40] Lichtenberg,F(xiàn).R.and De La Potterie,B.V.P.,1998,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A Com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2(8):1483\|1491.
[41] Melitz,M.J.,2003,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Econometrica,71(6):1695\|1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