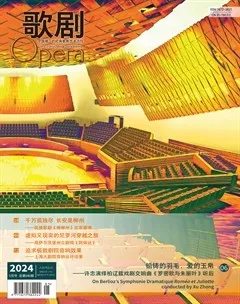喜歌劇之爭
王雅寧
喜歌劇之爭(Querelle des Bouffons)是18世紀中葉發生在法國巴黎的一場文化論戰。這場文化論戰的歷史背景可以追溯到17世紀末歐洲文化和社會環境之中。17世紀末,隨著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絕對王權制度的建立,法國宮廷文化的發展以及思想文化的昌明已經崛起于歐洲。代表王室威嚴的絕對君主制宮廷文化與啟蒙運動對于自然、理想的肯定及強調,使法國成為歐洲文化最為活躍的地區。這一時期的法國作為歐洲的文化中心之一,其歌劇依舊主要是以呂利(Jean-Baptiste Lully,1632—1687)和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1683—1764)為代表的抒情悲劇為主導。這些歌劇作品通常具有復雜的結構,強調和聲與管弦樂的配合,注重詩歌和舞蹈的融合,反映了法國宮廷文化的高雅與莊重。
到了18世紀中葉,隨著商業和文化交流的增加,意大利歌劇尤其是意大利喜歌劇(Opera buffa)開始在歐洲各地流行起來。與法國歌劇的莊嚴、正統風格相比,意大利喜歌劇更加輕松、幽默,情節常圍繞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愛情故事展開,音樂旋律流暢,易于大眾接受,強調歌唱家的表演和即興創作能力。這種音樂風格的歌劇在當時的歐洲引起了巨大反響。
交相輝映的雙重文化發展與非本土文化的交互影響,使法國成為一場歌劇爭端的新戰場。這場文化論戰爭論的核心是圍繞意大利喜歌劇與法國傳統歌劇之間對比的優劣之爭,但事實上爭論的實質是維護舊的宮廷貴族的美學觀點,還是提倡新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美學觀點之戰。①喜歌劇之爭不僅涉及音樂風格和審美取向的差異,也反映了當時法國社會中的文化、政治和社會問題。
一、意大利喜歌劇的起源
意大利喜歌劇起源于幕間劇。早在17世紀,幕間劇在意大利歌劇中已經非常流行。到了18世紀隨著意大利正歌劇逐步褪去了喜劇元素之后,喜歌劇體裁便發展起來。由于正歌劇中喜劇元素的缺失,為了娛樂觀眾,減輕正歌劇的嚴肅氛圍并在歌劇演出中提供輕松的間歇,這些短小的幕間喜劇表演受到了人們的喜愛。幕間劇的音樂與劇情大多與正歌劇沒有直接關系,且這樣的創作通常出自另一位作曲家之手。在這種情況下,幕間劇很快與它們的“母體”正歌劇相分離,開始獨立上演,或者融入其他的正歌劇演出,②并逐漸成為意大利喜歌劇的原型。
1733年,意大利作曲家喬瓦尼·巴蒂斯塔·佩爾戈萊西(Giovanni Battista Pergolesi,1710—1736)的歌劇《女仆作夫人》(La serva padrona,1733)于那波利的成功上演標志著意大利喜歌劇的誕生。這部作品是正歌劇《高傲的囚徒》(Il prigionier superbo)的幕間劇,在1733年的首演中大放異彩,贏得了觀眾的熱烈喜愛。

《女仆作夫人》全劇共兩幕,僅有三個角色。劇情圍繞女仆塞皮娜(Serpina)與主人烏貝爾托(Uberto)之間的互動展開。塞皮娜渴望成為烏貝爾托的夫人,因此巧妙地設下圈套,聲稱自己即將嫁人并需要辭職。烏貝爾托在內心經歷了長時間的斗爭后,最終發現了塞皮娜的精明能干,決定娶她為妻。佩爾戈萊西在創作《女仆作夫人》時,充分運用了清宣敘調(recitaivo secco)、詠嘆調和重唱等多種音樂形式。他通過音樂旋律的活潑與主調和聲的特點,展現了女仆塞皮娜的機智與主人的內心斗爭
《女仆作夫人》的出現,順應了啟蒙主義運動要求藝術“回歸自然”的歷史背景,為意大利歌劇藝術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動了歌劇藝術的多元化發展。同時,它的出現也引發了歐洲范圍內的“喜歌劇之爭”。
二、法國喜歌劇的發展

在勒薩熱和多爾內瓦爾的《集市劇場與喜歌劇院》(1712)的序言中,可見到關于法國喜歌劇的定義:“這些作品的特點是唱流行時事歌曲,一種法國人感到獨特、外國人尊崇、人人喜愛的詩歌,是表演俏皮話、防止荒唐、糾正道德的最恰當的手段。”③通過以上表述可以看出,法國喜歌劇是一種有著靈巧及情趣的喜劇特點、獨特的法國民族音樂戲劇形式并且具有音樂教化意義的歌劇體裁。
從歷史文獻的記載中發現,法國喜歌劇從簡單的娛樂形式發展成為復雜多樣的戲劇藝術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紀。當時,在法國諾曼底地區的維爾山谷有一種幽默、詼諧情趣的民謠合唱形式,到了16世紀,這種民謠被藝人們填上諷刺歌詞,演出針砭時事的寓意劇并稱為“滑稽劇”(Vaudeville)。隨后到了18世紀初,這種“滑稽劇”的民謠便成為早期法國喜歌劇的常用曲調,并以填詞創作為基本手法。④1752年,法國喜歌劇院建立,1762年與意大利喜劇院合并后,上演的劇目中,音樂除舊有的“滑稽劇”外,采用了新創作的意大利與法國混合風格的曲調,稱作小詠嘆調。讓-克勞德·吉里耶是法國喜歌劇的創始人,他早年供職于法國喜歌劇院,創作了很多的廟會喜歌劇。1742年,盧梭的歌劇《鄉村卜者》(Le Devin du Village,1752)的成功上演標志著法國喜歌劇的確立。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法國大革命和隨后的拿破侖時代為法國喜歌劇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法國喜歌劇迎來了黃金時期。這一時期的作品大多反映了時代的社會政治變革。隨后到了19世紀中葉,受到浪漫主義的影響,法國喜歌劇開始轉型與發展,吸收更多情感表達和個人主義的元素,完全廢棄了“滑稽劇”一類滑稽歌舞的曲調,音樂均為新創作,更重視樂隊、二重唱及各類重唱曲。歌劇中的神話題材變為市民們熟悉的現實生活,甚至涉獵到大革命之前令人們焦急不安的社會問題。雖然說白與音樂并存,但同時也融合了更多的浪漫主義音樂特色。進入19世紀末,法國喜歌劇開始與其他戲劇形式融合,產生了輕歌劇(opérette)、抒情歌劇(Lyric Opera)等多樣的音樂風格。
三、“喜歌劇之爭”
1752年2月,在德國人弗里德里希·格瑞姆男爵撰寫的名為《關于奧姆法萊的公開信》(Letter sur Omphale)的小冊子中,通過安德烈·卡阿迪·德圖什(Andre Cardinal Destouches,1672—1749)的歌劇《奧姆法萊》(Omphale,1701)來抨擊法國歌劇所特有的種種原則并引發爭論,在小冊子中,他頗有禮貌的批評法國音樂、法國的歌唱理念以及法國式宣敘調,將意大利歌劇風格樣式視為典范。⑤其觀點得到了以盧梭為代表的“百科全書派”強有力的支持,隨后意大利喜歌劇《女仆作夫人》在法國的上演,直接加速了“喜歌劇之爭”的全面爆發。
然而,《女仆作夫人》作為“喜歌劇之爭”的導火索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早在1729年,一個名為“喜劇演員”(Les Bouffons)的劇團來到巴黎演出,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但是很快被人們所忘卻。1746年,該劇團又來到巴黎,演出了佩爾戈萊西的歌劇《女仆作夫人》,因為時處啟蒙運動初期,理性時代的要求往往自相矛盾,“回到自然”這一“新的”信條在音樂上尚未正式公開受到贊揚,⑥所以這部歌劇在當時并未造成特殊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啟蒙運動迅速發展,1752年8月,“喜劇演員”劇團第三次訪問巴黎,再度上演了歌劇《女仆作夫人》,這次它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引發了巴黎觀眾的極大興趣和熱烈討論。之后,自1752年11月起,意大利喜歌劇與法國抒情悲劇的論戰爆發,并持續了近18個月,直至國王下令趕走意大利喜歌劇團,爭論尚未真正平息下來。逐漸,這次爭論不再僅限于音樂和戲劇領域,逐步開始涉及藝術的功能、美學的標準以及法國與意大利文化的比較等更廣泛的文化、社會和哲學問題。


爭論的兩方分別是以王后為首支持意大利喜歌劇的“百科全書派”和以路易十五為首的支持法國抒情悲劇的“保守派”。“百科全書派”認為意大利歌劇,尤其是意大利喜歌劇的風格更加自然、生動和富有表現力,而以皇家音樂學院為首的“保守派”則堅持認為法國歌劇代表著法國的傳統和高雅,其嚴謹的結構和莊重的風格不應被輕易拋棄。這場爭論吸引了許多知名人士的參與,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伏爾泰(Fran?ois-Marie Arouet,1694—1778)等哲學家、作家也都加入了論戰。盧梭作為“百科全書派”的支持者,在《關于法國音樂的書信》(Lettre sur la musique fran?aise,1753)和《皇家音樂學院樂師致樂隊同事的信》(Lettre dun symphonist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 musique, à ses camarades dans lorchestre,1753)等小冊子中批評法國音樂缺乏旋律之美,稱“法國人沒有也永遠不會有音樂”,⑦并在他為《百科全書》撰寫的歌劇條目中也強烈倡導意大利音樂的優越性。而伏爾泰等“保守派”則為法國歌劇辯護,強調法國傳統歌劇在表達和諧與秩序方面的價值。
盧梭的音樂思想與他在作品中闡述的哲學思想是一致的,從《論科學與藝術》(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1750)到《愛彌兒》(émile,1762)再到《社會契約論》(Contrat Social,1762),盧梭認為,在自然狀態下,人是自由和平等的,并提出了自然狀態和社會契約的概念。如同其哲學思想,他認為“音樂應該接近自然”,意大利喜歌劇的魅力便在于其簡潔、自然的風格,這種風格符合人性和自然美的原則。在音樂與語言的關系上,他認為音樂是對語言音調的模仿,強調民族語言對音樂的影響和制約。通過音樂可以更好地表達語言蘊含的情感,情感的表達不是通過復雜的和聲和對位法來展現技巧。他認為在法國傳統歌劇中,呂利吟誦式的對白打斷了戲劇節奏、拉莫規整的和聲與精致的伴奏都是不自然的、矯揉造作的裝飾且不理智。


1752年,盧梭將其音樂思想付諸實踐,創作了歌劇《鄉村卜者》。這部獨幕歌劇講述了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一個鄉村女孩柯萊特(Colette)發現她的戀人科林(Colin)對她不忠,她決定求助于一個占卜者,希望重新贏回科林的愛。占卜者建議柯萊特假裝對其他求婚者感興趣,以激發科林的嫉妒心。計謀成功,科林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并向柯萊特求婚。最終,兩人重歸于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根據《懺悔錄》(Les confessions)第8卷的記載,《鄉村卜者》在楓丹白露首演時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753年4月巴黎的首演時,宣敘調(口語化的對白)被重新引入并且獲得重視。對白連接了戲劇動作,維持了音樂與戲劇的統一,在加入了序曲和伴奏后更受歡迎,并且成為18世紀最經常上演的歌劇之一。盧梭為《鄉村卜者》中口語化的對白風格感到自豪,他聲稱這種風格更接近語言的自然節奏。劇中的宣敘調與語言(詩歌)聯系最為緊密,宣敘調中主題旋律和歌詞語言的聲調、節律相互融合為“念白”,器樂伴奏、和聲等都要服從于語言化的旋律。歌劇中的音樂簡潔明快,旋律優美,符合盧梭對音樂的審美傾向。他試圖通過清晰的旋律線條和富有表現力的和聲表達了角色的情感,使音樂與劇情緊密結合,表達音樂服務于戲劇的音樂思想。《鄉村卜者》以它內容淳樸、情節生動、感情真摯、形式活潑成為當時唯一能夠與意大利《女仆作夫人》相媲美的法國歌劇。盧梭通過這部作品展示了音樂應該簡單、自然、貼近人心的音樂理念,同時對后世音樂戲劇的發展產生了影響。他的這種音樂形式并很快被后人模仿,在18世紀70年代末的德國,這種音樂形式被稱為“情節劇”,并且在德國和法國找到了生存發展的方式,從梅于爾(Etienne Mehul,1763—1817)的《阿里奧丹》(Ariodant,1799)到馬斯內(Jules Massenet,1842—1912)的《曼儂》(Manon,1884)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盧梭音樂思想的影子。


從盧梭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盧梭在18世紀中葉對音樂戲劇美學的重要思考,不管是在音樂或者文學史上都具有非凡的意義。但是,著名的音樂學家保羅·亨利·朗(Paul Henry Lang,1901—1991)對盧梭的“回到自然”準則,提出了質疑。保羅·亨利·朗在《西方文明中的音樂》中指出:“若要摒棄這些理論(回到自然),并審視盧梭音樂的本身,我們必須承認,其音樂同其宣言毫無共同之處,可歸之于他的,也只有一種新式場景,即《鄉村卜者》故事的農村背景。”⑧劇中的羊群、田舍代替了抒情悲劇中的英雄與神話,似乎唯有這一點是符合“自然”法則,且盧梭音樂調和的自然理論過于理想化和絕對化,忽視了音樂藝術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這些爭議反映了人們對音樂功能和價值的不同理解和追求,也推動了音樂理論和實踐的不斷發展。
盧梭的音樂思想對后世的音樂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音樂戲劇形式法則上,格魯克是盧梭音樂美學的第一個受益人。盧梭反對當時流行的帶有復雜裝飾性的音樂形式,認為音樂應該回歸到表達情感的本質。他的自然主義音樂觀對莫扎特、海頓等人的音樂創作產生了影響。莫扎特根據盧梭的歌劇《鄉村卜者》,改編創作了歌劇《巴蒂斯蒂安和巴蒂斯蒂安娜》(Bastien und Bastienne,1768)。在音樂與語言的探討中,盧梭認為音樂是語言(詩歌)表達情感的工具,為后世的歌劇和聲樂作品的創作起到了啟示的作用。同時在《愛彌兒》等著作中,盧梭提出了關于音樂教育的思想,強調音樂教育的重要性,對后來的音樂教育理論和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思想預示了古典音樂的發展方向,對浪漫主義音樂的興起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四、意大利喜歌劇與法國喜歌劇的比較
法國喜歌劇與意大利喜歌劇之間的區別主要體現在音樂風格、戲劇結構、主題內容以及語言和文化背景上。雖然這兩種歌劇形式都強調幽默和輕松的劇情,但它們各自反映了不同的藝術傳統和審美偏好。


在音樂風格方面,意大利喜歌劇的音樂風格通常更加輕松、流暢,重視旋律的美感和歌唱家的演唱技巧。它強調簡潔明快的旋律線條和富有表現力的歌唱,經常采用大段的宣敘調且多為無伴奏的干念式宣敘調和重唱等音樂形式,節奏靈動且一般在終場以重唱、小合唱的形式將戲劇推向高潮。而法國喜歌劇在音樂上則更加注重和聲的豐富性和管弦樂的作用,同時重視樂隊和重唱的價值。雖然較少運用意大利式的宣敘調,但音樂結構和戲劇性表達上更為復雜和細膩。
在戲劇結構方面,意大利喜歌劇通常為分曲結構(如詠嘆調、二重唱、合唱等)組成,這些分曲之間通過簡短的對白連接,劇情發展依賴于分曲的情感表達和戲劇沖突的展現。而法國喜歌劇的特點是注重采用口語化對白的宣敘調,將唱段和對白結合起來,對白在劇中占據重要位置,用以推進劇情和描繪角色,不打破戲劇發展的結構,使得法國喜歌劇在敘事上更為連貫和多樣。
在戲劇主題方面,意大利喜歌劇主題內容通常圍繞日常生活、愛情和社會沖突,以普通人物和生活為中心,強調人性的普遍性和喜劇效果。而法國喜歌劇在敘事題材上摒棄了宏大的敘事結構,轉向對小市民日常生活瑣事的關注和描繪,同時法國喜歌劇也會探討一些道德、社會乃至政治問題,反映了法國文化中對理性和啟蒙思想的重視。
在語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意大利喜歌劇與法國喜歌劇最顯而易見的區別是語言的不同,分別使用意大利語和法語。語言不僅影響了歌詞的韻律和旋律的構造,也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審美傾向。意大利喜歌劇的流行反映了意大利音樂在歐洲的廣泛影響力,而法國喜歌劇則體現了法國對自身文化傳統和語言的自豪感。雖然兩者都屬于18世紀歐洲流行的歌劇形式,但它們各自保持了獨特的藝術特色和文化表達,也反映了不同國家的音樂傳統和社會風貌。

“喜歌劇之爭”是音樂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更是一場關于音樂和戲劇風格的爭論,它不僅改變了當時的音樂風格和審美觀念,也更深層次地反映了18世紀歐洲文化中的啟蒙思想、自然主義和民族文化之間的辯論。這場爭論促進了法國音樂風格的演變,鼓勵了音樂的簡化和自然表達,對德國作曲家格魯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的歌劇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也為后來的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音樂風格奠定了基礎。同時,這場爭論也反映了公眾音樂品味的轉變,格奧爾格·克內普勒(Georg Knepler,1906—2003)在《19世紀音樂史》中詳細記述道,在18世紀下半葉人們已經不滿足于只看到頂著神話英雄耀眼光環的歌唱家們在歌劇舞臺上“長著一個嗓門”的表演,而是要求“在歌劇舞臺上看到人看到現實的、表演真實生活的人”。隨著資產階級的崛起和公眾音樂會的增加,更廣泛的聽眾開始對音樂表達和風格提出要求。“喜歌劇之爭”促使音樂家們更多地關注聽眾的喜好和期望,逐漸擺脫了貴族宮廷音樂的束縛。
面對這場爭論,我們也應該持有一種辯證的態度客觀地評價這段歷史。這場爭論無疑是一場充滿進步意義的探討,但是以盧梭為首的“百科全書派”的思想有其局限性。我們肯定盧梭音樂思想在歷史上是有進步意義,同時也應該認識到歷史的局限性,學會審視藝術與社會的關系,繼而探索實踐反映時代精神的藝術形式。

(作者單位:上海音樂學院)
① 何乾三.盧梭的音樂美學思想[J].樂府新聲(沈陽音樂學院學報),1984,04.
② 菲利普·唐斯.古典音樂 海頓、莫扎特與貝多芬的時代[M].孫國忠,沈旋,伍維曦,等譯.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9:105-106.
③ 菲利普·唐斯.古典音樂 海頓、莫扎特與貝多芬的時代[M].孫國忠,沈旋,伍維曦,等譯.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9:551.
④ 錢苑,林華.歌劇概論[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3:32.
⑤ 菲利普·唐斯.古典音樂 海頓、莫扎特與貝多芬的時代[M].孫國忠、沈旋、伍維曦、孫紅杰,譯.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9:119.
⑥ 保羅·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樂[M].顧連理,張洪島,楊燕迪,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550.
⑦ 沈旋.西方歌劇詞典[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20:805-806..
⑧ 保羅·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樂[M].顧連理,張洪島,楊燕迪,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