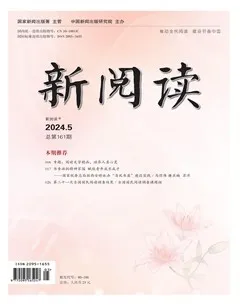長風鼓浪 掣鯨碧海
韓敬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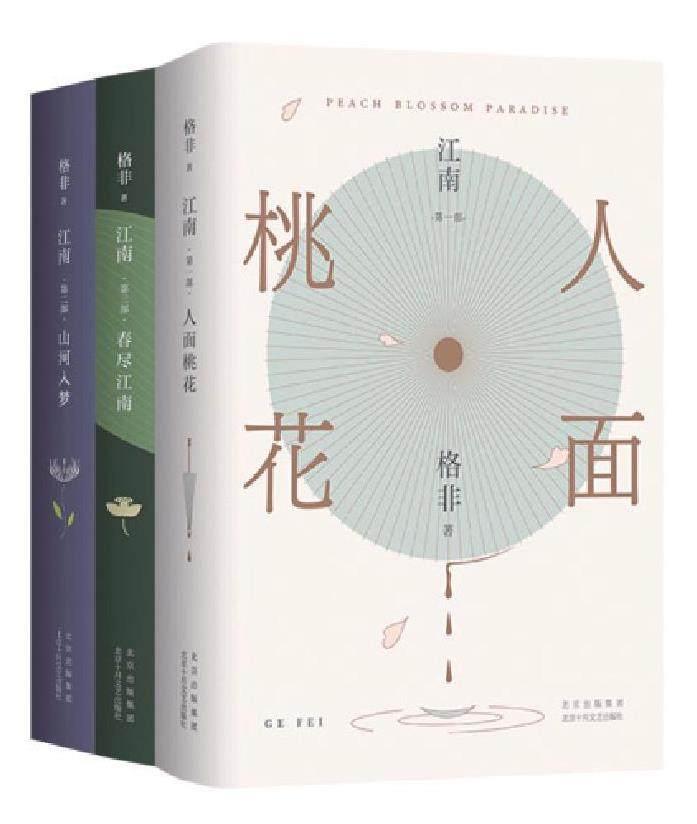
新時代文學與新時代洪波奔涌的生動實踐以及人民與時代同行共進的生活歷程相伴而生,呈現出“人人握靈蛇之珠,家家抱荊山之玉”的異彩紛呈景象。十年間,從兩屆茅盾文學獎、三屆魯迅文學獎的獲獎作品看,先后涌現了《繁花》《江南三部曲》《人世間》《北上》《主角》,以及《隱身衣》《美麗的日子》《如果大雪封門》《世間已無陳金芳》《李海叔叔》《山河袈裟》《荒原上》《地上的天空》等優秀作品。
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衡量一個時代的文藝成就最終要看作品。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最根本的是要創作生產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沒有優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熱鬧、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鳴的。”
新時代文學名家輩出,佳作不斷,但我們也必須看到,還應該創作生產更多與這個偉大時代的宏偉氣象相匹配、滿足人民群眾更高審美需求的高質量文學精品,筆者從三個面向,談一談對新時代文學創作與出版中幾個關鍵問題的理解。
●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新時代文學取之不盡的“寶山”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以及突出的和平性,認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講話對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撥云見日、導航定向的重大指導意義,對于文學界賡續中華優秀傳統文脈,從自己博大深厚的文化寶庫中尋找創作的靈感源泉、突破的著力點,指明了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傳承發展的講話正當其時。這些年,我們也看到了年輕一代作家轉向傳統文化的積極主動姿態,如作家葛亮先后創作了《北鳶》《燕食記》等與家國情懷、民族文化密切相關的長篇小說;作家徐則臣的《北上》以京杭大運河為書寫對象,借一條大河的新生寫民族的“舊邦新命”,“一條河活起來,一段歷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相信像葛亮、徐則臣這樣自覺轉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作家會越來越多,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山”也一定會讓他們滿載而歸。
● 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他專門講到了柳青的故事。為了深入農民生活,柳青1952年曾經任陜西長安縣縣委副書記,后來辭去了縣委副書記職務,定居在皇甫村,蹲點了14年,集中精力創作《創業史》。作為柳青創作上的學生,路遙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方面做得也毫不遜色,他的作品《早晨從中午開始》一書堪稱現實主義創作最好的教科書,值得每一位寫作者潛心細讀。路遙以驚人的毅力讀完了1975—1985年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和省報,他“提著一個裝滿書籍資料的大箱子開始在生活中奔波”,他說“在占有具體生活方面,我是十分貪婪的。我知道占有的生活越充分,表現生活就越自信,自由度也就會越大”。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寫出好作品,這已經成為當代作家的共識。的確有相當一部分作家是真正撮鹽入水化入了生活,由此寫出了生活復雜的褶皺與紋理,寫出了復雜的人物內心及人物與歷史的細密糾葛。作家喬葉書寫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的長篇小說《寶水》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這部作品她構思了七八年,大的思路變動了三四次,易稿足有十來回。她的創作談《“跑村”與“泡村”》寫到她艱苦的創作過程,“跑村”是面上的廣度,“泡村”是點上的深度。筆者曾在與喬葉通信中說:“我能想象你的寫作狀態,是與村莊人物與事件貼心貼肺、聲氣相通之后的熟稔與從容。我見過當代寫作太多的浮皮潦草、浮光掠影,看到你這樣的帶著自己情感濃烈投射的細致精確的描寫自是驚喜。”希望在未來,我還能收獲更多這樣的驚喜。
● 編輯力是提升文學原創力的“光輝寶藏”
“光輝寶藏”一詞出自加拿大作家艾麗絲·門羅的小說《機緣》,原文是bright treasure,李文俊先生譯為“光輝寶藏”。筆者認為,“光輝寶藏”就是我們每個人獨有的不可被復制、不可被取代的賴以安身立命的東西。一個文學編輯的“光輝寶藏”應該包括對時代的領悟力、穿透力,對生活的觀察力,與文本近身肉搏的細讀研判能力,與作者以文會友、同行共進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終身踐行、須臾都不放松的學習能力。作為文學編輯與出版人,作為藝術生產工作者,我們需要做的,是充滿耐心,充滿樂觀的盼望,展開雙臂,迎接一部又一部與這個時代互相照耀,與這些重大事件互相匹配的偉大作品。
黨的十八大以來,廣大文藝工作者與時代同行共進,與人民同呼共吸,推出了一部部“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這一部部精品力作固然是作家嘔心瀝血的創作成果,但其中也凝結著編輯無私而專業的奉獻。徐則臣的《北上》的創意構思則來自他與編輯在一家咖啡館的聊天,小說的主旨,借一條河流的新生寫出我們民族的“舊邦新命”,也是大家在討論中達成的共識。在寫作過程中,編輯與他一起研讀龔自珍的《己亥雜詩》,后期又專門找了中國近代史與運河史的專家把關書中相關的專業內容,并陪伴作家一起到通州運河做田野調查。一次編輯看到日本畫家安野光雅的《中國的運河》在國內出版,第一時間就找來寄給徐則臣。小說開篇的題詞,原來用的是白居易的詩:“事往唯余水,人非但見山。”編輯認為這句詩偏于文弱,提振不起全書,建議他換成了《己亥雜詩》第八十三首:“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既契合了運河盛期漕運繁忙的景象,也與書中主人公憂國憂民的心境吻合,使全書開篇氣象為之一新,體現了很高的編輯含量。從這些力作誕生的過程,可以清晰地看到編輯的用心與編輯力的作用。
2022年7月31日在湖南益陽,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啟動儀式上的致辭中說道:“我很懷念著名編輯章仲鍔先生和剛剛去世的崔道怡先生。他們對編輯事業有一種近乎狂熱的癡迷,對文學有持久不衰的激情。我的長篇小說《笨花》出版不久,就接到章仲鍔長達6頁的來信。他在信中詳述對這部小說的看法和評價,接著他認真地指出了一些錯字,并就某一節中的一個詞和我作了商榷。前些天,崔道怡先生去世,許多作家都感到十分悲痛……。我看到劉心武寫了一篇短文,回憶在寫作《班主任》之前,他曾投寄過一個短篇給《人民文學》。小說不久被退稿,但退回的稿件里夾著一封親筆信,大意是此篇不用,但顯示出你有寫作能力,希望繼續投稿,落款是崔道怡。這對于當時的劉心武是極大的鼓舞,某種意義上間接促成了《班主任》的問世。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一路走來的一大批中國作家,都得到過如章仲鍔、崔道怡這樣優秀的編輯老師給予的無私扶持和熱誠幫助。當我們回顧新時期文學成就的時候,恐怕不能否認,老一輩編輯家們精益求精的精神起了重要作用。我們現在是否應該思考一下,怎么能夠從體制機制上培養和鼓勵像章仲鍔、崔道怡這樣的編輯家?”著名作家張潔以《無字》獲得第二屆老舍文學獎時,動情地說:《無字》有兩個母親,除了她自己,還有責任編輯隋麗君老師。
當代中國要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堅持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相統一,加強現實題材創作,不斷推出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更加需要新一代的編輯在前一代編輯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以高超的編輯力推動當代文學從“高原”向“高峰”邁進。
作者系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