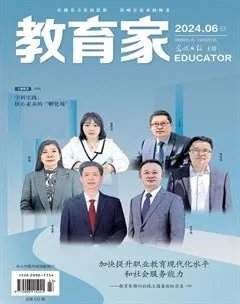教研員何以成為教師發展的促進者?
沈偉

教研制度隨著我國學校教育的發展,演變成我國“一枝獨秀”的教育制度,在落實課程改革理念、促進區域教學質量提升、帶動學科教師群體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由此,教研員也被賦予了諸多的稱號,如“教師的教師”“課改的先行者”“信息技術領導者”等,這些稱號一方面體現了教研員的最初來源和主要功能,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教研員隨著教育改革與發展所具備的新職能。然而時至今日,無論學界還是民間都有不少質疑教研員的聲音。學界在教研員“半官半民”的身份上討論已久,認為行政導向的職能不利于教研員專業影響力的發揮。民間則對教研員的工作方式、工作效果褒貶不一,近期有關教研員涉嫌職務違法被查的新聞爆出后,又一次引發了大眾對教研員職能的關注和討論。我們既不能因少數人的做法對教研員群體做出有失公允的判斷,也不能忽視長期以來教研制度中的痛點問題。
職能泛化導致教研員專業影響力下降
從歷史發展的視角審之,教研制度、教研員的確為大國辦教育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機制。20世紀50年代學校一級的教研組(即教學研究組)的成立或教導研究會議旨在研究改進教學工作,交流、總結經驗。1955年教育部機關刊物《人民教育》發布《各省市教育廳局必須加強教學研究工作》的評論,要求獨立設置教學研究室,強調“教學研究工作必須依靠廣大教師,尤其是比較有經驗的教師,將他們團結在研究室的周圍,共同研究教學中的主要問題,總結教學經驗”。在各地教育行政部門規劃下,從學校中的教研組到教育行政機構內部的教研室,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統,教育行政機構內部的教研室人員被稱作教研員,其來源于各學科的優秀教師,工作對象就是與其負責學科對應的學校教研組。根據20世紀50年代的制度設計,當時的教研工作旨在發揮教師的集體作用,在研究中提高教學質量。即便這一研究工作被納入教育行政系統,也是希望有經驗的教師可以研究教學問題,總結教學經驗。而被選進教研室的優秀教師,在對接學校教研組的工作中,在為教育行政部門提供專業意見時,其教學指導的職能也被合法化。此后,教育部、國家教委發布的若干政策文件均進一步肯定了教研員的教學研究、指導職能。需注意的是,教研員的管理職能在1990年頒布的《關于改進和加強教學研究室工作的若干意見》中得以確認。該意見將教研組織的屬性界定為地方教育行政部門設置的承擔中小學教學研究和學科教學業務管理的事業機構,教研員應承擔“為教育行政部門決策提供依據”“組織教材”“教學檢查和質量評估”“研究教育”“組織教學研究活動”“總結、推廣教學經驗”“指導教師”等職能。由此教研員的職能進一步泛化,其行政權威伴隨著“教學檢查和質量評估”“組織教學研究活動”日益提高,教學研究泛化為教育研究。由于教研員主導了與教師晉升有關的活動與評價,教研員“管理者”以及“利益相關者”的角色更為凸顯。加上職能的擴充,加速了教研員的“研”脫離了“教”,教研員開始對教育政策進行研究和解讀,忙于各種教育相關的事務,故一段時間里,教研員的“下水課”成為各地恢復、提升教研員教學指導能力的折中之舉。從本源上而言,教研員來源于優秀教師,以教學研究、指導為本業,其應一直在課堂的源頭活水中。“下水”成為一種巧妙的隱喻,反映了教研員職能的異化。
教研機構的歸屬和名稱的更迭也間接體現了教研員職能的分化與泛化,例如,有的地方在進行教育行政改革時,將教研機構遷出了政府大院,與其他事業機構進行了整合,有的地方將教研室獨立設置,有的地方則將教研室設于教育科學研究院(所)、教育學院之下,一些地方教研室與考試部門進行整合,一些地方的教研室則與電教館進行合并。教研員職能的分化與泛化雖然模糊了其教學領導者的專業形象,卻契合了國家教育管理對效能的訴求。在行政權力的加持下,在機構制度化的過程中,教研員的影響力得以進一步提升,但在這股影響力中,專業的教學領導力如同影子一般附著在管理能力之中。
去行政化是重塑教研員專業影響力的前提
去行政化成為教研員職能發展的一個重要轉向。2001年,教育部頒布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明確要求教研員回歸專業角色,指出“各級中小學教研機構要把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作為中心工作,充分發揮教學研究、指導和服務等作用”。此后,一系列的政策均強調了教研員在教育系統中的專業支撐作用,如推進中小學評價與考試改革制度,實現教師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深化教育教學改革等。“重專業影響力,去行政化”的趨勢尤以2019年教育部發布的《關于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基礎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見》為重,該文件鼓勵有條件的地方獨立設置教研機構,首次界定了教研員的準入條件、提出了教研員遴選配備方法及其發展方向,為教研員的專業導向提供了政策依據。然而現實中,教研員的角色定位、職能發揮還與機構特征、人員結構等有著重要的關聯。那些尚不具備獨立設置教研機構的地方在教研員的專業導向上必然還有較長的路要走。
另外,雖然當下的教研員遴選標準注重教研能力,提出教研員“具有扎實的教育理論功底,教學經驗豐富,原則上應有6年以上教學工作經歷,具有中級以上教師專業技術職稱,在教育教學中取得優異成績”,但教研隊伍中的人員更替、新標準的落實也需時日。事實上,根據我們2017年的“全國基礎教育教研工作現狀調研”數據,有學校(幼兒園)任教和管理經歷的教研員占教研隊伍人數的75.3%。按全國各級機構專職教研人員12萬計,約有10萬的教研員來源于中小學、幼兒園的教師和管理者,另有2萬的人員與當時設置教研員的初衷、期待其發揮的職能并不匹配。
去行政化不僅僅是明確教研機構的獨立性,還要對教研機構的工作方式去科層化,在教研員的任用上堅持專業性。如此才能讓教研員重返專業權威。
教研隊伍建設需關注教研員的職業發展
對教研員的批評幾乎伴隨著教育改革的全過程。20世紀90年代素質教育被提出時,教研員一度成為“應試教育”的代言人,甚至有文將其稱作“考研員”。隨著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運動的興起與發展,教研員在課程實施過程中表現出指導不足,繼而引發了課程專家的批評。然而回到教研員與教師的互動層面,我們過去的質性研究發現,教師對教研員的引領大多表現出認可,且認為教研員給予的指導有別于學校的帶教師父。結合我們對教研員的訪談則發現,教研員在職業發展中經歷了適應、發展與疲倦的不同階段。一些教研員在對職業前景進行展望時,表現出迷茫,或在工作中產生“為他人作嫁衣裳”的感受。究其原因,我們當下的教研制度設計缺乏對教研員職業發展的系統思考。一些資歷較深的教研員在回顧自己的從教經歷時,提到“以往做教師做到頭就是教研員,那時候覺得教研員很厲害,也覺得這份工作很有意義,但是做了教研員之后,怎么發展呢?”“教研員不能想自己,只能發展教師”。當把優秀教師從學校里選拔出來,放進教研室后,即便教研員享有教師編,但教研員的身份建構不再指向教師,其工作的性質也不同于學校教師,與學校教師發展的道路也不盡相同。當前并沒有針對教研員發展的軌道設計,卻在教育實踐方面要求教研員做出先行先試。尤其在鄉鎮一級,教研員數量不多任務多,所擁有的專業發展機會也不多,這導致一部分教研員安于現狀。雖然現有政策進一步完善了教研員定期到中小學任教的制度,即“教研員在崗工作滿5年后,原則上要到中小學校從事1學年以上教育教學工作”,但在保持教研員職業動力、促進教研員專業發展方面,還需從教學領導者的立場系統設計相關的制度。如此,教研員才能真正成為教師發展的促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