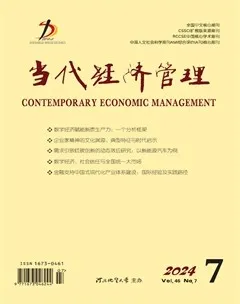數字化賦能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機理、挑戰和路徑
許唯聰
[摘?要]數字技術在傳統農產品貿易環節的深度應用引發了數字化發展浪潮,形成了傳統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能。當前,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面臨地區布局失衡、進出口市場結構單一、貿易品多樣性程度低等問題,導致國家間農產品貿易合作“大而不強”。而近年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互聯網普及率、信息和通信技術(ICT)使用率與ICT服務出口水平逐年提升,已經具有一定的數字經濟發展基礎。通過推動建立更高水平農產品貿易格局、促進農產品貿易供需雙側匹配和優化、降低傳統農產品貿易成本、催生農產品貿易新模式新業態,數字化發展正在深刻賦能傳統農產品領域的高水平高質量發展。現階段,數字化賦能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面臨著來自各國內部和國家間新舊矛盾疊加的困局,以及數字貿易治理摩擦和數字鴻溝等嚴峻挑戰。有鑒于此,文章提出了數字化賦能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實施路徑,包括加快數字技術同傳統農產品貿易的深度融合,培育數字貿易領域的高水平人力資本,打造共享、共研數字技術共同體,協調統籌開放合作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等。
[關鍵詞]?數字化;數字技術;農產品貿易;“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F3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461(2024)07-0063-14
一、引言
當今世界正經歷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經濟持續低迷,國際經貿局勢緊張,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農產品貿易發展受到影響,規模和增速均有所放緩。以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為首的逆全球化與單邊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農產品市場準入門檻不斷提高,對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農產品貿易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擠壓,例如,截至2022年年中,全球已有超20個國家宣布對農產品施行糧食出口限制或升級管理,嚴重制約了各國農產品貿易的發展①,盡快開辟新的農產品貿易發展路徑,尋求區域間農產品貿易合作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共同訴求。同時,俄烏沖突、日本核廢水排海和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等諸多不穩定因素,加劇全球農產品價格的波動和國際市場農產品貿易競爭激烈程度的同時,也形成一定的貿易創造和轉移效應,有望重新調整全球糧食供給關系和農產品貿易格局。
2023年正值“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周年,伴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持續推進,這10年來中國與共建各國基于互利共贏的農業經貿合作日益密切,貿易總量和增速呈現持續增長態勢,并形成了既具貿易競爭性又有互補性的雙邊和多邊農產品貿易合作伙伴關系。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2022年,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進出口總額從9933億美元增長至33907億美元,實現年均增速突破1857%的矚目成就②。這10年來,“一帶一路”倡議已獲得世界近2/3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認同并簽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本,中國也已成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最重要的貿易伙伴。盡管成績斐然,亮點眾多,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合作仍面臨風險與機遇并存的市場環境。一方面,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貿易摩擦不斷,以發達國家為首的眾多國家鼓吹“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嚴重影響中國與共建國家開展正常經貿合作。與此同時,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合作本身也展現出“大而不強”和低效率、粗放型增長等問題,在發展模式、質量效益、供應鏈體系不健全等方面還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另一方面,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等一系列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催生了大量貿易新業態,實現了數據要素跨境自由流動,以數字技術和相關配套設施的創新迭代擴展了貿易深度與廣度,深刻影響著當前國際貿易結構和形式,為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驅動力。2017年,習近平在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首次提出建設“數字絲綢之路”,指明數字化對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新格局的關鍵意義。2021年,習近平在第二屆聯合國全球可持續交通大會上再次強調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核心之一便是加快建設“數字絲綢之路”。方芳(2019)[1]對“數字絲綢之路”的概念做出界定,提出分區“精準”對接有效需求、統籌推進“數字絲綢之路”建設的可行路徑;姜峰和段云鵬(2021)[2]通過研究發現數字“一帶一路”可以有效降低貿易成本,提高貿易多樣性,進而提高中國產品出口的技術附加值和市場占有率。因此,在我國致力于構建新發展格局背景下,為應對世界經濟和貿易環境復雜多變的發展局勢,深入探討如何通過數字化賦能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和食品安全方面的優化升級,實現“量”和“質”雙重提高,推動農產品貿易領域的高質量發展,對于施行雙循環發展戰略、深化區域合作和加快中國農業強國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二、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對農產品貿易內涵的界定可以從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兩方面入手。農產品貨物貿易指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蔬菜水果、動物產品、谷物、水產品、油和油籽、糖類、咖啡和茶、棉花等WTO《農業協定》所劃定的一系列實物產品交易行為。農產品服務貿易特指因不同經濟體購買或提供一系列服務而產生的資金、人員、技術和數據等要素的跨國流動,具體包括兩方面:一是涵蓋農業生產、研發、加工、物流和消費等環節的生產性農業服務業的進出口貿易,如跨境物流、種子研發、技術支持、信息咨詢等服務,以及傳統服務業中涉農部分的服務貿易;二是以跨境金融服務、市場信息交換、農產品種植培訓等為主的傳統服務業中的涉農貿易相關部分。
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指出,要加快培育貿易競爭新優勢,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使“貿易結構更加優化,貿易效益顯著提升,貿易實力進一步增強,建立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指標、政策、統計、績效評價體系”。據此,本文從貿易水平、貿易結構、貿易動能和貿易效益四個維度對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加以界定。具體包括農產品貿易規模的穩步擴大、貿易結構的逐步均衡、具備支持農產品貿易創新發展的主體和動能、顯著的貿易效益等內容。從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四個維度來看,當前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雖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區域劃分和農產品種類界定
本文將“一帶一路”65個共建國家劃分為7個區域[3],包括東亞的蒙古、中亞5國、南亞8國、西亞北非18國、東盟10國、中東歐16國和獨聯體7國,具體劃分如表1所示。
本文將農產品范圍劃定為“WTO《農業協定》+水海產品”,具體商品范圍為海關統計商品目錄HS編碼1~24章和51~53章,具體類別如表2所示。
(二)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進出口現狀
近年來,在中美貿易摩擦的沖擊下中國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農產品貿易合作持續增強。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2022年中國與共建國家進出口總額逐年增加,進出口總額從2009年的2137億美元增長至2022年的89497億美元。其中,出口額從2009年的9933億美元增長至2022年的33907億美元,同期進口額從11437億美元增長至5559億美元,基本呈現貿易逆差特征,而且逆差規模逐年擴大,由2009年的1504億美元增至2022年的21683億美元(如圖1)。持續擴大的貿易逆差反映出我國出口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相對匱乏[4]。
從進出口市場結構來看,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表現出明顯的地區分布失衡特征[5](如表3和表4)。以2022年的進出口數據為例,2022年中國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出口農產品目的國前十位依次是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俄羅斯、新加坡、阿聯酋、印度、孟加拉國,出口額合計為273923億美元,占當年中國對共建國家農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為8079%。這其中,所屬東盟區域的國家有6個,出口額總計229684億美元,在總出口額中占比高達6774%。同年中國自“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進口農產品來源國前十位依次是泰國、印度尼西亞、俄羅斯、越南、印度、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巴基斯坦、摩爾多瓦,進口額合計為466929億美元,占當年中國自共建國家農產品進口總額的比重高達84%。這其中,所屬東盟區域的國家有6個,進口額總計356451億美元,在總進口額中占比高達6412%。可見,東盟是中國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和進口來源國,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進出口市場結構失衡問題較為突出。
對應地,本文進一步整理出2022年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進出口農產品排名后十位國家(如表5和表6)。仍以2022年的進出口數據為例,2022年中國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出口農產品目的國后十位依次是馬其頓、巴勒斯坦、黑山、馬爾代夫、烏茲別克斯坦、亞美尼亞、敘利亞、阿爾巴尼亞、阿塞拜疆、斯洛伐克,出口額合計為0974億美元,占當年中國對共建國家農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僅為029%。這其中,所屬中東歐區域的國家有4個,出口額總計0374億美元,在總出口額中占比僅為011%。同年中國自“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進口農產品來源國排名后十位依次是巴勒斯坦、也門、馬爾代夫、巴林、科威特、卡塔爾、烏克蘭、伊拉克、阿曼、阿爾巴尼亞,進口額合計為0008億美元,占當年中國自共建國家農產品進口總額的比重接近于0。這其中,所屬西亞北非區域的國家有7個,進口額總計0003億美元。總體上,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農產品貿易集中在東盟國家,對相對距離較遠的西亞北非和中東歐國家的農產品貿易水平偏低,在空間上呈現出明顯的梯度差異特征(如圖2)。
從商品結構來看(如表7和表8),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品主要以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的初級產品為主,深加工產品占比偏低。以2022年的進出口數據為例,2022年中國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出口農產品品類排名前三位依次是第52章(棉花)、第7章(食用蔬菜、根及塊莖)、第8章(食用水果及堅果;甜瓜或柑橘屬水果的果皮);進口農產品品類排名前三位依次是第15章(動、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制的食用油脂)、第8章(食用水果及堅果;甜瓜或柑橘屬水果的果皮)、第3章(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中國出口農產品仍以勞動密集型的果蔬水產產品為主,競爭力弱、附加值偏低、缺少自主品牌,導致潛在的貿易風險增大[6]。而進口商品主要以高附加值的食糖和油料作物等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為主,反映出中國與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具有較強的互補性。
從“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不同區域的農產品商品結構來看,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表現出區域產品集中度偏高,不同區域產品集中度差異較大的特點。以2022年中國對共建國家分區域出口農產品類別比較為例(如表9),2022年中國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第52章棉花出口目的國集中在東盟和南亞等國家,占當年對共建國家棉花出口總額的比重高達8881%;第3、7、8、16章農產品出口主要流向東盟國家,占當年各類農產品出口總額比重分別達到8252%、8065%、7598%、9007%。對其他農產品出口規模整體較低,對東亞主要出口第17章(糖及糖食),對中亞農產品出口以第8章(食用水果及堅果;甜瓜或柑橘屬水果的果皮)為主,對中東歐農產品出口以第24章(煙草、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制品)為主,對獨聯體國家的主要農產品出口品類為第20章(蔬菜、水果、堅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對西亞北非出口以第20、24、52章產品為主。中國對共建國家出口農產品集中度偏高,表明我國農產品出口種類單一,產品多樣性程度不強,對農產品深加工水平不足,面臨較高的市場風險。
(三)“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數字經濟基礎
加快數字經濟發展是實現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7]。隨著數字“一帶一路”建設的持續推進,“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互聯網普及率出現顯著提升。
區域的互聯網普及率由1409%提升至5969%,東亞區域的互聯網普及率由1994%提升至8433%,年均增速分別為4623%和4613%,成為共建國家互聯網普及率增長最快的兩大區域。其次是中亞、東盟及西亞北非等國。獨聯體和中東歐國家雖然互聯網普及率增速較低,但互聯網普及率水平均達到60%以上,為數字化賦能共建國家的貿易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表11給出了2017年和2019年“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分區域信息和通信技術(ICT)使用指數的平均得分,該得分用以衡量一國使用信息和通信技術的頻率、程度和水平,得分越高表明該國的信息和通信技術越發達。表11所示,中亞、南亞、東盟和獨聯體國家整體的信息和通信技術使用指數出現顯著上升趨勢,而東亞、西亞北非、中東歐地區的信息和通信技術使用出現下降趨勢。相比之下,中國的信息和通信技術使用水平提高最快,年均增速高達1486%,而南亞等部分共建國家的信息和通信技術使用水平較低,這也為中國與這些國家開展數字經濟合作提供了空間和動力。
信息和通信技術(ICT)服務貿易是各國產業技術進步的重要來源和提升產業自主創新力的重要基礎。從2014—2021年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信息和通信技術(ICT)服務出口占比來看(如圖3),中國與共建國家ICT服務出口規模雖然整體呈現逐年擴張的趨勢,但各國的ICT出口水平差距較大,其中南亞國家ICT服務出口占比最高,說明南亞地區對信息和通信技術出口的依賴性最強,中亞國家ICT服務出口占比最低,反映出該區域國家信息化基礎和應用相對落后。但共建各國ICT服務出口占比均大于0,說明“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已經基本形成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中國與共建國家的數字經濟合作潛力巨大,如何以數字化賦能共建各國產業高質量發展,帶動各國實現跨越式增長成為當前亟待探索的關鍵問題[8]。
三、數字化賦能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
國際貿易領域數字化是在數字經濟時代背景下貿易標的物、貿易工具和貿易方式“數字化轉型的發展趨勢[9]。依托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物聯網和虛擬現實等數據技術,數字化發展能夠對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相關的海量信息數據進行即時處理,有效降低數據分析、傳輸和存儲成本,提高貿易流程的精準度和高效性,從而深刻地影響和轉變傳統貿易活動。因此,厘清數字化應當如何賦能我國與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問題,是目前我國加快農業強國建設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中亟待深入思考的關鍵議題之一。
依托數字技術在傳統貿易領域的廣泛滲透和深度融入所引發的一系列貿易模式、貿易標的和貿易工具的創新變革[9],數字化賦能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和影響途徑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運用數字技術拓寬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現有農產品貿易合作領域,深化農業貿易合作層次,從各個方位全面激活區域農業貿易合作潛能;二是利用數字化技術提高農產品貿易市場中供需匹配精準度[10],有效防范因信息不對稱引致的貿易低效率問題,促進農業貿易結構優化升級;三是憑借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有效降低運輸、物流和倉儲等環節的貿易成本,有效提高農產品貿易效益和質量;四是打造農產品貿易新業態新模式,全面激活農業特色產業集群發展新動能。
(一)數字化推動建立更高水平農產品貿易格局
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能夠以信息流推動技術、人才等知識性要素和數據生產要素在地理空間上無限延展,表現出廣泛鏈接特性;在時間上具有即時性和高速性[11]。隨著數字技術與傳統農產品貿易的深度結合,以數字技術所創造的數字化趨勢動能成為推動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建立更多方位、更寬領域和更深層次的貿易開放與合作新格局。
第一,數字化破除了區域要素流動桎梏,疏通了信息流通的“脈絡”[12],實現了要素、交易與傳輸的虛擬化和貨物貿易的數字化交付過程,加速了信息跨地區的傳輸速度,形成了生產環節的集約化管理,提高了要素的跨區域協調分配效率,釋放農業資源要素優化配置活力,同時加快了農業領域先進技術的域內溢出與擴散,有利于實現跨區域產業間知識和技術要素共享,從而形成更具國際競爭優勢的智慧農業產業綜合生態圈。此外,數字技術的普及應用使得傳統農業與配套服務業之間的聯系強度、深度和高效性得到極大提升,尤其是配套服務業同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結合協作能夠加快構建農產品上下游相互配套銜接的全產業鏈,讓農產品生產趨于個性化、柔性化和高端化,從而實現單一農產品購銷貿易轉向多元要素融合共享,為強化我國農產品貿易和服務競爭優勢提供持續動能。
第二,數字技術在傳統農業的廣泛應用及由此形成的數字化動能推動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更寬領域農產品貿易合作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數字化發展能夠加速推進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農業科技合作,包括應用智慧精準農牧漁業、農業信息化數字化管理、現代農業生物技術、衛星遙感與導航定位技術等,充分挖掘共建國家的農業貿易潛力,幫助它們發揮各自的農業比較優勢,能夠有效利用國際市場資源,提高各國農產品進口來源地和出口目的地的多樣性,優化調整雙邊農產品貿易結構,提高貿易效率,從而增強中國與共建國家在更廣泛的領域開展農業發展經驗互鑒及農產品貿易合作,通過農業國際合作聯盟實現互利共贏;另一方面,數字技術憑借其廣泛輻射性、滲透性和靈活性特征,突破了實體市場地域分割、制度距離和文化性貿易壁壘限制,搭建了中國本土市場跨區域線上市場合作平臺,有利于延長農業產業鏈,提高農業集聚度和出口產品附加值,幫助更多企業通過引進國外優良品種和先進技術與國內企業自主研發創新相結合的方式實現傳統農業向外貿企業轉型,有效提升我國不同地區的農業對外貿易水平和開放程度。同時,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實現了各省跨區域農業產業間高級要素自由流動、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共享,加快了本土企業開發自主知識產權產品的能力,也提高了農產品加工在國際市場的核心競爭力。
第三,數字化推進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對接農業標準國際化步伐,形成用數字經濟發展相統一的農產品貿易合作規則、標準、制度和管理。作為當前極為重要的經濟形態,數字經濟的發展使得傳統國際經貿規則面臨巨大挑戰,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和國際經貿規則的發展演變需要不斷適應數字經濟時代下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大趨勢。因此,農業強國建設必然要求充分把握數字化所帶來的前沿技術及其發展趨勢變化,以同當前國際數字經貿規則標準有效對接。以數字化賦能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能夠及時追蹤跟進國際市場標準動態,并制定相應對接農業標準國際化方案,降低貿易壁壘,加快推進本土農業對接國際市場標準,從而逐步提升雙邊國家農產品國際貿易話語權,有助于各國進一步參與和融入到國際農產品標準的制定設計之中,也是我國加快實現農業標準國際化的重要途徑。
(二)數字化促進農產品貿易供需雙側匹配和優化,充分釋放供給端與需求端潛力
一直以來,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農產品跨境貿易模式中長期存在因供需匹配效率偏低、信息溝通時效性差引致的貿易低效率問題。數字化憑借其虛擬性、即時性和無界性特征[13],能夠有效縮短農產品貿易供給國和需求國之間的信息傳輸鴻溝,提高雙邊溝通時效性和供需匹配效率,解決供需兩端升級轉換錯位滯后問題,并有效緩解貿易主體因對市場反應遲緩引發的矛盾。隨著農產品貿易領域及其上下游產業環節和配套服務業與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傳統農產品貿易領域涉及的生產、包裝、銷售、運輸、交付和消費的完整鏈條體系發生重大變革,數字化成為加速傳統農產品貿易供需兩端間的數據信息傳輸效率的有效工具之一。
具體地,數字化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供需雙側匹配和優化主要體現在三方面:第一,數字化有效提高了中國與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供給側的生產效率。數字時代背景下,數據成為新型生產要素,依托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關鍵數字技術[14],供給端企業能夠對市場消費需求及時作出比較精準的預測,改變傳統農產品貿易供給端要素投入、組合及利用模式,降低低端無效供給規模,有效提升農業生產領域各類投入要素的綜合利用率和最優配置,實現農業最適配、最高效、效益最大化的產出水平,從而實現農業供給端轉型升級和提質增效,助力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高水平可持續發展。第二,充分發揮數字化創新驅動和賦能作用,可以全面激活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消費端潛力,刺激消費需求規模擴張和結構升級。伴隨著農產品貿易產品、途徑和工具的數字化轉型,國內外市場對農產品的消費需求日趨多樣化、個性化、柔性化,跨境電子商務通過數字化賦能線上線下消費場景,一對一滿足定制需求的“零單貿易”逐漸增多,為傳統農產品貿易開辟新的零售渠道,塑造品牌優勢,同時通過海外倉孵化模式引進國際市場優質產品,為線上貨物訂單提供各類數字化服務,從而持續拓寬國內外農產品市場消費需求邊界。第三,數字化有助于破除供給側和需求側的信息壁壘,暢通數據信息傳輸渠道,縮短供需市場信息互換時間,有效提高供給側對市場需求變化的反應速度,從而緩解因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供給端與需求端市場失衡與不匹配問題。
(三)數字化降低傳統農產品貿易成本,提升貿易主體的效益空間
傳統農產品貿易活動中,從提供跨境產品和服務、客源需求對接、磋商、跨境物流運輸、交付貨物到貨款結算等各個環節構成了貿易成本的支出來源。數字化背景下,傳統農產品貿易的產品、工具和途徑等加快實現數字化創新升級,使得各貿易環節的成本支出顯著降低,更多的農產品市場主體既可以利用數字技術降低供需雙方因市場搜尋匹配所付出的額外搜尋成本,也可以在更為廣闊的市場平臺配置資源要素,憑借數字化物流系統提高商品流通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推動我國農產品出口目標市場趨于多元化,同時幫助更多小農企業降低運營成本,將更多資金投入到農產品加工及其跨境服務的研發創新中,從而加快傳統農產品加工業的轉型升級。首先,數字技術與傳統貿易的深度融合改變了傳統農產品生產模式和貿易方式,加速了跨境電子商務、個性化定制訂單、跨境云服務等各類新型、多樣化的貿易模式興起,引起世界農產品貿易由大宗貿易模式向平臺化、分散化模式轉變,同時農產品生產企業需要及時獲取國際市場差異化農產品需求信息并做出相應調整,并基于國際市場消費者個性化和差異化需求提供定制化生產與服務。數字技術既能夠高效傳遞國際供需市場信息,也可以依據農產品供需市場海量數據的量化分析搭建供需端多樣化對接方案,降低潛在客戶搜尋成本,增強企業對于多元化市場需求的供給創新能力和適應性,通過供需雙側協同發力,持續有效挖掘農產品貿易市場潛力,提高貿易效率。其次,數字技術驅動下傳統農產品貿易逐漸向網絡化和智能化轉型,依托數字化公共服務平臺[15],買賣雙方能夠縮短商務談判和交易磋商的時間,國與國之間能夠增進彼此了解與信任,降低因制度差異引致的貿易低效率問題。在數字化發展的影響下,地理邊界、語言溝通障礙、社會文化差異等傳統貿易壁壘的影響趨于弱化,農產品貿易成本顯著下降,貿易效率明顯提升。再次,在農產品清關交付和貿易結算階段,數字技術賦能通關口岸數字化轉型,通過對訂單信息、支付憑證、物流溯源等電子數據進行自動采集分析,并及時形成報關數據,極大地提高通關貿易便利化水平,通過這種“數字清關”模式有效縮短貨物清關時間,降低農產品損耗率。最后,在冷鏈物流運輸過程中,農產品因其易腐爛、不易儲存的本質屬性,對冷鏈運輸及配套設備有較高的要求,長期面臨高昂的運輸成本、倉儲成本和管理成本等。伴隨著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跨境物流體系中,數字化能夠加快實現海外倉數字化和物流數字化系統的建設與完善,幫助涉農貿易企業合理規劃選擇低風險、高效率和全程可視化的農產品冷鏈貨物運輸路徑與運輸方式,使用高效的冷藏保鮮技術、形成智能溫控儲藏和分區倉儲,實施農產品質量溯源和全程監控,最大限度地延長產品保質期,降低壞品率,從而極大地降低傳統農產品貿易冰山運輸成本。
(四)數字化催生農產品貿易新模式新業態,培育重塑貿易鏈條的全新動力
數字經濟時代背景下,數據成為新型農業生產要素,數字化加快了傳統貿易領域新模式、新業態、新形勢的出現與發展。傳統貿易模式已然難以適應當今國際市場個性化、集約化、高彈性和多元化的新興市場需求,以區塊鏈、物聯網、5G技術和大數據為代表的數字技術為傳統貿易轉型與創新發展提供了關鍵契機。一方面,數字技術的應用拓展了現有農產品貿易及其配套服務品類,精簡跨境貿易流程,縮短貿易鏈條,改變了農產品貿易鏈條上生產者、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加快形成線上線下雙線聯動的貿易模式,實現了傳統農產品貿易的創新升級與轉型優化;另一方面,利用數字技術能夠高效整合“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差異化、個性化的市場需求,催生出更加多樣化的貿易產品,提升我國與共建國家的消費者福利。同時,數字技術加速了新模式新業態的出現與發展[16],如農產品跨境電商、訂單農業、海外倉、外貿綜合農業服務業等,為特色優質農產品出口提供暢通高效的貿易渠道,持續釋放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增長新動能。更重要的是,數字技術有助于加速農業與第二、三產業的深度融合和有效聯動,形成完整的農業貿易產業鏈和價值鏈,進而優化中國與共建國家農業資源優化配置,更好發揮各方的農業資源優勢,提高我國與共建國家農業生產現代化和規模化程度,拓展農產品貿易增值空間,充分挖掘各方農業多功能性和創新競爭力,也驅使各國農產品貿易市場利益分配格局優化升級,加快農業價值鏈的分工升級。
四、數字化賦能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的現實挑戰
(一)“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數字貿易治理摩擦和數字鴻溝問題突出
數字化時代背景下,數字技術在產業和貿易領域的廣泛應用與數字化發展加快推進了數字“一帶一路”建設,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創造了更加多元、更為開闊的經濟發展路徑。但由于不同國家處于不同的數字發展階段,各國產業基礎、國別利益和監管理念等具有較大差異[17],導致“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數字經濟治理機制和數字貿易規則上呈現出泛化、碎片化和缺乏約束力的特點,不利于中國與共建各國從數字貿易和數字經濟發展中獲取更大效益。一方面,“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之間的數字治理摩擦不斷,各國針對數字稅收治理、數字技術倫理、數字平臺競爭、源代碼保護、網絡數據安全、數據跨境自由流動等方面的價值取向和核心主張存在顯著差異,既加劇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數字經濟治理和數字貿易合作過程中的矛盾與摩擦,限制了數字化發展所營造的協調一致性和包容性發展機遇,也增加了我國建設農業貿易強國在國際合作領域的挑戰和壓力;另一方面,與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長期致力于強化數字貿易規則話語權,尋求數字經濟戰略發展同盟來確立和鞏固他們在全球數字經貿領域的主導地位不同,“一帶一路”共建發展中國家對數字經貿發展的核心訴求更傾向于推動本國現有產業鏈和經貿體系的升級優化,更側重于采取更為公平開放,更加循序漸進的制度安排和對外開放策略,以達到降低數字化變革對國內市場沖擊的目的。
(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數字空間治理水平較低,人才配套基礎薄弱
數字空間治理水平對“一帶一路”數字化發展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一直以來,“一帶一路”共建不同國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差異較大,部分國家互聯網普及率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處于較低水平,多數傳統企業缺乏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相關數字貿易技術支持和數字金融工具的使用,也尚未建立統一的數字空間治理機構,導致各國農產品產業鏈的數字化轉型成本較高,難以有效形成相互包容、彼此合作的“一帶一路”數字化發展領域協同治理格局。此外,部分共建國家及地區的恐怖主義高發與政權更迭頻繁,不利于貿易的數字化轉型,加上眾多國家人口生育率偏高、基數過大,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嚴重滯后于人口增長速度,導致“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空間治理水平出現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和逆全球化思潮涌動背景下,共建國家的部分跨國企業產業鏈在國際市場顯示出其脆弱性,并逐漸加強本土企業生產能力,縮小多步驟、多國家供應鏈,更不利于“一帶一路”數字化治理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有關數字技術領域的復合型人才和高級研發技術人員存在嚴重短缺,技術“卡脖子”的現狀尚未得到根本改善。在核心數字技術領域人力資源嚴重匱乏背景下,共建各國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核心元器件、操作系統和國內高端芯片研發使用等領域同樣面臨著低自給率和技術攻關遲緩難題,嚴重制約了各國產業數字化轉型進程。
(三)有關農產品數據跨境傳輸安全威脅持續升級,傳統關稅監管面臨挑戰
實現數字化賦能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的關鍵在于解決跨境網絡開放共享的需求與數據安全保護之間的關系問題。數字貿易的發展使得“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數據跨境流動、存儲和使用變得更為頻繁,目前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尚未建立有效、相對完善的數字知識產權保護和數據傳輸安全保護體系,網絡恐怖主義和網絡犯罪問題頻發,如竊取商業機密、數據濫用、網絡詐騙、侵犯隱私、被他國監控數據等問題已經成為數字化賦能我國與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合作過程中面臨的最大障礙之一。此外,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尚未建立協調一致的數字服務稅體系,數字化發展驅動下雙邊和多邊農產品貿易的跨境電商交易規模日益擴大,共建各國逐漸采取單邊開征數字稅的方法來維護其稅收主權地位和利益,加大了中國與共建各國農產品的貿易摩擦,也可能影響未來跨境數字貿易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準入和開展。
五、數字化賦能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實施路徑
以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物聯網、虛擬現實和大數據等數字技術與傳統貿易相結合所形成的數字化新動能是實現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著力點。因此,有必要針對數字化賦能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針對當前數字化賦能中國與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的現實挑戰,提出利用數字化發展新機遇,加快推進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與中國農業強國建設的“中國方案”。
(一)加快數字技術同傳統農產品貿易的深度融合,塑造“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新底座”
針對當前不確定性風險增強的國際經濟形勢和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長期低效率低質量的現狀,一方面,我國應強化戰略統籌,加快數字技術同傳統農產品貿易的深度融合,充分利用數字化新機遇,既要高效率、高質量發展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又要完善跨區域農產品貿易發展的機制體制,切實保障新形勢下國家糧食安全;另一方面,我國應緊抓數字經濟發展機遇,以數據為關鍵要素,以發展智慧農產品貿易為重點,以農業供應鏈數字化轉型為主線,全面聚焦“一帶一路”區域資源要素,創新貿易合作機制,實現數據資源共享互聯、農業全產業鏈賦能增效,提高我國農產品在與共建國家貿易中的國際競爭優勢。首先,應將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5G通信、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與傳統農產品貿易模式進行深度融合,瞄準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三環節,促進共建國家農產品加工現代化和智慧化轉型,為生鮮農產品打造智能化加工體系,賦能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和附加值提升。同時重視建構農產品產業數字交易平臺,通過整合線上線下農業資源、提升貿易配套服務、實時監測和傳遞農資采購和農產品流通等數據實現農產品貿易流通環節的精簡,降低信息不對稱成本,優化貿易結構,從而實現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的高質量發展。其次,我國應大力推進國內智慧農業發展,促進數字技術與農機、農藝、農業生產等領域的融合應用,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步伐。一是加快農業生產要素的網絡化、數字化、在線化。利用數字技術實現對農業種植環境、養殖業生長信息、農機裝備機械供求信息的數字化獲取和標示,同時實現遠程數字化信息共享和調度,實現農業生產要素的最優配置與有效利用。二是強化智能化和云計算技術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的調控和決策力度,全力打造智能加工車間。憑借云計算技術對農業生產數據進行有效分析和加工處理,優化農產品加工和動植物優化生產結構調控模型,實現農業生產周期的全面化、及時化、智能化調控,從而有效提高農產品加工效率和質量,強化農產品出口競爭優勢。三是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加速實現農業全過程、全環節、全鏈條協同化與一體化。通過云計算平臺和區塊鏈去中心化技術將分布式農業生產、流通交易及消費系統整合為一體,從而實現國內各地區農業加工生產、經營管理、消費出口等環節與農業生產主體工作保持協同優化和同頻共振。最后,強化利用數字技術推進農產品標準化和品牌化建設意識,賦能中國出口農業品牌產業發展。例如,利用射頻識別技術(RFID)自動、快速、準確搜集和存儲農產品全鏈條全周期的跟蹤監測,建立農產品質量追蹤溯源信息管理系統,對農產品質量和安全標準要求未達標的農產品及時作出預警,強化出口農產品跨境存儲、流通、銷售的全流程質量檢測服務,塑造安全、生態、健康的出口農產品品牌形象。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農業龍頭外貿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引領帶頭作用[4],加快建設農業品牌產業數字化平臺,通過為傳統企業在農業生產、品牌營銷管理、品牌服務等環節提供數字技術支持,深度挖掘農業品牌數字化轉型空間,塑造中國農產品出口品牌優勢。此外,應充分重視我國農業企業通過跨國投資方式將農業技術和數字技術在共建國家推廣應用,統籌推進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的可持續高質量發展。
(二)培育數字貿易領域的高水平人力資本,打造“一帶一路”共享、共研數字技術共同體
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應重視加強科技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各國的前沿科技基礎,為“一帶一路”數字化發展提供長期的人力資本支持[8]。在數字經濟發展和貿易數字化轉型的主流趨勢下,加快推進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數字貿易領域創新型、技能型和研究型人才隊伍建設,打造“一帶一路”共享、共研數字技術共同體應是優化區域內農業資源配置,推動技術、資本、信息與服務等高級要素在域內自由流動,提高共建國家數字技術與農業深度融合,加速數字化賦能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的破局之路。一是我國應充分重視數字技術領域技能和研發人才培養,在“一帶一路”共建優化算網融合和先進計算等技術空間布局優化,塑造農產品貿易數字化轉型新優勢,助力我國與共建國家緊抓數字化發展機遇,建設高質量、高效率、高效益的農產品貿易合作網絡,實現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二是我國應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共同打造共研、共享數字技術共同體,充分利用各自的前沿技術基礎,加快數字技術人力資源的跨境交流往來,持續強化科技交流共享,加快建立完善資金性和政策性的共享、共研數字技術合作關系,鼓勵和支持擁有數字技術先行優勢的國家或企業基于尊重原創、保護知識產權的原則開展數字技術人才培訓,主動分享前沿技術,加快共建各國農業供應鏈數字化轉型,共建國家也應為提供技術指導的國家或地區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此外,中國應與共建國家共同推進數字技術人才聯合培養長效機制,探索成立跨區域數字經貿人才培訓中心和數字技能學習平臺,加快形成滿足我國與共建各國貿易數字化發展需求的高素養、高水平和復合型人力資本蓄水池,實現域內數字技術專業人才合作務實化和常態化,打造服務于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優質人才儲備,從而為中國與共建各國農產品貿易合作提供長期的技術支持。三是應由我國牽頭,推動共建“一帶一路”數字服務平臺,深化全方位數字技術交流合作,并聯合絲路基金、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政策性銀行設立農業數字化轉型專項資金或種子基金,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數字標準聯通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定向資金支持,降低農業企業數字化轉型融資壓力,有力保障“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傳統農業企業的數字化發展,拉動各國農產品供應鏈數字化轉型,提高對進口農產品的需求程度和消費水平,從而扶持和引導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數字化發展。此外,成立第三方數字技術評估機構也是保障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數字技術標準公平、公正、合理的可行方案,助推數字化賦能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
(三)協調統籌開放合作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開拓農產品貿易合作新空間
數字化發展雖然為傳統農產品貿易增長創造了新的突破口,但也間接帶來國家間數字貿易壁壘和數據安全爭端問題。數字技術是貿易數字化的關鍵工具載體,而數據信息則是關鍵的生產要素和核心戰略資源。因此,在協調統籌好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各國國家開放合作和國家安全關系的同時,更要加快推進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與傳統農產品貿易充分、高效地有機結合,不斷拓展現有農業經貿合作邊界,開拓農產品貿易國際合作新空間,提升我國在“一帶一路”農業貿易戰略競爭與合作過程中的影響力。這是實現我國與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制度保障,更是我國推動農業強國建設中的聚焦重點。一是應盡快建立完善“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安全治理機制。應由中國牽頭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區域網絡數字安全治理合作,完善數字治理機制,充分利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海合作組織、互聯網治理論壇、亞信會議和金磚國家組織等合作機制,定期交流、分享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治理經驗,積極推動“一帶一路”數字安全治理合作平臺建設,在數字貨物、數據監管、跨境數字稅收、網絡安全治理和數字知識產權保護等國際規則與技術標準等方面建立長效的溝通機制和國際合作治理方案,加快形成以“一帶一路”共建各國政府為主導,社會各方協作的數字空間治理格局。同時,應充分借鑒吸納歐美發達國家的數字安全治理經驗,盡快完善相關跨境傳輸、數據安全、隱私保護、反壟斷和平臺保護等一系列規則體系,推進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各國的數據保護法律法規建設,加快完善數據要素確權、交易、轉讓和使用等相關標準制度,規范海關進出口、移動支付、跨境運輸、跨境物流、個人出入境等數據的頻繁交流互動、匯集、處理和保護,形成統一的“一帶一路”數字經貿合作領域法律制度框架,切實保障中國與共建國家數據信息跨境自由流動的安全性。二是面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龐大的農產品市場規模和極為迫切的農業轉型升級需求,我國應立足“數字絲綢之路”建設,充分利用數字化賦能契機,科學、有效、循序漸進地挖掘我國與共建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合作空間,實現互利共贏。一方面,我國應利用數字技術加快布局高效、安全、穩定的“一帶一路”農產品供應網絡,大力發展農產品生產的數字信息化指導系統、農產品數字化結算平臺,創新數字化與農產品流通體系和農產品電商品牌塑造等一系列農產品貿易相關的數字產品和服務出口,積極擴大數字貨幣合作和移動支付,率先探索和落實域內數字化賦能農產品貿易規則[18];另一方面,中國應在“一帶一路”域內推廣產業數字化轉型的中國經驗,努力打造農產品貿易糾紛處理機制和數字貿易協同發展機制,強化雙邊和多邊數字經貿規則磋商,縮小和彌合中國與共建各國的數字鴻溝,構筑“共商共建共享”的“數字命運共同體”,提高數字化發展背景下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開展農產品貿易合作過程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在當前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世界經濟發展充滿不確定性風險大背景下,實現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農產品貿易高質量發展,對于推動我國本土農業產業結構高級化、加快農產品外貿市場多元化布局,進而實現農業領域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建設具有重大意義。當前中國與共建國家農產品貿易合作仍面臨諸多風險和挑戰,貿易合作潛力仍未得到有效發揮,如何借助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化發展的力量,科學、有效、合理地解決農產品貿易合作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充分盤活共建各國農產品貿易合作活力,有效提升我國農產品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貿易競爭力,不斷創新貿易模式、擴大貿易規模、強化貿易保障,是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共建更高層次、更高水平、更高質量農產品貿易合作所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
[注?釋]
①
資料來源于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發布的《2022年全球食物政策報告》。
②?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農產品進出口月度統計報告》。
③?農產品品類52代表HS編碼第52章(棉花)、7代表第7章(食用蔬菜、根及塊莖)、8代表第8章(食用水果及堅果;甜瓜或柑橘屬水果的果皮)、16代表第16章(肉、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的制品)、20代表第20章(蔬菜、水果、堅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3代表第3章(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21代表第21章(雜項食品)、24代表第24章(煙草、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制品)、9代表第9章(咖啡、茶、馬黛茶及調味香料)、17代表第17章(糖及糖食)。
④?農產品品類15代表HS編碼第15章(動、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制的食用油脂)、8代表第8章(食用水果及堅果;甜瓜或柑橘屬水果的果皮)、3代表第3章(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10代表第10章(谷物)、52代表第52章(棉花)、23代表第23章(食品工業的殘渣及廢料;配置的動物飼料)、7代表第7章(食用蔬菜、根及塊莖)、11代表第11章(制粉工業產品;麥芽;淀粉;菊粉;面筋)、12代表第12章(含油子仁及果實;雜項子仁及果實;工業用或藥用植物;稻草、秸稈及飼料)、2代表第2章(肉及食用雜碎)。
⑤?農產品類別1代表HS編碼第1章(活動物)、2代表第2章(肉及食用雜碎)、3代表第3章(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4代表第4章(乳品、蛋品;天然蜂蜜;其他食用動物產品)、5代表第5章(其他動物產品)、6代表第6章(活樹及其他活植物;鱗莖、根及類似品;插花及裝飾用簇葉)、7代表第7章(食用蔬菜、根及塊莖)、8代表第8章(食用水果及堅果;甜瓜或柑橘屬水果的果皮)、9代表第9章(咖啡、茶、馬黛茶及調味香料)、10代表第10章(谷物)、11代表第11章(制粉工業產品;麥芽;淀粉;菊粉;面筋)、12代表第12章(含油子仁及果實;雜項子仁及果實;工業用或藥用植物;稻草、秸稈及飼料)、13代表第13章(蟲膠;樹膠;樹脂及其他植物液、汁)、14代表第14章(編織用植物材料;其他植物產品)。
⑥?農產品類別15代表HS編碼第15章(動、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制的食用油脂)、16代表第16章(肉、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的制品)、17代表第17章(糖及糖食)、18代表第18章(可可及可可制品)、19代表第19章(谷物、糧食粉、淀粉或乳的制品;糕餅點心)、20代表第20章(蔬菜、水果、堅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21代表第21章(雜項食品)、22代表第22章(飲料、酒及醋)、23代表第23章(食品工業的殘渣及廢料;配制的動物飼料)、24代表第24章(煙草、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制品)、51代表第51章(羊毛、動物細毛或粗毛;馬毛紗線及其機織物)、52代表第52章(棉花)、53代表第53章(其他植物紡織纖維;紙紗線及其機織物)。
[參考文獻]
[1]方芳.“數字絲綢之路”建設:國際環境與路徑選擇[J].國際論壇,2019,21(2):56-75.
[2]姜峰,段云鵬.數字“一帶一路”能否推動中國貿易地位提升——基于進口依存度、技術附加值、全球價值鏈位置的視角[J].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21(2):77-93.
[3]蘇昕,張輝.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網絡結構與合作態勢[J].改革,2019(7):96-110.
[4]劉藝卓,尹文淵,林志剛.高質量發展視域下我國農業貿易:內涵、現狀及對策分析[J].國際貿易,2022(9):10-19.
[5]祝志勇,崔凌瑜.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推進策略[J].理論探討,2021(6):119-124.
[6]喻美辭,蔡宏波.自由貿易協定能緩解中國出口農產品質量升級困境嗎[J].國際貿易問題,2022(8):136-155.
[7]程大為,樊倩,周旭海.數字經濟與農業深度融合的格局構想及現實路徑[J].蘭州學刊,2022(12):131-143.
[8]姜峰,藍慶新.數字“一帶一路”建設的機遇、挑戰及路徑研究[J].當代經濟管理,2021,43(5):1-6.
[9]夏杰長,李鑾淏.數字化賦能國際貿易高質量發展:作用機理、現實挑戰和實施路徑[J].國際貿易,2023(1):56-65.
[10]王定祥,彭政欽,李伶俐.中國數字經濟與農業融合發展水平測度與評價[J].中國農村經濟,2023(6):48-71.
[11]戴翔,楊雙至.數字賦能、數字投入來源與制造業綠色化轉型[J].中國工業經濟,2022(9):83-101.
[12]BIRNER?R,?DAUM?T,?PRAY?C.?Who?drives?the?digital?revolution?in?agriculture??A?review?of?supplyside?trends,?players?and?challenges[J].?Applied?economic?perspectives?and?policy,?2021(43):1260-1285.
[13]ROTZ?S,?DUNCAN?E,?SMALL?M,?et?al.?The?politics?of?digital?agricultural?technologies:?a?preliminary?review[J].?Sociologia?ruralis,?2019?(59):?203-229.
[14]LIOUTAS?E?D,?CHARATSARI?C.?Innovating?digitally:?the?new?texture?of?practices?in?agriculture?40[J].?Sociologia?ruralis,2022(62):250-278.
[15]RUNCK?B?C,?JOGLEKAR?A,?SILVERSTEIN?K,?et?al.?Digital?agriculture?platforms:?driving?dataenabled?agricultural?innovation?in?a?world?fraught?with?privacy?and?security?concerns[J].?Agronomy?journal,?2022(114):2635-2643.
[16]倫曉波,劉顏.沿著數字“一帶一路”實現高質量發展[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23,25(1):64-78.
[17]楊繼軍,艾瑋煒,范兆娟.數字經濟賦能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工的場景、治理與應對[J].經濟學家,2022(9):49-58.
[18]劉雪梅,董銀果.中國出口農產品存在質量升級困境嗎[J].國際貿易問題,2021(6):80-95.
Digitization?Enabling?Highquality?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
Trade?between?China?and?Countries?along“the?Belt?and?Road”:
Mechanism,?Practical?Challenges?and?Implementation?Path
Xu?Weicong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Xianyang?712100,?China)
Abstract:???The?deep?application?of?digital?technology?in?traditional?agricultural?product?trade?has?triggered?a?wave?of?digital?development.?This?has?formed?an?important?driving?force?for?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raditional?agricultural?product?trade.?At?present,?the?agricultural?trade?between?China?and?“the?Belt?and?Road”?countries?is?facing?problems?such?as?unbalanced?regional?layout,?single?structure?of?import?and?export?market,?and?low?degree?of?diversity?of?products,?which?leads?to?the?“large?but?not?strong”agricultural?trade?cooperation?among?countries.?In?recent?years,?the?Internet?penetration?rate,?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y?(ICT)?utilization?rate?and?ICT?service?export?level?of?the?countries?along?the“the?Belt?and?Road”?have?increased?year?by?year,?which?has?laid?a?certain?foundation?for?the?development?of?the?digital?economy.?By?promoting?the?establishment?of?a?higher?level?of?agricultural?product?trade?pattern,?promoting?the?dual?matching?and?optimization?of?supply?and?demand?in?agricultural?product?trade,?reducing?the?cost?of?traditional?agricultural?product?trade,?and?promoting?new?models?and?formats?of?agricultural?product?trade,?digital?development?is?deeply?empowering?the?highlevel?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raditional?agricultural?product?fields.?At?present,?digitization?empowering?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product?trade?between?China?and?countries?along?the?route?faces?both?the?old?and?the?new?contradictions?within?and?between?countries,?as?well?as?severe?challenges?such?as?digital?trade?governance?frictions?and?digital?divide.?In?view?of?this,?this?paper?proposes?a?feasible?path?for?digital?empowerment?of?highquality?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trade?between?China?and?the?“the?Belt?and?Road”?countries?from?the?perspective?of?accelerating?the?deep?integration?of?the?digital?technology?and?the?traditional?agricultural?trade,?cultivating?highlevel?talents?in?the?field?of?digital?trade,?creating?a?digital?technology?community?of?sharing?and?coresearching,?and?coordinat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open?cooperation?and?national?security.
Key?words:digitalization;?digital?technology;?agricultural?trade;?“the?Belt?and?Road”;?highquality?development
(責任編輯:張麗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