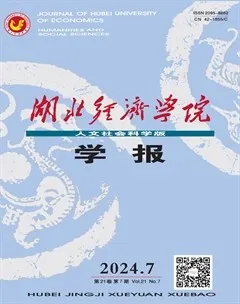新時代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實踐進向
摘 要:政治學研究扎根現實情境,走進田野,拓寬新時代中國政治學研究進向。建構中國特色政治學,回應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現實關切。田野調查耦合中國政治學理論創新的內在價值,助益政治學學術概念建構與研究范式轉型。針對新時代中國政治學發展中的基礎理論應用偏差、研究范式與研究情境脫嵌、研究價值的挖潛拓展不足等現實梗阻,可從田野理論再造、田野空間嵌入與田野價值創新三個維度建構契合中國本土研究情境與政治實踐的政治學研究創新發展路徑,實現中國政治學守正創新的價值歸向。
關鍵詞:田野調查;研究進向;范式轉型;政治實踐;概念建構
作者簡介:吳合慶(1992- ),男,安徽安慶人,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政治與鄉村治理。
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1]是當前學科建設的重要任務,這為新時代政治學學科建設指引了前進方向。202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2]。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按照黨中央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以深化調查研究推動解決發展難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調查研究重要論述是堅持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抓手[3]。調查研究自身兼具學術傳統與問題意識[4],契合于新時代中國政治學研究,田野調查研究以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學理論基礎與研究范式成為推進政治學發展的創新動能。
一、田野調查耦合政治學理論創新的內在價值
將田野調查研究帶入政治學研究視域,拓寬政治學新的研究進向,創新新時代中國政治學概念的生成范式。政治學發展過程中,“田野政治學”研究發展逐漸受到政治學學界內諸多學者的關注,亦逐漸成為拓寬中國特色政治學研究的重要實踐探索。
(一)拓寬新時代中國政治學學科的研究取向
回溯中國政治學復建之初期,中國政治學的學科與西方政治思潮相互影響與包容發展。時代性的發展促使中國政治學理論基礎與研究范式的建構需要在借鑒西方政治理論基礎之上做出更具契合于本土研究的實踐探索。新時代,立足于新的歷史方位,政治學發展結合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引領作用取得一系列豐碩成果。社會現代性加速時代發展,政治學的發展更需要著力于實踐調查,從實際出發,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夯實政治學學科理論基礎。在國家治理現代化背景下,政治學的學科價值在于將理論價值轉化為治理效能,需要結合治理實踐,事實先于經驗,從實際出發。由此,以田野調查方法為本質特征的田野政治學的外在表征與之相對應,其“田野”具有雙重性,一是強調研究情境的現實性,二是強調研究過程的方法性。進言之,需要回溯至政治學研究的現實場域空間與遵循客觀事實依據,而田野政治學與之相契合,為政治學的研究取向的拓展提供了新視角,日益成為政治學話語體系現代化建設目標里新的研究進向。
(二)創新新時代中國政治學概念的生成范式
政治學自20世紀80年代初恢復重建以來,其學科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既有的傳統研究規范,也受到西方政治學深入影響,傳統西方政治學概念與研究方法的“舶來品”傳入中國境內。這為我國政治學學科提供借鑒與運用價值,但也存在著喬萬尼·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提及的“概念延展”(concept stretching)的問題[5],即西方的政治學的概念并不適用于各國政治實際的研究現象。由此而言,突破傳統研究范式的“桎梏”并實現研究方法的創新,需要結合新時代的特征引入新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視域。田野政治學是基于田野調查而形成的政治學研究路徑[6],其深入基層調查的研究現狀與研究成果,以及對豐富的經驗事實進行理論提煉,國內“華中鄉土學派”學者創造性地提出諸多符合中國研究情境新的政治學概念,諸如鄉政村治[7]、祖賦人權[8]、家戶制國家[9]、韌性小農[10]等。田野政治學順應政治學學科發展的時代性要求,也為政治學研究范式的轉向提供了新的思路與生成范式,為田野政治學的創新發展提供創造性的條件。
二、田野調查嵌入政治學研究體系范疇的邏輯性
思維方式決定了科學研究的路徑和方法[11],田野調查研究的思維方式創新新時代中國政治學研究的路徑與方法。田野調查研究以其時代性、客觀性與實踐性融合政治學理論、現象與概念的創新發展、內在機理與本土情境,構成新時代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
(一)田野調查的時代性契合政治學理論的創新發展
社會科學的建設發展折射出時代性的外在表征,其表現于社會科學的議題以及學科研究范式的變革與創新。新的政治實踐與政治現象涌現,為政治學學科研究供給豐富的研究資源與研究動能。一是在政治學議題上,基層社會治理以及鄉村治理始終是受到學界學者持續關注的研究主題,此類議題隨著時代的發展內生出的社會現實問題需要以客觀直接的形式去觀察、記錄與研究,總結政治實踐發展的經驗與規律。結合客觀事實的內在因素與現實背景,提煉出新的研究結果促成政治理論的豐富,作為深入實踐調查形式的田野調查方法逐漸走進政治學研究的視域內。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大數據、區塊鏈、ChatGPT人工智能等技術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的廣泛運用,政治學田野調查式研究方法也與時俱進地實現創新,在進行實地調查、深入訪談、問卷調查以及數據分析層面充分結合新技術的運用。這不僅提升了田野調查的研究效能,也為田野調查研究的真實性提供了技術維度上的保障。政治學研究的深入發展與時俱進,以田野調查方法提煉研究結論回應現實問題,契合社會科學發展的時代性,增進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創新性。
(二)田野調查的客觀性刻畫政治學現象的深層機理
學術概念是科學研究的基本單位,是研究思維的邏輯起點,更是學術共同體交互中的基本共識與通識性語言,以其高度概括性與凝練性詮釋出豐富的理論基礎。共識性學術概念的生成過程需要立足于實踐基礎與理論基礎,從事實層面出發,剖析社會現象的本質規律。概念建構的理論來源于實踐,實踐則促成理論的螺旋式上升,在理論與實踐的相互作用之中,田野調查以實踐視角檢驗學術概念在實際政治現象中是否具有共識性與普適性。田野調查方法是推動理論與實踐的相互作用的動力源泉,深入實踐調查的形式,發現新現象與既有研究的互質性,以客觀獨立的實證研究提煉出新的學術概念。這不僅促進政治學新概念生成,也在研究方法上實現了轉換,更在政治學概念上實現了原創性。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到“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以田野調查的方法深入社會研究,是收集概念構成元素的基礎性工作,從鮮活的故事背后探尋事實真相與還原本質,從而減少主觀因素與先驗論的干擾,使得新生概念緊密貼合基本事實與普遍現象,體現其概念的客觀性與原創性。
(三)田野調查的實踐性耦合政治學概念的本土情境
田野政治學是在學術研究中采取田野調查研究方法而形成“方法論學派”[12],在政治學研究視域實現了政治學研究扎根具體社會實踐的目標。這主要體現在從既往的文本分析與理論邏輯推演走向深入中國基層政治的實際情境,將規范化的政治理論知識與鮮活的實踐案例相結合。一是,田野調查方法發掘與培育了中國政治學本土性概念的生成土壤。新的政治議題的產生緊隨時代的發展而豐富,政治理論的新發現源于現實生活而創新。田野調查將具體研究方法與現實生活情境的深度融合能夠發現新理論與新概念產生的特殊情境,而這一情境與現實背景正是新概念生成的土壤,附有“本土性”內在屬性。二是,田野調查拓寬了本土性概念的生成空間。新概念的產生需要基于政治學研究調查實踐,隨著政治學學科現代化發展推進,建構本土政治學話語體系與政治學概念尤為重要。田野調查的方法立足中國實踐致力于本土政治學理論的建構,隨其深入推進,諸如新生問題與現象被學者關注,從而引起學術上的爭鳴與探討,激發出政治學學者的學術熱情。田野調查在發現諸多新的政治現象與政治實踐的同時,也為政治學本土概念的生成拓寬了廣闊的研究視野。
三、新時代中國政治學研究為何需要田野調查
西方的政治思想體系是建立在西方國家具體國情之上,在面對國家社會中復雜多變的新生問題,中國引入借鑒西方政治知識與既有的經驗總結并未能充分回應現實問題,對理論知識的創新運用與現實相脫節。因此,需要建構中國現代政治科學的方法論體系,著力于研究范式轉變和研究方法創新[13],結合當前政治學發展在理論基礎、研究范式與研究價值上的問題,新時代中國政治學需要以田野調查的實踐性補足其發展。
(一)基礎理論應用偏差與認知“路徑依賴”
在基礎理論維度上,政治學的田野調查研究是指向政治學學科理論基礎,需來源于政治實踐的規律與經驗的總結,而這一過程需要通過實地調查走向現實生活,走向田野場域,走向富含政治樣態與政治元素的現實試驗場。而政治學理論基礎與現實生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距離感,使得理論基礎缺乏一定的“田野性”與社會現實性。其一,初期政治學科重建后政治學理論基礎在借鑒于運用西方政治學知識時,忽略了政治學知識生成的過程,也未能充分地基于本土實地的田野調查研究背景,而直接運用于本土社會情境,因此存在著理論基礎與實際運用的偏差性。其二,“鏡像思維”[14]的效應桎梏了對政治學新理論與新知識的創新積極性。先入為主的認知偏差使得對政治實踐中的特有現象解讀存在著個人主觀性,缺乏客觀事實的真實性。這種鏡像思維模式造成總結出的經驗跨越了事實且遮蔽了來源于現實調查研究所建構理論基礎的實踐性,與實地調查的情境研究相脫節。由此而言,政治學的理論基礎的生成需要以實地調查形式深入實際情境中總結得出。
(二)研究范式與現實研究情境的雙向脫嵌
在研究方法維度上,“田野”不僅是研究場域,亦是研究方法。田野調查實踐的不足體現在政治學研究中局限于基于文本分析與邏輯推演的既有范式,與政治實踐的真實場域與空間存在一定的距離感。其一,實踐研究中田野調查法運用并不充分,體現在研究對象、研究地點與研究時間上。研究對象上,在方法運用過程中缺乏對關鍵研究對象的識別,使得最終的研究呈現偏差。研究地點上,對研究地點缺乏精準定位,研究的場域空間與案例分析不具有典型性與代表性。研究時間上,缺乏持續性研究的時間,抑或是研究的時長未能達到生成研究結果的要求,因而導致研究結論的偏差。其二,方法運用中缺乏對“概念源”的探索與新概念的創造。概念的源頭在田野調查中[15],政治學研究方法的運用也是新理論與新概念的產生過程,高質量與多元化的概念供給為政治學概念的可持續生成提供動力[16]。局限于文本研究方法與概念應用存在搬運式的借鑒,既有的理論與概念在操作化應用階段,需要結合其背后的生成機理與研究中的新問題與新現象相關聯。通過實地調查的方式發現并改進研究方法的不足之處,使之基于本質與現象的真實情境中得出新的理論與新的政治學概念。
(三)研究價值的深層挖潛與研究拓展不足
在研究價值維度上,政治學研究的價值不僅體現于學術價值,更應面向個體與國家社會整體發展。其一,研究主體性價值需要重視,彌補問題意識與人文關懷的缺失。人以及與之構成的復雜社會關系成為政治學調查研究的關鍵對象。“田野”提供調查研究的場域空間與方法手段,但“人”這一因素始終是貫穿調查研究過程的主體性要素。研究主體的價值性被忽略將弱化政治學調查研究中的問題意識,致使調查研究的結果偏差,學術的人文關懷未能具體表達,研究價值被遮蔽其中。其二,研究價值的深層挖潛不足,拓展研究有待進一步開展。政治學研究素材來源于歷史與現實情境,其深層價值的挖潛不可局限于文本研究與邏輯演進。研究視域的束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政治學調查研究的空間拓展,進而使得潛在的現實問題不被發現與解決,研究價值生成受阻。從宏觀層面研究政治學固然為國家制度建設與國外政治研究的借鑒提供一個傳統研究路徑,但廟堂連接著田野,“國家-社會”“制度-生活”“結構-功能”等研究范式不斷延伸學術研究的價值外延,政治學調查研究需要在現實情境中持續發掘價值的整體性視野。
四、田野調查何以賦能政治學研究創新發展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田野調查是政治學研究的關鍵性起點。政治學的繁榮發展需要結合時代性去拓寬其理論生產與方法創新的空間,基于社會運轉的“社會底蘊”[17],以田野調查的方式從構建本土政治學的話語體系與理論基礎等策略來構筑政治學學術共同體。通過政治學研究的路徑自覺、方法自覺、概念自覺推進田野政治學的范式自覺[18],進而豐富政治學理論基礎與提升政治學理論與概念的應用力,建構田野政治學式理論基礎、研究范式與研究價值來創新政治實踐的“中國之治”。
(一)田野理論再造:以田野實踐夯實政治學理論基礎
走進田野實踐的空間場域,擴容理論的存量與提升理論的增量,豐富政治學理論基礎。一是從田野深度提煉理論,理論蘊含田野底色。田野調查與政治學的深度融合形塑出更具中國特色的政治學理論,田野調查的直觀性與客觀性,消弭了因個人主觀價值偏好帶來的理論偏差這一弊病。此外,政治學理論需要接受現實問題檢驗,田野政治學調查實踐中生動形象的事實材料能夠支撐起理論在實際政治情境中的應用。以田野調查內嵌于政治學理論的創新過程之中,有助于政治學理論與政治實踐的有效銜接,轉化為理論基礎生成的內在驅動力因素。二是延伸拓展田野研究,理論回應現實關切。田野政治學的“田野”并非狹義的鄉村政治場域,而是隨著時代發展,政治學需要以實地調查與實地實踐的形式來促進新理論與新方法的增量生成。以田野實踐調查形式與遵循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是田野政治學的深層底色。新時代,以既有理論去回應復雜多變的新生問題,時而存在著缺乏解釋力與說服力的窘境。因此,緊扣時代性,探尋政治實踐與政治現象背后的生成機理,立足于客觀的直接調查,形成直觀感受,將一手調查資料經過加工處理形成具有學理性的經驗總結,通過理論論證,建構出新的政治學概念與理論基礎。
(二)田野空間嵌入:以田野調查調適政治學研究范式
“嵌入”由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基于經濟行為與社會結構關系提出的學術概念[19]。在研究范式層面,將田野調查方法嵌入政治學研究,走進田野調查的空間場域,把握調查的“進場-在場-退場”各環節,以充分增強調查研究的科學性。一是,統籌布局調查研究的前置工作,開啟“進場”。研究者需要在確定調查研究的時間、地點與人物,完善調查問卷與訪談提綱的基礎性工作。在定點觀察與走讀觀察過程中“入鄉隨俗”,積極融入當地文化氛圍,破解交流溝通壁壘,推進田野場域內“調查者”向“本地者”的轉換。研究者與調查對象的互動性構成田野調查的根本特征[20],增進互動性助益于研究者與調查對象主體間建立互信,便于研究工作的深入推進。二是,深度融入調查研究的過程環節,持續“在場”。田野調查堅持“現場主義”原則,研究者在調查研究的“第一現場”是獲取第一手真實資料的前置條件。研究的“在場”體現在時空維度上的特定地點與長周期觀察。研究者在場的“身臨其境”營造出“感同身受”的共鳴感,通過事物發生的因果機制與關鍵人物敘事過程方能還原調查研究的真實原貌。三是,提煉總結調查研究的客觀結論,理性“退場”。個人的情感偏向與價值判斷構成影響調查研究的不利因素,從而導致調查研究結論的偏差。恪守“價值中立”是研究者深入田野調查的基本原則,在實際調研過程中重視實地調查的重要性,剔除情感偏好,感知事實價值,厘清事實脈絡,在實踐中形成學術研究價值中立的自覺性。
(三)田野價值創新:以田野理念躍升政治學研究底蘊
創新田野調查的價值之于政治學研究體現在以田野理念堅持問題導向與研究價值生成。創新田野價值需要注重調查研究過程中對人這一主體的關切以及整體性把握研究進向與研究拓展。一是,突出強調田野調查的“人民性”,兼具人文關懷與問題導向。在政治學調查研究中,“田野”始終是歸去來兮之地,即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在人民群眾中發現現實中的“真問題”,解決“真問題”。“一枝一葉總關情”,政治學田野調查研究關系國家社會民生生活大小事,堅持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立場,傾聽人民利益訴求,并注重民主參與性調查研究。同時,帶著問題意識進入實際研究情境,將研究問題視為“靶心”,有的放矢。二是,把握整體性的研究視野,推進調查研究拓展。田野調查的時空差異導致難以把握整體性地研究進程,通過運用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兩者是田野調查的重要方法,將其與諸多研究方法相結合,多種方法的運用的最終目的是獲取真實可靠的研究結論。以長周期的實踐調查為基準,在持續的政治研究互動中,創新與調適研究方法形成科學合理的政治學研究范式。此外,田野調查研究基于“田野”這一現實研究情境,但又超越田野[21],在此基礎之上提煉出符合國情的本土化政治學理論,見微知著,拓展延伸政治學的研究價值。
五、結論與討論
政治學理論與概念的生成來源于現實的政治實踐以及對政治現象的剖析,并最終走進事實與服務于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創新是政治學發展緊隨時代性與現實性的必然條件。政治學研究扎根于現實情境,促成理論的“在地化”與“落地化”,從而與實踐調查相結合,獲得直觀感受與客觀事實經驗,增進政治學理論的理論價值與解釋力,創建具有中國特色、風格、氣派的政治學學科。由“殿堂”走進“田野”,政治學聚焦于問題意識、研究關懷、概念建構、理論創新與培養模式研究正是田野價值所在[22]。田野政治學的出場成為當今政治學學科中新的研究取向,同時代性結合衍生新的政治學概念與政治學理論,拓寬當今政治學研究的視野。建構本土政治學理論基礎與學術概念需要以田野實地調查的視角去創新政治學理論與研究范式,讓田野調查研究運轉起來,推進邁向人民的田野調查、邁向政治生活的田野調查,助益政治學學術共同體的建設。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EB/OL].(2016-05-18)[2023-08-31].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html.
[2] 習近平.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 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扎根中國大地 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N].人民日報,2022-04-26(01).
[3] 李麗,陳健.習近平關于調查研究重要論述的主要內容及時代價值[J].湖北社會科學,2023(4):25-32.
[4] 麻國慶.邁向人民的田野調查[N].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05-08(002).
[5] GIOVANNI SARTORI.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0,64(4):1034.
[6] 徐勇.田野政治學的核心概念建構:路徑、特性與貢獻[J].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1(1):4-13+157.
[7] 張厚安.鄉政村治——中國特色的農村政治模式[J].政策,1996(8):26-28.
[8] 徐勇.祖賦人權:源于血緣理性的本體建構原則[J].中國社會科學,2018(1):114-135+206-207.
[9] 黃振華.國家治理的家戶邏輯:基于田野政治學的分析進路[J].學術月刊,2021,53(7):91-104+178.
[10] 陳軍亞.韌性小農:歷史延續與現代轉換——中國小農戶的生命力及自主責任機制[J].中國社會科學,2019(12):82-99+201.
[11] 張康之.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認識[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8(2):98-107.
[12] 房寧.政治學為什么需要田野調查[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60(1):10-16.
[13] 房寧.談談當代中國政治學方法論問題[J].政治學研究,2016(1):2-9+125.
[14] 小理查德·J.霍耶爾.情報分析心理學[M].張魁,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15-17.
[15] 徐勇,郭忠華.政治學概念建構的意識與方法——基于田野政治學的視角[J].天津社會科學,2022(1):60-65.
[16] 吳春寶,李旻昊.“錯位式生產”:田野政治學概念研究歷程及其供給特征[J].理論導刊,2022(12):58-63.
[17] 楊善華,孫飛宇.“社會底蘊”:田野經驗與思考[J].社會,2015,35(1):74-91.
[18] 陳軍亞.中國式現代化與田野政治學的范式自覺[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62(4):64-70.
[19] 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M].劉陽、馮鋼,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5.
[20] 盧凌宇.政治學田野調查方法[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1):26-47+156-157.
[21] 黃振華.田野政治學:構建中國特色政治學的重要路徑[J].探索,2021(6):70-79.
[22] 白利友.政治學的田野:概念、場域及價值[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