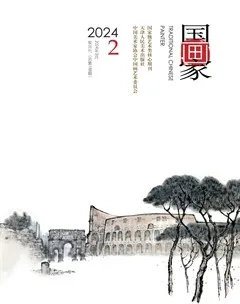國家級非遺楊柳青木版年畫的藝術(shù)特色與當(dāng)代傳承研究
基金項目:西北師范大學(xué)人文社會科學(xué)研究項目(NWNU-SKQN2020-51),甘肅省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基金規(guī)劃項目(2023YBWT03)階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天津楊柳青木版年畫因其特殊的區(qū)位環(huán)境,受到多元文化的共同滋養(yǎng),展現(xiàn)出雅俗共賞的藝術(shù)特質(zhì),在傳統(tǒng)社會受到各階層的廣泛青睞,成為中國木版年畫之翹楚。但隨著近現(xiàn)代以來社會、經(jīng)濟、文化的劇烈變遷,楊柳青年畫賴以生存的土壤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原有存續(xù)模式逐漸與現(xiàn)代生活疏離,遭遇嚴(yán)重的生存危機。為解決這一問題,應(yīng)搶抓非遺保護運動契機,采取以旅游商品化為實踐路徑的生產(chǎn)性保護策略,正確處理好傳承與創(chuàng)新的關(guān)系,既保持楊柳青年畫核心技藝、核心價值、核心特色的穩(wěn)定,又與時俱進,適時調(diào)整其題材、版式、工藝、材質(zhì)等外延性要素,以適應(yīng)客觀環(huán)境的變化,最終實現(xiàn)楊柳青年畫在當(dāng)代社會的活態(tài)傳承。
關(guān)鍵詞:楊柳青木版年畫;藝術(shù)特色;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生產(chǎn)性保護;當(dāng)代傳承
中國傳統(tǒng)木版年畫是以繪稿、刻版、印刷等工藝制作,供年節(jié)時張貼于門戶或室內(nèi)的民間畫,是繪畫藝術(shù)與雕版印刷技術(shù)的有機結(jié)合物。它發(fā)端于漢代的門神習(xí)俗,后隨著唐宋雕版印刷術(shù)的發(fā)展普及而逐步流行,并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1]木版年畫作為兼具藝術(shù)價值與文化價值的復(fù)合體,既呈現(xiàn)出鮮明的藝術(shù)特色與豐富的表現(xiàn)手法,建構(gòu)出一個獨特的繪畫藝術(shù)體系;又承載著特定時空下民眾的需求與希冀,蘊藏著民族的精神情感,展現(xiàn)著地方社會的立體影像。誠如馮驥才先生所言:“在我國燦如繁星的民間美術(shù)中, 木版年畫是最奪目的。”[2]它是傳統(tǒng)社會為我們留下的一宗重要民族文化遺產(chǎn)。
我國木版年畫在漫長的發(fā)展過程中,形成了數(shù)十個別具地域特色與藝術(shù)風(fēng)格的流派,其中以天津楊柳青、江蘇桃花塢、山東楊家埠、四川綿竹最負(fù)盛名,被譽為“木版年畫四大家”。而天津楊柳青年畫因其特殊的區(qū)位環(huán)境,受到多元文化的共同滋養(yǎng),展現(xiàn)出雅俗共賞的藝術(shù)特質(zhì),一直受到廣大民眾青睞,成為中國木版年畫之龍頭。[3]
一、楊柳青木版年畫發(fā)展概述與藝術(shù)特色
楊柳青鎮(zhèn)因當(dāng)?shù)厥a(chǎn)楊柳而得名,其地處京津要沖,水陸交通便利,尤其是明代南運河的開通,使毗鄰南運河,連接子牙、大清兩河的楊柳青成為交通重鎮(zhèn),商肆縱橫,經(jīng)濟繁榮。特殊的地理區(qū)位為楊柳青年畫的形成與發(fā)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明代中后期,楊柳青鎮(zhèn)開始出現(xiàn)畫鋪,成為楊柳青木版年畫之濫觴,后隨著清初的不斷發(fā)展,楊柳青年畫憑借吉祥喜慶且貼合民風(fēng)民俗的題材與內(nèi)容,別具特色又符合大眾審美情趣的設(shè)色、造型、構(gòu)圖而風(fēng)靡全國,至清代康乾年間,楊柳青已成為我國木版年畫的重要集散地。鼎盛時期,楊柳青有年畫作坊上百家,畫樣上千種,產(chǎn)品既進貢宮廷皇家,又遠銷大江南北,刻印地也不再局限于楊柳青鎮(zhèn)一地,逐漸蔓延至鎮(zhèn)南的三十二村落,形成享譽全國的“戶戶善丹青、家家能點染”的年畫之鄉(xiāng)。同時,特殊的歷史、地理條件,使楊柳青年畫除受到本土市井文化的影響外,還受到皇城宮廷文化、運河漕運文化以及舶來西洋文化的影響,相較于其他地區(qū)的木版年畫,其展現(xiàn)出獨特的文化特質(zhì)與藝術(shù)特色。
首先,就構(gòu)圖而言,楊柳青年畫較之他地木版年畫,更為注重構(gòu)圖的整體性與均衡性,即在尺幅之間展現(xiàn)出主次分明、賓主清晰、虛實結(jié)合、聚散有致的畫面布局。楊柳青年畫一方面繼承了傳統(tǒng)年畫構(gòu)圖的鋪陳堆疊,力求畫面的飽滿、厚實與勻稱。另一方面又追求飽滿之上的靈動與雅致,給予觀者視覺上的層次感,呈現(xiàn)生動且富含規(guī)律的變化,畫面繁復(fù)但不雜亂,有主次,有虛實,匠心巧思,既彰顯華麗富貴,又飽含輕盈典雅,給人以雅俗共賞之感。
其次,就造型與筆法而言,楊柳青年畫吸收了宮廷畫技,充分運用國畫工筆重彩之法,以達到細(xì)膩工致之效,如畫匠在繪制人物造型時,僅臉部刻畫就涉及十余道工序,連毛發(fā)亦描繪得細(xì)致入微,呈現(xiàn)出的形象真實鮮活,躍然紙上。楊柳青年畫還非常注重在造型寫實基礎(chǔ)之上刻畫人物的特點,勾勒造型過程中融入民眾的審美情趣與主觀意象,既寫實又傳神,形成各有諧趣、獨具特色的臉譜化造型。如楊柳青年畫流傳下來的畫訣所言:“畫貴者像訣:雙眉入鬢,雙目精神,動作平穩(wěn),方是貴人;畫財主像訣:腰肥體重,耳厚眉寬,項粗額隆,行動豬樣;畫寒士訣:頭小額窄,口小耳薄,垂眉促肩,兩腳如跛……”[4]可見楊柳青年畫在諸形象塑造上,皆具有固定程式,這種程式源于對事物寫實把握之上的藝術(shù)性加工,充分融合民眾的集體記憶,既追求形似又追求神似,展現(xiàn)出寫實與寫意的完美融合。
再次,就色彩而言,地處交通要沖,受多元文化共同影響的楊柳青年畫,其設(shè)色典雅柔和,與傳統(tǒng)木版年畫色彩艷麗、對比鮮明、視覺刺激強的風(fēng)格大相徑庭。楊柳青年畫一般采用紅、黃、藍綠、粉紅、黑五套色版,喜慶卻不失清麗,其整體色調(diào)多偏向高明度,常采用粉紅、粉黃、黃綠予以暈染,彼此沁潤,給人以自然清新之感。與此同時,楊柳青年畫強調(diào)設(shè)色的統(tǒng)一性,即呈現(xiàn)出一個主色調(diào)統(tǒng)領(lǐng)全局,其多用暖調(diào),以紅黃暖色為主,輔之以冷色調(diào)點綴陪襯,色調(diào)和諧,不似他處年畫那般五彩斑斕、爭奇斗艷。此外,楊柳青年畫制作常有一些文人畫家的加入,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往往貼合年畫主題與人物性格予以賦色。比如楊柳青年畫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文相軟、武相硬”色彩搭配原則,即強調(diào)文官賦色需色調(diào)溫和,多選用明度較淺、色彩不太飽和的淡黃、粉紅等“軟性”顏色;武官賦色需色調(diào)濃重,多選用較為凝重、明度較深的深藍、黑色、褐色等“硬性”顏色。在賦色過程中,楊柳青年畫還開創(chuàng)了套版與手繪結(jié)合之方式,尤為注重人物的開臉表現(xiàn),融合工筆國畫意蘊于版畫之中,設(shè)色自然、畫工精細(xì),兼具立體感與層次感,形成了所謂“高古俊逸”之風(fēng)格。
二、楊柳青木版年畫遭遇的現(xiàn)代性危機
楊柳青木版年畫以其獨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與文化意蘊,在傳統(tǒng)社會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歡迎。長期以來,廣大民眾視楊柳青年畫為祭祀祈福的實踐載體與生活希冀的象征性符號,其題材既包括神像紙馬、吉慶紋飾,又涵蓋戲曲傳說以及生活風(fēng)俗圖景。廣大民眾在年節(jié)之際將楊柳青年畫張貼于牖戶墻垣,有祛兇辟邪、祈福迎祥之意,亦體現(xiàn)出民眾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與愿景。可以說楊柳青年畫是依托于農(nóng)耕文明生產(chǎn)生活方式,蘊含著豐富民俗文化的民間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它反映了特定時空環(huán)境下民眾的審美情趣與功能需求,表達著傳統(tǒng)社會鄉(xiāng)民對于幸福美好生活的期盼,同時在潛移默化之中傳承著中華傳統(tǒng)文化。
但隨著近現(xiàn)代以來社會、經(jīng)濟、文化劇烈的變遷,楊柳青年畫賴以生存的土壤與環(huán)境發(fā)生了巨變,其逐漸與現(xiàn)代生活疏離與脫節(jié),遭遇所謂現(xiàn)代性危機。具體而言,在當(dāng)代社會,城市化進程的發(fā)展、科學(xué)主義的盛行、民眾審美情趣的變更、傳統(tǒng)年俗的淡化使得楊柳青年畫的傳承與發(fā)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
首先,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使楊柳青年畫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土壤。以往年畫張貼于院落大門上、堂屋內(nèi),既有功能性又富裝飾性。現(xiàn)今高速發(fā)展的城鎮(zhèn)化進程,使得民眾的居住方式從坊間院落變?yōu)槌擎?zhèn)樓宇,房屋門廳內(nèi)大都不再張貼傳統(tǒng)年畫,即便為美觀需要,也會張貼其他更為“時尚”的現(xiàn)代裝飾畫。
其次,科學(xué)主義的盛行瓦解了楊柳青年畫的實用性功能。近現(xiàn)代流行的科學(xué)主義,一度將以神像紙馬、吉慶紋飾為主要題材的傳統(tǒng)年畫斥為“封建迷信”,即便在當(dāng)代社會,年畫逐漸擺脫“迷信”帽子,但其原本具有的祈福納祥的實用性功效仍被消解,民眾不再篤信年畫背后蘊含的特殊功能,功能性的缺失使得年畫風(fēng)俗日漸式微。
再次,年俗的淡化與民眾審美取向的變化對楊柳青年畫傳承造成全方位的沖擊。年畫與春節(jié)、年俗唇齒相依,春節(jié)作為傳統(tǒng)中國民眾的實踐生活與共享文化空間,源于農(nóng)耕時代,由民眾通過迎神祭祖、燃放花炮、張貼年畫、吃年夜飯等年俗活動共同營造形成,同時春節(jié)文化空間亦反向賦能于上述年俗。隨著當(dāng)代社會傳統(tǒng)年俗的淡化與春節(jié)營造方式的變更,張貼年畫被從年節(jié)必備環(huán)節(jié)中篩除,加之民眾審美取向的變化,年畫這一農(nóng)耕社會盛行的風(fēng)俗習(xí)慣被新的年節(jié)風(fēng)尚所代替,楊柳青年畫藝術(shù)亦失去了基本依靠。
綜上所述,當(dāng)我們審視楊柳青年畫發(fā)展現(xiàn)狀時發(fā)現(xiàn),原本“畫店百家、年畫千種、畫版數(shù)萬”的盛景早已不復(fù)存在,年畫產(chǎn)地日益萎縮,傳承藝人寥寥無幾且后繼乏人,楊柳青年畫的活態(tài)傳承遭遇嚴(yán)重危機,面臨淪為“故紙堆”與歷史遺留物的風(fēng)險。
三、生產(chǎn)性保護:楊柳青木版年畫當(dāng)代傳承振興的必由之路
面對上述危機與困境,如何促使楊柳青木版年畫與時俱進,適應(yīng)當(dāng)代社會生活,如何使其在新時代新環(huán)境中找尋到適合自身的生存方式得以活態(tài)傳承,是今天楊柳青年畫保護工作中面臨的根本性問題。而近年來蓬勃發(fā)展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運動或成為解決問題的關(guān)鍵契機,作為國際、國內(nèi)雙重話語體系下均有鮮活呈現(xiàn)的系統(tǒng)性工程,其積累了許多有益經(jīng)驗,有利于我們紓難解困。
針對保護與傳承以楊柳青年畫為代表的傳統(tǒng)手工藝類非遺(2006年楊柳青木版年畫入選我國首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作名錄),近年來我國在實踐工作中總結(jié)與提煉出的“生產(chǎn)性保護”策略頗具實用功效與借鑒意義。所謂生產(chǎn)性保護即以保持非遺本體文化核心元素的真實性為前提,借助生產(chǎn)、流通、銷售等手段,將非遺及其資源轉(zhuǎn)化為適應(yīng)當(dāng)代社會生活需要的文化產(chǎn)品,[5]同時積極構(gòu)建文化空間,為非遺技藝與產(chǎn)品提供了制作、展示、交流的平臺。通過生產(chǎn)性保護能夠提升手工藝類非遺的自我造血能力,亦在客觀上促進非遺活態(tài)融入當(dāng)下民眾日常生活實踐之中,增強了非遺的文化吸引力,使其迸發(fā)出時代活力。
非遺生產(chǎn)性保護的重要實踐路徑即旅游商品化,它是以旅游市場需求為導(dǎo)向,挖掘、利用地域性、民族性特色鮮明的非遺資源,尤其是手工藝類非遺資源,因地制宜地開發(fā)出集紀(jì)念性、地域性、民族性、藝術(shù)性、實用性、時代性等特征于一體的民間藝術(shù)及相關(guān)旅游商品的過程。[6]針對楊柳青年畫面臨的現(xiàn)代性危機,實施基于旅游商品化的生產(chǎn)性保護策略,具有很強的貼合性與適用性,其解決了楊柳青年畫在當(dāng)今社會中依靠舊有運營模式無法實現(xiàn)新陳代謝的弊病,通過解決終端需求問題,實現(xiàn)了自我造血功能,以產(chǎn)品需求帶動保護與傳承,既符合楊柳青年畫的自身特質(zhì),又充分關(guān)照其所遭遇的現(xiàn)實困境。
具體而言,國家級非遺楊柳青木版年畫旅游商品化存在兩條路徑,即直接旅游商品化與間接旅游商品化。[7]直接旅游商品化是指將楊柳青年畫本體作為旅游產(chǎn)品予以商品化開發(fā)的過程。該過程首先考量旅游市場需求,調(diào)研分析游客群體對于特色旅游商品、旅游紀(jì)念品的訴求;繼而在堅持楊柳青年畫“核心符號”(核心技藝、核心價值、核心藝術(shù)特色)穩(wěn)定與原真的基礎(chǔ)上,以客戶需求為導(dǎo)向,調(diào)整“隨機符號”(題材、版式、材料等外延性要素)以適應(yīng)客觀環(huán)境與受眾需求的變化,深入挖掘、利用傳統(tǒng)年畫藝術(shù)資源,融合現(xiàn)代技術(shù)與思潮,返本開新,將傳統(tǒng)的楊柳青年畫轉(zhuǎn)化為現(xiàn)代旅游產(chǎn)品。
實施楊柳青木版年畫直接旅游商品化,一方面要因時因地因需擴充年畫題材,對于傳統(tǒng)年畫題材需有所揚棄,既根植于傳統(tǒng),著墨于地方性與民俗性,又擁抱現(xiàn)代生活,順應(yīng)市場需求,創(chuàng)新題材類型,開發(fā)當(dāng)代民眾喜聞樂見的題材內(nèi)容。另一方面,要突破傳統(tǒng)年畫原有功能的局限性,根據(jù)受眾需求,擴展年畫類旅游商品的用途范圍,借以提升吸引力,滿足游客多元化的消費需求。傳統(tǒng)年畫不再僅僅作為祭祀祈福的神像紙馬與打扮屋院的吉祥裝飾繪畫,要充分發(fā)揮楊柳青年畫設(shè)色典雅、高古俊逸、雅俗共賞、神形兼?zhèn)涞乃囆g(shù)特質(zhì),將其開發(fā)為掛歷、卷軸、手帕、絲巾、車掛飾品等,滿足游客的實用性需求,真正做到想受眾之所想,供受眾之所需。
當(dāng)然,實施傳統(tǒng)年畫直接旅游商品化的過程必然會涉及楊柳青年畫材質(zhì)、工藝的革新,在該過程中要合理利用新材料與新工藝,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中找尋連接點,在古今交融中尋求平衡點。比如在材料上,可以使用布藝、絲綢乃至合成纖維;在工藝上,可以將傳統(tǒng)工藝與現(xiàn)代工藝相結(jié)合,加入部分機械生產(chǎn),提高勞動生產(chǎn)率。以往手工藝類非遺生產(chǎn)性保護工作中,被質(zhì)疑最多的便是機械化規(guī)模生產(chǎn)與工藝革新會破壞手工藝的匠心獨具。傳統(tǒng)觀念普遍認(rèn)為,手工藝與機械化生產(chǎn)是二元對立的,手工藝是溫暖的用心之作,而機器生產(chǎn)往往是冰冷且缺乏感情的。實則兩者并不相悖,因為體現(xiàn)年畫價值與技藝的精細(xì)化環(huán)節(jié),一直是由傳承人手工繪制、雕版,傳承人的身體力行與匠心獨具牢牢地把握著“道”之氣韻,構(gòu)建出整個年畫作品之精髓;而機械化生產(chǎn)主要從事下料、切割、印制等工序,僅體現(xiàn)“器”之功用。在旅游商品化中將傳統(tǒng)工藝與現(xiàn)代科技結(jié)合,適當(dāng)融入一定機械化生產(chǎn)既不妨礙手工藝的匠心獨具,也提升了勞動生產(chǎn)率,有利于促進楊柳青年畫作為非遺旅游商品的規(guī)模化生產(chǎn)。
間接旅游商品化是指將楊柳青年畫中所蘊含模式化、符號化的圖樣、紋飾進行提煉、加工,融合現(xiàn)代工藝技術(shù)、設(shè)計理念與旅游消費者審美需求,應(yīng)用至旅游商品造型、包裝設(shè)計的過程。抽析于楊柳青年畫中的設(shè)計元素提升了旅游商品的文化性與歷史感,飽含傳統(tǒng)年畫元素的旅游商品,更富鄉(xiāng)土特色與民族情調(diào),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賦能旅游商品的范例。當(dāng)然,楊柳青年畫的間接旅游商品化不僅是借助傳統(tǒng)年畫所蘊含的獨特符號價值提升旅游商品文化附加值,促進旅游商品銷售的過程,其在客觀上亦推動了楊柳青年畫的傳承與發(fā)展,使其自然地貼近當(dāng)代,潤物細(xì)無聲地融入民眾的物質(zhì)生活與精神世界,從而提升當(dāng)下楊柳青年畫的群眾基礎(chǔ)與藝術(shù)影響力,達到“見人見物見生活”的理想狀態(tài)。
結(jié)語
楊柳青木版年畫憑借精致典雅、柔和細(xì)膩、神形兼?zhèn)涞乃囆g(shù)風(fēng)格,受到傳統(tǒng)社會各階層的廣泛青睞,成為我國傳統(tǒng)木版年畫之翹楚。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地方社會環(huán)境、民眾生產(chǎn)生活方式、大眾審美需求皆發(fā)生了變化,作為鄉(xiāng)土社會年俗必需品的楊柳青年畫似乎在當(dāng)下喪失了生存土壤,變得可有可無。面對楊柳青年畫遭遇的現(xiàn)代性危機,我們不能故步自封,實施僵化的保護策略,要主動擁抱現(xiàn)代化、全球化帶來的變革,因時因境轉(zhuǎn)變保護思路,搶抓非遺保護運動契機,借鑒非遺保護的新經(jīng)驗與好做法,采取基于旅游商品化的生產(chǎn)性保護策略。以旅游產(chǎn)品為引領(lǐng),讓楊柳青年畫重新走向消費市場,以需求拉動供給,在需求端解決楊柳青年畫的存續(xù)問題。當(dāng)然在這一過程中,需科學(xué)合理地處理傳承與創(chuàng)新的關(guān)系,既保持楊柳青年畫核心技藝、核心價值、核心特色的穩(wěn)定,又與時俱進,適時調(diào)整題材、版式、工藝、材質(zhì)等外延性要素,以適應(yīng)客觀環(huán)境的變化,最終實現(xiàn)楊柳青年畫在當(dāng)代社會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換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注釋
[1]劉虹、鄭植,《新媒體時代下木版年畫創(chuàng)新發(fā)展策略研究》,《國畫家》,2023年第4期。
[2]馮驥才,《中國木版年畫的價值及普查的意義》,《民間文化論壇》,2005年第1期。
[3]李莉,《朱仙鎮(zhèn)年畫與楊柳青年畫的藝術(shù)風(fēng)格之比較》,《民族藝術(shù)》,2012年第2期。
[4]王樹村,《楊柳青民間年畫畫訣瑣記》,《美術(shù)研究》,1958年第4期。
[5]《文化部關(guān)于加強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生產(chǎn)性保護的指導(dǎo)意見》,《中國文化報》,2012年2月27日。
[6]張中波、周武忠,《民間藝術(shù)旅游商品化的路徑》,《民族藝術(shù)研究》,2012年第6期。
[7]席輝,《中國傳統(tǒng)雕塑類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發(fā)展困境與生產(chǎn)性保護路徑探索》,《雕塑》,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