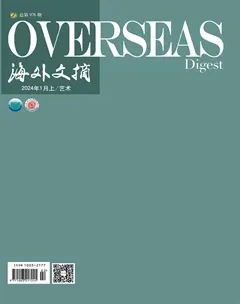博物館涉外講解中的跨文化意識
隨著我國文博事業的迅猛發展,前來參觀中國博物館的外籍游客絡繹不絕。當面對具有異國文化背景的海外游客時,文博接待人員能否跨越文化障礙,將展品中的文物信息精準地傳達給海外游客,是我們應該關注的一個焦點。本文基于博物館的數個案例,結合自身接待工作經歷,探討博物館涉外接待中應具備的跨文化意識,以便為文博景區的涉外講解工作提供借鑒。
1 博物館涉外接待講解中的跨文化性
跨文化交際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的交際;從心理學的角度講,信息的編、譯碼是由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進行的交際,也就是跨文化交際[1]。顯然,博物館涉外接待是跨文化交際的一個組成部分。不論是文物標識牌,還是展覽文本譯文,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不可能每一個文本的英譯本都面面俱到,這就要求從業人員在平時的工作中具備一定的跨文化意識。而當前我國博物館涉外接待工作中,從業人員的文化意識和能力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間,應當給予關注。
2 涉外講解中跨文化意識的必要性
對于常見的博物館而言,其文本在短時間內一般不會有太大變化,但在實際應用中,情況復雜多變,僅僅依靠背誦導游詞無法勝任實際工作。從業新人往往誤以為熟背講解詞就可獨當一面,殊不知講解詞只能起到參考作用,全靠背誦根本無法應對各種復雜的情況,尤其是在涉外講解中,隨機應變和跨文化意識能力必不可少,其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幾種因素決定。
(1)個別文物標識牌文本內容存在錯譯和漏譯,并且由于展牌文本的局限性,導致內容不完整或信息出現偏差。比如:在武漢市博物館青銅器展廳,有獸面紋爵,Bronze Jue(an ancient bronze wine vessel)with animal mask motif;獸面紋青銅爵,Bronze Jue with animal mask design。這兩件文物的標牌看似沒有問題,實則存在著錯誤。該標識牌英文采用的是音譯加注釋的方法。爵是中國古代青銅器上的一種,其表面精美璀璨的紋飾是青銅文化形成的重要標志之一,反映了青銅時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審美、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內容,是早期人民智慧的結晶[2]。而這兩個英文標識中,都出現了單詞mask,mask是口罩和面具的意思,獸面紋并非面具,所以譯文和中文意思出現了偏差,故講解人員在針對此類展品講解時,如果完全相信標識文本就會在講解中傳遞錯誤信息,降低講解質量。
(2)中西文化差異的存在導致英文名稱無法完整展現文物故事。比如我國的節氣文化,僅僅做簡單介紹顯然是不夠全面的,可以較為詳細講解中國的地理位置,農業生產與節氣的關系。由于我國是傳統農業大國,所以傳統節日多為時令性節日,并且慶祝的方式多以家庭為單位,以飲食為中心,比如春節的餃子、端午節的粽子、元宵節的湯圓、中秋節的月餅等。中國節日,不僅大多與農業節氣相關,而且節日的飲食中有豐富的內涵和寓意[3]。相比之下,西方節日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他們的節日多與宗教有關聯,并且慶祝節日多注重交往和感受快樂。所以,在介紹中國節氣時,應多從節日、節氣、過節方式、飲食等多方面做介紹,體現出中國節日與西方節日的差異性,才能讓外賓感受到中國傳統節日文化的魅力。
(3)功能主義目的論是德國翻譯家費米爾在萊斯的文本類型學基礎上不斷完善提出的翻譯理論,該理論認為:“在目的語的背景下,為目的語的目的,和目的語的環境讀者,產生一個文本”,所以翻譯的目的語文本,根據接受者的不同,會有所不同[4]。這種由同一種文本,因目的語接受者不同而產生不同譯文的思想,在翻譯史上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創新。博物館的旅游涉外講解,雖然不完全等同于文本筆譯,但這種思想完全可以借鑒于涉外講解工作。畢竟外籍人士擁有的文化背景和中國游客有著本質的區別,并且屬于不同文明的各國游客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性,同時,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們對于同一事物、同一景點的關注面也不完全一致。如果能根據實際情況,尤其是根據具體的講解對象,對講解內容的一些細節做出適當的調整,則能激發游客的興趣和好奇心,而這一過程中跨文化意識是必不可少的。
3 跨文化意識的應用
(1)從上文可知,由于文物標牌上可能出現的細微錯誤,講解人員應根據情況做修正,而不是過分相信標識牌的譯文。就上文的例子來說,講解員可以先介紹中國青銅文化和發展過程,爵的用途、制作過程以及青銅器的各種紋飾圖案。獸面紋爵的圖案又稱為饕餮紋,饕餮是神話傳說中極為貪吃的猛獸,它其實是古人融匯了各種猛獸的特征,同時加上某些幻想元素想象出來的。所以獸面紋并沒有mask(面具、面罩)的含義;而在此類圖案中,用animal一詞也不精準,因為獸面紋大多是猛獸的圖案,而小貓、小兔子等動物也屬于animal,但并不屬于獸類,故可將文本試譯為:Bronze Jue(an ancient bronze wine vessel)with beasts motif,同時在講解中說明,類似紋飾中的猛獸有的屬于legend animal,在現實中并不一定存在。由此可見,針對文物英文標識中可能出現的錯誤,講解人員應及時糾正,防止對外交流中文化信息的誤傳。
(2)同一元素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差異,在講解時應引起重視。比如中國科舉博物館導覽詞,在介紹到中國古代科舉有如下一段話。
明清學子沿著童試、鄉試、會試、殿試的程序逐級應試,通過后分別給予不同的科名,一旦考中進士,即被稱為“登龍門”,“魚”變為“龍”,從此踏上仕宦之路。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scholars would take the exams step by step, from metropolitan exam to the palace exam, then they would be given different titles according to the levels. As long as they could be selected as Jinshi, they were called “enter the dragon gate”,as if the “fish” became the “dragon”. Since then, they began their official careers.
在中國人眼中,龍是中華民族的吉祥物,是精神和凝聚力的標志。在漢語中,跟龍有關的詞語多為褒義詞,比如:生龍活虎、龍馬精神、龍騰虎躍等。但是在西方人眼中,“龍”是“A fabulous animal which represented as a monstrous winged and scaly serpent or saurian with a crested head and enormous claws”[5],這是邪惡的象征。在看到以上譯文時,西方人會很納悶:為什么從小接受教育、刻苦學習是為了長大后成為邪惡的人呢?所以我們應意識到同一元素在東西方文化中的差異性,對中國文化中的“龍”做補充解釋,才能讓游客避免誤解。
(3)注意文物表層信息傳達和深層信息的挖掘。
文物文本譯文與一般物品的名稱翻譯不同的是:文物不是普通的物品,其漢語名稱中本身就包含著大量的文化信息,在極為有限的篇幅之內,要將文物中所包含的所有信息都準確表達,本身就具有一定難度。從文物名稱看,一般來說有三層信息:表層文化信息、中層文化信息、深層文化信息。表層文化信息反映的是文物基本表象的直接性認知,是文物命名的落足點,說明了文物“是什么”;中層文化信息是從文化角度對文物進行的更深刻全面的描述,說明了文物是“什么樣的”,涉及人們的審美意識和文物本身的文化藝術價值;深層文化信息是指在文物背后所體現的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風俗、宗教、哲學、心理等方面的暗含文化信息,這是文物信息中最深層次的信息,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體現[6]。對于我國游客來說,感受和理解文物中深層信息并不難,因為其中的文化內涵對中國人來說是不言而喻的,但對于海外游客來說,那就大相徑庭了。由于跨文化因素的存在,某些面對中國游客三言兩語就能解釋清楚,甚至不用解釋都心知肚明的信息,在面對外賓的時候往往絞盡腦汁解釋對方也不知所云。比如:元青花瓷松竹梅瓶,其表層信息是青花瓷器,中層信息為青花瓷的造型、質地、產地、主題花紋、燒瓷技術等,而深層信息則為松竹梅的圖案寓意。深層的文化信息,對于中國游客來說顯然是不需要過多的解釋的,但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海外游客,并不知道松竹梅這三種植物的寓意。在中國文化中,松竹梅為“歲寒三友”,是高尚人格的象征,是對高尚品格的追求和面對困難時堅定不移的勇氣的象征;而在英語國家文化中,就竹子而言,英國本身就不產竹子,所以英語中竹子的寓意很少;松樹(pine tree)與漢語中堅韌不拔的寓意非常相似;而梅花(plum)在英美俚語中表示“獎賞、獎品”,這三種植物在英美文化中的寓意與我們的理解存在較大的差異。對于該類文物講解,除了說明文物的年代、質地、瓷器制造技術以外,對圖案的文化內涵也應詳細介紹,才能全面體現文物的價值。同樣一件文物,跟普通話講解員相比,外語講解員的講解內容可能會有偏差,這個偏差就是文物的深層次信息。對于中國游客來說這是不言而喻的信息,但如果沒有跨文化的意識,這也正是涉外講解中極其容易被忽略的內容,因為母語和母語文化造成的慣性思維會讓我們誤以為此類信息外賓也非常熟悉。恰恰相反,這正是對外傳播中最能體現中華傳統文化特色的部分,應加以提煉,不可遺漏。
(4)對中外游客講解的著重點不同。
多年前旅游從業者曾經對海外游客做過調查,讓他們在游覽南京后選出最喜愛的景點。令人意外的是,他們對國內游客首選的中山陵、總統府并不感興趣,取而代之的是湯山猿人洞、南京城墻和秦淮河夜景。這說明中外游客對景區的興趣點有著巨大的差別。畢竟對于總統府之類的景區,只有內賓和外籍華人才有興趣。就同一個文博景區來說,外賓和內賓的關注點也有較大的差別。比如:江南古典民居甘熙故居對于內賓來說,甘氏家族的歷史是重點,但是對于外籍游客,其建筑構造、風格設計、防火功能、排水系統等元素,才是他們的興趣點所在。此外,還有這座博物館的重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示,他們更希望看到手工藝人的各種工藝美術作品及其制作過程的展示。由此可見,即使是同一個文博景區,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性,其講解內容的側重點也應該有所變化,應根據需要做適當的調整,適應游客的需要。
4 總結
我國幅員遼闊,博物館和文物種類眾多,文化博大精深,除英語以外,其他語種需求分布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外籍游客不一定都來自英語國家,不一定都擁有西方文化背景,他們有可能來自與我們相近的東亞文化圈國度,也有可能來自中東地區,擁有伊斯蘭文化背景。因而在跨文化交際中,雙文化能力有時比雙語能力更重要。鑒于此,外語講解員在新展覽開展前,應盡可能多地搜集展品相關的資料,在充分理解文物內容的基礎上,仔細對每件展品的中外文本進行研究,并結合自己的語種和客源國的游客特征做適度的調整,力爭從不同文化背景的海外游客視角出發,細致解讀文物展品信息,從而讓外籍游客在游覽中國博物館的過程中能夠順利跨越文化障礙,深刻感受我國傳統文化的無窮魅力!■
引用
[1] 賈新玉.跨文化交際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2] 王冕.看懂青銅器[M].北京:新華出版社,2022.
[3] 李雯,吳丹,付瑤.跨文化視域中的英漢翻譯研究[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4] 劉軍平.西方翻譯理論通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9.
[5] 張福民.文化交融視域中的英語翻譯研究[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9.
[6] 李開榮.試論文物名稱英譯文化信息的處理[J].中國科技翻譯,2001,14(4):10-13.
作者簡介:李健(1981—),男,江蘇南京人,碩士研究生,文博館員,就職于南京市博物總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