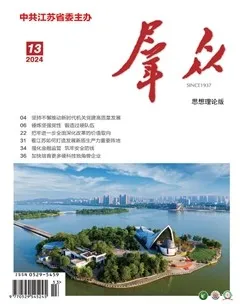深刻理解中華法治文明的精神內涵
以中華法系為標志的中華法治文明,是中華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獨一無二的歷史地位。2023年11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中華法系源遠流長,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蘊含豐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華文化的瑰寶。要積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賦予中華法治文明新的時代內涵,激發起蓬勃生機。這就要求我們深刻理解中華法治文明的精神實質,把握中華法治文明的內在邏輯。
準確界定中華法治文明概念
理解中華法治文明,離不開對中華文明形態的把握。站在中華文明高度,才能科學認識中華法治文明。綜合來看,學界盡管經常使用“中國法律文明”“中華法制文明”“中華法治文明”等概念,但卻很少對此類概念進行清晰而準確的定義。究其原因,一方面,難以對法律范圍有所框定;另一方面,文明概念本身也經常與文化概念相互混同,以至于常常因語境不同而有所差別。由于中華法治文明更多地體現了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特殊族群對法觀念和法規范的認知模式和行動邏輯,從而使其在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上表現出不同于其他族群的做法。鑒于此,可將中華法治文明界定為中華民族關于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法傳統。要進一步理解中華法治文明概念,需要把握“中華”“法治”和“文明”三個要素。
認同“中華”的歷史觀念。“中華”由“中國”和“華夏”組合而成。所謂“中國”,首先代表一個地理概念。最初為漢人自稱國家,即使在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也常常稱呼國家為中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已經成為統治一定區域的王朝對政權疆域和國家正統的認知概念。而所謂“華夏”,更多地代表著禮儀概念。最初,其蘊含著華夷之辨的意涵,代表了衣冠文物的禮儀文化。所以,中華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化概念,代表了中華民族自身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
厘清“法治”的傳統語境。從歷史來看,“法制”和“法治”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均有出現。盡管法治理解有古今差異,但是在本質上均體現了對秩序的認識。中國古代無論是圣人之治,還是圣法之治,其對秩序規則的理解始終不能脫離禮、樂、刑、政四個方面。這既代表著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也蘊含著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因此,必須要從廣義上理解傳統法治的范圍,而不能局限于刑罰部分。即使局限于法制范疇,也更多地指向各種制度,而非局限于刑事制度。
領會“文明”的價值目標。中國古代文獻既有“文化”概念,也有“文明”概念。文明大致指一種狀態,而文化則指一種方式。無論何者,其均站在人文立場之上,相對于蠻夷而言。此種做法也是近代文明和野蠻二分觀念的來源。在理解中華法治文明時,要站在人文角度來認識。人文在秩序維度上體現為人倫。而人倫文明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著鮮明的有序認識,其沒有停留在維持人的生存需要這一物質維度層面,而是上升到對天、地、人三才的認識這一精神維度。這種文明觀念必然影響到法律制度層面。
科學把握中華法治文明的基本特征
正因為中華法治文明具有獨特的精神內涵,因此也呈現出自己的獨有特征。眾多研究者歸納出中華法治文明各種各樣的特點,如人本主義、禮法結合、無訟調解,等等。然而,從文明形態來觀察,大致可以從價值、形式和路徑三個方面予以把握。
在價值目標上崇尚抑強植弱。中華文明具有重視人倫的文化傳統,其在道義上始終以民為本,強調重視民心向背,關注民生保障,關懷窮人弱者,從而在法律上始終站在弱者或者受害者立場之上,秉持抑強植弱的價值目標。一方面,對社會中弱勢群體,如對老幼鰥寡孤獨者等要從精神和物質層面予以關心和幫助;另一方面,對于社會中的強勢群體或者惡意行為則往往予以嚴格約束或者嚴厲懲處,如對于奸猾行為乃至黑惡勢力予以打擊,防止其滋生蔓延。
在法律形式上多元統一。中華法治文明在法律形式上的表現始終是多元統一的。這種多元性表現為:既重視禮樂規范,也重視刑名規范;既重視成文規范,如律令格式,也重視解釋規范,如決事比、故事、大誥、斷例、判例等,還重視不成文規范,如經義、家法族規、習俗習慣等。盡管隨著中華法系的發展,由于歷史階段不同,這些不同法律淵源形式名稱各異,但是無論哪一種形式,其均始終統一于人倫秩序之下。
在實施路徑上教化懲罰并行。中華法治文明在法律實施上注重教懲并舉,將教化和懲罰有機結合起來。一方面,積極揚善,通過道德禮儀、學校教育、民生保障等方式從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予以保障。在遇到婚姻家庭等民事糾紛時常常采取勸諭、調解、自省等方式。另一方面,嚴厲懲惡,通過律令宣講、公開刑罰等方式樹立刑名的威嚴性,使人知法避法。這種教化和懲罰方式既是官員處理政務的基本方式,也體現在聽訟斷獄之中。
重新認識中華法治文明的歷史定位
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唯一沒有間斷過的文明,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始終在中國區域生生不息。中華法治文明也是人類法律史上沒有間斷過的法律文明。盡管近代以來,由于外來侵略,中華法治文明從法律形式上一度出現斷裂,但是中華法治文明在語言和價值層面上始終得到普遍認同。伴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華法治文明的歷史地位應當重新被認識,因為中華法治文明無論在時間、空間以及所影響的群體上均具有深刻的印記。
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中華法治文明同中華文明一樣自古以來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這種連續性雖然經歷了先秦、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元明清等朝代的更迭,但其始終保留著中華法治文明的基本特點。即使近代以來法律變革使法律體系發生變遷,法律概念重新得以闡釋,但是作為法律表達的語言和詞匯始終離不開傳統觀念。
在空間上,具有擴散性。從考古來看,中華文明在中華大地上呈現出滿天星斗似的分布狀態。不過,通常認為,中華文明以中原為中心不斷向外擴展,從而將各地文化乃至域外文化匯聚在一起,實現融會貫通。這種匯聚過程并沒有改變中華文明的原生性。中華法治文明在空間發展上同樣如此。雖然不同朝代在中國各個地方建立政權,但是其法治模式始終圍繞政權中心向外拓展,從而呈現出同心圓狀態。
在群體上,具有全球性。中華法治文明的影響力并不局限于中國區域內,而是向周邊國家擴展,從而形成了朝貢法律制度。在歷史上,受到中華法治文明覆蓋影響的藩屬國有日本、朝鮮、越南等。同時,西域諸國在歷史上也一度接受這種朝貢法律制度的安排。盡管不同藩屬國在法律制定上有的直接采用中國傳統律令制度,有的則沒有專門制定律令,但是中華法治文明的域外影響力始終存在。此外,隨著東西方交流的日益頻繁,中華法治文明也對歐洲諸國產生深遠影響。這表明,中華法治文明所影響的民族和群體實際上已經超越東方,而遠播世界。
(作者系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責任編輯: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