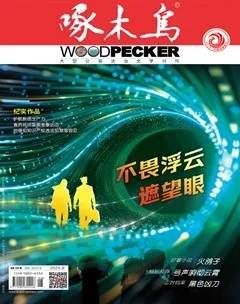木匠記

1
父親學木匠還不算樂天師父的正式徒弟,他沒有送樂天師父的拜師禮,也沒有在魯班像前下跪作揖。按當時學木匠的收徒儀式,應該由人介紹,經樂天師父同意后,選擇一個良辰吉日,送上一只雞、一條魚、一斗米、一壺酒、一只豬腿,然后點上一掛鞭子炮進屋。
進屋后,堂內點了香燭。樂天師父坐在神壇之下的一張雕花椅子里,我父親對他三叩九拜,敬奉了香茶,才算拜了師父。拜了師父的徒弟,一年內沒有工錢,第二年工錢有一半,第三年才得全工錢。這些,在拜師儀式上有三五個德高望重的見證人見證,和父親簽字畫押沒有兩樣。
父親之所以不算樂天師父的徒弟,是因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大家過的日子苦,沒有錢,更沒有拜師的雞魚肉,自然,僅憑一句話就跟了樂天師父。
我奶奶后來戲言,要說沒拜師,其實也拜了,在我家吃了一鍋蒸紅薯。當時樂天師父從鎮上趕集回來,路過我家門前進屋討碗茶喝,沒想到奶奶和他閑聊了幾句,說了父親學木匠的事,便邊吃紅薯邊拜了師。
跟了師的父親與樂天師父出門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糧倉。
那是吃紅薯的第二年,樂天師父家收了不少糧食,要擴建幾間糧倉。他想,教徒弟就從自家屋里建糧倉開始,先練練手,免得手生讓別人說閑話。他托人捎信來說,讓子光來吧,要學,就這兩天來。
那時父親有二十多歲了,學木匠確實不易,但還是去了。他趕早去的,到樂天師父家門前時,天還沒亮透。樂天師父開門見了他,說,這么早,先吃了早飯再說。
父親吃過早飯,樂天師父首先讓他摸木匠斧頭,練的是砍削的基本功,把一根根圓木劈出方木的雛形。木匠斧頭五六斤重,起先覺得輕,揮動自如。斧頭在圓木上砍削,一塊塊木皮屑應聲而落。父親想,這活兒,可以勝任。
可久了,手倦了,斧頭也就重了。一雙手掌上全是血泡。到了晚上,父親已經腰酸背痛,四肢像散了架一樣。
樂天師父見罷,從一側廂房端來一盞油燈,手上捏著針線,然后蘸上少許桐油,點燃一端線條,叭的一聲,穿過了父親手掌上的血泡。父親疼得齜牙咧嘴,樂天師父湊近父親的手掌,吮吸血泡里的血水,然后,又依此穿過了另一個血泡,再吮吸。
父親說,師父,斧頭還咬人呢!
樂天師父笑道,還才開始呢!
作為木匠,建糧倉是農村最常見的活計,也是一戶人家是否殷實的象征。在我們命田灣,誰家建的糧倉多,就說明這家糧食足,人過得很殷實。樂天師父之所以在原來的三個糧倉上又加建了兩個,也是他家過得衣食無憂的表現。
樂天師父住的是三廂式的吊腳樓,中間是堂屋,廂房在堂屋的兩邊,共分四間,前后各一。廚房接著左廂房,算是加蓋的披舍,全椽檁山架梁。而他要建的糧倉,在披舍里。
每天早晨,父親比樂天師父起得早,在廚房燒火煮飯。做徒弟的,應該如此。奶奶讓他來學木匠時就交代說,要幫師父干活兒,不要偷懶,還要給師父盛飯,端洗臉和洗腳水。父親嗯嗯地應著。
裊裊的炊煙從瓦檐上冒出來,被路邊的風吹散了。父親那時體質好,昨晚的血泡通過油針線的穿刺,已好了十之五六,結了血痂,也不那么痛了。他生了火,煮了飯,便幫著師父挑水、劈柴、擇菜。師娘聽到廚房有聲響,起來一看是我父親在做飯,喜了,道,這伢子,能學好木匠。
學木匠,得有一挑擔子的行頭,斧頭、鋸子、鑿子、刨子、木鉆、油擦子、墨斗、銼刀、馬夾、錘子、鏟子、魯班尺,一樣都不能少。就像讀書的人,少不了紙筆和課本。
樂天師父的披舍里要建兩個糧倉,地方有點兒擠,卻剛好能建下。父親依照樂天師父的教學,先學好了砍削,把圓木削成了方木;然后用魯班尺一量,再用墨斗彈線,用刨子刨去了多余的薄薄的一層木花;再用鑿子鑿眼、挖空、剔槽,才總算把糧倉建好了。
父親學會了建糧倉,是成為木匠的第一步,還不算真正入門,真正入門要建大活兒——吊腳樓。但命田灣是個糧窩子,過了八九月,只要一眼望去,田里的谷子黃澄澄堆了起來,像小山似的。
這時候村里的人趕著收稻田里的谷子,便爭著找父親打糧倉。那陣子,老木匠師傅忙得干不過來,只要會打糧倉,哪怕是個學徒也會被請進命田灣。
有一次,山上有戶人家請父親打糧倉,他挑著木匠擔子氣喘吁吁地走,心想,這是他第一次打糧倉,樂天師父沒有跟來,一定要打好。
陽光從山巔上流瀉下來,曬得松針都出油了。看一眼高高的山腰,那戶人家的屋檐好像隱約藏匿在一片樹林里。他放下擔子歇腳,一屁股坐在一塊大石頭上,坡下一個老人也挑著木匠擔子走來了,沖父親喊,你怎么坐在我的石頭上了?
父親脾氣倔,也不慣著老人,說,這石頭是你的?
老人的脾氣更倔,放下擔子,抽出擔子里的毛巾就敲了父親的頭,說,我是老師傅,你要懂得讓座。
老人這么一說,父親覺得有幾分道理,就起身讓老人坐,還掏出一包煙敬了老人一根。
歇了片刻,老人挑著擔從一條岔路走了。父親也挑起擔,翻過一個山口來到一個山坳里,乍然見到一棟破舊的吊腳樓。坪內青草萋萋,墻上青苔覆蓋。他推開堂屋門,里面蜘蛛網滿掛,塵土飛揚。喊了兩聲沒有人應,原來是一棟沒人的房子!
他環顧了一下四周,左廂房下有一片缺了一邊的石磨斜躺在荒草里;右廂房棄了一只沒腿的木長凳,幾乎被風雨侵蝕殆盡;朝前的一個窗子下可見一把半截的掃帚,上面拉滿了蟲糞;就是土坪那扇歪歪的籬笆上,也沒有一只鳥兒在鳴叫。
父親走錯路了,干脆坐在屋前矮塌塌的基腳石上掏出煙吸了幾口,順便打了個盹。可在這端兒,迷迷糊糊被人踹了一腳,整個人倒在了基腳石的荒草里。父親睜眼一看,原來是那個挑木匠擔的老人。他說,要不是看你許久沒跟來,我才懶得理你。小伙子,在深山老林里走,一旦迷路,今晚可能就睡在這荒山野地了!
父親也察覺到危險,跟著老人輾轉到岔路口,朝中間的路尋去。他七拐八拐好不容易走了一段,一抬頭,突然又看見了一棟吊腳樓,沒錯,就是某某家。他站在路上,都可聽見吊腳樓里的牛哞聲和人在坪里曬稻谷的吆喝聲。
在命田灣,一年種的稻谷幾乎就是這戶人家的全部財產。主人見了父親,接過擔子道,怎么這會兒才到,日頭都到頭頂了!
主人有責怪的意思,父親有點兒不悅,不想打糧倉了。可這是他重要的第一次,轉念一想自己還是學徒,讓主人責備幾句是應該的。他松開擔子,把家伙什兒拿出來,腳都沒歇一下就準備開干。
只是這一次開張有點兒奇怪,也許是心急、緊張,也許是手生,主人拿出的硬圓木,不是卡住了截木的鋸子,就是硬得咬去了斧頭的刃口。父親覺得自己被什么戲弄了,好像有人在逗著他玩。
他躁動得滿頭大汗,但不信邪,力氣又大,“呸呸呸”往手掌上吐了幾口唾沫,一斧頭下去,斧頭柄又震斷了。屋漏偏逢連夜雨,父親倒霉到家了!這時,主人把門關得砰砰響,臉上也陰云密布,或許他以為這個學徒真的只是學徒,自己請人太草率了。
好不容易熬到吃晚飯,父親一個人坐在土坪里歇涼,這時,白天的那個老人來串門了,他手里拿一條長手帕擦汗,坐在小板凳上看一地打糧倉的圓木,再瞄一眼可憐兮兮的父親,提醒道,開斧要請魯班呀!
父親本不信這個的,認為是故弄玄虛,可第二天開工他還是屈服了,在神壇下請了魯班,就這樣,手里的斧頭似乎使得比昨天順手了,在坪上砍呀、刨呀、削呀、挖呀,干得可歡了。
2
父親走南闖北碰多了奇奇怪怪的事,日子久了,也不覺學了一些跑江湖的招數。像請魯班,就是行走江湖時的一種炫技,有時我聽了也覺得很神奇。
這一年的一天,父親在給一戶人家打糧倉。陽光在杉樹上走,紅彤彤的光像個火球子。他摸出刨子,一個又一個箭步地在木頭上推,刨出了一卷又一卷的刨花。刨花很薄,卻很均勻。這叫刨子的功夫。主人的糧倉還要下點兒料,今天刨完,明天就可以組裝了。
父親賣力地忙著,偶爾抬起頭望一回滾過來的太陽,熱辣辣的。他脫下了上衣,打著赤膊汗水直流,身上的腱子肉也隨著他的起伏在涌動。
主人和他閑聊一陣,突然湊過來,說,木匠師傅,聽說你們木匠也會治病?
這廝也是病急亂投醫,父親刨了一遍木頭,順口道,我們的老祖師魯班能治。
我有個親戚,趕山被斷枝刺了,三年了,流著膿水至今沒好,可治?
沒緣呀,父親說,我們木匠沒進屋,魯班也就沒進屋,不能治呀。
哦哦,主人瞬間明白了,知是木匠的行走之詞。他說,碰巧了,我親戚也要打糧倉,他今年收成好。
主人的親戚姓劉,是個趕山的好手。一次劉老爺子進了山,跟著一排蹄印尋找在森林里隱蔽的麂子,卻不小心腳下一滑,一根尖尖的斷枝就狠狠地插進了大腿,血如泉水般噴射出來。幾個獵人把他抬去醫院,治了半個月沒有好,至今膿水不斷。說來奇怪,大腿上流著膿水,卻不見紅腫痛熱。
主人說,我的親戚碰到了麂子仙。
父親笑道,什么麂子仙,這是陰毒,叫木蛇開口,故而不紅腫痛熱,如蛇吐信子一樣,流著膿水。
你這么一說,還真像。主人佩服。
第二天破曉,父親就跟著主人進了他親戚家的吊腳樓。
劉老爺子也起得早,瘸著一條腿在門口迎接。他說,我還以為木匠師傅是個老爺子呢,沒想到這么年輕。
父親放下擔子,說道,老爺子,我們是一家呢,我也姓劉。
倆人寒暄了會兒,父親就準備拿木匠擔子里的家伙什兒。老爺子忙攔住父親,說,不急,先吃了早飯再說。
父親拗不過熱情的劉老爺子,也就不急著忙活什么了,只囑咐他的一個兒子把打糧倉的木料找來,需要多少圓木,云云。他兒子更不急,說,咱家今年收成好,不差師傅一頓飯。這話說得明白了,打糧倉慢慢打,無所謂,治劉老爺子的病要緊。
吃過早飯,父親就在堂屋里擺上了香案。他說,平時碰巧遇見,也就不講究,今兒個專門來了,就要講究點兒,得先在香案上擺一坨豬肉、一升米、三碗酒,再請魯班祖師爺。
劉老爺子也懂禮節,把東西都置辦齊了,還在一升米上插了一個紅包。父親斜著眼目測,不厚不薄,應該不比一天的工錢少。
這么有儀式感地請魯班,父親還是第一次。他虔誠地下跪作揖之后,點了香,燒了紙,便念念有詞了。他的詞含糊不清,嘴里咕嚕咕嚕說了一會兒,便把香灰和紙灰抓一把丟進了三碗酒里,說,好了!然后往每個酒碗里倒一點兒,遞給劉老爺子喝。劉老爺子也不嫌棄碗里的香紙灰,一閉眼,喉結一動,就吞了下去。
父親這般完畢了,一揮手,示意讓他們收了香案,劉老爺子把一升米上的紅包塞給了父親。父親也不推辭,這錢是替魯班收的,他不敢怠慢。但是,就在這端兒,父親才猛然想起沒看劉老爺子的傷口。他不慌不忙地撩起劉老爺子的褲管,左腿上有一個手指大的洞,正汩汩地流著腥臭的膿水。
父親說,我找幾樣草藥來外敷,應該十天半月就收膿汁了。
他走出吊腳樓,屋外的荒野里雜草豐茂,空氣中飄著淡淡的花香。這些有著生命的草都是一味藥,只是人不知怎么用而已。父親在田埂上找到了田基黃和半邊蓮,然后在山腰上找到了七葉一枝花。他陸陸續續找了十幾味草藥,搗爛成泥,敷在了劉老爺子的左腿上。
劉老爺子敷上草藥后,感覺腿上涼颼颼的,像有不少蟲子沿著傷口爬進里面的膿汁里。他說,劉師傅,這藥敷上去舒服,像一蔸含羞草,一碰葉子就收攏了,這感覺老帶勁了!
父親把木匠擔子里的吃飯家伙拿了出來,不無戲謔地說,我不是醫生,我是木匠,得給你打糧倉了。
父親看著一堆圓木,揀了一根,掄起斧子就劈開了。他從中午掄到下午,沒有停歇。陽光也從對面山轉到了后山,沒有停歇。父親說,我和太陽一個命,都是辛苦命,天天轉。
而我認為父親雖然辛苦,和太陽一個命,但是幸福的命。你沒見糧倉里的谷子,每一粒都是太陽的顏色?哪個人吃了它不是幸福的樣兒?
父親給劉老爺子打糧倉,也就是十來天的時間,這些天他除了摸刨子揮斧頭,還給劉老爺子換草藥。劉老爺子很是感恩,每天好酒好菜招待,父親也盡心盡力。不幾日,傷口的膿汁少了,最后竟然真的沒有了。老爺子一家欣喜若狂,說,劉師傅,妙手回春啊!
父親說,治好病的哪是我呀,是魯班祖師爺。
劉老爺子認為父親謙虛,說,不是你,我怎么能好呢?
嘿嘿,父親笑了,說,我只是冥冥之中受魯班祖師爺的差遣而已。
父親說的話劉老爺子不一定聽得懂,他說的其實就是一個緣字,緣在,隔著千山萬水也會見面;緣盡,哪怕門對門,面對面,也會失之交臂。
3
父親打了三年糧倉,到第四年的時候,樂天師父說,基本功練扎實了,該學建吊腳樓了。
父親聽了頓時像打了雞血,一連吃了三大碗飯。其實他早想跟樂天師父學建吊腳樓了,只是師父沒松口,也不好嚷求。而糧窩子里的人經過幾年的豐收,一個個家庭豐衣足食,一改過去單薄和空落落的貧窮樣子。有了糊口的飯,就想改變一下居住條件。
樂天師父把父親帶到一戶建吊腳樓的人家,見到不少的幫工和木匠師傅,還碰到了那次迷路時遇到的老人。父親很驚喜,說,我差點兒把你當魯班仙人了呢!
樂天師父聽罷覺得倆人是一樁神奇的邂逅。他認為父親魯莽,卻也甚為有趣,說,這是你師爺,我的師叔。
就這樣,父親卸下了那件荒誕的事,與師爺正式認識了。
建吊腳樓不像建糧倉那么容易,復雜多了。有一天晚上,樂天師父丟給父親幾本手抄書,讓他仔細領悟。父親看里面畫有不少符、寫了不少咒語,還有各樣吊腳樓的構建圖,暗暗下了決心,一定要弄懂、弄透它們。下了工,他就歪著頭瞇著眼細細地看,或用毛筆蘸墨,抄寫在自己的本子上。
這戶人家蓋的是一個大宅院,請的木匠師傅都是行業里的老師傅,會全套的方梁削柱,以及木雕設計與雕刻。父親被安排在一間左廂房,前臨資水,后靠靈峻的高山,云兒縹緲,常有鳥雀鳴叫、野獸奔走。主人穿一件白色襯衫,套一條大短褲,騎一輛載重單車,整天在家與建吊腳樓的場上來回跑。
場上熙熙攘攘。進入場上,是老房子拆后留下的兩根麻石柱子,柱子上左右雕著兩條尾擺頭揚的大龍,龍爪下懸浮著一圈圈的云朵;中央雕刻了一副鎏金的對聯,云:虎踞龍盤地,夏涼冬暖家。
過了石柱子,是一個大石頭掏出的水缸,水缸上架了一根空竹,泉水從空竹中流淌出來,指頭粗,落到水缸里濺得嘩嘩響。再往上看,水缸上遮了一棵大桂樹,有腿粗,枝葉茂盛,掩映了不少的陽光。
主人為建宅院已經請了三班木匠師傅了,最先的一班做了一個月,錯鋸了主人一根珍愛的紫檀木,被辭退。再來一班,可只會建吊腳樓,不會雕花窗,也被辭了。到父親這一班已是第三班,樂天師父說,你得拿出建糧倉的功力,與那些老師傅較著勁,要做得既快又細,說話還要討人喜歡,讓主人留下你。
父親觀察了場上的老師傅,覺得可以先從雕刻上露一手,他在打糧倉的三年中見過一些黃花梨木上的雕圖,并且琢磨著偷偷練過。他松開了木匠擔子,把工具一字擺開,在一根大圓木上構建了一幅浣紗圖。主人看他用刀細膩開闊,慢慢把西施的溫婉和柔美表現了出來,嘖嘖稱贊。而那些老師傅也圍攏了一圈,看父親把浣紗圖雕琢得豐富盡致、舒展有度,也倍感高興。
樂天師父說,浣紗圖分前浣紗和后浣紗兩部分,共有四十四組畫面,人物有兩百余個,再現了范蠡與西施在若耶溪邊相識,然后歷經吳越之戰,最終歸隱深山的故事。子光雕的,只是其中的一幅而已。
如果四十四組全雕琢出來,需要多久?主人問。
至少兩年。樂天師父淡淡地說。
兩年太久了,我哪有那么多錢。主人笑道。
在大宅院雕花窗,父親傾注了滿腔的熱情和才氣,他很珍惜這次機會,因為很多木匠師傅一生建了不少的吊腳樓,卻沒有碰到過一次做大宅院的機會,尤其是雕那么多的窗花。這一次是父親第一次建吊腳樓,更是第一次建大宅院,他感到是自己的造化,冥冥之中注定有這么一次學習和歷練的機會。
父親要雕刻的窗花很多,按照他對山水蟲魚鳥的理解,去雕出自己心中所想的模樣和畫面。但是,主人找來的木頭有些木質松軟、不緊密,不能雕琢,這就需要父親具備識木的眼力。他看著那些杉木、樟木、楓木、檀木、桎木、野梨木、櫻桃木、松木、棗木、油茶木,看紋理,聽聲音,察蟲蛀,忙得滿頭大汗。
有些木料是主人收了不少年的,像那根楓木,外皮已被風雨腐蝕了一層。不過更多的木頭被主人放在干燥通風處陰干,無裂縫,木質如新。父親把一堆一堆的木頭揀出來,一根根地量好長度和周長,然后用竹筆點墨,畫上標記。
父親在大宅院里雕窗花,其他的一些老師傅插不上手,慢慢地干脆甩手不管了,由父親一個人干。父親說,雕窗花,除了會識木,還要與雕刀心靈相通,人、木、雕刀,時間混長了,三者就渾然一體了。
父親摸刀,有大刀、小刀、彎刀、圓刀、平刀、斜刀、中鋼刀、三角刀、玉婉刀,刀光在木頭上發亮,錘子在刀的木柄上敲得砰砰響。
刀硬,木頭也硬。父親說,有些木頭硬,可把刀銼鈍了;但有些刀,無論木頭怎么硬,慢慢地也能將其銼鏤空了。
父親這么說,好像在詮釋一種人生哲理。
等樂天師父主持的大宅院完工了,是又一年之后。樂天師父操心操得人都消瘦了,像一根麥稈似的,頂著一坨麥穗。
在糧窩子里,誰家的吊腳樓建好了,定會擺酒席、贊梁、唱紫徽高照。這時,冬天的雪花從門對面的山上飄飄蕩蕩地落下來,云也是漆黑的,像屋檐上的鱗瓦,一層疊著一層。
這么冷的天,糧窩子里的人也會來。吃酒席的人看著大宅院里的雕花,說,刀筆遒勁,構圖古拙,圖與圖又互為相連,像這幅喜鵲躍紅梅,與那幅雄雞報曉寓意相通,代表吉祥如意。
我覺得那幅浣紗圖有味道,栩栩如生,圖中的西施細腰柔美,長裙飄逸,腳步輕盈。另一個人說。
樂天師父坐在堂中的八仙桌旁,喝著茶,聽著人們的贊賞,心里美滋滋的。
其實,學木匠多是傳承。父親在大宅院里的雕花,只是在傳承的基礎上有了少許的創新。這會兒父親沒有在大宅院,他被樂天師父派到另一個地方去了。
4
這個糧窩子,離命田灣有幾十里路,父親打糧倉時來過。
此糧窩子叫月塘灣,有草原一樣遼闊的稻田,風雪從稻田里過,稻禾黑黑的茬子上一片白茫茫的。他挑著木匠擔子來到一棟吊腳樓前,咚咚咚敲了敲緊閉的大門。許久,里面了無人響。
吊腳樓的主人出去了。父親想。
他放下擔子,推開了大門,只見院里早年種下的梨樹,枝頭邁過了瓦檐。墻角的一叢月季開著幾朵淡紅的花,在冰凌里搖曳。一群雞在雪地上巡回,踩出的爪子印像一片片竹葉。裸露于雪中的幾塊大黑石礫,仿佛是看見父親進了院子驚著一樣,紛紛探出頭來。
這時,從門外進來一個男人,四十多歲,戴一頂狗皮帽子,鼻涕清亮,身上的舊棉襖破了幾個小洞,露出了雪白的棉絮,褲管上沾了不少雪。見了父親,喊了一聲,師傅來了。
他把父親迎進屋,在火塘邊坐下,又摸出了一盒煙。父親擺了擺手,表示不抽煙。待把身上的雪寒烤盡了,這才仔細打量起了屋里的陳設,一張爛雕花餐柜,一張小小的木桌子,幾只木凳,還有一只少了一條腿。父親發現屋里的家具和這棟吊腳樓一樣,老舊、破敗。
主人說,這是道光年間建的一棟吊腳樓,出過一個進士,也是盤古開天地以來村里出的唯一一個進士。
那不要拆呀,修繕一下,又是一棟好房子。
不,太老舊了。
第二天,樂天師父也趕來了。主人叫來了不少幫工,樂天師父在院子前點燃了香紙,殺了一只雄雞,高高舉起,圍著吊腳樓遛了一圍,邊遛邊念念有詞。這是木匠師傅必做的祭祀儀式,據老人講,這樣做可保拆房時不出幺蛾子,人人平安。
好在院子不大,拆了幾天,木材就堆了半個土坪。主人見大伙身冷,便抱著那些木板和柱子當柴火燒。父親讓主人保管好的幾扇花窗也被他一斧劈開,燒了。
父親說,這是好寶貝哩,燒了可惜。
主人說,破窗爛木,有個鳥用!
樂天師父用手悄悄捅了捅父親,低聲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冬天的風像一路撒開的雪花,開滿了溝溝壑壑。土坪下的幾蔸白菜摟緊了身上的幾片葉子,在風中跺了跺腳。一條條的柳絲掛了一層冰,亮晶晶的,像裹了一層玉。一只鳥在荒草叢里跳躍、穿梭,似乎在尋找遺失的種子。
一天夜里,父親躺在床上,忽然聽見外面的雪地被踩得亂響。樂天師父緊張地推開了木門,說,你回去一趟吧。
為什么?
嘿嘿嘿,樂天師父笑了,說,我藏了幾扇最好的窗花和木雕,你給我送回去。
父親驚詫了,說,舍不得他糟蹋?
我們拿回去仔細琢磨、研究,老手藝也26Mg8BAouCpcFJUZtAdCrg==是老師傅哩。
糧窩子月塘灣到命田灣,山高路遠,惡獸時常出沒,前不久,一只老虎還拖走了一個夜行的人。這會兒月光冷淡,云兒烏黑,父親心里恐懼,但聽樂天師父要他回去,還是動身了。師父的事怎敢怠慢呢!
父親跟著樂天師父鉆進了月塘灣的一片竹林。竹子是楠竹,桿桿彎曲,被雪壓得“唆唆”地喘。空曠而幽暗的山溝里,寒風冷冽地哈氣,一只夜鳥在竹林里“餓——餓——”地叫,叫得人忐忑不安,心慌意亂。樂天師父刨開一堆亂草,只見有一小堆窗花和木雕,一扇百鶴圖、兩三扇幽谷蘭花圖,還有幾面梅花傲雪圖、祥云朝陽圖、碧海明月圖、千壑萬泉圖、進士及第圖、八仙圖,等等。
父親說,這么遠,肯定挑不了這么多,山路崎嶇不平,晚上不安全。
樂天師父道,那怎么辦?放這兒幾天了,再放幾天,陽光一出,雪一融化,這里的人上了山不就發現了么?
父親沉吟了一會兒,說,今晚送出月塘灣,明兒請假,說回去有事,咱們就挑回去了。
樂天師父同意了父親蹩腳的建議。
他們把窗花和木雕送出村時,已是夜里二三更了。回來后樂天師父興奮得睡意全無,一個人坐在堂屋里喝著米酒。他平時滴酒不沾,今晚為何如此,父親也沒看出個所以然來。
父親也不喝酒。他說,我至今只喝過一次,就是那晚陪師父喝。
師徒倆坐在堂屋里喝酒,等著天亮。當一壺米酒盡了,樂天師父和父親也醉了。樂天師父說,徒弟呀,我們木匠一代不如一代呀。
父親說,要我雕那些窗花和木雕,練一輩子怕也是妄想。
是呀……
天逐漸亮了,山里的風吹散了晨霧,一裊一裊地不見了。樂天師父已醉得如一攤稀泥。父親把樂天師父背進屋,放到床上,蓋了一床棉絮。這時,火塘里的木炭已經熄滅了,剩下一些冷冷的白灰。
等樂天師父醒來,已是中午。父親壓低了聲音說,師父,送窗花和木雕去。
樂天師父沒搭理他。等一會兒再叫,他才慢慢地起身。
他們趕到昨晚藏匿的地方,樂天師父說,子光,你來撥開那些荒草。
父親把手伸進荒草里,只覺空蕩蕩的。父親說,師父,不見了!
什么不見了?樂天師父急了。
木雕和窗花。
樂天師父一下子蹲到雪地上,喃喃道,完了,什么也沒有了!然后失望地望著父親說,子光,你說作為一個木匠,最重要的是什么?
父親頓時語塞,站在樂天師父的面前像一片干癟內陷的豆莢,不知所措。是的,父親沒有想過一個木匠最重要的是什么。
樂天師父說,木匠最重要的是精學精做,心細手巧,不斷學習前輩和身邊人的技藝。
父親低著頭,為昨晚自己的懶惰而自責。
你如果想成為一個大師傅,就必須這么做。樂天師父轉過身,淌下了一行渾濁的淚水。
父親成不了大師傅。許多年后,樂天師父走了,糧窩子也變了,整個溝里都是紅磚料石的小別墅,而家里的糧倉也變成了鐵皮大桶子。糧窩子徹底拋棄了木匠。
這時,父親的木匠擔子蒙了塵,鋸子、鑿子、刨子、木鉆、銼刀、馬夾、錘子、鏟子都生了一層銹跡。
責任編輯/吳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