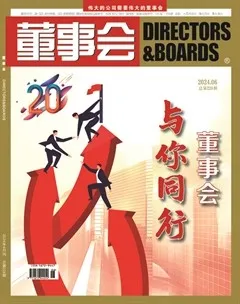利益相關者治理=利益相關者參與治理
編者按:
現代公司治理應超越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傳統觀念,通過賦予員工等利益相關者更多權力,以增強公司的透明度和效率,并提升員工的忠誠度。利益相關者治理有著多元化的實現形式,例如,在董事會中為員工代表留有席位,這能夠促進公司長期發展、平衡內部利益。
在我國7月1日起施行的新公司法中,員工參與公司治理的權利在法律層面得到了強化。新公司法鼓勵企業通過職工代表大會、董事會職工代表參與審計委員會或員工持股計劃等途徑,增強員工在公司決策中的參與度。然而,盡管法律在制度層面提供了支持,實際執行中仍面臨許多挑戰。例如,職工代表大會、審計委員會可能會流于形式,員工持股計劃往往只賦予員工分紅權,而缺乏對公司治理具有實質性影響的投票權和其他權利,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員工參與治理機制的效能。因此,要真正發揮員工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需要進一步的法律細化和實施監督,確保員工不僅僅是名義上的股東,而且能夠實際參與到公司的重大決策中。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法學院的布雷特·麥克唐納教授對于利益相關者治理的重要而精彩的觀點與分析,顯然值得人們關注與思考。
1931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阿道夫·伯利與哈佛大學法學教授梅里克·多德開啟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公司在社會中所扮演的根本性角色究竟是什么?伯利認為,公司的宗旨只是為了股東能夠賺錢,相反,多德則認為,公司的宗旨還包括為員工創造穩定的就業機會,為客戶生產更優質的產品,并盡可能為整個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他們發起的這場論戰持續至今,尚無定論。
目前,論戰的焦點在于公司目標和公司治理。著名法學教授史蒂芬·班布里奇為這場論戰提供了指引,他對公司治理的目的與手段進行了區分,指出二者不能混淆。這一區分具有指導性意義,無異于提供了一張戰場全景地圖。
公司治理:為誰治理
公司目標是論戰的兩個焦點之一,它主要討論什么才是公司治理的適當目的。傳統觀點認為,董事會的職責僅在于謀求股東利益的最大化。然而,有不少人也慢慢轉變了態度,他們認為,董事會的關注重點也可以稍稍傾向于其他利益相關者。而公司治理的手段則關乎應該授權給哪些內部人員。
班布里奇主張,強有力的董事會追求股東利益的最大化,而范德堡大學法學教授瑪格麗特·布萊爾和康奈爾大學法學教授林恩·斯托特則認為,應當賦予董事會權力,并要求其協調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哈佛大學法學教授盧西恩·貝布丘克對班布里奇的論述表示支持,他也認為董事會應追求股東財富最大化,不僅如此,他還希望看到股東能夠讓董事會為追求股東財富最大化承擔更多責任。但是,有的人既同意貝布丘克關于公司治理手段的觀點,即董事會需要承擔更多責任,又同意布萊爾和斯托特關于公司治理目的的觀點,即董事會應當平衡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這兩種觀點該如何取舍呢?在這一問題上,筆者與明尼蘇達大學法學教授馬特·博迪、南衛理公會大學法學教授格蘭特·海登等學者的觀點不謀而合。我們認為,如果在治理目的上能夠考慮利益相關者,在手段上就應當賦予他們治理權力。畢竟,如果公司治理是為了利益相關者,那么由利益相關者進行治理自然也理所應當。
那么誰是被治理和管理的對象呢?以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為代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羅納德·科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奧利弗·威廉姆森和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奧利弗·哈特等學者認為,員工是真正被管理的群體。企業若想實現盈利,通常需要管理者善用自由裁量權,例如,他們可以指導員工如何利用該公司的各類資產。雖然各位股東也可能受制于管理者們的自由裁量權,但由于股東是出資方,所以這一限制的強制性較弱,管理者可以在有限的合同限制下利用這些資本,從而追求股東的利益。而這些合同或者不連續的交易事實上也決定了債權人、供應商和客戶的權利與義務。
在關于治理目的,即公司治理為誰服務的爭論中,主張股東財富最大化的學者提出了以下幾個論點:
·明確的評價標準可以促使管理者對公司事務更負責任;
·在某些假定條件下,最大化地提高公司利潤能夠同時最大程度地增加社會福利待遇;
·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創造利潤,至于社會目的的實現,則通過立法機關制定的就業保護法案、消費者保護法案等法律保護其他利益相關者;
·股東是剩余索取權人,享有分紅權益,他們的利益需要得到保障,畢竟,他們的利益與公司利潤的最大化緊密相連,因此,也與社會福利的發展趨向一致。
但支持利益相關者主義的學者對此予以辯駁:
·股東財富最大化在實踐中難以實現,因不夠清晰明確;
·在各種外部因素影響下,即使公司能實現利潤最大化,社會福利也無法隨之最大化;
·雖然有其他領域的法律規定了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權益,但事實上往往收效甚微,而公司治理為平衡利益的相互沖突提供了一種更為靈活的方式;
·股東是剩余索取權人,但員工也是剩余索取權人。
利益相關者治理:新問責機制的發展
然而,貝布丘克對利益相關者治理提出了不一樣的看法。他的觀點聚焦于管理者問責機制的缺位,該問題的直接后果是公司將出現更多的自我交易,難以達到理想的經營效果,從而傷害到利益相關者自己。但是,這種觀點建立在一種假設之上,即通過限制問責機制的適用范圍和程度來推進利益相關者的治理,從而給予董事會和高管權力。這種觀點是對布萊爾和斯托特的“團隊生產理論”的合理質疑。然而,利益相關者治理可以促進新的問責制的誕生,從而對股東以外的利益相關者負責,它可以積極地賦予一些利益相關者權力。對美國上市公司而言,這似乎略顯激進,對其他的發達國家則較為合適。德國的共同決定制度最為顯著,此外的歐洲大部分地區,例如英國,在公司治理時也都借鑒了德國的先進經驗。當然,如果我們關注除上市公司之外的美國公司,可以發現諸如消費者合作社、生產者合作社和員工合作社等組織形式的存在相當普遍。同時,還有一些公司的治理結構內在邏輯是利益相關者治理,例如某些合伙企業的所有權是由其內部的一些服務提供者所持有,律師事務所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例子。
在確定公司治理的適當目的時,我們通常會運用利益相關者被賦予獨立權重的方法,畢竟,對我們而言,最容易論證的其實是利益相關者治理的正當性。如果我們真的希望董事和高管能夠做出有助于股東以外的其他人的決定,我們就不應該讓他們最終只對股東負責。在目前的權力格局下,以犧牲股東利益為代價,明確偏袒他人利益的董事將面臨被起訴或被撤職的嚴重風險。當壓力來臨時,受這些規則約束的人自然會偏袒股東。如果這不是我們想要的,就應該改變這些規則。即使對一些將股東財富最大化視為公司正確目標的人來說,他們也應當認識到,在一定限度內賦予利益相關者權力是合情合理的。很多時候,所謂“實現更好的工作目標”不僅僅是為了幫助員工做得更好,也是在促使公司提高效率和盈利能力,從而有可能增加股東的財富。正如貝布丘克的觀點,增加對股東的問責制可能會使其他利益相關者受益,我和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教授本·內爾持有相同觀點,增加對利益相關者,尤其是員工的問責制也可能會使股東受益。
賦權利益相關者:以員工為中心
既然公司治理是為了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那么是否也應該由利益相關者擔任治理者來管理公司?著名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家布萊爾和斯托特給出了否定答案。他們主張,董事會應該表現得更為強勢,從而有能力來協調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但現實表明,現有機制無法確保董事會有能力來協調利益相關者,所以,我們應該進一步直接賦予利益相關者權力,讓利益相關者直接參與治理。而且利益相關者的治理事實上也將帶來許多好處:利益相關者可以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他們也有動力利用這些信息來實現公司效益的更大化;此外,賦予員工權力可以降低監督成本,并且,一旦這些利益相關者有了治理公司的權力,他們對公司的忠誠度也會隨之高漲。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論點中提及的賦予權力的對象,主要指的是員工。這與我的觀點不謀而合,也就是說,在所有利益相關者中,員工應該獲得最多的權力。但是,我們也必須考慮利益相關者治理公司所帶來的潛在成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決策成本,畢竟,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有可能會相互沖突。舉例而言,雖然支付給員工高額的薪水可以提高他們的績效,但在某些情況下,這也意味著客戶會負擔高昂的成本,股東們的收益也會隨之減少。所以,在我們考量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以及如何賦予他們權力時,也必須考慮到這些成本。
假設人們認為,激進地賦予利益相關者權力利大于弊,那么該方式可以在形式和內容上均實現多樣化。首先,哪些利益相關者能夠被賦予權力。正如本文所述,員工在被授予權力時處于獨特的有利地位,作為公司內部最為直接的被管理的人群,他們更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是,他們有強大的信息來源和自身動力來為企業運行保駕護航。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在各種維度上,可以通過各類方式得到不同的授權。在特定的利益相關者群體中,誰被賦予權力可能因人而異。他們有可能被賦予考慮不同問題的權力;有可能決定對該問題的表決是直接投票,還是選舉代表以間接投票;他們有可能擁有作出決定的唯一權力,也可以與他人分享,或者該群體可能只有否決權或咨詢權;他們有可能被賦予執行受托責任的起訴資格。
大型公司已經通過正式會議、問卷調查、社交媒體、員工資源小組和利益相關者委員會等多種方式讓利益相關者來治理公司,有些公司還為部分員工成立了工會。美國有合作社的形式,而其他國家,尤其是德國,也允許員工加入董事會參與決策。但是,對大多數美國大公司來說,它們并不會讓任何利益相關者都直接參與公司的決策。
員工是最有理由獲得授權的群體,授權的形式可以是授予員工董事會席位、建立職工委員會或增加更多的工會代表。公司賦予客戶、供應商和環保人士等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權力可以比員工少一些,這些人士可以加入利益相關者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建立初期以咨詢為主,而公司會漸進性地賦予委員會一些有限的權力,例如可以通過委員會來提名董事。通過諸如此類的改革,我們可以確保利益相關者的治理權、由利益相關者進行的治理以及為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而進行的治理將得到顯著發展。
布雷特·麥克唐納(BrettMcDonnell)系明尼蘇達大學法學院Dorsey&Whitney法學講席教授;編譯者李高宇、唐智彬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本文來自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BlueSky網站,內容基于作者此前發表的同題論文
編譯/李高宇唐智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