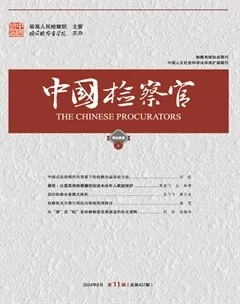民事支持起訴保障特殊群體權益問題思考
摘 要:民事支持起訴在經歷近幾年的探索、嘗試之后,逐漸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工作模式,案件量呈現較快增長趨勢,但依然存在知曉度不高、線索來源渠道不暢、案件類型較為單一、職能定位不夠清晰等問題。為做實做優民事支持起訴工作,檢察機關還需要在加強宣傳引導、豐富案件類型、強化內外聯動、推動多元共治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尤其是加強與相關特殊群體權益保障部門的溝通協作,對打開支持起訴工作局面將大有裨益。
關鍵詞:民事支持起訴 特殊群體 權益保障 協作配合
民事支持起訴是檢察機關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落實司法為民理念的一項重要舉措,是專門針對特殊群體的司法幫扶制度,目的是暢通司法救濟渠道,解決特殊群體不敢起訴、不能起訴等情形,讓特殊群體能夠共享法治發展的成果。
一、E市民事支持起訴工作實踐
H省檢察院下轄15個市州分院,E市是H省最小的地級市,下轄3個區。從全省數據看,自2019年初最高檢明確提出對特殊群體開展民事支持起訴以來,2019年處于認識和探索階段,全省未見關于民事支持起訴案件的描述和統計,2020年開始統計辦案數據,并且數量逐年增加,其中2020年110件、2021年151件、2022年521件、2023年1202件。[1]民事支持起訴工作在經歷探索、嘗試之后,逐漸形成穩定模式,案件量呈現較快增長趨勢,E市表現尤為明顯。全省15個市州分院中,E市作為最小的市院,2023年支持起訴辦案量149件[2],在全省占比達12.4%;可以說辦案成效顯著。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案件中,有將近87%的案件線索來源于相關部門的移送,這與2023年下半年E市檢察機關對全市相關特殊群體權益保障部門開展走訪調研、摸排線索工作息息相關。
在我國,司法救濟途徑并不是群眾維權的首要選擇,尤其是特殊群體,在權益受到侵害時,更傾向于向相關部門求助,較少訴諸于司法。因此,對特殊群體權益負有保障職責的相關部門往往掌握了諸多案件的第一手資料,他們對特殊群體權益保障的具體情況是最了然的,對于是否需要檢察機關介入開展民事支持起訴具有相當的發言權。從E市檢察機關走訪調研的情況看:
一是大部分農民工投訴案件,都能在勞動保障監察部門的協調下得到解決,小部分協調無法解決的案件則有可能進入民事司法領域,成為民事支持起訴的案件來源。例如,2022年勞動保障監察部門共受理勞動者投訴199件,其中,協調處理177件,協調未果22件,向檢察機關移送支持起訴線索5件,涉及農民工36人;2023年共受理271件,其中,協調處理219件,協調未果52件,向檢察機關移送支持起訴線索41件,涉及農民工73人。[3]強化與勞動保障監察部門協作,做好行政與司法的銜接,是拓展支持起訴線索渠道的有效手段。
二是申請法律援助的案件在形式上通常也是符合檢察機關支持起訴的案件,但實體上是否符合還要具體審查其訴求的合法性、合理性。例如,2022年司法局共受理申請法律援助案件236件,其中,涉及婦女43件、殘疾人12件、農民31件、農民工92件、老年人32件、未成年人20件、退役軍人3件、少數民族3件;2023年共受理223件,其中,涉及婦女16件、殘疾人26件、農民43件、農民工98件、老年人28件、未成年人10件、退役軍人1件、少數民族1件。[4]從數據看,農民工是申請法律援助的主要群體,婦女、農民、老年人、殘疾人亦占比較高,這些都是典型的特殊群體。此外,軍人軍屬、退役軍人也是近兩年檢察機關重點關注的群體。對申請法律援助的案件進行主動對接,對符合條件的開展支持起訴,是豐富案件類型、提升辦案效果的有效方法。
三是預付式消費領域的群體性消費維權案件多發,信訪壓力大,檢察機關或可開展支持起訴。近年來,預付式消費領域出現大量群體性投訴,全市12315平臺接到涉及預付式消費的投訴逐年增加,占消費投訴總量的比例越來越大。其中,2021年1308件,占比20.79%;2022年1923件,占比29.72%;2023年3633件,占比40.56%。[5]其中將近一半投訴是因商家關門停業引發的追償糾紛,許多經營者通過關門停業將資金損失轉嫁給消費者,甚至有經營者將圈錢跑路作為牟利手段,消費者追償十分困難。預付式消費維權已成為消費者權益保障的難點、痛點。檢察機關可以積極探索嘗試,對符合條件的群體性消費維權案件開展支持起訴,緩解政府信訪壓力,助力打擊不法商家的囂張氣焰,構建安定有序的消費環境。
二、民事支持起訴案件特點
以E市為例,近幾年的民事支持起訴案件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案件類型以農民工討薪案件為主
近幾年辦理的支持起訴案件有一半以上是農民工討薪案件,尤其在2023年上半年以前,農民工討薪案件占比在80%以上。這有一定的現實原因。因為每逢歲末年初農民工討薪難的問題都會成為社會焦點問題,最高檢于2020年部署開展了“發揮檢察職能助力根治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專項活動,自此農民工討薪問題成為檢察機關的關注重點,E市檢察機關與勞動監察部門建立了聯系機制,為民事支持起訴工作打開了最初的案源渠道。
(二)標的額不大
民事支持起訴案件通常屬于“群眾身邊的小案”,訴訟標的額較小,絕大多數在5萬元以下,甚至很多在1萬元以下。[6]原因在于,一是很多農民工是臨時性務工,隨工程開工而來、工程結束而走,工作時間較短,從1個月到幾個月不等,流動性較大,工資總額不多;二是有些公司前期經營狀況良好,未發生欠薪問題,后期因經營不善或資金鏈斷裂等原因導致欠薪,數額累計還不大;三是辦理的預付式群體性消費維權案件中,消費者充值金額一般不大,多數不超過1萬元。
(三)權利義務關系較為明確
民事支持起訴案件的標的主要是金錢給付,并且以給付勞動報酬居多,2023年下半年辦理的一批對消費者支持起訴的案件則是要求退還預付資金,除金錢給付之外通常無其他訴訟請求,法律關系較為簡單,權利義務關系較為明確,爭議焦點主要在于給付金額的多少問題,有部分案件如存在掛靠、違法轉分包等關系的還會涉及到義務主體的確定問題,總的來說爭議焦點較少。
(四)法院調解率較高
近幾年E市檢察機關民事支持起訴的案件,有67%是法院調解結案的,這與前面所說的標的額不大、權利義務關系較為明確的特點直接相關,同時因為有檢察機關支持起訴,事實通常已經查清,證據鏈較為完整,被告對檢察機關調取的證據認可度較高,且檢察機關在辦案中注重釋法說理、引導和解,支持起訴之后還會配合法院開展調解工作,為調解結案打下了基礎。
(五)上訴率較低
目前看,E市檢察機關支持起訴的案件還沒有出現上訴的情況。法院對支持起訴案件庭審大多適用簡易程序,大部分案件提起訴訟后經法院調解后達成和解協議。在法院作出判決的案件中,未發現上訴或者申請再審的情況,糾紛通常可以一次性化解,其原因與調解率較高的原因大體相同。
三、E市民事支持起訴工作存在的問題
(一)案件類型較為單一
如前所述,民事支持起訴案件類型以農民工討薪案件為主,消費者權益保護案件剛有辦理,其他案件類型諸如涉及老年人、婦女、殘疾人等權益保護的案件尚沒有突破,案件類型比較單一。主要原因是民事支持起訴工作還沒有全面鋪開,大多停留在某個領域,對其他領域的探索和摸排不夠。
(二)線索來源渠道不暢
E市檢察機關在走訪調研時,大多數單位人員表示不了解民事支持起訴的含義,也不知道檢察機關有民事支持起訴的職能。由于公眾知曉度低,相關部門也不了解,導致民事支持起訴的線索來源渠道不暢。近幾年辦理的案件,主要是從勞動監察部門獲取的線索,這還要得益于2020年根治欠薪專項期間建立的聯系機制。2023年下半年通過走訪調研與其他部門建立的協作機制還沒有完全發揮效用,一些部門對于線索篩查和移送較為被動,需要在日后工作中逐步推動機制運行落地生效。
(三)職能定位不夠清晰
在辦理的民事支持起訴案件中,當事人基于自身困難和對檢察機關的信賴,幾乎將整個案件都托付于檢察機關處理,從政策法規咨詢、證據調查收集、被告財產線索查詢到訴訟文書制作、起訴流程推進等,幾乎由檢察機關包辦,大部分當事人都沒有請律師或申請法律援助。檢察機關職能定位不夠清晰,介入過多,導致在辦案中承擔的工作量過大,不利于民事支持起訴工作的持續穩定發展。
(四)檢察和解率低
最高檢強調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促進民事支持起訴案件在檢察環節實現和解,以減少訴累,節約司法資源。但實踐中,真正實現檢察和解的案件很少,在E市不足3%。原因在于,一是法院對案件爭議具有最終裁判權,有些案件的雙方當事人對事實或證據存在爭議,需要法院運用裁判權對案件爭議一錘定音;二是申請人渴望獲得具有強制執行力的法律文書,檢察機關推動達成的和解協議不具有強制執行力,事后一旦一方當事人反悔或者不履行和解協議約定義務,另一方當事人的權益將難以保障。正因如此,有些案件在檢察機關的調解下,盡管雙方當事人已經對權利義務進行確認,但申請人依然希望檢察機關支持其向法院提起訴訟,以獲得法院的生效裁判。
(五)延伸履職不夠
一些案件存在一訴了之的情況,對于案件后續是否得到執行、特殊群體權益保障是否到位、法院是否存在怠于執行的情況等關注較少,特殊群體權益保障還面臨“最后一公里”的問題。因檢察系統對民事支持起訴案件的考核是以取得法院生效判決、調解書為標準,因此辦案人員對后續情況關注較少,實踐中有申請人反映一兩年還沒有拿到執行款。
四、做優民事支持起訴的對策探析
(一)積極探索嘗試,豐富案件類型
準確把握特殊群體的內涵和外延,明確民事支持起訴的范圍。特殊群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自身能力有所欠缺的人,如農民工、老年人、婦女、兒童、殘疾人、下崗職工等,由于生理和社會原因,缺乏經濟能力和訴訟能力,維權非常艱難;另一類是限于經濟社會結構原因,其訴訟能力明顯比對方弱的,如一些勞動者、消費者、特定事故受害人等,在相關勞動爭議、消費糾紛、賠償糾紛等案件中,責任方在專業知識和訴訟能力上具有顯著優勢,訴訟結構嚴重失衡,受害人得到賠償十分困難。[7]對于以上兩類群體,檢察機關可以積極探索開展民事支持起訴,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二)強化部門聯動,凝聚工作合力
一是內挖潛力。強化民事檢察部門與刑事檢察部門、控申部門的溝通協作,刑事部門辦理涉及特殊群體刑事案件時,發現存在申請宣告兒童父母失蹤或死亡、撤銷監護權、被家暴婦女離婚訴訟等支持起訴案件線索的,要積極移送民事檢察部門,構建民刑無縫銜接的保護網。二是外借助力。堅持“走出去”“請進來”的工作方針,在線索摸排、拓展案源上積極聯系、主動出擊。加強與殘聯、婦聯、民政、法律援助中心、人社等相關部門的溝通聯系,多渠道了解特殊群體維權需求,宣傳民事支持起訴價值功能,鼓勵相關單位積極向檢察機關移送案件線索,引導特殊群體依法維權。
(三)堅持有限介入,維護訴權實質平等
檢察機關要準確把握民事支持起訴制度的職能定位,將保障特殊群體訴權實質平等作為民事支持起訴的核心要義,始終堅持客觀公正的立場,避免過度干預、包辦代辦,甚至變相成為當事人的訴訟代理人。[8]在案件處理方面,著重審查當事人是否屬于特殊群體范疇、訴訟結構是否嚴重失衡、是否經過行政部門履職仍無法維權等實質條件,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存在訴訟能力差別懸殊的情況,則不宜支持起訴。在調查核實方面,堅持必要性原則,積極引導當事人自行收集證據材料、申請法律援助,對于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或自行收集確有困難的,檢察機關可依法進行調查核實。在與當事人關系方面,以尊重當事人意愿為前提,在充分釋法說理的情況下,對于是否起訴、是否和解、是否撤訴、是否上訴等事項充分尊重當事人行使處分權。在出庭方面,除當事人受暴力、威脅等特殊情形認為確有必要出庭外,檢察機關一般不宜出庭。[9]
(四)積極促進和解,盡早化解糾紛
檢察機關辦理民事支持起訴案件,要積極運用多元化解糾紛機制。經審查,認為可以通過協調、督促有關行政機關、社會組織等依法履職維護申請人合法權益的,積極協調、督促相關部門依法履職;根據案件情況和雙方當事人關系情況,檢察機關可以開展公開聽證和訴前調解,積極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監督員等參加,共同引導當事人達成和解;積極與法院協調,探索建立“檢察和解+司法確認”糾紛解決機制,賦予檢察和解協議強制執行力,消解當事人后顧之憂,推動民事糾紛實質性化解;檢察機關決定支持起訴的,可以聯合法院開展調解工作,促進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盡早化解糾紛,減少訴累。
(五)堅持多元治理,提升辦案效果
充分運用“支持起訴+”的辦案模式,提升工作質效。一是“支持起訴+跟進監督”。檢察機關辦理民事支持起訴案件,不能一訴了之,還要對法院的審判活動、裁判結果、執行活動進行跟進監督,確保特殊群體的合法權益得到實實在在的維護。二是“支持起訴+司法救助”。開展支持起訴后,發現因對方當事人下落不明或者沒有履行能力等,導致判決結果中的經濟利益難以執行到位,且原告生活困難,符合司法救助條件的,積極向控申部門移送司法救助線索,幫助弱勢群體渡過難關。三是“支持起訴+社會治理”。在辦理支持起訴案件中,發現有關方面存在明顯監管漏洞、相關單位怠于履行職責等情形的,及時向有關主管部門發出改進工作、完善治理的檢察建議或意見,促進社會規范管理,引領社會法治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