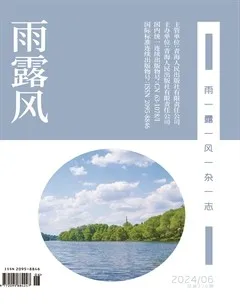從孔子文質(zhì)觀論《文心雕龍·情采》
《文心雕龍》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系統(tǒng)論述文學(xué)理論的專著,它體大思精,質(zhì)文并茂,在中國古代文論史上具有深遠(yuǎn)影響。作者劉勰將全書內(nèi)容概括為“文之樞紐”“論文敘筆”“剖情析采”三部分。[1]567今之研究者又將“剖情析采”分為“創(chuàng)作論”與“批評論”,第三十一篇《情采》屬于“剖情析采”中的“創(chuàng)作論”部分。劉勰尊儒崇圣,在繼承孔子文質(zhì)觀的基礎(chǔ)上對其進(jìn)行超越,形成自己獨到的見解,在《情采》篇中不僅論述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內(nèi)容與形式的辯證關(guān)系,還批判了當(dāng)時“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文壇浮靡風(fēng)氣,提出了“為情而造文”“述志為本”“聯(lián)辭結(jié)采”等創(chuàng)作要求,于古于今,都具有普遍的學(xué)術(shù)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情”“采”概念對于孔子“質(zhì)”“文”觀念的繼承發(fā)展
孔子對于藝術(shù)提出“盡善”“盡美”的要求,“善”指藝術(shù)作品思想內(nèi)容的純正真誠,“美”則從藝術(shù)形式方面做出規(guī)定,孔子反對“淫聲”,認(rèn)為“善”“美”統(tǒng)一才能造就完美作品。“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2]68孔子認(rèn)為樸實多過文采就容易粗野;文采多于樸實就趨向虛浮,文采和樸實統(tǒng)一才堪稱君子。孔子的“文”“質(zhì)”本指人的外在形式和內(nèi)在品質(zhì),但也可以從中看出孔子思想中提倡內(nèi)容與形式并重、追求文質(zhì)協(xié)調(diào)的特點,以及其所提倡的“盡善盡美”“文質(zhì)彬彬”的理想境界,這對之后劉勰文論思想的形成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劉勰尊崇孔子,儒家思想在其思想中始終居于主導(dǎo)地位。劉勰繼承了孔子的“文”“質(zhì)”說法并引入文學(xué)中,在《原道》《征圣》《通變》等多篇論述中都滲透著其“文質(zhì)彬彬”的美學(xué)理想。此外劉勰還對孔子的“質(zhì)”“文”概念進(jìn)行了發(fā)展超越,在《情采》中分別賦予其“情”“采”的新表達(dá)。“情”指情性、情理、情志,是情感與理性的結(jié)合,是由創(chuàng)作者思想情感所決定的文章思想內(nèi)容。這種解釋也與儒家講求“情理和諧”的情性觀有著很強(qiáng)的關(guān)聯(lián)性。“采”指文采,即文章的外在表現(xiàn)。“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1]367劉勰在此論述了構(gòu)建文采的三大要素:視覺上五種色彩形象摻雜而成的華麗辭藻;聽覺上五種音律排列產(chǎn)生的和諧聲韻;心靈上五種性情喚起的動人情感。劉勰認(rèn)為這三點是建立文采藻飾的具體途徑。
二、辯證統(tǒng)一的“文質(zhì)”與“情采”
劉勰尊儒崇圣,其情采思想不免受到孔子文質(zhì)觀的影響,兩種觀點之間具有一定的關(guān)聯(lián)性。二人辯證看待文章內(nèi)容與形式的關(guān)系,認(rèn)為二者相互依存,不片面強(qiáng)調(diào)某一方而否定另一方,主張以內(nèi)容為基礎(chǔ)和主導(dǎo),發(fā)揮形式的作用,使文章內(nèi)容和形式和諧統(tǒng)一。
(一)文質(zhì)互存,因文顯志——孔子“文”“質(zhì)”的辯證關(guān)系
“情欲信,辭欲巧。”孔子認(rèn)為感情要真實,言辭要美麗。《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中援引孔子語:“‘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之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yuǎn)。”其中含義是:“人們用言語表達(dá)思想,用文采使語言更完備。不說話,不能知道一個人的思想,所說的話語如果沒有文采,就不可以傳播到遠(yuǎn)方。”結(jié)合孔子對于“文勝質(zhì)”與“質(zhì)勝文”兩種片面傾向性的不滿,及其對于“文質(zhì)彬彬”理想境界的贊賞與追求,可知孔子主張文質(zhì)兼?zhèn)洌岢珒?nèi)容與形式和諧統(tǒng)一。
《說苑·反質(zhì)》:“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zhì)有余者,不受飾也。”孔子認(rèn)為事物的本質(zhì)如果已經(jīng)純正完美就不再需要加以裝飾。孔子提出“辭達(dá)而已矣”[2]193,認(rèn)為言辭足以達(dá)意便罷了。由此可知孔子在主張文質(zhì)兼?zhèn)涞幕A(chǔ)上更加注重質(zhì)的價值,主張內(nèi)容決定形式。
但是孔子的“辭達(dá)而已矣”亦非不要文采,他強(qiáng)調(diào)的是不能過分追求文采。正如孔子對于“美”和“善”的態(tài)度,他認(rèn)為“善”是“美”的根本和內(nèi)容,但卻也從未輕視或否認(rèn)過“美”作為“善”的表現(xiàn)形式的相對獨立性及其重要作用。“為命,裨諶草創(chuàng)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chǎn)潤色之。”[2]166孔子要求鄭國創(chuàng)制外交辭令時要經(jīng)過反復(fù)磋商、修改、潤色,公文尚且如此,其他文藝作品就更要處理好言辭與文采的關(guān)系。在孔子得意門生子貢與棘子成的對話中,則更為直接地強(qiáng)調(diào)了文采的重要性,《論語》顏淵篇中,面對棘子成“君子只需具備好的品質(zhì),儀節(jié)、形式等文采是沒必要的”的觀點,子貢道:“文猶質(zhì)也,質(zhì)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在這里子貢精辟地闡發(fā)了孔子的思想,論述了文采、形式的重要作用。
孔子認(rèn)為文章的內(nèi)容與形式是相互依存的,要使兩種因素適度地發(fā)展、和諧地統(tǒng)一,是其文質(zhì)觀的辯證之處。孔子主張文質(zhì)互存,先質(zhì)后文,因文顯質(zhì)。沒有質(zhì),文就沒有存在的依據(jù)和意義;沒有文,就無法反映質(zhì)的特征和價值。這種“文質(zhì)彬彬”理念中所體現(xiàn)的內(nèi)容與形式辯證統(tǒng)一的思想對劉勰也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
(二)情采兼?zhèn)洌橹鞑蓮摹獎③摹扒椤薄安伞钡霓q證關(guān)系
文質(zhì)并重、情采兼?zhèn)洹③耐ㄟ^“水”“樹木”“獸皮”等自然的特征屬性強(qiáng)調(diào)“文采要依附于一定質(zhì)地,質(zhì)地也需要文采”,他認(rèn)為文章內(nèi)容與形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文中“文附質(zhì)也”“質(zhì)待文也”的總結(jié)以及“虎豹無文,則鞟同犬羊”的比喻都體現(xiàn)了劉勰對于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中文質(zhì)觀的繼承與運用。
“言以文遠(yuǎn)”,強(qiáng)調(diào)“采”的重要性與創(chuàng)立文采的途徑。劉勰認(rèn)為圣賢的著作被叫作“文章”正是因為具有文采。“若乃綜述性靈,敷與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漁網(wǎng)之上,其為彪炳,縟采名矣。”[1]366劉勰認(rèn)為抒情、描寫、琢磨文字辭句之所以能產(chǎn)生光輝熠熠的效果,正是因為具有繁復(fù)的文采。劉勰還根據(jù)《孝經(jīng)》《老子》的內(nèi)容、莊周在刻畫事物時對于辭藻修飾的講究、韓非對于文辭綺麗之美的追求的具體事例,再次印證了辭采在文章中的重要性。《情采》篇最后提到的“言以文遠(yuǎn)”也強(qiáng)調(diào)了文采在文章流傳中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此外劉勰也具體劃分了文采的構(gòu)成,即“形文”“聲文”“情文”,分別在視覺、聽覺以及情感方面確立了文采藻飾的三要素。劉勰在《文心雕龍》的其他篇章如《聲律》《章句》《麗辭》等中也對如何創(chuàng)造“文”進(jìn)行了具體陳述,他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對辭采的重視與強(qiáng)調(diào),與孔子“言之無文,行而不遠(yuǎn)”的思想是一致的。
“情經(jīng)辭緯”,強(qiáng)調(diào)文章內(nèi)容對于文章形式的決定性作用。劉勰認(rèn)為黛料可以起到修飾容貌的作用,但若是要達(dá)到顧盼生姿的效果還是要依靠美好的本質(zhì)。同樣地,文采可以修飾語言使其得到美化,但巧妙華麗的美文還是出自作者的性情。文采繁復(fù)卻缺乏情思的文章,讀起來令人生厭。“故情者文之經(jīng),辭者理之緯;經(jīng)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1]368劉勰認(rèn)為情性、情理是立文的根本與源頭,文辭與聲律是具體的手段與途徑,文章的巧妙華麗應(yīng)以思想感情為基礎(chǔ)。從“情經(jīng)辭緯”說中可見劉勰以“情”為體、以“采”為用的“情主采從”觀念。
可見,劉勰受到孔子文質(zhì)觀的影響,主張在以內(nèi)容為基礎(chǔ)的前提下,充分發(fā)揮形式的作用,使得情采互凝,文質(zhì)并重,最終使文章內(nèi)容和形式達(dá)到完美的統(tǒng)一。《情采》篇中的這種“情主采從”思想也是對儒家“質(zhì)主文從”思想的進(jìn)一步推衍。
三、為情而造文——劉勰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所提出的要求
劉勰不僅提出了情采的概念與辯證關(guān)系,還針對當(dāng)時文人創(chuàng)作現(xiàn)狀,概括了兩種不同傾向,并為文人們的創(chuàng)作實踐提出了“為情造文”等具體要求,提倡向《詩經(jīng)》學(xué)習(xí),用精練的語言寫出真情實感,反對堆砌辭藻的浮靡文風(fēng)。而在劉勰本人的創(chuàng)作中,也可見其對于此原則的堅守與踐行。
(一)兩種不同傾向
對于處理內(nèi)容與形式時的不同傾向,孔子提出了“文勝質(zhì)”與“質(zhì)勝文”并一一進(jìn)行了反對。基于此理論加之對于情采辯證關(guān)系的理解,劉勰指出“為情而造文”和“為文而造情”兩種創(chuàng)作傾向并進(jìn)行對比分析。前者以《詩經(jīng)》為代表,由作者“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所作,這是劉勰所肯定的創(chuàng)作路徑;后者以辭賦家們?yōu)榇恚麄冊趧?chuàng)作中使用過分夸飾的文辭,為了寫作而造作感情,是不良的創(chuàng)作傾向。
“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泛濫。”[1]369在劉勰看來,為抒發(fā)情感而作的文章,言辭簡要精練,寫出了真情實感;為寫作而造作感情的文章,文辭過分浮華,內(nèi)容雜亂不實。劉勰指出當(dāng)時作家多宗奉辭賦家的浮靡文風(fēng),忽略了內(nèi)容的真實性,拋棄了《風(fēng)》《雅》中“為情而造文”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走上了“為文而造情”的錯誤道路,使得表現(xiàn)真實情感、合乎規(guī)范的好文章越來越少,而追逐浮夸文辭的文章則越來越多,這正是劉勰所極力糾正的。
(二)創(chuàng)作實踐要求
為進(jìn)一步發(fā)展推動“為情而造文”的創(chuàng)作傾向,劉勰提出“為情造文”“述志為本”“聯(lián)辭結(jié)采”等創(chuàng)作要求,要求作者從所要表達(dá)的情理、情思出發(fā)選擇恰當(dāng)?shù)谋憩F(xiàn)形式;確定情思后連綴音韻、聲律;思想端正后鋪墊展開文辭。這樣可以避免內(nèi)容為文采所掩蓋、情思為廣博的事例和辭采所淹沒,也就是“言隱榮華”情況的產(chǎn)生,使得文章“文不滅質(zhì),博不溺心”。劉勰認(rèn)為如此一來,內(nèi)容與形式在規(guī)范中得到統(tǒng)一,文章格調(diào)雅正,作者成為善于雕飾作文的才士,達(dá)到了孔子提倡的“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的理想境界。
在劉勰本人的創(chuàng)作中也能看出其對于內(nèi)容與形式和諧統(tǒng)一的執(zhí)著。劉勰在《序志》篇開頭解釋了“文心雕龍”一名的由來,“文心”是為文的用心,是此書的內(nèi)容;“雕龍”指寫作時講求文采的修飾,使文章如雕刻龍紋般精致,是寫此書所采取的形式。劉勰認(rèn)為自古以來的文章都是經(jīng)雕飾而成,以能夠更翔實、真切地表達(dá)內(nèi)容為目的,同時也強(qiáng)調(diào)雕飾要順乎自然,反對過繁過濫。如此,“文心”“雕龍”結(jié)合,可謂“質(zhì)文并茂”“華實相扶”。
在《文心雕龍》的其他諸多篇章中也可見劉勰情采觀的滲透貫穿。《征圣》篇中,“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劉勰提出將具有真實性的內(nèi)容與精巧的藝術(shù)形式結(jié)合起來,并以其作為創(chuàng)作的根本原則。在此篇中劉勰還認(rèn)為孔子文章雅麗,“銜華而佩實”,是內(nèi)容與形式都美好的統(tǒng)一體,也可見劉勰對于孔子文質(zhì)觀的繼承與發(fā)揚。文體論部分,劉勰按照其情采觀分析多種文體的發(fā)展,評論作家作品,提出相應(yīng)的寫作原則。創(chuàng)作論與批評論中,劉勰從“情”與“采”、“意”與“辭”、“風(fēng)骨”與“文采”等關(guān)系中更為系統(tǒng)地闡明了如何在創(chuàng)作中把握內(nèi)容的主導(dǎo)作用,做到內(nèi)容與形式的完美結(jié)合,并結(jié)合創(chuàng)作中的具體問題闡明其情采說。
四、“文質(zhì)觀”及“情采說”的價值與意義
孔子和劉勰關(guān)于內(nèi)容與形式的觀點,對矯正當(dāng)時的浮靡文風(fēng)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對文壇現(xiàn)實有著很強(qiáng)的針對性。同時,二者對于文藝內(nèi)容與形式的規(guī)定,對我國美學(xué)理論、文學(xué)理論的發(fā)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孔子多次提到并反對“鄭聲”,他認(rèn)為鄭國的樂曲靡曼淫穢,過于浮夸。與之相對,孔子認(rèn)為舜時樂曲《韶》的內(nèi)容與聲音和諧統(tǒng)一,美好極了。李澤厚曾說:“在孔子看來,真正美的、有益于人的藝術(shù)作品,其情感的表現(xiàn)應(yīng)是適度的。如果超出了應(yīng)有的適當(dāng)?shù)南薅取@樣的藝術(shù)作品就是有害的。”[3]孔子贊揚《關(guān)雎》做到了“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為糾正浮靡文風(fēng)提出的重大命題。孔子首次提出“文質(zhì)對舉”,其文質(zhì)觀是文質(zhì)理論的萌芽,文質(zhì)統(tǒng)一的思想由孔子奠定,從此成為中國美學(xué)的重要傳統(tǒng),“文質(zhì)彬彬”也成為中國人的一種審美追求,文與質(zhì)的關(guān)系從此便對中國文學(xué)理論批評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于文學(xué)的審美特征的關(guān)注度日益提升,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為對聲律辭藻的講究、對語言形式之美的追求。到了劉勰所處的時期,這種追求已過于泛濫而形成靡麗的風(fēng)氣,人們片面追求形式的奢華,忽略了內(nèi)容的質(zhì)樸,發(fā)展成形式主義創(chuàng)作傾向。因“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使“文體解散”[1]573,劉勰集孔子以來文質(zhì)觀之大成而發(fā)揚光大之。劉勰分析了當(dāng)時文人創(chuàng)作漸趨華艷的原因,針對“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1]369的文壇狀況,從作者品格方面入手,批判六朝形式主義文風(fēng),對糾正當(dāng)時靡麗浮詭的文風(fēng)具有重要意義。
文質(zhì)理論發(fā)展到南北朝時期劉勰的《文心雕龍》已趨于成熟,劉勰的情采觀源于孔子,經(jīng)過專門、系統(tǒng)的深化與闡發(fā)后,更加完善、成熟,不僅成為批判、糾正文章內(nèi)容與形式問題的有力理論武器,也為古代乃至現(xiàn)在的文學(xué)理論發(fā)展作出了重大貢獻(xiàn),具有普遍且有價值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作者簡介:高安(1999—),女,曲阜師范大學(xué)中國語言文學(xué)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文藝學(xué)。
注釋:
〔1〕劉勰.文心雕龍[M].王志彬,譯注.北京:中華書局, 2012.
〔2〕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
〔3〕李澤厚,劉綱紀(jì)主編.中國美學(xué)史(第一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