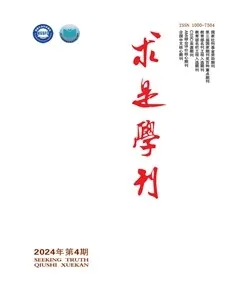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習(xí)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創(chuàng)性貢獻(xiàn)
摘 要:“中國向何處去”的道路尋找在思想文化上表現(xiàn)為“古今中西之爭”,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中體西用”,由進(jìn)化論背景到唯物史觀視域,這一爭論的演進(jìn)逐步深化。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破解“古今中西之爭”過程中經(jīng)過了長期努力,李大釗、毛澤東、鄧小平的貢獻(xiàn)尤為突出。習(xí)近平文化思想從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建設(shè)目標(biāo)的確立、“文化生命體”的現(xiàn)代文明觀的確立和通過全球文明倡議促進(jìn)形成人類文明共識(shí)體等方面,為徹底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創(chuàng)造了根本的理論條件、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礎(chǔ),這是習(xí)近平文化思想重要的原創(chuàng)性貢獻(xiàn)。
關(guān)鍵詞:習(xí)近平文化思想;根本條件;“古今中西之爭”;“文化生命體”;“人類文明共識(shí)體”
作者簡介:范鵬,蘭州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蘭州 730000);楊麗,蘭州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博士研究生(蘭州 730000)
DOI編碼: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4.04.002
習(xí)近平總書記指出:“經(jīng)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gè)時(shí)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①“古今中西之爭”對(duì)中華民族究竟意味著什么?我們?yōu)槠平狻肮沤裰形髦疇帯苯?jīng)過了怎樣的長期努力?習(xí)近平文化思想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創(chuàng)造了哪些理論條件?在中國式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征程上、在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進(jìn)程中我們究竟應(yīng)該如何正確認(rèn)識(shí)、妥善處理“古今中西之爭”?這些問題的科學(xué)解答通過學(xué)習(xí)領(lǐng)會(huì)習(xí)近平文化思想將更加明晰。
一般說來,在“古今中西之爭”的話語體系中,“古”主要指中國的過去,“今”代表著世界潮流主要指現(xiàn)代化;“中”無疑就是中國,而“西”則主要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其中相對(duì)發(fā)達(dá)的國家及其文化。當(dāng)然,正如馮契先生指出的那樣:“對(duì)‘古’和‘今’、‘中’和‘西’,不同的階級(jí)有不同的理解。同時(shí),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這幾個(gè)概念也有不同的含義。”②講“古”有的特指中國傳統(tǒng)社會(huì),有的則指的是古代中國的思想文化;說“今”有的指世界走向現(xiàn)代化的趨勢,有的則說的是“當(dāng)下”的中國;言“中”有時(shí)是地理概念,有時(shí)是“文化中國”;論“西”有人只說歐美的“船堅(jiān)炮利”,有的則側(cè)重是制度文化或思想文化。如此等等,如不分階段按類別“別共殊明層次”①,“古今中西之爭”就會(huì)成為一筆說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賬。為此,本文略加分疏,以期有一個(gè)大體的線索與基本的把握。
一、“古今中西之爭”的由來與演變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社會(huì)的主要矛盾演變?yōu)榈蹏髁x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這種雙重的矛盾日益激烈尖銳,催生了以反帝反封建為主題的近現(xiàn)代中國革命。“中國向何處去”成為仁人志士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直接動(dòng)因,也是當(dāng)時(shí)最迫切的歷史之問。災(zāi)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如何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奴役?如何才能推翻封建主義的重壓?如何才能從官僚資本主義的枷鎖中解放出來?一百多年來,無數(shù)志士仁人前仆后繼、浴血抗?fàn)帲瑸榈木褪菍で筮@個(gè)歷史之謎的答案。這個(gè)問題表現(xiàn)在思想文化領(lǐng)域就是“古今中西之爭”,其實(shí)質(zhì)就是如何通過向西方學(xué)習(xí),如何通過反思我們固有的傳統(tǒng),來找到一條救民族于危亡、使人民出火海的正確道路,從而使古老的中華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康莊大道。
(一)“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夷夏之別思維中的興中制西之策
近代一開始,魏源就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②的策略,主張向西方學(xué)習(xí),主要是學(xué)習(xí)其技術(shù)特別是“船堅(jiān)炮利”。顯然,在魏源眼中“中西”之爭主要是器物層面的,中西之別仍被置于夷夏之別的思維方式之中與“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認(rèn)識(shí)基礎(chǔ)之上。“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是魏源把林則徐在鴉片戰(zhàn)爭期間提出的“師敵之長技以制敵”③的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上升為“興中制西”策略得出的結(jié)論,其所撰《海國圖志》全面闡述了這一主張,這可以說是近代“中西”之爭的開始。其“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有一個(gè)前提就是“制夷”必先“識(shí)夷”。他明確地說:“然則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④夷之所以有“長技”者在于其不斷更新器物善變古成今。于是,中西之爭在魏源那里自然而然地演變?yōu)楣沤裰q,演變?yōu)橹鲝堊児懦山瘛N涸凑J(rèn)為,“時(shí)愈近,勢愈切”“善言古者,必有驗(yàn)于今矣”⑤。魏源雖然認(rèn)為中國應(yīng)該學(xué)習(xí)西方的技術(shù),變革不合時(shí)宜的器物,但中國治國的根本之道則無需變也不能變不可變,這就為后來的“中體西用”觀念提供了認(rèn)識(shí)前提。
(二)“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文化保守主義的價(jià)值觀念與思維方式
19世紀(jì)中期,清王朝統(tǒng)治者內(nèi)部出現(xiàn)了洋務(wù)派與頑固派的分化,頑固派繼續(xù)堅(jiān)持“祖宗之法不可變”,而洋務(wù)派則將“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付諸行動(dòng),向外國購買槍炮船艦,在國內(nèi)興辦大機(jī)器生產(chǎn)的工業(yè)企業(yè),客觀上向近代化跨出了第一步。19世紀(jì)60年代初,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qiáng)之術(shù)”⑥的主張。到了19世紀(jì)70至80年代,王韜提出“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⑦,至19世紀(jì)90年代,這一主張便被概括為“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⑧。體用是中國古典哲學(xué)的重要范疇,最基本的含義是實(shí)體與功用的關(guān)系。“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yùn)動(dòng)處,便是用”⑨,同時(shí)也是本體與現(xiàn)象、原則與方法的關(guān)系。在這三種含義中,都有體用不二、體本用末、體主用次、體源用流、體恒用變的意義。作為文化保守主義的價(jià)值觀念與思維方式,“中體西用”主要說的是中國傳統(tǒng)的天道學(xué)說、綱常名教的主體主導(dǎo)地位是不可動(dòng)搖的,可改變者主要是器物應(yīng)用層面的工具理性和具體技術(shù)。“中體西用”最初實(shí)際上是清代康、雍、乾三世的西學(xué)政策。1895年,沈壽康發(fā)表《救時(shí)策》寫道:“夫中西學(xué)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jì)宜以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①1898年,張之洞作《勸學(xué)篇》集近代“中體西用”思想之大成,使西學(xué)政策、洋務(wù)思想、立學(xué)宗旨、修身治國之理一以貫之,故后人多以張之洞為“中體西用”說的主要代表。他認(rèn)為,“今欲強(qiáng)中國,存中學(xué),則不得不講西學(xué)。然不先以中學(xué)固其根柢,端其識(shí)趣,則強(qiáng)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于不通西學(xué)者矣”②。
(三)從進(jìn)化論到唯物史觀:“古今中西之爭”的破解開始趨于正確方向
甲午戰(zhàn)爭的慘敗使“中體西用”的美夢(mèng)事實(shí)上趨于破滅。從中西交往來說,帝國主義大炮洋槍把西方文化“送到”了中國,傳教士們也不遺余力地傳播基督教信仰,同時(shí)西方的科學(xué)也陸續(xù)被他們介紹到中國。懼西崇西的洋奴思想與真誠學(xué)習(xí)西方科學(xué)技術(shù)的思潮并存。嚴(yán)復(fù)從歷史觀的角度分析了“古今中西之爭”,他“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③。20世紀(jì)30年代,馮友蘭在其《新事論》中論西方智富強(qiáng)、中國愚貧弱的原因,也作如是觀。他認(rèn)為前者之智富強(qiáng)并不因?yàn)樗麄兪俏鞣降亩且驗(yàn)樗麄兪乾F(xiàn)代的;后者愚貧弱也并非因?yàn)樗麄兪侵袊亩灰驗(yàn)樗麄兪沁^去的。因此,中西之異實(shí)質(zhì)是古今之別。而從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上說,西方之強(qiáng)在其以社會(huì)為本位,中國之弱全因其以家為本位,中國之落后是社會(huì)發(fā)展階段之滯遲的結(jié)果。這已經(jīng)不單純是進(jìn)化論思想,其實(shí)已經(jīng)有唯物史觀的成分了。④資產(chǎn)階級(jí)維新派的領(lǐng)袖康有為把“公羊三世”說改造成為歷史進(jìn)化論,嚴(yán)復(fù)倡導(dǎo)“天演哲學(xué)”,他們共同的思想鋒芒是指向頑固派、洋務(wù)派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和“中體西用”的。章太炎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對(duì)待“古今中西之爭”,提出了“用國粹激動(dòng)種性,增進(jìn)愛國的熱腸”⑤的主張,強(qiáng)調(diào)有選擇地學(xué)習(xí)西方目的是要超越西方。
“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李大釗首先由進(jìn)化論者轉(zhuǎn)變?yōu)轳R克思主義者,開始以唯物史觀立場和辯證方法分析“古今中西之爭”,鮮明地提出了崇今勝古、學(xué)西興中的主張,提出:“今是生活,今是動(dòng)力,今是行為,今是創(chuàng)作”⑥,只有以今勝古才能推動(dòng)歷史前進(jìn)、創(chuàng)造美好未來。作為“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主將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先驅(qū),李大釗、陳獨(dú)秀在“新舊思潮之激戰(zhàn)”中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矛頭直指作為綱常名教理論依據(jù)的天命論和經(jīng)學(xué)獨(dú)斷論,高舉科學(xué)民主之旗幟,對(duì)復(fù)古主義和全盤西化論展開兩條戰(zhàn)線的斗爭。胡適在“古今中西之爭”中也是一個(gè)進(jìn)化論者,其思想歷程經(jīng)歷了從反對(duì)封建主義到“全盤西化”而“充分世界化”的演變。在中西文化論戰(zhàn)中,還有一派是繼承了晚清國粹派章太炎、劉師培等人思想的“中國文化本位論”者,黃凌霜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專門撰寫的《民族文化建設(shè)綱領(lǐng)》主張民族本位的文化建設(shè),認(rèn)為中華民族是極其偉大的民族、是人類歷史上最悠久的民族,恢復(fù)和發(fā)揚(yáng)中國傳統(tǒng)文化,必須遵循“積極地啟發(fā)民族自覺與自信”和“以過去民族文化為基礎(chǔ)吸收現(xiàn)代思潮”兩大原則,以期達(dá)到“民族至上、國家至上”“民主政治與民族主義相輔而行”“建國之首要在民生”之目標(biāo)。⑦黃凌霜的主張是極具民族情懷和文化自信又不完全排斥學(xué)習(xí)西方的。過去對(duì)中國文化本位論完全否定也是有失偏頗的,至少他們與極端的復(fù)古主義者還是有區(qū)別的。
縱觀“古今中西之爭”的形成與演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基于“中國向何處去”的交鋒實(shí)質(zhì)上是近代以來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各種政治實(shí)踐、經(jīng)濟(jì)演變、制度探索、軍事斗爭的反映,“復(fù)古主義”與“全盤西化”是兩個(gè)極端,“古今中西之爭”并非涇渭分明地一分為二或一分為三,而是有相當(dāng)多的過渡色,形成了豐富多彩的譜系。
二、中國共產(chǎn)黨人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而進(jìn)行的積極探索
“古今中西之爭”在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之前就是一個(gè)歷史之問,這一爭論留給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問題是如何看待中國長期延續(xù)的古代社會(huì)及其文化即所謂“古”;如何認(rèn)識(shí)中國的民族復(fù)興、國家獨(dú)立、人民解放即“今”;如何正確認(rèn)識(shí)與妥善處理“走自己的路”與“學(xué)習(xí)別人”的問題即“中西”問題。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過程中經(jīng)過了長期努力,其中,李大釗、毛澤東、鄧小平的貢獻(xiàn)尤為突出。
(一)中國共產(chǎn)黨的先驅(qū)和創(chuàng)始人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而進(jìn)行的“真理尋求”
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前夕,以陳獨(dú)秀、李大釗為代表的激進(jìn)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意識(shí)到:要在中國建立一個(gè)名副其實(shí)的民主共和國,首先要在思想領(lǐng)域展開一個(gè)深入的鏟除舊觀念、批判舊道德的思想啟蒙運(yùn)動(dòng)。陳獨(dú)秀以民主與科學(xué)為旨?xì)w,由此揭開了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序幕。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主將陳獨(dú)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對(duì)尊孔思潮與舊禮教發(fā)起了猛烈抨擊,并大力倡導(dǎo)“文學(xué)革命”,提倡白話文,獲得廣大青年廣泛響應(yīng)。然而,這卻使林紓、辜鴻銘等復(fù)古派極為不滿,這是“古今中西之爭”的新展開。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激化了“古今中西之爭”,加速了中國文化進(jìn)步的步伐。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中國先進(jìn)知識(shí)分子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全新的思想武器。于是,便運(yùn)用它來觀察中國之命運(yùn),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由此而逐步演變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dǎo)的思想解放運(yùn)動(dòng)。中國思想文化的發(fā)展伴隨著中國革命實(shí)踐的進(jìn)程進(jìn)入了一個(gè)新的歷史階段。“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之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中國共產(chǎn)黨的先驅(qū)和創(chuàng)始人陳獨(dú)秀、李大釗完成了由激進(jìn)的民主主義向科學(xué)社會(huì)主義的思想轉(zhuǎn)變,由進(jìn)化論的倡導(dǎo)者升華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宣傳家。這一轉(zhuǎn)變根植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工人運(yùn)動(dòng)的興起,借助了“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社會(huì)動(dòng)力與思想激流,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提出了新要求。中國共產(chǎn)黨的先驅(qū)和創(chuàng)始人認(rèn)識(shí)到:資產(chǎn)階級(jí)共和國的種種方案在政治上回答不了“中國向何處去”的歷史之問,要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必須形成新的革命方案、引進(jìn)新的思想觀念,需要掌握和運(yùn)用新思想武器,這就是他們完成思想轉(zhuǎn)變的內(nèi)在邏輯。正如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言,“在‘五四’以后,中國產(chǎn)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所領(lǐng)導(dǎo)的共產(chǎn)主義的文化思想”①。這一時(shí)期的“古今中西之爭”將“學(xué)西”的重點(diǎn)集中轉(zhuǎn)向了傳播解讀馬克思列寧主義,將“興中”的希望寄托于“走俄國人的路”;使“變古”的矛頭直指封建舊文化,而把“今勝”的希望寄托于社會(huì)主義,使“古今中西之爭”逐漸邁上希望之路。
(二)毛澤東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而展開的理論探索
在中國共產(chǎn)黨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探索中,毛澤東無疑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青年毛澤東由于受楊昌濟(jì)等人的影響,在對(duì)待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問題上并沒有陳獨(dú)秀那么激進(jìn),而是相對(duì)溫和的。他認(rèn)為,“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nèi),要占個(gè)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yīng)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xué)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xué)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②。毛澤東既不全盤否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反對(duì)盲目學(xué)習(xí)西方,認(rèn)為“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yīng)與東方思想同時(shí)改造也”①。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中國革命和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時(shí)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黨的指導(dǎo)思想,對(duì)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采取批判繼承的科學(xué)態(tài)度,提出并不斷推進(jìn)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dǎo)下,在中國革命實(shí)踐的基礎(chǔ)上,在批判繼承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地對(duì)待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過程中,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gè)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又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的。”②其“古今中西”觀首先是建立在對(duì)普遍與特殊規(guī)律的正確認(rèn)識(shí)和對(duì)文化的科學(xué)界定基礎(chǔ)之上的,用共殊關(guān)系解決中西之爭超越了用體用關(guān)系看此問題的思維方式。關(guān)于文化,毛澤東指出:“一定的文化(當(dāng)作觀念形態(tài)的文化)是一定社會(huì)的政治和經(jīng)濟(jì)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huì)的政治和經(jīng)濟(jì)……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忘記這個(gè)基本觀點(diǎn)。”③1954年9月,他明確提出:“領(lǐng)導(dǎo)我們事業(yè)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chǎn)黨。指導(dǎo)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chǔ)是馬克思列寧主義。”④同時(shí),從一開始毛澤東就十分注重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shí)際相結(jié)合,主導(dǎo)提出并有力實(shí)施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里的“相結(jié)合”和“中國化”事實(shí)上是應(yīng)該包括與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和在思想內(nèi)容與表達(dá)形式上都有中國特點(diǎn)。毛澤東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的理論。不應(yīng)當(dāng)把他們的理論當(dāng)作教條看待,而應(yīng)當(dāng)看作行動(dòng)的指南。……學(xué)習(xí)我們的歷史遺產(chǎn),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jié),是我們學(xué)習(xí)的另一任務(wù)。我們這個(gè)民族有數(shù)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diǎn),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duì)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xué)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gè)發(fā)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yīng)當(dāng)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yīng)當(dāng)給以總結(jié),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ǎn)。這對(duì)于指導(dǎo)當(dāng)前的偉大的運(yùn)動(dòng),是有重要的幫助的。共產(chǎn)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diǎn)相結(jié)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shí)現(xiàn)。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gè)國家具體的革命實(shí)踐相聯(lián)系的。對(duì)于中國共產(chǎn)黨說來,就是要學(xué)會(huì)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yīng)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huán)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gè)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chǎn)黨員,離開中國特點(diǎn)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xiàn)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diǎn)去應(yīng)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diào)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fēng)和中國氣派。”⑤這段論述實(shí)際上概括地涉及了當(dāng)時(shí)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古今中西”觀,為“兩個(gè)結(jié)合”奠定了方向性基礎(chǔ)。毛澤東還提出了“民族的科學(xué)的大眾的文化”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shè)目標(biāo),這更是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文化綱領(lǐng)。后來的文化建設(shè)事實(shí)上也是遵循這個(gè)綱領(lǐng)進(jìn)行的。毛澤東在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時(shí)期的《論十大關(guān)系》《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等論著中,進(jìn)一步對(duì)“古今中西之爭”進(jìn)行了具體深入的分析,并提煉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⑦“推陳出新”⑧。這些內(nèi)容是破解“古今中西之爭”長期努力中最值得珍視的,為我們今天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指引了正確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礎(chǔ)、提供了寶貴經(jīng)驗(yàn)。
(三)鄧小平對(duì)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作出的獨(dú)特貢獻(xiàn)
進(jìn)入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shí)期,鄧小平繼承發(fā)展毛澤東思想,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作出了獨(dú)特貢獻(xiàn)。這主要表現(xiàn)在“對(duì)外開放”“學(xué)習(xí)西方先進(jìn)科學(xué)技術(shù)與管理經(jīng)驗(yàn)”“實(shí)質(zhì)性運(yùn)用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等多方面。鄧小平有一句名言:“老祖宗不能丟啊!”①這里的“老祖宗”主要是指馬克思主義的先驅(qū),但事實(shí)上也適用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等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代表人物。鄧小平很少引經(jīng)據(jù)典講中國傳統(tǒng)文化,卻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而進(jìn)行實(shí)質(zhì)性運(yùn)用的典范。縱觀鄧小平對(duì)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實(shí)質(zhì)性運(yùn)用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gè)方面:一是對(duì)墨家功利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與應(yīng)用。墨家與儒家當(dāng)時(shí)并稱“顯學(xué)”,影響極大。墨家思想以其主要代表人物墨子的“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等為中心,以強(qiáng)調(diào)“功利”而與儒家相區(qū)別甚至有對(duì)立。墨家重利而不輕義,強(qiáng)調(diào)“民之利”“國家之利”“天下之利”的重要性。鄧小平理論的實(shí)質(zhì)和核心就是對(duì)不對(duì)看實(shí)踐、好不好老百姓說了算、行不行看“三個(gè)是否有利于”。這些思想集中體現(xiàn)了他堅(jiān)持實(shí)踐第一、生產(chǎn)力第一、群眾利益第一的實(shí)事求是的立場,也是對(duì)墨子功利主義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與應(yīng)用。二是對(duì)儒家民本思想的創(chuàng)新與升華。儒家主張“以民為本”“民貴君輕”,荀子甚至提出過“天之立君,以為民也”②。儒家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重民思想的杰出代表,道家、墨家在很多方面與儒家持不同主張,但在重民這一點(diǎn)上立場觀點(diǎn)卻幾乎完全一致。鄧小平從歷史觀的高度深刻揭示了黨的根本宗旨和群眾路線的實(shí)質(zhì),也使中國傳統(tǒng)重民思想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歷史觀、價(jià)值觀中獲得了新生。鄧小平指出:“工人階級(jí)必須依靠本階級(jí)的群眾力量和全體勞動(dòng)人民的群眾力量,才能實(shí)現(xiàn)自己的歷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時(shí)解放全體勞動(dòng)人民。人民群眾的覺悟性、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愈是發(fā)展,工人階級(jí)的事業(yè)就愈是發(fā)展。因此,同資產(chǎn)階級(jí)的政黨相反,工人階級(jí)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dāng)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rèn)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shí)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wù)的一種工具。”③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發(fā)展,也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重民思想的新運(yùn)用。三是對(duì)道家無為思想的揚(yáng)棄與繼承。道家主張“道法自然”,從天道無為、萬物自化的觀念出發(fā),在否定古代神權(quán)主宰和天命論方面發(fā)揮了積極作用。鄧小平對(duì)道家思想予以揚(yáng)棄并精妙地運(yùn)用,形成了獨(dú)具特色、效果奇特的治國理政高超藝術(shù)。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主張簡政放權(quán)。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的各級(jí)領(lǐng)導(dǎo)機(jī)關(guān),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規(guī)章,放在下面,放在企業(yè)、事業(yè)、社會(huì)單位,讓他們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處理,本來可以很好辦,但是統(tǒng)統(tǒng)拿到黨政領(lǐng)導(dǎo)機(jī)關(guān)、拿到中央部門來,就很難辦。誰也沒有這樣的神通,能夠辦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這可以說是目前我們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gè)總病根。”④擴(kuò)大基層自主權(quán)的改革開放搞活政策由此而廣泛施行,產(chǎn)生了良好效果。鄧小平在“簡政放權(quán)”的過程中成功運(yùn)用了道家的治理智慧。這一智慧同樣也體現(xiàn)在國際事務(wù)的處理中。在蘇聯(lián)解體、東歐巨變之后,鄧小平審時(shí)度勢地提出了冷靜觀察、沉著應(yīng)對(duì)、善于守拙、穩(wěn)住陣腳、埋頭實(shí)干、韜光養(yǎng)晦、絕不當(dāng)頭的戰(zhàn)略方針,看似“無為”,實(shí)則“有為”,使我們?cè)趪?yán)峻的考驗(yàn)面前成功地應(yīng)對(duì)了復(fù)雜的國際局面,贏得了戰(zhàn)略主動(dòng)與發(fā)展機(jī)緣,不僅救了中國,也救了社會(huì)主義。
除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長期努力之外,學(xué)術(shù)界的長期探索同樣不可忽視,其中不少事實(shí)上也為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努力提供了學(xué)理支撐與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這其中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活動(dòng)家和著名學(xué)者的張申府的主張引人注目,他明確主張要把馬克思主義與西方文化資源、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機(jī)結(jié)合起來,提出“中國文化,要孔子、羅素和馬克思三位一體結(jié)合起來”⑤。其弟張岱年在他的影響下,努力嘗試把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羅素哲學(xué)與中國哲學(xué)打通,寫成了融三種思想資源于一體的《天人五論》,晚年提出“綜合創(chuàng)新論”,被認(rèn)為是學(xué)術(shù)界正確認(rèn)識(shí)“古今中西之爭”的可行結(jié)論。20世紀(jì)50年代,馮友蘭提出“抽象繼承法”,今天看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馮契提出:“對(duì)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但也必須同中國的革命實(shí)踐和中國的優(yōu)秀傳統(tǒng)相結(jié)合,使它中國化,取得民族的形式。”①蕭萐父晚年形成了“通觀涵化說”,方克立在對(duì)“體用”作出自身界定后主張“馬魂中體西用”。如此等等,充分說明“古今中西之爭”一百多年來始終是學(xué)界與政界共同關(guān)注的歷時(shí)最久的共同話題,學(xué)界與nP3fFdILmnQuY4366gEcjQ==政界在一個(gè)話題上的互動(dòng)互啟也莫能超過這一爭論,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審視習(xí)近平文化思想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創(chuàng)造的全方位多方面的完備的理論條件,更彰顯其重大的歷史意義與理論價(jià)值。
三、習(xí)近平文化思想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創(chuàng)造了豐富的理論條件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進(jìn)入新時(shí)代,文化強(qiáng)國建設(shè)成為中國式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重要目標(biāo),在實(shí)現(xiàn)這一目標(biāo)的過程中,形成了習(xí)近平文化思想,這一思想立足中國現(xiàn)實(shí)、放眼世界大勢、深刻把握文明發(fā)展規(guī)律,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創(chuàng)造了多方面豐富的理論條件。
(一)從增強(qiáng)文化自信到堅(jiān)守文化主體性:建設(shè)熔鑄古今、會(huì)通中西的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
我們黨在新時(shí)代先后提出了堅(jiān)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明確要求,并將其提升到了政治判斷力、政治領(lǐng)悟力、政治執(zhí)行力的高度。習(xí)近平對(duì)文化自信有過專門的論述,他認(rèn)為,“文化是一個(gè)國家、一個(gè)民族的靈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礎(chǔ)、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②。文化自信極端重要的地位作用源于我們黨高度的文化自覺、清醒的政治意識(shí)和敏銳的戰(zhàn)略洞察力。習(xí)近平強(qiáng)調(diào):“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③文化自信對(duì)道路自信有歷史縱深的啟迪作用,對(duì)理論自信有中華智慧的滋養(yǎng)作用,對(duì)制度自信有精神力量的支撐作用。因此,我們說堅(jiān)定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jiān)定文化自信。自信是作為實(shí)踐力量主體的意志狀態(tài),離開了源自實(shí)踐主體的文化自信,其他三個(gè)自信就缺乏主體力量。可見,習(xí)近平正是基于對(duì)文化自信深刻認(rèn)識(shí)與“四個(gè)自信”內(nèi)在聯(lián)系的規(guī)律性把握才特別強(qiáng)調(diào)增強(qiáng)和堅(jiān)定文化自信的。增強(qiáng)文化自信旨在激發(fā)全民族文化認(rèn)同感和創(chuàng)新力,以文化主體的創(chuàng)造活力不斷鑄就中華民族文化新輝煌,不斷增強(qiáng)實(shí)現(xiàn)中國式現(xiàn)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智慧支撐與精神力量。
習(xí)近平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huì)上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提出:“在新的起點(diǎn)上繼續(xù)推動(dòng)文化繁榮、建設(shè)文化強(qiáng)國、建設(shè)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是我們?cè)谛聲r(shí)代新的文化使命。”④完成新時(shí)代新的文化使命同樣需要進(jìn)一步堅(jiān)定克服文化自卑、防止文化自大基礎(chǔ)上的文化自信,更需要樹立和堅(jiān)守文化主體性。習(xí)近平指出:“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yuǎn),要有引領(lǐng)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⑤樹立、堅(jiān)守、鞏固文化主體性說到底是為了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中國共產(chǎn)黨“精神上的獨(dú)立自主”。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根本條件就在于是否能夠真正樹立起中華文明、中華民族和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的文化主體性。因?yàn)樗^“古今中西之爭”歸根結(jié)底爭的是文化主體性、爭的是文化主導(dǎo)權(quán)。“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從文化上來看,歸根到底就是中華文明是否能夠真正實(shí)現(xiàn)自身的現(xiàn)代更新,中華民族是否能夠真正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文明之路,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是否能夠真正體現(xiàn)自身是從中華文明之路中生長出來的,習(xí)近平文化思想指出了中華文化自我更新的正確方向,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道路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根基,完成了堅(jiān)定文化自信到堅(jiān)守文化主體性的升華,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創(chuàng)造了必要條件。這里的關(guān)鍵在于習(xí)近平文化思想強(qiáng)調(diào)的“第二個(gè)結(jié)合”。習(xí)近平指出:“‘第二個(gè)結(jié)合’,是我們黨對(du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shí)代化歷史經(jīng)驗(yàn)的深刻總結(jié),是對(duì)中華文明發(fā)展規(guī)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們黨對(duì)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rèn)識(shí)達(dá)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dá)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推進(jìn)文化創(chuàng)新的自覺性達(dá)到了新高度。”①這一方面深刻揭示了“第二個(gè)結(jié)合”的重大現(xiàn)實(shí)意義和深遠(yuǎn)歷史價(jià)值,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示了通過“第二個(gè)結(jié)合”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提供的根本條件、創(chuàng)造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只有在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dá)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的前提下,在對(duì)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的自我認(rèn)識(shí)與認(rèn)同達(dá)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的基礎(chǔ)上,在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推進(jìn)文化創(chuàng)新的自覺性達(dá)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的語境中,才能完成對(du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shí)代化歷史經(jīng)驗(yàn)的深刻總結(jié)并在新的實(shí)踐中創(chuàng)造積累新經(jīng)驗(yàn),才能對(duì)中華文明發(fā)展規(guī)律有深刻的把握和自覺的運(yùn)用,才能使當(dāng)代中華文化既延續(xù)民族的根脈又體現(xiàn)現(xiàn)代的風(fēng)采。“兩個(gè)深刻、三個(gè)新高度”所依據(jù)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是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精華的必由之路,也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自覺契合馬克思主義理論精髓的必由之路,馬克思主義由此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成為與現(xiàn)代社會(huì)相適應(yīng)、與當(dāng)代文化相協(xié)調(diào)的現(xiàn)代文化。
建設(shè)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作為新的文化使命是近代以來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志士仁人艱難探索“中國向何處去”的出路在當(dāng)代中國錨定的戰(zhàn)略目標(biāo),是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必然選擇與客觀要求,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百年奮斗主題的文化回應(yīng)。“一百年來,中國共產(chǎn)黨團(tuán)結(jié)帶領(lǐng)中國人民進(jìn)行的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chuàng)造,歸結(jié)起來就是一個(gè)主題: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②建設(shè)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是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主題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甚至是首要之義,這一目標(biāo)的確立終結(jié)了“古今中西之爭”的立論前提,解構(gòu)了“中體西用”的適用語境,使毛澤東指引的方向變得更加明確,把鄧小平對(duì)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實(shí)質(zhì)性運(yùn)用提升到了新境界,走出了“古今中西之爭”中時(shí)空分割的困境。習(xí)近平新時(shí)代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思想指引了“中國向何處去”的新方向,其文化篇?jiǎng)t提供了對(duì)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新方法,使原則性的倡導(dǎo)升華為具體化的路徑,為增強(qiáng)文化自信和堅(jiān)守文化主體性創(chuàng)造了必要條件、提供了實(shí)踐舞臺(tái)、夯實(shí)了理論依據(jù)。需要特別強(qiáng)調(diào)的是,在對(duì)待“古今中西之爭”語境中的任何一個(gè)方面的問題時(shí),習(xí)近平文化思想都堅(jiān)持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最新成果全面、辯證、系統(tǒng)、歷史的立場、觀點(diǎn)和方法,并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了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比如,對(duì)待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兩創(chuàng)”原則,目的是“傳承發(fā)展”、手段是“創(chuàng)造創(chuàng)新”,這本身就超越和解構(gòu)了“古今中西之爭”中的認(rèn)識(shí)視角和思維方式,而使問題的解決達(dá)到了新境界,當(dāng)然就能凸顯其“深刻”、體現(xiàn)其“新高度”,從而筑牢了道路根基,讓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道路有了更加宏闊深遠(yuǎn)的歷史縱深,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
(二)從尊重文明多樣性到文化生命體:確立古今貫通、中西融通的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現(xiàn)代文明觀
造成“古今中西之爭”百余年不休的一個(gè)重要甚至根本原因是“西方中心論”和“東方依附西方說”,是西方式的文明觀與現(xiàn)代化語境。因此,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前提性條件就是要超越和解構(gòu)這一類話語體系,形成我們自己的現(xiàn)代文明觀和現(xiàn)代化話語體系。習(xí)近平文化思想之所以能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創(chuàng)造根本條件、提供必要條件,就在于這一思想自始至終尊重文明的多樣性,而在認(rèn)識(shí)的不斷深化、視野的持續(xù)開闊和理論的不懈探索中形成和確立了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chǎn)黨人新的、現(xiàn)代的、科學(xué)的、民族的、大眾的文明觀。
文明多樣性是世界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的基本特征,人類創(chuàng)造的各種文明都有自身不可替代的內(nèi)容和與其他文明不同的表現(xiàn)方式,“每一種文明都是獨(dú)特的”①。尊重文明的多樣性是習(xí)近平文化思想面向世界的基本立場,他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②文明是多彩的,世界也是多彩的。“一個(gè)國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個(gè)國家和民族的集體記憶。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從茹毛飲血到田園農(nóng)耕,從工業(yè)革命到信息社會(huì),構(gòu)成了波瀾壯闊的文明圖譜,書寫了激蕩人心的文明華章。”③從文明多樣性到文明平等觀,從文明包容性的主張到文化生命體的界定,習(xí)近平文化思想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提供了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觀,正是這一中國式的現(xiàn)代文明觀破除了“西方中心論”,超越了“東方依附說”,開創(chuàng)了人類文明觀的新境界。
習(xí)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的結(jié)果是相互成就,造就了一個(gè)有機(jī)統(tǒng)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成為現(xiàn)代的,讓經(jīng)由‘結(jié)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文化形態(tài)”④,“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文化形態(tài)”也就是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在此,“文化生命體”是單數(shù)的,特指通過“第二個(gè)結(jié)合”創(chuàng)造性傳承、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而形成的當(dāng)代中國的“文化形態(tài)”和中華民族的“現(xiàn)代文明”。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破解“古今中西之爭”而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體”是習(xí)近平文化思想的一種全新的現(xiàn)代文明觀,在面向世界時(shí)“文化生命體”成為復(fù)數(shù)的,其所揭示的正是認(rèn)定文明多彩而尊重文明多樣性、主張文明平等、倡導(dǎo)文明包容的“文明”的內(nèi)涵。有學(xué)者認(rèn)為,“‘第二個(gè)結(jié)合’通過打通中華文明道路與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道路之間的連續(xù)性,讓中華文明道路與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道路一氣貫通,成為同一條中國道路”⑤。因此,“‘結(jié)合’筑牢了道路根基”⑥。“第二個(gè)結(jié)合”筑牢道路根基的理論基礎(chǔ)與觀念前提正是“文化生命體”的現(xiàn)代文明觀。這一文明觀的實(shí)質(zhì)、核心和關(guān)鍵就在于用“文化生命體”來界定、審視和對(duì)待豐富多彩的世界范圍內(nèi)從古至今的所有文明,在這一文明觀看來,所有人類文明都不過是各種各樣的、豐富多彩的、平等互鑒的、廣泛交流的、互相包容的諸多“文化生命體”。
習(xí)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生命體”的現(xiàn)代文明觀走出了長期以來在文明問題上的認(rèn)識(shí)誤區(qū),打破了“ 文明觀”上“ 西方中心論”的話語獨(dú)斷。長期以來,“ 關(guān)于‘ 文明’的認(rèn)識(shí),我們實(shí)際上是基于‘civilization’這個(gè)英文詞的漢譯來理解的,也就是說想當(dāng)然地把‘文明’兩個(gè)漢字的意義直接等同于‘civilization’的含義。但實(shí)際上,由漢字‘文明’所表達(dá)的文明觀與根據(jù)‘civilization’而來的文明觀,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⑦。根據(jù)布羅代爾⑧、劉禾⑨等學(xué)者的研究,“civilization”一詞一開始就具有把文明狀態(tài)分成若干等級(jí),并以西方文明高人一等的姿態(tài)排斥人類其他文明狀態(tài)的明確含義,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論”的文明觀。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所特有的文明觀源于《周易》“見龍?jiān)谔铮煜挛拿鳌雹猓饔凇渡袝贰盀F哲文明”①,唐代孔穎達(dá)對(duì)《尚書》此句的疏解稱“經(jīng)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②,可謂東方文明觀的第一個(gè)明確定義,這一定義所界定和倡導(dǎo)的文明觀與“西方中心論”的文明觀的根本不同在于:中華民族的古代文明觀指的是“人依循天德而實(shí)現(xiàn)的人德”③。“文”是天人合一中人效法天而獲取的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等美德,而“明”則是人發(fā)明彰顯實(shí)現(xiàn)這種天人共有之德的修悟過程與教化結(jié)果。這種東方式中華文明觀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等級(jí)觀念與排他意識(shí)。在這種意義上的“古今”只不過是貫通一氣、從未中斷的中華民族古老文明走向現(xiàn)代文明的全過程,而“中西”則是中華文明與其他文化生命體以開放包容的態(tài)度平等對(duì)待的不同對(duì)象。“文化生命體”的現(xiàn)代文明觀的形成與確立,為我們尊重文明多樣性的主張和文明互鑒互融的倡議提供了堅(jiān)實(shí)的理論基礎(chǔ),也為堅(jiān)定文化自信與堅(jiān)守文明主體性、建設(shè)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提供了思想前提,這是習(xí)近平文化思想對(duì)人類文明發(fā)展規(guī)律深刻把握的原創(chuàng)性貢獻(xiàn),從根本上解構(gòu)了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jié)論”,從根本上駁斥了“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也從根本上超越了“文明沖突論”。這不僅為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建設(shè)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理論基礎(chǔ),也為人類文明未來發(fā)展提供了新的視角,作出了獨(dú)特的貢獻(xiàn)。
(三)從文明互鑒到全球文明倡議:推動(dòng)形成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人類文明共識(shí)體
習(xí)近平文化思想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創(chuàng)造的理論條件不僅立足中國現(xiàn)實(shí),而且面向世界未來,進(jìn)入了馬克思所說的“世界歷史”范疇,為構(gòu)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提供了中國智慧、講出了中國道理、貢獻(xiàn)了中國方案。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中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tài)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chǎn)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④歷史和現(xiàn)實(shí)都證明了這一科學(xué)論斷的真理價(jià)值。當(dāng)今世界日益緊密地聯(lián)結(jié)為一個(gè)整體,正如習(xí)近平所說的那樣:“人類生活在同一個(gè)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xiàn)實(shí)交匯的同一個(gè)時(shí)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yùn)共同體。”⑤這一命運(yùn)共同體的構(gòu)建是全人類在“歷史和現(xiàn)實(shí)交匯的同一個(gè)時(shí)空里”進(jìn)行的,這種全球視野和世界眼光同樣使中國進(jìn)入了當(dāng)年志士仁人們期望的“世界之中國”⑥,在此境界中運(yùn)用“文化生命體”的文明觀觀察世界的未來和人類的明天,必然持文明互鑒以共同進(jìn)步的態(tài)度。習(xí)近平指出:“每種文明都有其獨(dú)特魅力和深厚底蘊(yùn),都是人類的精神瑰寶。不同文明要取長補(bǔ)短、共同進(jìn)步,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推動(dòng)人類社會(huì)進(jìn)步的動(dòng)力、維護(hù)世界和平的紐帶。”⑦文明互鑒的前提是尊重文明的多樣性、堅(jiān)持文明的平等性、擴(kuò)大文明的包容性。在世界各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前途命運(yùn)緊密相連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合作共融,在推動(dòng)人類文明進(jìn)步和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023年3月,習(xí)近平在中國共產(chǎn)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duì)話會(huì)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議”,指出我們?cè)竿瑖H社會(huì)一道,努力開創(chuàng)世界各國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讓世界文明百花園姹紫嫣紅、生機(jī)盎然。全球文明倡議倡導(dǎo)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堅(jiān)持文明平等、互鑒、對(duì)話、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yōu)越;倡導(dǎo)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jià)值,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不將自己的價(jià)值觀和政治模式強(qiáng)加于人,不搞意識(shí)形態(tài)對(duì)抗;倡導(dǎo)重視文明繼承和創(chuàng)新,推動(dòng)各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實(shí)現(xiàn)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倡導(dǎo)加強(qiáng)國際人文交流合作,促進(jìn)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共同推動(dòng)人類文明發(fā)展進(jìn)步。①這一倡議與全球發(fā)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一道構(gòu)成中國為維護(hù)世界和平、促進(jìn)共同發(fā)展、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三大倡議”,得到世界各國愛好和平、主張合作、堅(jiān)守公平正義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各方人士、各國人民的積極響應(yīng)與充分肯定,越來越多的人認(rèn)知、認(rèn)可、認(rèn)同這一主張,逐步了解理解肯定中國道路、日益讀懂且贊同中國道理。正如習(xí)近平指出的那樣:“只要我們牢固樹立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意識(shí),攜手努力、共同擔(dān)當(dāng),同舟共濟(jì)、共渡難關(guān),就一定能夠讓世界更美好、讓人民更幸福。”②這里的“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意識(shí)”是推動(dòng)建設(shè)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認(rèn)識(shí)前提和思想基礎(chǔ),只有不斷擴(kuò)大人類命運(yùn)共識(shí)、文明共識(shí),全力推動(dòng)構(gòu)建“人類文明共識(shí)體”,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建設(shè)才有正確方向與共同遵循。在此意義上,我們認(rèn)為“生活在歷史和現(xiàn)實(shí)交匯的同一個(gè)時(shí)空里”的世界各國人民應(yīng)當(dāng)共同樹立“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意識(shí)”的倡議中蘊(yùn)含的“人類文明共識(shí)體”理念。
如果說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目標(biāo)與理想是建設(shè)一個(gè)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的話,人類文明共識(shí)體就是要將這些目標(biāo)的內(nèi)容和理想的內(nèi)涵全面揭示出來、推廣開來,以求更多的國家、更多的政要、更多的學(xué)者歸根到底要讓世界各國人民認(rèn)知認(rèn)可認(rèn)同,作為人類文明共識(shí)體的同心圓、共識(shí)圈畫得越大,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建設(shè)就越有基礎(chǔ)、越有成效、越有前途。我們破除西方國家以“普世價(jià)值”名義販賣其自視至上、獨(dú)霸排他的價(jià)值觀,提出了“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jià)值”③。也許有人會(huì)說這只不過是“普世價(jià)值”的另一種說法而已。其實(shí)不然,“普世價(jià)值”是霸權(quán)式的、單數(shù)的、唯一的、排他的、強(qiáng)行推廣的,貌似站在全人類共同立場上主張所謂不可懷疑的核心價(jià)值,而事實(shí)上旨在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fā)達(dá)國家的文明觀念、價(jià)值理念和政治模式強(qiáng)加于人,誰敢說一個(gè)“不”字,就被扣上反“普世價(jià)值”、反“自由平等博愛”的大帽子。而我們所主張、倡導(dǎo)的以“全人類共同價(jià)值”為主要內(nèi)容的“人類文明共識(shí)”是平等協(xié)商式的、復(fù)數(shù)的,其實(shí)現(xiàn)方式是多樣的、非排他的,是倡議式而非強(qiáng)行推廣的,如此等等,在增進(jìn)共識(shí)的基礎(chǔ)上以對(duì)話的方式、合作的途徑和和諧的目的而推進(jìn)的。“歷史和現(xiàn)實(shí)交匯的同一個(gè)時(shí)空”、“和平與發(fā)展”的共同愿景、“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意識(shí)”是積極推進(jìn)“人類文明共識(shí)體”建設(shè)的基礎(chǔ)和條件。只有先推進(jìn)“人類文明共識(shí)體”形成,才能實(shí)質(zhì)性推動(dòng)“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建設(shè)。這就是習(xí)近平文化思想、外交思想共同創(chuàng)造的全球文明視野下的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國際話語條件。
結(jié) 語
綜上所述,“古今中西之爭”由來已久,而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長期努力”曲折、復(fù)雜且艱難,但“路雖遠(yuǎn)行將必至”,為使中華文明再度復(fù)興、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為使中華文化立得住、行得遠(yuǎn)、傳得開,以習(xí)近平為主要代表的當(dāng)代中國共產(chǎn)黨人大力推進(jìn)文化實(shí)踐創(chuàng)新基礎(chǔ)上的文明理論創(chuàng)新、以人民為中心的價(jià)值理念創(chuàng)新,形成了以“文化生命體”為內(nèi)涵的新的現(xiàn)代文明觀,提出了“歷史與現(xiàn)實(shí)交匯”的新的現(xiàn)代文明時(shí)空觀,揭示了“牢固樹立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意識(shí)”蘊(yùn)含的人類文明共識(shí)體的極端重要性,進(jìn)而確立了新的現(xiàn)代共同體觀。這些思想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創(chuàng)造了根本條件、提供了必要條件、營造著國際話語條件,從而趨向于充分條件。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我們說習(xí)近平文化思想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創(chuàng)造了完備的理論條件,對(duì)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發(fā)展作出了原創(chuàng)性貢獻(xiàn)。當(dāng)然,創(chuàng)造了完備的條件并不等于徹底地解決了問題,真正完全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依然要靠實(shí)踐,只有實(shí)踐的力量才能真正破解歷史之謎、理論之謎,中國式現(xiàn)代化建成之日、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形成之際、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屹立于世界東方之時(shí)才能真正完全徹底破解“古今中西之爭”。
“中國向何處去”的歷史之問在新時(shí)代終于有了一個(gè)明確的回答,這有賴于當(dāng)代中國共產(chǎn)黨人不斷推進(jìn)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shí)代化。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的過程中,當(dāng)代中國共產(chǎn)黨人不僅深刻揭示了科學(xué)社會(huì)主義價(jià)值觀的主張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高度契合性,而且經(jīng)過自己的長期努力,使這種“高度契合性”從自在的狀態(tài)經(jīng)過自發(fā)的接觸和自覺的努力進(jìn)入了自主創(chuàng)新的新境界。這個(gè)自在、自發(fā)、自覺、自主的演進(jìn)歷史就是“古今中西之爭”形成、演變、破解和消解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從蒙難、蒙辱、蒙塵到自發(fā)、自覺、自主,書寫了啟蒙救亡與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雙重主題融合的壯麗史詩,昭示著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建設(shè)的光明前景,展示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持久的生命力,也使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qiáng)起來具有了人類文明意蘊(yùn)。
[責(zé)任編輯 付洪泉]